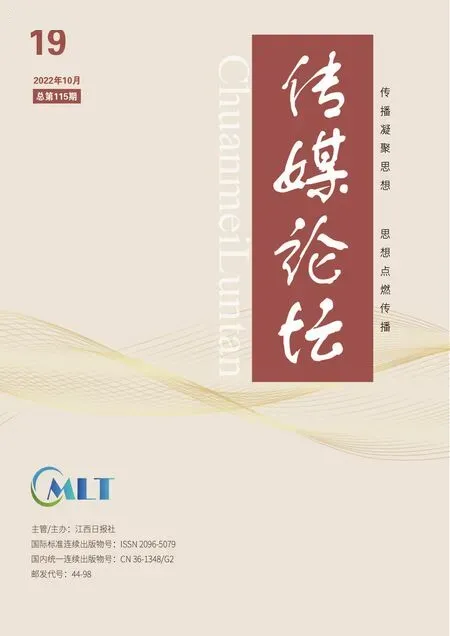我國對外傳播的理念轉向及“三聚”特性
邱 凌 牛一冰
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提出:“必須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輿論引導力。”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首次使用“戰略傳播”一詞,標志著這一概念已經進入了決策層的話語體系中,對推動我國國際傳播在新時代實現轉型升級具有重要價值和時代意義。這也意味著我國對外傳播事業要有全局性,要主動配合國家戰略,加強戰略傳播自覺,實現國家戰略傳播目標。
一、“戰略傳播”概念的提出以及在西方的發展概況
戰略傳播這一概念源自美國,最早主要應用于商業領域,隨著美國對外傳播理念的發展,戰略傳播逐漸被引入國際政治領域。戰略傳播涵蓋了宏觀層面的“戰略”與微觀層面的“策略”兩層含義,前者與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治理等相關,實施主體主要是國家;后者則偏向商業領域,實施主體以企業為主,在國際傳播領域多采用第一層含義。目前,對于戰略傳播概念的認知也是處于不斷演進的過程中。
美國對外傳播理念的發展主要經歷了傳統外交、公共外交、軟實力外交和戰略傳播四個階段。2001年“9·11”恐怖襲擊后,美國政界、學界和業界開始反思“軟實力”“公共外交”等概念在國際傳播實踐中的局限性,美國政府于是大規模地調整對外信息傳播機構和戰略構想,強調統一而清晰的傳播戰略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2004年美國國防科學委員會首次提出了戰略傳播的定義,指“國家政府層面作為實踐主體,綜合使用政治、軍事、文化、經濟、外交等各種渠道和工具把握全球輿論、態度及文化,并透過傳播策略來影響人們的態度與行為,以強化或維持有利于國家利益、政策和目標的環境的整合營銷政治傳播”。①2010年3月,美國總統奧巴馬向美國參眾兩院提交的《國家戰略傳播構架》中首次系統地闡述美國國家戰略傳播的性質、目標和實施體系。2016年建立了“全球互動中心”及隨后設置了“戰略傳播總監”等職位,承擔起社交媒體時代白宮繼續開展國際傳播的重要職能。近日,美國國內兩黨對拜登政府建立的“虛假信息治理委員會”的斗爭、推特被收購等焦點話題以及俄烏戰爭中的傳播戰,再次揭開了美國各派為新一輪競選進行的輿論爭奪戰,其激烈程度和復雜背景,暴露出戰略傳播作為重要的國家戰略工具,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中的重要性。②
除美國之外,西方其他國家也紛紛從頂層設計對戰略傳播進行規劃,整合優勢形成合力,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和最優化。歐盟、北約從各自的戰略利益出發對戰略傳播進行系統研究并制定策略,2009年9月北約頒布了《北約戰略傳播政策》。以此為標志,北約的戰略傳播體制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進入穩步發展時期。截至目前,北約的戰略傳播機制已經形成和完善,并成為北約對內整合和對外影響的重要手段。澳大利亞也組建了負責戰略傳播的兩個部門,一是戰略傳播局,二是傳播與媒體局,已經實現常態化運行。
二、戰略傳播:我國對外傳播發展的理念轉向
我國對外傳播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變,而是根據我國自身實際發展狀況及我國與世界的關系不斷進行調整,從而更好地適應新環境、新形勢、新挑戰,因此呈現出了階段化的發展特征。
(一)對外宣傳階段:以我為主,單向言說
我國解放初到1978年改革開放這段時間內主要是以對外宣傳為主。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對外傳播事業還處于起步階段,面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封鎖和美蘇冷戰的兩級格局,中國采取了“一邊倒”的國家政策,關閉資本主義國家在華設立的新聞機構,禁止外國通訊社對中國報紙發稿。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對外傳播范圍十分有限,這一時期的對外傳播主要是為政治服務的。傳播主體以單一的官方機構和主流媒體為主,主要由《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負責。1952年,中共中央曾發文要求國際時事評論與報道經中央審查后統一由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發表,其他報紙只能轉載③;傳播內容是有關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正面報道以及國家政策、主張的闡釋和宣傳,意識形態色彩鮮明,具有較強的政治性和口號化特征,敘事宏大,力圖塑造積極正面的中國形象;從傳播對象來看,對外宣傳缺乏受眾意識,受眾群狹窄,很少考慮到他國受眾的接受和反饋情況。這種單向輸出,傳播效果有限,很難贏得其他國家受眾的認可,有時甚至受到抵制。
(二)對外傳播階段:關注受眾,雙向交流
改革開放后,我國對外傳播理念開始從以傳播者為中心的單向宣傳變為以受眾為中心的對外傳播,注重雙向的互動交流。這與“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背景息息相關。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與各國建立友好關系,努力讓中國的聲音走出去、走得更遠,讓世界更了解中國。除了政府和官方媒體外,非政府組織、市場化媒體以及企業等也加入了對外傳播的陣營中,傳播內容也更加注重新聞價值,選擇用事實說話替代之前具有強烈政治色彩和宣傳意味的內容。開始重視受眾的反饋,通過了解受眾的心理特點,用受眾感興趣、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傳播中國聲音。面對國外受眾所關注的中國熱點問題,不再采取回避政策,而是主動回應和解釋,形成了雙向溝通的對外傳播模式。
(三)國際傳播階段:多元主體,復調傳播
對外傳播主要是內與外的雙向交流,與對外傳播階段泛化的、并不具體劃分客體的大傳播相比,國際傳播強調“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傳播,是“一個國家以上的個人、群體或政府官員的跨越被承認的地理性政治邊界的各種傳播”④。國際傳播階段最為突出的新特點就是多元傳播主體形成的“復調傳播”模式。從傳播主體來看,我國建立起了“1+6+N”的大外宣立體格局(1家旗艦媒體+6家央媒+其他部門)。⑤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人民日報》等官方媒體也紛紛開通社交媒體賬號,個人、自媒體等也成為了國際傳播中中國故事的敘事者,形成了包含政府、官方媒體、商業化媒體、智庫、非政府組織、企業等多元主體的復調傳播格局,建立起國際傳播新體系。從傳播內容來看,國際傳播階段強調講好中國故事,這些故事既包含宏大敘事,也包含“小而精”的貼近個體生活的真實而生動的故事,并根據不同的受眾制定差異化、定制化的傳播內容。媒介形式也更加多元,中國外文局也在2015年4月成立了融媒體中心,以“新媒體、新外宣”為使命,重點經營多語種移動化、社交化、可視化新媒體產品的策劃、生產與國際化傳播⑥。但是由于中國的國際傳播依然存在著被曲解、被污名化的困境,亟須進一步提升國際話語權。
(四)全球傳播階段:超越國別,開放包容
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跨國信息交流的便捷性使世界越來越趨向于一個整體,國與國之間的傳播界限逐漸模糊。“全球”意味著國家和國家主權的作用正在下降,意味著比國際更為普遍,更具地域包容性。在這一背景下,中國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主張,以全球化的視角應對當今世界的問題與挑戰,試圖打破目前世界東西對立、南北割裂的狀態,致力于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傳播秩序和格局,中國對外傳播觀念也實現了由“國際傳播”到“全球傳播”的改變。
美國學者霍華德·弗里德利認為:“全球傳播是研究個人、群體、組織、民眾、政府以及信息技術機構跨越國界所傳遞的價值觀、態度、意見、信息和數據的各種學問的交叉點。”⑦國際傳播則具有很強的政治性,在傳播中強調國家主權概念以及不同國家之間的雙邊關系和多邊關系,更多地會從自己國家的立場和利益進行考慮。與國際傳播相比,全球傳播更強調整體性,傳播內容是關于全人類共同關注的世界性議題,例如人口問題、環境問題、貧困問題和資源問題等,較少受到國家意識形態和政治立場的影響和限制,是超越國界,超越地理空間的多維度信息傳播,受眾是整個世界的公眾,最終是為了能夠實現世界范圍內的價值和意義共享。全球傳播的去意識形態化和全球立場能夠降低各國受眾的戒備和抵觸心理,通過講述中國與世界共同發展的故事收獲更多的認可和關注,從而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大化,像抖音的海外版TikTok,采用“淡化中國”的策略,尋找各國公眾興趣的共通點,淡化民族和國家的差異,更好地實現了國際化。
(五)戰略傳播階段:頂層設計,宏觀統籌
雖然全球傳播超越國界、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有助于全球傳播新秩序的確立,促進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但是,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輿論環境,中國的聲音存在著傳不出、傳不遠、傳出的又被曲解的困境。因此,想要提升中國國際話語權,展現立體、真實、全面的中國形象,有效地回應、反擊國際負面輿論,實現傳播效果的最優化,對外傳播理念需要向戰略傳播轉型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在“5·31”重要講話中提出要“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為這一階段對外傳播的發展點明了方向,戰略傳播更能體現國家戰略、服務國家發展,更具頂層設計的宏觀性、指導性和統籌性。
三、轉向戰略傳播的現實需要及價值意義
促使我國對外傳播理念向戰略傳播轉型升級,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中國面臨的國際傳播形勢依然嚴峻,⑧中國提出的理念、倡議以及參與全球治理建設的相關工作頻頻被西方媒體“標簽化”,甚至“污名化”。西方部分媒體利用、引導國際輿論,鼓吹“中國威脅論”,還試圖在涉疆、涉藏問題以及防疫等議題上引起國際社會批評中國的熱潮。2021年,西方媒體利用輿論炒作、制造出的“新疆棉”事件,就是戰略傳播的一種體現。西方部分國家的政府、智庫、企業及社會組織多方協同運作,綜合運用外交、商貿等手段對中國進行打壓和遏制。因此,面對海外媒體的刁難圍堵,中國亟須提升本國的戰略傳播能力,對負面輿論予以有力回擊。
其次,單一傳播主體力量有限,難以覆蓋多重領域,專業性和針對性不夠強。不同傳播主體的專業領域和優勢都不同,單一傳播主體很難對非自身專業領域的內容進行有權威性和說服力的傳播。對于國家方針政策和領導人講話等內容,外交部和中央媒體的闡釋會更加嚴謹專業;而對于某一經濟現象的分析則需要經濟學家、企業以及經濟類媒體的參與;對于學理層面的科研討論則是學者和智庫的強項。此外,講述中國故事,展現全面真實的中國形象,既需要專業性、理論化的宏觀解讀,也需要貼近生活、貼近民眾的微觀敘事,這就需要民間主體、個人以及外國民眾的參與。因此,需要協調整合涵蓋人際傳播、組織傳播、群體傳播、大眾傳播等多種傳播類型的傳播主體,融合官方媒體、商業化媒體及社交媒體平臺,綜合運用各種傳播手段和策略,發揮不同主體的優勢和專長,從而形成最大傳播合力。
第三,隨著互聯網和新媒體的發展和普及,全球性社交媒體和平臺型媒體已經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信息的海量化、社交媒體議題的碎片化容易分散傳播對象注意力,使傳播重點難以聚焦,層出不窮的媒介議題和熱點事件也使人們很難持續關注某一議題。例如2022年2月爆發的俄烏沖突引發了全世界的關注和討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新的國際熱點事件的出現,其他地區的人們對俄烏沖突的關注度不斷降低。同時,由于這種關注度的短時性,人們對還未知真相的事件往往會先入為主,被輿論帶節奏,這使后續的辟謠和澄清變得更為困難。這就要求我國運用戰略傳播提升主動議程設置的能力,主動設置核心議題,揭露事件的真相,聚集傳播合力,從而提升國際受眾對焦點議題的關注度。
對外傳播理念從國際傳播轉向戰略傳播,是快速提升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和國際話語權的重要路徑。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應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和使命擔當,為全球治理和全球發展提出更多有益有效的中國方案,促進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的建立。這就需要注重并提升中國的戰略傳播能力,加強頂層設計和整體布局,主動引領塑造大國走向,將“中國方案”進一步嵌入到戰略傳播體系當中,破除當前的輿論困局,讓世界看到中國為全球發展作出的努力和貢獻。
四、戰略傳播的“三聚”特性及優勢
在當今嚴峻、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下,戰略傳播相對于與其他傳播理念更適合我國的現狀,戰略傳播具有“三聚”特性及優勢。
(一)聚焦——傳播更具目標性、針對性
戰略傳播并不是毫無目的、隨意地傳播,它具有目標性,是在國家既定的統一目標下開展行動的。但在實施過程中是有層次性,分步驟、分階段地逐步推進。同時,戰略傳播具有針對性,傳統的國際傳播和公共外交實踐所關注的對象主要是廣泛意義上的外國公眾,但戰略傳播的對象通常是更為具體的“關鍵受眾”,如各領域專家、政府官員等“關鍵性意見領袖”⑨。這些意見領袖在各自的領域中都具有較強的話語權和權威性,他們的觀點能夠廣泛影響到身邊的受眾,他們之間互動討論又能極大地提升話題的關注度。通過聚焦這些關鍵受眾,能夠大大拓寬傳播的范圍,提升影響力。
戰略傳播在傳播受眾及目標的聚焦性有助于精準傳播,改變過去傳播行為的分散化、隨機化的狀態,對目標國家、目標地區及目標受眾進行精準施策。如中國外文局聯合其他部門針對世界青年群體及不同國家展開了多層次的文化交流活動:全球青年多維對話、針對印度青年群體的“中印青年對話論壇”、2022中日文明對話、“一帶一路”人文交流青年領袖大連論壇、巴基斯坦青年媒體人士研修班等。這些傳播活動聚焦國際青年群體,青年是世界的未來也是推動國際關系發展的新生力量,這樣的交流促進和增進了國際青年群體對中國的認知及了解。
(二)聚合——多種資源的整合利用
通過協調和配合,綜合調動政府、媒體、智庫、企業、民間組織等多元主體,聚合人際、組織和媒介等多個層面的溝通與交流行為,實現資源利用的系統性和最大化,同時從中選擇最適合關鍵受眾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資源的整合利用并不意味著做重復的事、傳遞同一種聲音,而是根據各自的特性和優勢,制定符合自身的傳播策略,多個部門、多種資源配合緊密,對外發出服務于整體目標的統一但不完全相同的聲音,能夠避免各說各話、分散焦點的狀況,展示統一的國家形象。
特別是在西方主要媒體進行議程設置,炮制針對我國的某個話題,形成聯盟,在國際輿論中“帶節奏”地抹黑中國時,我國戰略傳播的反擊就顯得尤為重要。如在新疆議題上,我國外交部、駐外使館及央級媒體等通過新聞發布會、使館播放相關視頻、媒體現場報道、海外社交媒體賬號刊載及邀請外國記者實地探訪等系列活動,形成反擊“組合拳”,針對抹黑議題各個擊破。
(三)聚積——時間及效果的長期導向
戰略傳播是對外傳播的轉型升級,是一種更加主動的公共外交,具有長期導向的特點。戰略傳播目標往往比較宏觀,需要較長的時間積累才能逐步實現,因此效果很難在短期內顯現出來,而且當全球傳播格局、世界發展局勢等發生變化時要根據新的環境條件適時對傳播戰略進行調整。因此要做好科學系統的規劃和工作管理機制,制定好階段性的目標,合力協同推進。
雖然全球化時代世界各國依存度不斷增加、交流合作日益頻繁,但意識形態之爭、制度之辯、霸權主義、文明沖突等始終存在,從國家安全層面來說,我國目前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而戰略傳播正是國家安全戰略具體施行的重要抓手,其目的就是通過整合國家全部的傳播資源,通過內外傳播有效地服務于國家安全。從其他國家戰略傳播的布局與規劃我們也已看到,戰略傳播具有長時間的累積效應,傳播目標的實現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需要系統規劃、長遠布局、多方聯動。
五、結語
中國的對外傳播理念經歷了對外宣傳、對外傳播、國際傳播、全球傳播等階段,轉向戰略傳播符合當前的時代要求和中國的發展實際。應發揮本國的制度和文化優勢,在既有國際傳播工作的基礎、資源和積淀之上建立具有本國特色的戰略傳播體系,加強頂層設計和系統規劃,設立合理的遠中近期戰略傳播目標,協調整合多個部門、多方資源、多種手段,實現傳播合力的最大化和最優化,針對關鍵受眾制定精準化的傳播方案,并建立一定的效果評估機制,根據反饋及時對傳播方案進行調整。與此同時,中國應與國際社會廣泛開展對話,加強同世界各國媒體的溝通和合作。
注釋:
①李沫.戰略傳播:國家利益爭奪前沿的較量[N].中國國防報,2016-12-08(004).
②戰略傳播:國家軟實力重器[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H6OR0DF905537JDH.html.
③張宏瑩.1949-2019:新中國對外傳播的變遷與發展[J].對外傳播,2020(01):44-46.
④李智.國際傳播(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2-5.
⑤史安斌,張耀鐘.聯接中外、溝通世界:改革開放40年外宣事業發展述評[J].對外傳播,2018(12):4-7.
⑥楊明星,周安祺.新中國70年來外交傳播體系的歷史演進與發展方位[J].國際觀察,2020(05):107-133.
⑦周慶安.公共外交研究的四個理論維度[EB/OL].https://news.ifeng.com/c/7fYqwUEug1s.
⑧張君昌,陳積流,張引.構建中國特色戰略傳播體系,著力提升國際傳播能力[J].新聞戰線,2022(15):10-14.
⑨史安斌,童桐.從國際傳播到戰略傳播:新時代的語境適配與路徑轉型[J].新聞與寫作,2021(10):1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