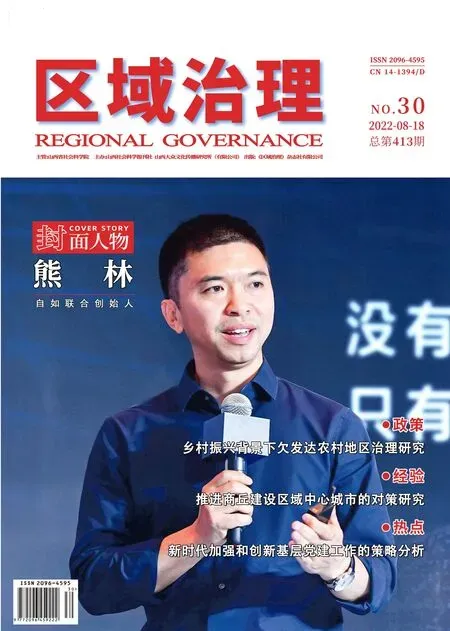視頻廣告屏蔽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規制
長春理工大學法學院 李艷
一、問題的提出
目前,視頻網站往往對于不收取會員費用的消費者采“先觀看廣告,再播放視頻”的模式。收取會員費的用戶可以直接播放或者點擊按鈕跳過廣告來觀看點播的視頻;未付費的用戶則需要等廣告播放完畢之后才可以觀看其點播視頻。從傳統媒體時代到互聯網時代,用戶對于所欣賞作品中發布的廣告,完成了從無計可施到掌握一定主動權的轉變。尤其是廣告屏蔽軟件的使用,極大地節約了消費者等待廣告播放完畢的時間。
隨著此類屏蔽技術的普及,互聯網平臺一方與屏蔽軟件使用者一方對于此類行為是否違法的爭議隨之而來。一方面,由于屏蔽軟件無法準確區別騷擾廣告和互聯網平臺發布的商業廣告,所以此類軟件會將互聯網平臺中存在的廣告全部屏蔽。[1]考慮到正常商業廣告利潤為互聯網平臺的收入來源之一,此類軟件的使用不但會影響互聯網平臺的廣告收入,也會觸發會員消費者停止支付會員費的心理,這便引起了互聯網平臺的不滿;另一方面,視頻廣告屏蔽軟件的出現有利于推動用戶自主選擇權的實現,非會員用戶不需要付費便可以跳過廣告直接欣賞正片,這類軟件當然會受到此類用戶的歡迎。
那么,此類行為是否應該受到法律規制呢?如果應當規制該如何展開違法性認定呢?在實務界,此類案件往往聚焦于行為不正當性的認定上,但立場不同的競爭主體從各自的角度出發往往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鑒于此,討論視頻廣告屏蔽行為規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行為違法性的認定標準具有極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二、視頻廣告屏蔽行為規制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視頻廣告屏蔽行為規制的必要性
學術界和實務界認為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無規制必要性的理由大概有以下兩點:第一,此類行為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第二,技術中立原則下此行為不違法。下文將針對兩個理由逐一提出反駁,利用逆向思維印證此類行為規制的必要性。
1.保護消費者利益說難以成立
反對規制者提出的第一個理由,是屏蔽行為有利于消費者。有觀點認為,消費者利益是利益衡量的重要考量因素,廣告屏蔽軟件的應用,可以讓消費者跳過廣告直接觀看點播的內容,的確提升了觀看體驗,有利于消費者利益的增進。[2]在考量競爭行為正當與否時,的確應當考慮消費者利益,但將消費者利益的保護定位在短期利益的增進上有所不妥。
2.技術中立說難以成立
反對規制者提出的第二個理由,是視頻屏蔽技術有技術中立性。有學者認為技術中立原則可以適用在視頻廣告屏蔽技術中,所以此類屏蔽行為不具有違法性。[3]實際上,此觀點沒有認清技術中立原則的適用范圍,此原則的適用范圍被限定在版權法侵權的判斷中。[4]
綜上可得,反對規制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的兩個理由,均難以成立,所以本文認為視頻廣告屏蔽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有規制的必要性。那么,規制此類行為是否可行呢?下文將進一步論述其規制的可行性。
(二)視頻廣告屏蔽行為規制的可行性
1.立法層面
理論上,《反不正當競爭法》互聯網專條和具有抽象性的一般條款給了其規制的空間。一般條款,一方面是判斷類型化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原則性規定,一方面也是判斷未類型化競爭行為正當性的直接法律依據。有著劃分競爭行為領地,調解市場機制的重要作用。互聯網專條是規制互聯網領域不正當競爭的法律依據,理論上,發生在互聯網領域的市場競爭行為都應當由此專條規制。
2.司法層面
司法層面上,多數法官認為此類行為具有違法性,是不正當競爭:但也有少數法官認為其不具有違法性,不構成不正當競爭。需要說明的是,雖然在少數案例的一審程序中,有法官認為此類行為不構成不正當競爭,但在二審程序中,法院支持了原告的訴訟請求,最終認定此類行為具有違法性。
三、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的違法性認定方法
司法實踐中,法官通常以《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為依據來認定廣告屏蔽行為的違法性。作為抽象的原則性條款,在以其為法律依據規制競爭行為時,需要將一般條款具體化,即對抽象的價值詞進行具體化解釋之后才可以在案件中適用。[5]一般條款的抽象性,決定了在具體化其內容時必然會產生諸多爭議,因此有必要厘清利用一般條款進行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認定的具體方法。近年來,針對競爭行為違法性的認定,司法實踐中進行了諸多嘗試,利益衡量和商業道德具體化逐漸成為公認的違法性認定方法。
(一)利益衡量法認定行為違法性
競爭行為會造成多方主體的損益交織,同時競爭法是獨特的行為規制模式,這就決定了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對競爭行為的違法性進行認定時,必須進行利益衡量。[6]司法實踐中對利益進行衡量的兩種方式:多元利益定性比較的方法、商業道德具體化的方法。
1.對多元利益進行定性比較
《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三元利益,即市場競爭秩序、消費者利益、競爭者權益。多元利益定性比較法,即先對多元利益進行分析,然后比較各方損益,最終得出行為正當與否的結論。在對多元利益進行定性分析時,有對各種利益等地位比較的,也有側重某種利益的,具體如下:
一種是對訴爭行為涉及的全部利益等地位比較,衡量各方利益得失。若總獲得大于總損失,那么競爭行為具有正當性,反之競爭行為即具有非正當性。比如,在評價視頻廣告屏蔽行為時,先分析出所有利益主體的總增進和總損害,如果利益的總增進大于利益的總損害,此類行為即為正當競爭行為。
一種是側重對比互聯網平臺與訴爭行為實施者利益的損益,同時考察消費者及公共利益,以“厚此薄彼”的方式判斷廣告屏蔽行為是否違法。比如,實務中,法官在認定訴爭行為的違法性時,指出被告損害了原告的利益,雖然屏蔽行為短期內可以增加消費者利益,但長遠來看必將導致消費者利益受損,所以此類行為是不正當競爭。
2.以比例原則進行利益衡量
比例原則可以將抽象標準具體化,從而限定出司法干預競爭行為的邊界,最終達到平衡各方利益之目的。比例原則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實現了地域普遍化和領域普遍化。從構成上看,比例原則包括適當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均衡性原則,此原則傳達的是一種適度、均衡的理念。那么比例原則具體在視頻廣告屏蔽領域應當如何應用呢?具體而言,在判斷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時,法官須運用“比例原則”的思維,考察視頻網站經營者的利益、廣告屏蔽軟件經營者的利益、市場競爭秩序、消費者利益及社會整體利益。首先,適當性原則要求,廣告的屏蔽應該有利于改善消費者的上網體驗。若此類屏蔽行為的應用無法達到此目的,那么行為便不符合適當性原則的要求;其次,必要性原則要求,廣告屏蔽技術的應用,應當遵循“最少、必要”原則。如果確實存在更少侵害視頻網站經營者的方式,但廣告屏蔽技術的使用者卻并未采取則是違反此原則的行為;最后,均衡性原則要求,廣告屏蔽技術帶來的積極效果應大于消極效果,否則行為就會違反均衡性原則。
(二)以商業道德認定行為的違法性
另外一種進行利益衡量的方式是將商業道德具體化,以相對具體化的規則評價競爭行為正當與否。最新頒布實施的《反不正當競爭法司法解釋》中,對商業道德作出了解釋,規定了行業慣例可作為商業道德認定標準,同時經營者主觀心理也影響著競爭行為的評價。就視頻廣告屏蔽行為而言,法官在認定行為正當與否時,可以考察待評價的競爭行為是否符合行業慣例,以及行為者是否為故意。
司法實踐中,也早有以行業慣例解釋商業道德的情況。需要說明的是,商業道德依然是原則性條款,法官仍需要結合個案案情,對其進行解讀,最終得出相應的評判結論。以行業慣例解釋商業道德,雖然的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縮一般條款的適用范圍,但行業慣例同樣是一個不確定性概念,存在著不確定性概念適用的固有難題。
四、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認定方法的不足與改進
總結完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認定方法之后,可以得知,雖然《反不正當競爭法》提供了具體規制方案,但這些方案中存有一些不足之處。從不足出發,找尋改進方法,才能更好地規制此類行為。
(一)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認定方法的不足
1.消費者利益的定位存在偏差
2017年《反不正當競爭法》修訂后,新法的一般條款明確將消費者權益作為判斷競爭行為違法與否的要素之一。新法此次的改進與完善,在明確了三元利益疊加保護的同時,也確立了前置“市場競爭秩序”要素的優先性,實現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現代化轉型。[7]消費者利益因素的添加是意義重大的,但此法中消費者利益的定位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定位有什么不同呢?若消費者利益指的是短期個人利益,那么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的確可以推進消費者利益;若指的是長期整體利益,那么結論則截然不同。換言之,消費者利益的定位勢必會影響競爭行為的評價,所以明確消費者利益的定位十分重要。
2.經營者利益受損的考察不當
《反不正當競爭法》是一部以排除過度干涉,鼓勵市場競爭為根本價值導向的競爭法。然而,在司法實踐中,有部分裁判者在認定行為違法性時,過度關注經營者受損的情況,忽視行為對市場競爭秩序產生的影響。此類裁判者錯將變化的動態利益歸屬于經營者,甚至可以說,對經營者利益的錯誤考察會造成對壟斷性權利的變相保護。長此以往,不僅市場競爭秩序會受到影響,消費者利益也會受到不利影響。
3.行業慣例合法與否存在疑問
雖然在司法實踐中,早有以行業慣例評價競爭行為的先例,但不能否認的是,行業慣例有自發性與滯后性的特點,以行業慣例解釋商業道德是否合法存在不確定性。自發性是指市場競爭行為具有盲目性,難以形成固定的慣例,即使形成固定慣例,也可能會偏離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倡導的價值理念。滯后性,是指慣例的形成需要逐漸積累,而在新型互聯網不正當競爭領域,先前經過不斷積累形成的慣例可能已不再適合此領域。行業慣例的這些特點,意味著如果對其不加審查,直接適用的話,很可能會將競爭行為正當性地認定引向錯誤的方向。
(二)視頻廣告屏蔽行為違法性認定方法的改進
1.整體視角考察消費者利益
《反不正當競爭法》中的消費者權益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的定位是不同的,前者所保護的消費者權益,應為整體消費者的長遠權益,而不是針對部分消費者的短期權益。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以個別消費者的短期權益作為衡量競爭行為正當與否的案例。這種做法雖然確實考察了消費者利益,但也需要承認其對消費者個別性的保護偏離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的價值取向。所以在認定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的違法性時,應當從整體視角考察消費者利益,改變以往錯誤定位,才能更好地保護消費者長遠利益。
2.重塑經營者利益受損的考察
在市場競爭環境中,競爭者的損和益會形成一種動態平衡。也正是在這種動態平衡的過程中,市場本身可以更好地發揮其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進而才可以保障整體消費者的長遠利益。所以,經營者因競爭而遭受損害是非常正常的情況,僅僅考察經營者受損情況,無法直接判斷某一競爭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
鑒于此,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保護的經營者權益,應當是一種根本性的核心利益。如果某一待評價行為雖對于經營者利益構成了損害,但未觸及其核心利益,那么此行為是否具有不正當性還需綜合其他因素予以判別,而不是據此便直接將其認定為需要被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3.先行審查行業慣例的合法性
先行審查行業慣例的合法性是解決其自發性與滯后性的有效方式,這在司法實踐中,也有所體現。比如,有被告認為此類行為是其行業普遍存在的行業慣例,所以此行為符合商業道德,不具有違法性。實際上,行為違法與否絕不能僅以該行業此類軟件的存在及規模來驗證,如果具有違法性的行為在某一個行業內大規模存在,只能說明違法現象的嚴重,行業慣例并不能成為此類行為合法性的證明。現實生活中的諸多案例都可以印證行業慣例并非一定是好的,故采用行業慣例來解釋商業道德之前,先行審查行業慣例的合法性是十分必要的。
五、結語
經過上文幾個部分的分析可以得知,文章首先從推翻反對規制視頻廣告屏蔽行為的兩個理由出發,可以得出此類行為具有規制的必要性,再結合立法及司法現狀得出此類行為具有規制的可行性。然后,進一步總結出其違法性認定方法通常有利益衡量法與商業道德具體化兩種,指出認定方法存在著“消費者利益定位有誤、經營者利益考察不當、行業慣例合法性不明”三個方面的不足。最后,針對性地從“整體視角考察消費者利益、重塑經營者利益的考察、先行審查行業慣例的合法性”三個方面對違法性認定方法進行改進,以期能夠最大限度地保護市場競爭秩序、消費者利益、經營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