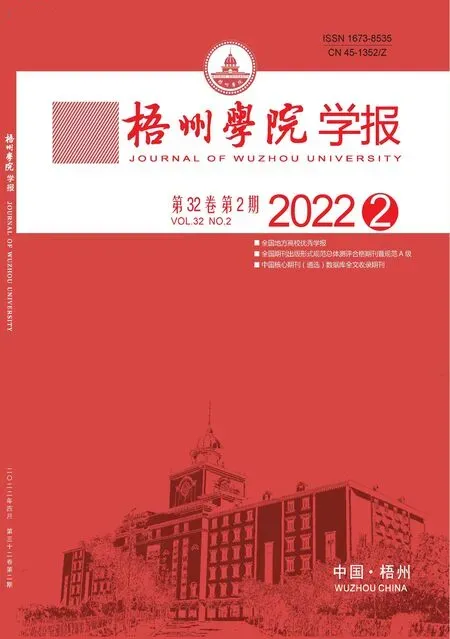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的限制及其處置方式
傅哲明
(北京大學 法學院,北京 100871)
2013年11月12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國家公園體制”,我國的國家公園熱由此興起。2015年5月18日,國務院批轉的《發展改革委關于2015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工作意見》(國發〔2015〕26號)提出:“在9個省份開展國家公園體制試點”。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2017年9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規定了建立統一事權和分級管理體制。自然資源分為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明確了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權由中央政府和省級政府分級行使,但是未規定非全民所有,即集體所有權的行使。國家公園自然資源存在復雜的權屬關系。在劃清全民所有和集體所有之間的邊界后,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是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的具體行使。2019年6月26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要求創新自然保護地建設發展機制,并提出“對劃入各類自然保護地內的集體所有土地及其附屬資源,按照依法、自愿、有償的原則,探索通過租賃、置換、贖買、合作等方式維護產權人權益,實現多元化保護。”此外,“對集體和個人所有的商品林,地方可依法自主優先贖買。”2021年10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昆明召開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宣布:中國正式設立三江源國家公園等第一批國家公園。我國《國家公園法(草案)》的撰寫正在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的組織下緊鑼密鼓地進行中。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的行使和限制是在立法過程中遇到的一大問題。本研究在理清國家公園和集體所有權概念的基礎上,展示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受到的限制,論證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受到的限制的正當性,對比分析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限制的處置方式,以期為開展相關立法工作提供參考。
一、國家公園中所有權限制的具體表現
(一)國家公園中的集體所有權
“國家公園”概念一般認為是由美國的喬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提出的[1]。1872年,美國國會批準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美國黃石國家公園[2]。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為“國家公園”設立了定義,得到國際廣泛認可:“大面積自然或近自然區域,用以保護大尺度生態過程以及這一區域的物種和生態系統特征,同時提供與其環境和文化相容的精神的、科學的、教育的、休閑的和游覽的機會。”[3]《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為國家公園設立了定義:“國家公園是指由國家批準設立并主導管理,邊界清晰,以保護具有國家代表性的大面積自然生態系統為主要目的,實現自然資源科學保護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陸地或海洋區域。”
《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中將集體所有權定義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權是指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組織的財產所有權。”[4]《中華法學大辭典·民法學卷》寫道:“集體組織所有權又稱勞動群眾集體組織的財產所有權,是勞動群眾集體組織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其財產的權利。”[5]
在我國國家公園中存在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如,四川、陜西、甘肅三省大熊貓國家公園內國有土地面積19 378km2,占公園總面積的71.41%;集體土地面積7 756km2,占公園總面積的28.59%。東北虎豹公園總面積149.26萬hm2,其中,國有土地面積136.44萬hm2,占虎豹公園總面積的91.41%,集體土地面積12.82萬hm2,占8.59%。
(二)國家公園對集體所有權的限制
2007年,杭州市國土資源局的一紙房屋拆遷爭議裁決書讓多位西溪濕地原住民感到不滿,其中有人向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訴訟,但訴訟請求被駁回[6]。由此案可以看出,國家公園中的集體所有權行使頗具爭議。一方面,承包權人、經營權人主張基于集體所有權而獲得的承包權、經營權應當受到保護,他們可以利用土地等自然資源。而另一方面,國家公園的建設限制了他們對土地等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
國家公園中的集體所有權受到一定限制,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均受到限制。在占有權方面,由國家公園占有土地;在使用權方面,由國家公園管理機構統一決定使用方向。在收益權和處分權方面受到的限制更多:在收益權方面,除不損害生態系統的原住民生產生活設施改造和自然觀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開發建設活動①(1)注:①《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要求:“除不損害生態系統的原住民生產生活設施改造和自然觀光、科研、教育、旅游外,禁止其他開發建設活動。國家公園區域內不符合保護和規劃要求的各類設施、工礦企業等逐步搬離,建立已設礦業權逐步退出機制。”,禁止大部分的收益活動;在處分權方面,國家公園土地專供國家公園建設使用,禁止例如抵押、流轉等。在國家公園建設中,集體所有土地不得隨意發包,承包權受到限制。“除不損害生態系統的原住民生產生活設施改造和自然觀光、科研、教育、旅游外”,通常是通過特許經營實現,經營權受到限制。
所有權作為一種絕對權,權利人之外的一切人均為義務人。那么,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受到限制呢?答案是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其可以限制所有權的取得和行使。根據中國《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條規定:“民事主體不得濫用民事權利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具體落實到國家公園,我們回顧國家公園的雛形——自然保護區相關立法,自然保護區內禁止開展砍伐、放牧、狩獵、捕撈、采藥、開墾、燒荒、開礦、采石、挖沙等活動②(2)②《自然保護區條例》第二十六條規定:“禁止在自然保護區內進行砍伐、放牧、狩獵、捕撈、采藥、開墾、燒荒、開礦、采石、挖沙等活動;但是,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內,不得建設任何生產設施。在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內,不得建設污染環境、破壞資源或者景觀的生產設施③(3)③《自然保護區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在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內,不得建設任何生產設施。在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內,不得建設污染環境、破壞資源或者景觀的生產設施;建設其他項目,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污染物排放標準。在自然保護區的實驗區內已經建成的設施,其污染物排放超過國家和地方規定的排放標準的,應當限期治理;造成損害的,必須采取補救措施。”。
二、國家公園限制集體所有權的理論基礎
具體落實到國家公園層面,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對集體所有權進行了限制,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優位于集體所有權。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國家公園管理機構統一管理國家公園內的土地和生產資料。早在羅馬法時代,查士丁尼就提出:“任何人不應濫用自己的財產,這是與公共利益有關的。”[7]美國學者博登海默指出:“公共福利(即公共利益)這一概念意味著在分配和行使個人權利時絕不可以超越的外部界限……個人對于實現自身自由、平等和安全的要求乃是深深的根植于人格的傾向和需要之中的,對上述三個價值的效力范圍進行某些限制是和公共利益相符的。在這些情形下,正義提出了這樣一個要求,即賦予人的自由、平等和安全應當在最大限度上和公共福利相一致。”[8]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按照國家公園管理機構這一權威的要求,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受到約束和限制,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均受到限制。
具體到國家公園層面,為何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優位于集體所有權,其理論來源和環境立法目的類似,即來源于可持續發展理論、代際公平理論和公共信托理論[9]。這3個理論除了為環境立法目的提供了理論依據,也可以用以論證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的優位性。在人類活動嚴重破壞自然生態環境的當下,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應當“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我國2014年的《環境保護法》第四條后句要求:“……使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區別于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第四條后句“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新《環境保護法》明確環境保護為基本國策,使環境保護的地位大大提升。這樣的提升除了反映了我國政府對環境保護的重視外,也體現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的優位性。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這樣的限制必須經由正當程序的立法予以規定,這種限制是符合比例原則的。
首先,對于權利的限制(公共利益)和權利之間的邏輯關系,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外在限制說”認為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外在與基本權利的限制,公共利益乃是基本權利之外的對基本權利的制約;“內在限制說”則把公共利益看作是基本權利的內在限制,也就是基本權利按其本性的自我規定,公共利益這種限制實際上是依基本權利自身的性質產生的,是存在于基本權利自身之中的限制,任何權利按照其社會屬性,都有一個“固定范圍”,所謂“權利的限制”不過是在此固定范圍的邊界之外的東西。
“外在限制說”明確地把“權利的構成”和“權利的限制”區分為兩個層次的問題,但是卻隱含著導致“公共利益優位論”的危險:很容易產生公共利益高于個人利益,公共利益絕對而個人利益相對的認識。“內在限制說”雖然沒有這種危險,但是它認為權利自始就有一個固定的范圍,在討論基本權利構成的時候,先驗地、人為地把一些事項作為基本權利本質上就不能包括的內容,這樣就會過早地將一些本來可能成為基本權利內涵的事項武斷地排除了。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翔認為,可以采納的學說應當為“外在限制說”,但需要注意在“外在限制說”的基礎上對公共利益進行限定,即“對限制進行限制”:首先是對公共利益優位論的否定,其次是對抽象公益條款效力的否定,再者是明確法律的明確性與比例原則,最后是司法審查[10]。權利位階原則、法律保留原則、比例原則和正當程序原則都是對權利限制中的權利保護的基本原則[11]。
“對限制進行限制”體現在國家公園中對集體所有權的限制上,就是這種對集體所有權的限制必須經由正當程序的立法予以規定,并且符合比例原則。
三、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限制的處置方式
對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和私人所有權限制的處置方式可以分為絕對限制和相對限制。絕對限制由國家公園管理部門獲取完整的土地及資源所有權,例如征收、贖買、置換、捐贈等;相對限制則由國家公園管理部門獲取部分的土地及資源權利,以約定方式體現,如設定地役權合同、租賃等。絕對限制和相對限制的區別在于國家公園管理部門是否獲取完整的土地及資源所有權。這些方式可能被單獨或混合使用,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方式的使用需要按照每一個國家公園的具體情況量身定制。詳述如下。
(一)絕對限制
1.征收、贖買和置換
在我國,征收通常和征用同時出現,但值得注意的是征收要強制專一所有權,征用的目的旨在獲得使用權;“征用必須是在緊急狀態下才能進行”[12],故征用不適用于本研究討論的情形。我國《憲法》第十條第三款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土地管理法》第二條第四款同樣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給予補償。”2012年修正的《農業法》第七十一條規定:“國家依法征收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應當保護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合法權益,依法給予農民和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征地補償,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截留、挪用征地補償費用。”我國征收的案例有岳麓山風景名勝區和前文提到的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建設①(4)注:① 2006年11月30日湖南省第十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批準通過《岳麓山風景名勝區保護條例》,其第十條規定:“風景名勝區內的土地、森林等自然資源和房屋等財產的所有權人、使用權人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市人民政府按照規劃的要求,征收核心景區內的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時,應當依法做好補償安置工作。”。我國臺灣地區《國家公園法》第九條規定:“國家公園區域內實施國家公園計劃所需要之公有土地,得依法申請撥用。前項區域內私有土地,在不妨礙國家公園計劃原則下,準許保留作原有之使用。但為實施國家公園計劃需要私人土地時,得依法征收。”征收強制性強,有利于統一規劃管理國家公園。但是,通常補償標準較低,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且補償方式單一,簡單的貨幣補償并不能完全解決集體所有權人失去土地帶來的生存問題,容易引發原住民與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
贖買是指國家出資使資本國有化的過程。贖買可以使集體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國有化,以便統一管理,但是所需資金成本較大。具體案例如湖南南山國家公園管理局編制了《湖南南山國家公園體制試點區生態補償機制實施意見(征求意見稿)》。同時,擬對試點區內生態公益林實行“擴面”和“提標”,將所有林業用地全部劃為公益林,逐步提高生態公益林補償標準,并探索推進政府“贖買”“租賃”集體公益林途徑[13]。
征收、贖買由國家權力保障,方便國家公園統一規劃建設,需要給予補償,但相對而言補償標準較低,而且會使農民喪失賴以生存的土地。
“土地置換的涵義是指通過土地用途更新、土地結構轉換、土地布局調整、土地產權重組等措施,實現土地現有功能和潛在功能的再開發,從而優化用地配置。”[14]
2015年9月23日深圳市人民政府印發的《關于征地安置補償和土地置換若干規定(試行)的通知》(深府〔2015〕81號)第九條:“因原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所在社區的全部土地被整體征收,或者位于水源保護區及農用地、未利用地區域內,無法按本試行規定在繼受單位經濟關系未理順的土地上進行安置的,原則上采取貨幣補償,但經市政府批準,可以在國有儲備土地上進行安置。”由此可見,集體所有的土地可以和國有土地或集體所有土地進行置換。土地對于農民來說是生存之本,土地置換相對于征收、贖買等以資金換取土地的方式,以地換地的方式相對來說更能保障農民的基本生活。
2.捐贈
捐贈按照我國《合同法》第十一章“贈與合同”的規定,由國家公園管理機構和農民或集體經濟組織等簽訂贈與合同,國家公園管理機構依合同取得相應物權。由于捐贈對于農民或集體經濟組織犧牲較大,目前并未發現有這樣的例子。但不排除理論上的可行性。捐贈雖然出于權利人自愿,但依舊會使農民喪失賴以生存的土地,且得不到相應補償,在我國非可通行之例。
(二)相對限制
1.設定地役權合同
設定地役權合同為物權合同,地役權優先于債權保護,對農民補償較為到位。《民法典》第三百七十二條規定:“地役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定,利用他人的不動產,以提高自己的不動產的效益。”簽訂地役權合同,國家公園管理機構依法取得地役權,該地役權屬于用益物權,受《民法典》保護。
具體案例如《開化縣人民政府錢江源國家公園管理委員會關于印發錢江源國家公園集體林地地役權改革實施方案的通知》(開政發〔2018〕44號)中規定:“錢江源國家公園集體林地地役權改革補償標準為48.2元/(畝·年),其中:公共管護和管理費用5元/(畝·年),地役權補償金43.2元/畝;集體林地地役權改革后,原享有的生態公益林補助政策不再重復享受。”[15]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設定地役權合同的對價較低,在一定程度上并不利于集體所有權人的利益。應當提高地役權合同對價,才能更好地保護集體所有權人。
2.租賃
租賃按照我國《民法典》第三編第十四章“租賃合同”的規定,由國家公園管理機構和農民或集體經濟組織等簽訂租賃合同。具體案例可以參考舊自然保護區的做法。例如,2006年3月,寧夏回族自治區出臺《寧夏回族自治區六盤山、賀蘭山、羅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條例》,其中第十四條規定,自然保護區內集體土地可以由自然保護區管理機構與當地有關集體經濟組織簽訂社區共建協議,按照自然保護區管理規定進行管理。2011年10月浙江衢州市出臺的《浙江衢州烏溪江國家濕地公園保護管理暫行辦法》第五條規定,規劃區內的土地權屬關系維持不變,農村集體土地未經合法征收,不得改變為國有,農民享有自主經營權。國家公園管理機構依合同取得租賃權。該租賃權屬于債權,不需要不動產登記,權利形成較為方便簡單,形式較為靈活,但是法律保護“剛性不足”[16]。
四、結語
我國國家公園可能存在集體所有的土地和生產資料。出于保護生態自然環境的公共利益需要,國家公園中的集體所有權受到一定限制,其占有、使用、收益、處分權能均受到限制。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按照國家公園管理機構這一權威的要求,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受到外部的約束和限制。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公共利益優位于集體所有權。對國家公園中集體所有權限制的處置方式可以分為征收、贖買、置換、捐贈、設定地役權合同、租賃等。總體而言,針對中國目前的國情,征收、贖買、租賃、捐贈缺陷較大,而采用設定地役權合同和置換較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