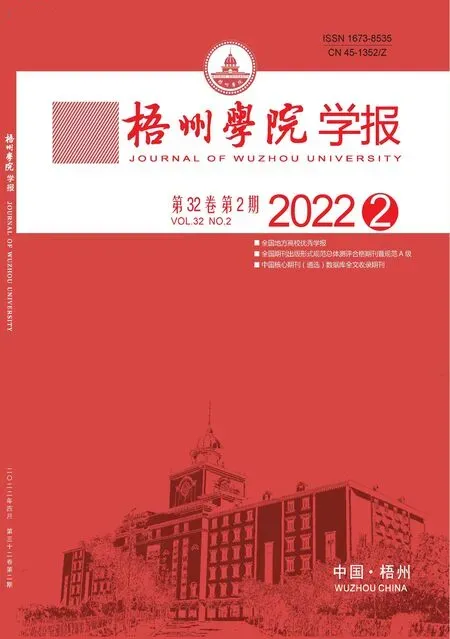高校開(kāi)設(shè)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課程的必要性
王 丹,高 魏,李城宗
(1.重慶工商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重慶 南岸 400067;2.西南大學(xué) 漢語(yǔ)言文獻(xiàn)研究所,重慶 北碚 400715;3.梧州學(xué)院 文學(xué)與傳媒學(xué)院,廣西 梧州 543002)
中華民族是由多個(gè)民族共同構(gòu)成的命運(yùn)共同體,擁有豐厚淵源、多元璀璨的民族文化。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載體和媒介,我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也是異彩紛呈、博大浩渺的。“多民族文學(xué)”概念是在強(qiáng)調(diào)獨(dú)特性和差異性的“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概念的基礎(chǔ)上發(fā)展起來(lái)的,旨在彰顯民族文學(xué)原本交融、富有彈性、多元一體的有機(jī)聯(lián)系。可以說(shuō),“多民族文學(xué)”是對(duì)“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概念的探索、拓展和超越,體現(xiàn)了文學(xué)研究領(lǐng)域在思維方式和心理認(rèn)知層面的轉(zhuǎn)變,而這一文學(xué)觀念的轉(zhuǎn)變正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自覺(jué)[1]。高校是弘揚(yáng)優(yōu)良民族文化、建構(gòu)多元民族史觀、實(shí)踐平等民族政策的重要場(chǎng)所,更是我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研究的核心陣地。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歷史背景下,針對(duì)當(dāng)前“中華多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在高校仍處于極度缺失與偏頗之境遇”[2]的現(xiàn)實(shí)狀況,在各高校,特別是更具學(xué)科設(shè)置條件和師資人才優(yōu)勢(shì)的高校中文院系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教學(xué)教研活動(dòng)就很有必要。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時(shí)政需求
自古以來(lái),中國(guó)就是一個(gè)幅員遼闊、文化豐厚的多民族國(guó)家,中華文明是由其歷史上諸多民族的人民共同締造的,這是寫(xiě)入《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憲法》,為世人所公認(rèn)的事實(shí)。“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是全國(guó)各族人民共同締造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guó)家”,“中國(guó)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光輝燦爛的文化,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tǒng)”[3]。
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一直都特別重視民族團(tuán)結(jié),注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建構(gòu),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lái),全國(guó)上下對(duì)“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認(rèn)識(shí)不斷深化。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會(huì)議提出要“積極培養(yǎng)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4];2017年黨的十九大進(jìn)一步提出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5],并將此寫(xiě)入了黨章;201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憲法》中首次寫(xiě)入“中華民族”一詞;2019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的《關(guān)于全面深入持久開(kāi)展民族團(tuán)結(jié)進(jìn)步創(chuàng)建工作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意見(jiàn)》“強(qiáng)調(diào)要加強(qiáng)中華民族共同體教育”[6];2021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huì)議強(qiáng)調(diào),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作為新時(shí)代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是鞏固和發(fā)展平等團(tuán)結(jié)互助和諧社會(huì)主義民族關(guān)系的必然要求,只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才能增進(jìn)各民族對(duì)中華民族的自覺(jué)認(rèn)同,夯實(shí)我國(guó)民族關(guān)系發(fā)展的思想基礎(chǔ),推動(dòng)中華民族成為認(rèn)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強(qiáng)的命運(yùn)共同體。”[7]
文化是“人類(lèi)面對(duì)不同環(huán)境建立的自我保護(hù)、自我表達(dá)的機(jī)制,因此是共同的人性在不同狀況下的不同表述”[8]109。了解并尊重民族文化,是各民族之間實(shí)現(xiàn)交往、交流、交融,實(shí)現(xiàn)平等團(tuán)結(jié)和諧的基本前提。文學(xué)是人類(lèi)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shí)更是表述文化和傳播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媒介。通過(guò)民族文學(xué)來(lái)了解民族文化,進(jìn)而達(dá)到對(duì)民族文化的認(rèn)識(shí)、理解、包容和尊重,這對(duì)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具有極其重要的促進(jìn)作用。
高校是傳授知識(shí)文化、培養(yǎng)專(zhuān)業(yè)人才的關(guān)鍵場(chǎng)所,同時(shí)也是幫助青年學(xué)生樹(shù)立正確世界觀、人生觀、價(jià)值觀等思想觀念的重要陣地。大學(xué)生是未來(lái)社會(huì)發(fā)展的中堅(jiān)力量,他們正處于“人生社會(huì)化的關(guān)鍵時(shí)期”[9],同時(shí)也處于“人的各種心理品質(zhì)全面發(fā)展、急劇變化”的青年時(shí)期。大學(xué)生的心理發(fā)展存在著不穩(wěn)定、可塑性大的特點(diǎn),他們“喜歡接受新事物和新觀念的特性,使他們?nèi)菀资艿酵饨绛h(huán)境因素的影響,特別是教師、父母、同齡人、大眾傳播媒介的影響,朝著積極的方向發(fā)生變化,具有很大的可塑性”[10]。在高校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以此強(qiáng)調(diào)中華民族共同體教育、深化民族團(tuán)結(jié)進(jìn)步教育、拓展多民族文化教育,進(jìn)而促進(jìn)大學(xué)生對(du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的自覺(jué)認(rèn)可、認(rèn)同,切實(shí)做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可見(jiàn),在我國(guó)特定的民族文化關(guān)系和社會(huì)政治制度下,當(dāng)前,推動(dòng)高校進(jìn)行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課程教學(xué),具有迫切的現(xiàn)實(shí)意義和深遠(yuǎn)的歷史意義。
二、推進(jìn)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傳播與研究的學(xué)科需求
中國(guó)文學(xué)是多民族的文學(xué),強(qiáng)調(diào)的是“多文學(xué)”,即在民族多元的基礎(chǔ)上體現(xiàn)出的文學(xué)多樣性[11]。除了卷帙浩繁、博大豐厚的漢族文學(xué)之外,我國(guó)其他民族的文學(xué)也是群星璀璨、異彩紛呈、成就斐然的。總體而言,我國(guó)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活動(dòng)的時(shí)間跨度、空間跨度、文化形態(tài)跨度、作品形態(tài)跨度、語(yǔ)言形態(tài)跨度等都很大,文學(xué)作品數(shù)量豐厚,內(nèi)容琳瑯滿(mǎn)目,極具豐富性和特殊性。其中“有優(yōu)雅的文人之作,也有質(zhì)樸的人民口頭創(chuàng)作。有關(guān)于宇宙形成、萬(wàn)物由來(lái)的解釋,也有關(guān)于民族起源的記錄。有講述一人一事的故事,也有蔚為大觀的百科全書(shū)式的作品”[12]。單就史詩(shī)體裁而言,這種長(zhǎng)篇敘事詩(shī)作在我國(guó)許多民族的文學(xué)史中是熠熠奪目、數(shù)不勝數(shù)的。《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這三大史詩(shī)“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的巔峰,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還流傳著數(shù)百種中小型神話史詩(shī)”[13],諸如赫哲族的《滿(mǎn)豐莫日根》、鄂倫春族的《英雄格帕欠》、蒙古族的《勇士谷諾干》、維吾爾族的《艾里甫與賽乃姆》、哈薩克族的《英雄托布吐克》、彝族的《阿詩(shī)瑪》、苗族的《娘阿莎》、納西族的《黑白爭(zhēng)戰(zhàn)》、壯族的《布洛陀》、瑤族的《密洛陀》,等等。如此豐富多樣多彩的民族文學(xué),它們不僅是其所屬民族的精神財(cái)富,更是中華子孫共同的文化積淀,理應(yīng)為世人所普遍認(rèn)知、熟識(shí),以實(shí)現(xiàn)中華精神文化的共存、共享、共榮。
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以后,我國(guó)圍繞“多民族文學(xué)”開(kāi)展了一系列相關(guān)的實(shí)踐活動(dòng),例如“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概念的提出,以及“多民族文學(xué)”概念的探索;各民族文學(xué)史或文學(xué)簡(jiǎn)史的編纂;集中展現(xiàn)民族文學(xué)作品的專(zhuān)欄和專(zhuān)刊的設(shè)置及創(chuàng)辦;對(duì)民族民間文學(xué)的廣泛搜集整理和集結(jié)出版;民族文學(xué)研究機(jī)構(gòu)的創(chuàng)立;民族文學(xué)研究雜志的創(chuàng)刊;置于“中國(guó)語(yǔ)言文學(xué)”一級(jí)學(xué)科之下的“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學(xué)”學(xué)科的設(shè)立,等等。國(guó)家有關(guān)多民族文學(xué)的具體歷史實(shí)踐,就是中國(guó)共產(chǎn)黨“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為主線”來(lái)開(kāi)展民族工作的重要體現(xiàn)。在這些實(shí)踐過(guò)程中,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資源得到了廣泛而深入的挖掘、挽救、保護(hù)、整理和研究,成果豐碩,這對(duì)于維護(hù)中國(guó)文學(xué)的民族多樣性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1979年2月3日,由賈芝、毛星、馬寅、馬學(xué)良、王平凡5人起草并送交黨中央、國(guó)務(wù)院的《關(guān)于成立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的請(qǐng)示報(bào)告》指出:“從發(fā)展文學(xué)事業(yè)的方面看,少數(shù)民族有著豐富的民間文學(xué)、作家文學(xué)以及文藝?yán)碚撨z產(chǎn),可以說(shuō)占據(jù)著中國(guó)文學(xué)的半壁江山;從政治意義上來(lái)說(shuō),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的研究能夠增強(qiáng)民族團(tuán)結(jié),提升民族自尊,增強(qiáng)民族凝聚力。”[14]請(qǐng)示中的這段文字,不僅強(qiáng)調(diào)了成立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的根本目的,同時(shí)也明確指出了我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對(duì)于發(fā)展中國(guó)文學(xué)事業(yè)的學(xué)術(shù)意義和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政治意義。
面對(duì)如此豐富多樣且優(yōu)秀的民族文學(xué)作品,以及日漸豐碩的民族文學(xué)研究成果,在不斷壯大的民族文學(xué)研究隊(duì)伍的支持下,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在高校教學(xué)活動(dòng)中得到了一定的重視。例如,由袁世碩、陳文新等人主編、例屬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shè)工程重點(diǎn)教材”的《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中就增加了一章專(zhuān)門(mén)介紹和分析中國(guó)三大英雄史詩(shī)的內(nèi)容[15]。再如,作為我國(guó)綜合性(非專(zhuān)門(mén)的民族類(lèi))重點(diǎn)高校之一的四川大學(xué),在相關(guān)師生的倡導(dǎo)和參與下,于該校的全校通識(shí)選修課程“中華文化”、國(guó)家精品課程“比較文學(xué)”、校級(jí)公選課程“文化人類(lèi)學(xué)”中也列入了“多民族文學(xu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積極貫徹著以“多民族史觀”為核心的文學(xué)教育,用具體的教學(xué)實(shí)踐展現(xiàn)了多民族文化互補(bǔ)共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8]96。另外,諸如南開(kāi)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四川大學(xué)、南京大學(xué)、內(nèi)蒙古大學(xué)、新疆大學(xué)、西藏大學(xué)、云南大學(xué)、廣西大學(xué)等綜合性重點(diǎn)高校,北京師范大學(xué)、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新疆師范大學(xué)、青海師范大學(xué)、云南師范大學(xué)、貴州師范大學(xué)、四川師范大學(xué)、廣西師范大學(xué)等師范類(lèi)重點(diǎn)高校,也開(kāi)設(shè)了“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文學(xué)”相關(guān)專(zhuān)業(yè)或方向的課程[2]。
上述實(shí)踐表明,隨著我國(guó)各項(xiàng)民族政策的有效貫徹及對(duì)“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思想討論的不斷深入,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育在我國(guó)部分高校得到了一定組織和開(kāi)展。與此同時(shí),高校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存在的問(wèn)題也顯現(xiàn)出來(lái),高校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學(xué)的缺失和偏頗也是不容忽視的。首先,就是多民族文學(xué)課程設(shè)置的缺失。“相對(duì)于研究屆而言,綜合性大學(xué)中文系教學(xué)系統(tǒng),多數(shù)沒(méi)有把各民族文學(xué)經(jīng)典納入教學(xué)與研究視野,絕大多數(shù)講授只是局限于漢語(yǔ)文學(xué)經(jīng)典。”[16]另外,還有諸如“多民族文學(xué)史觀”在教學(xué)中的貫徹力度不足[17],多民族文學(xué)的價(jià)值與課程教學(xué)量不對(duì)等,教學(xué)主體的教學(xué)觀念及方法與多民族文學(xué)現(xiàn)狀脫節(jié),多民族文學(xué)的比較性教學(xué)缺失等問(wèn)題[18],亟待解決。
在我國(guó)各高校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課程教育,面向全校學(xué)生進(jìn)行相關(guān)內(nèi)容的教學(xué),通過(guò)秉持“多元文學(xué)史觀”的文學(xué)教育,對(duì)于拓展學(xué)生的知識(shí)視野和學(xué)術(shù)視野、培養(yǎng)學(xué)生的比較思維和多元思維、強(qiáng)化學(xué)生的包容意識(shí)和團(tuán)結(jié)精神、激揚(yáng)學(xué)生的愛(ài)國(guó)熱情和民族情懷,都將是不無(wú)裨益的。同時(shí),這種文學(xué)教學(xué)勢(shì)必也將大大擴(kuò)展多民族文學(xué)的傳播范圍,增強(qiáng)民族文學(xué)的認(rèn)知廣度和研究深度。
我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多具有綜合性質(zhì),與其他若干學(xué)科的知識(shí)有著千絲萬(wàn)縷的聯(lián)系,也“發(fā)揮著極為綜合的社會(huì)文化功能,對(duì)它的研究也就不能過(guò)于局限于文學(xué)學(xué)的方法,像民族學(xué)的、社會(huì)學(xué)的、宗教學(xué)的、文化人類(lèi)學(xué)的和藝術(shù)的等角度和方法,都會(huì)有用武之地”[12]。只有通過(guò)普及高校學(xué)生的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教育,激發(fā)不同學(xué)科學(xué)生的興趣,引導(dǎo)他們將其所學(xué)專(zhuān)業(yè)知識(shí)與民族文學(xué)的相關(guān)內(nèi)容加以聯(lián)系,從多維的專(zhuān)業(yè)角度來(lái)審視民族文學(xué),這樣才能將我國(guó)的民族文學(xué)研究得更深更透,進(jìn)而使其更好地發(fā)揮社會(huì)文化功能。當(dāng)代高校大學(xué)生將是推動(dòng)我國(guó)社會(huì)不斷發(fā)展的生力軍,時(shí)下要努力吸引他們對(duì)我國(guó)民族文學(xué)的持續(xù)關(guān)注,并從他們中間培養(yǎng)出研究民族文學(xué)、傳播民族文化的后繼者,以及發(fā)展民族文學(xué)學(xué)科的接班人。
由上可見(jiàn),在高校進(jìn)行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內(nèi)容教學(xué),對(duì)于學(xué)生而言,是拓展他們文化視野的有效方式,具有即時(shí)意義;對(duì)于學(xué)科發(fā)展而言,是培養(yǎng)后繼研究者的重要渠道,具有長(zhǎng)遠(yuǎn)意義。
三、完善中國(guó)文學(xué)課程的教學(xué)需求
中國(guó)文學(xué)應(yīng)當(dāng)是中國(guó)所有民族的文學(xué)的總匯,是由多民族文學(xué)融合而成的多元性、整體性文學(xué),“拋開(kāi)各族文學(xué)的所謂中國(guó)文學(xué)是不完全的,或者是漢族文學(xué)”[19]。然而,目前多數(shù)高校中國(guó)文學(xué)課程的教學(xué),無(wú)論是所用教材的框架還是具體授課的內(nèi)容,主要還是漢族文學(xué)。近年來(lái),一般較有規(guī)模的中國(guó)文學(xué)教材,都會(huì)為多民族文學(xué)專(zhuān)辟一些章節(jié),這是值得肯定和借鑒的。例如,前文提到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shè)工程重點(diǎn)教材”《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以及1997年初版(10卷)、2010年再版(12卷)由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和民族文學(xué)研究所合編的《中華文學(xué)通史》(列屬“九五”國(guó)家社會(huì)科學(xué)規(guī)劃項(xiàng)目)[20]。但是,這種板塊拼接的形式只是通過(guò)在以漢族文學(xué)為主體的文學(xué)史書(shū)寫(xiě)或講授中增設(shè)一些有關(guān)多民族文學(xué)的章節(jié),這樣還是顯得有些機(jī)械和生硬[21]。教材如此,教學(xué)活動(dòng)亦然。如此看來(lái),要真正樹(shù)立起“中華多元一體”的民族史觀和文學(xué)史觀,真正展現(xiàn)出中國(guó)文學(xué)的多元性、融合性和完整性,各高校應(yīng)當(dāng)高度重視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教學(xué),特別是滲入深層肌理的教學(xué)活動(dòng)。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中國(guó)現(xiàn)代文學(xué)、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學(xué)的教學(xué)都需要有這種觀念、態(tài)度和思路。
例如,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課程都會(huì)講到屈原,講到他的創(chuàng)作深受楚地民歌的影響。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寫(xiě)到:南方楚地,本有自己獨(dú)特的文化藝術(shù)系統(tǒng),有“南冠”“南音”之稱(chēng),與“南音”直接相關(guān)的楚地民歌,也有不同于北方的語(yǔ)言形式。公元前六世紀(jì)中葉出現(xiàn)的一首越人“擁楫而歌”譯成的楚歌《越人歌》《孟子》引用的《滄浪歌》等,其詩(shī)句的參差不齊,就與《詩(shī)經(jīng)》有別[22]。這里有關(guān)《越人歌》的介紹是極為簡(jiǎn)單的,我們不禁會(huì)問(wèn):《越人歌》是怎樣的內(nèi)容?它如何能脫穎而出進(jìn)入中國(guó)文學(xué)史冊(cè)?越人的歌是如何成為楚地民歌的?如果沒(méi)有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史觀和視野,這些內(nèi)容可能就會(huì)一帶而過(guò),從而錯(cuò)過(guò)諸多精彩。《越人歌》是“中國(guó)古代使用壯侗語(yǔ)族語(yǔ)言民族的古老民歌”[23],也是我國(guó)“第一首譯詩(shī)”[24]。一年的舟游盛會(huì)上,越人歌手擁楫而歌,用越語(yǔ)對(duì)楚國(guó)令尹鄂君子皙唱出了心悅之情,有人用楚語(yǔ)將該歌譯作:“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越人歌》清新自然、優(yōu)美動(dòng)聽(tīng),最后一句更是用諧音、比興、雙關(guān)等手法來(lái)點(diǎn)明真情,溫婉而細(xì)膩。通過(guò)閱讀和比照,方能真切地感受到屈原作品與楚地民歌的相近風(fēng)格。從《越人歌》我們可以了解到當(dāng)時(shí)南方民歌是怎樣的一個(gè)水平,它與北方民歌有怎樣的區(qū)別,同時(shí),還可以大致了解到中國(guó)文學(xué)之翻譯文學(xué)的發(fā)端狀況,了解到中國(guó)文學(xué)之比較文學(xué)的民族特性。如果教育工作者具有中國(guó)多民族史觀和文學(xué)史觀,在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的教學(xué)實(shí)踐中有機(jī)地融合相關(guān)的民族文學(xué)作品,分析漢族文學(xué)與其他民族文學(xué)的互動(dòng)、融合關(guān)系,勢(shì)必能增加中國(guó)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的廣度和深度,進(jìn)而達(dá)到更為理想的教師智性教學(xué)和學(xué)生趣性受學(xué)的雙向目的。
可見(jiàn),要完善和健全當(dāng)下我國(guó)各高校中國(guó)文學(xué)的課程教學(xué),必須加入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內(nèi)容,開(kāi)設(shè)專(zhuān)門(mén)的課程進(jìn)行系統(tǒng)化教學(xué),才能達(dá)到更好的效果。
綜上所述,當(dāng)下在各高校開(kāi)展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課程教學(xué)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有利于滿(mǎn)足推進(jìn)黨的民族政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需求,也能滿(mǎn)足傳播民族文學(xué)文化、增進(jìn)民族文學(xué)研究的學(xué)科需求,還能滿(mǎn)足完善和健全中國(guó)文學(xué)現(xiàn)行課程的教學(xué)需求。當(dāng)然,高校如何進(jìn)行系統(tǒng)、全面且深入的中國(guó)多民族文學(xué)的課程教學(xué),并達(dá)到理想的教學(xué)效果,還需要不斷實(shí)踐、不斷探討,需要在點(diǎn)點(diǎn)滴滴的教學(xué)活動(dòng)中砥礪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