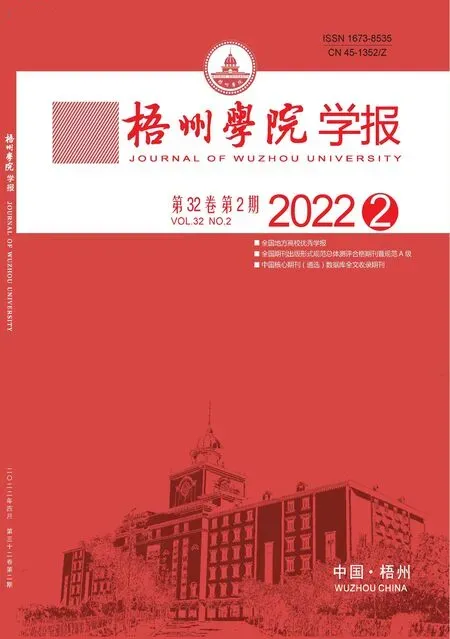論愛倫·坡的效果聚合
岳俊輝
(合肥學院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愛倫·坡是美國文學史上最知名的作家之一,也是美國黑色浪漫主義的代表。他在小說、詩歌和評論方面均有建樹。尤其是其“效果統一論”作為核心原則貫穿于其小說創作中,也吸引了學界的持續關注。愛倫·坡在評論霍桑的小說集《故事重述》時明確提出“效果統一”理論,并強調“在幾乎所有寫作中,效果或印象的統一是最具重要意義的一點”[1]298。作家“先精心構思一種獨特或單一的效果,將其凝練出來,然后虛構此類事件,并將其組合連接,以期可最有助于建構這種預期效果”[1]298。也就是“每一事件、每一細節的描寫,甚至一字一句都要收到統一的效果,收到預想的效果”[2],“文本中的每一個事件均要有助于統一效果的營造”[3],旨在“產生攪動讀者心靈的效應”[4]。
預期效果是小說的初始效果,其最終形成依賴讀者的接受,“統一”與否難有定論。預期效果是文本意圖達致的目標,而文本最終形成的則應該是游離于作家預期的效果集合。后者始終保持對前者的“回歸”趨勢,但永遠無法回到原初。盡管如此,在愛倫·坡看來,作者也應對文本、讀者等相關方面進行權力操控,保證效果話語的生成。本研究認為,“統一效果”意味著一種效果話語生成過程,其文本通過具體要素的話語陳述實現效果聚合,要素的關系結構生成效果也在效果中得以確認和展示。非理性因素在愛倫·坡的效果營造中扮演重要角色,協同理性構建了效果聚合的動力結構。而在文本創作層面愛倫·坡也應用了具體手法促成效果聚合。
因此,從話語視角透析效果內在運行機理、權力關系以及要素展布或將革新愛倫·坡效果統一論的認知模式。本研究發現,愛倫·坡在突出作者中心的同時也展布了文本要素的關系,規訓了讀者角色,借用了第一人稱敘事視角生成了效果話語。非理性作為愛倫·坡小說的重要構件,與理性協同構建了效果運行的動力結構。愛倫·坡還使用3種具體手段,聚合效果。本研究將從話語視角呈現統一效果權力的展布,藉借非理性探析效果聚合的動力結構,評估3種具體手段的效果聚合作用,以期重新解析愛倫·坡的統一效果論。
一、權力展布:話語視角
話語就是權力,形成于權力,是權力的關系,更是關系的權力。愛倫·坡主張作家要按照預定效果進行創作,效果就是文本織就的基礎色調,規范著文本存在、甚至解讀的恰當模式。在愛倫·坡看來,小說文本就是權力展布的修辭空間,各種關系被提前布置,旨在生產那統一的效果。作家之于文本的權力理應受到重視。“作者在文學創作中處于絕對中心的位置,作品的一切要素都是作者用來向讀者施加影響的手段,作者支配、決定讀者的體驗,而讀者則完全被作者掌控,處于附屬位置。”[5]預設效果是作者意圖傳達之意識,當意識指向表達之對象時即產生意義。而作者的意義生產未必能夠左右讀者的意義習得,因為讀者的意識指向文本時并無特定意圖,效果則會隨閱讀推進而產生“非理性繁殖”。由于文本是效果的物質載體,增殖效果因此仍處預設效果的“拓撲”形構和話語體系中。
愛倫·坡的小說著力于文本要素的空間布置和關系構建,謀劃最優關系圖譜,具體體現在愛倫·坡對地理物像間復雜關系的展布。短篇小說《厄舍古屋之倒塌》中,烏云、山池、古宅、地窖等從天空、地面、地下三維構建場景,敘述者從外到內進入古宅和地窖。故事插敘家族的血脈承襲,從外而內勘定羅德里克的心理狀態。暴風雨將至、瑪德琳將死、羅德里克神經近毀、古宅破敗、疾病肆虐、家族滅亡等因素勾連了一個由外部到內部、由物質世界到精神世界、由無生命之物到有生命之物的關系圖譜。這些都為最后厄舍兄妹的死亡和厄舍古屋的倒塌做好符合邏輯和心理預期的鋪墊。《黑貓》中的心理自白、火災、貓形浮雕、地窖、殺妻、黑貓的叫聲和死而復生、藏尸地點等典型兇殺案發生的要素建構出死亡、兇殺的恐怖氛圍,這些功能各異的模塊協同作用于讀者,促成了效果聚合。在愛倫·坡的小說中,一系列相關因素被巧妙布置并勾連,繪制出能夠影響讀者閱讀、生成特定效果的關系圖譜。效果實際上形成一種無形的微觀權力,規劃要素關系,進行效果聚合。
愛倫·坡還展布并規訓讀者角色,通過讀者配合延展其小說效果。愛倫·坡要求讀者將表面意義投射于“視網膜的中心”,將半隱蔽的意義投射于“視網膜的外圍”,“真正發揮‘側目而視’在文學認知活動中的審美功效”[6]。于是讀者需投下“暗示性的一瞥”方能解碼隱含的意義,最大限度地接受效果。其次,愛倫·坡還堅持閱讀時間的持續性。主張小說應適合半小時至兩小時研讀的長度,即使是“一次簡單的停頓也足以摧毀那真正的統一性”[1]298。這是對作家的要求,更是對讀者審美聚合能力的規劃。閱讀行為的一貫性能夠保證效果的內化,有效進行精神性審美活動。對讀者閱讀行為的距離設置和閱讀時間的長短規定反映出愛倫·坡對作家權力的重視,以及對作品和作品效果的負責任態度。為了統一效果的最大化,讀者的配合必不可少。
愛倫·坡還借助第一人稱視角的權力布置位置,創設作者、讀者與文本一體化關系形構,助力效果聚合。第一人稱視角表征多重身份,映射多個位置。首先,“我”是事件的實施者,如在《黑貓》《泄密的心》等短篇小說中那樣;也可能是觀察者或記錄者,如《厄舍府之倒塌》《以比曼尼斯》等。其次,“我”又游離于文本,保持特定距離便于觀察文本。最后,“我”是文本創制者。故事經其講述,由其參與,讀者也由其接觸故事,接收效果。可見,第一人稱集多重身份于一身,結構上構架分散,關系上勾連聚集,邏輯上融合統一。總之,第一人稱展布位置,構建關系,在邏輯上保證了文本效果最終向統一回歸的趨勢。
因此,愛倫·坡的小說創作通過布置文本要素,規訓讀者位置,借用第一人稱敘述視角,生產話語陳述,從而促進了統一效果的話語本質構建。如果文本是把“作者的經驗特征變成一種超驗的匿名狀態”[7],對閱讀經驗的超驗就是文本效果發揮作用的典型體現。而效果的話語本質又使這種超驗得以在更高、更為超然的層次運作,在文本、作家、讀者間的體系化機制中實現效果的統一。
二、非理性:動力結構
在愛倫·坡的小說中,效果聚合的重要組件是非理性及理性的“狡計”,它們形成了話語運行的動力結構。愛倫·坡作品中理性、非理性交織,理性隱藏于非理性,運用權力于無形。有學者認為“愛倫·坡的文學批評和理論都體現了他在感性和理性、客觀和主觀之間的矛盾和平衡”[8],但在筆者看來,“矛盾”或可商榷,“平衡”未必能輕易達到,且這種簡單的二分法割裂了兩者的一體化狀態,無益于效果話語的澄清。預設效果時理性思維必不可少,且“離奇詭異的情節、波折流動的情感也大多通過縝密理性的思維加以表達”[9]。需要注意的是,正是非理性的運行昭示并強化了理性的權力。
非理性是愛倫·坡故事的主要表現手段,但理性又多混入其中。瘋癲、失常、夢境、僵死等非理性主題在《黑貓》《厄舍府之倒塌》《塔爾博士和費瑟爾教授的療法》《催眠啟示錄》《埃洛斯與沙米翁的對話》等中小說中清晰可見。總之,愛倫·坡故事的主人公多是疾病患者、甚至是精神病患者,處于“非理性的瘋癲狀態”[10]。這也是愛倫·坡一直被稱為“黑色浪漫主義”的緣由之一。而理性又時常夾雜其中。例如,《黑貓》中“我”被非理性占據,犯罪行為因怒而生,而藏尸則是理性計劃之果。犯罪行為明顯瘋狂,而敘述者以一種鎮靜得無以復加的理性進行記錄,更憑添恐怖效果。正如其所言,“若是我期望別人相信連我自己的理性都否認其真實性的故事,那我的確是瘋了”[11]1。作者之理性必讓讀者信以為真,而敘述者之理性(已為非理性)判定其為假(非理性)。可見,并不存在理性、非理性的簡單二分,相反,兩者深度融合,協助構建了讀者、作者、作品彼此互指的關系結構,促進了小說效果的最大化。
《泄密的心》的非理性主要體現于“對人的變態心理的初步探索”[12]。觀其行為,敘述者喪心病狂,必瘋無疑,但他自己否認,“我現在怎么會瘋呢?聽好,并注意我能多么神志健全、多么沉著鎮靜地給你講這個完整的故事”[11]160。《厄舍府之倒塌》中“他(羅德里克)的沉著鎮靜只有當他不自然的興奮到達頂點之時才能見到”[11]15。“鎮靜”的理性只有在“到達頂點”的“興奮”才能獲取,兩者的彼此依賴可見一斑。因此,在愛倫·坡看來,理性、非理性界限模糊,且兩者隨時可能轉化,在特定語境下某種特性的理智能夠看出所述之事乃“普普通通且自然而然的原因和結果”[13]。換句話說,文中所述反常之事將來可能在更高理智眼中就是符合邏輯的理性事件,理性與非理性涇渭不明,且界限可能隨時消失。
界限的模糊既維護了理性的地位,也為非理性的影響開辟疆域。正是非理性偶然、短暫的顯現言說了理性的存在,一時的“變態”反而又強化了“正態”理性的地位。理性成為人類的“特權”,但是非理性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完全被剔除。理性的純一和絕對時刻摻雜著非理性的雜多和無序。理性的邊緣就是非理性的緣起,或者,理性并沒有邊緣,因為理性存在的正當性就是以非理性的非法性為前提的,正如只有犯法才現法律的界限。非理性的非法正是理性賦予的本能,因為只有犯事之時,才是理性顯現之際。非理性作為理性他者,受其壓抑、格柵、消解,暴露了理性的伎倆。愛倫·坡小說中非理性只是面具,理性才是始作俑者,通過非理性發揮作用,顯示權力。
愛倫·坡小說的非理性與理性交織,前者為明面,后者為背面,可以說,理性為非理性“背書”。愛倫·坡的小說在效果營造過程中緊握這兩根主線,駕馭效果聚合的主要方向,搭建了其理性—非理性的動力結構。啟蒙“理性”和浪漫“非理性”的結合使愛倫·坡小說成為“非理性因素的理性理解”[14]。浪漫主義作家重視非理性因素,但鮮見如愛倫·坡這般以非理性為綱要來譜寫理性主旋律的作家。
三、效果呈現:聚合三法
愛倫·坡的效果美學借理性操控非理性,實現話語系統的多維建構及其權力的層層滲透。而在小說創作中,愛倫·坡必須要采取具體措施方可落實其美學主張及其操控意圖。以前研究已經發現,愛倫·坡“將哥特因素與偵探手法、感官娛樂和心靈內省以及小說技巧與其他藝術手法相結合”[15],運用視覺、聽覺、繪畫、音樂等多重藝術手段,最大限度營造效果。更為重要的是,愛倫·坡通過動(人)物變形、空間封固、形態幻化等具體手段,促進相關因素發生效果聚合,呈現效果的話語體系。
形變一般涉及3個方面。首先,動物會發生神秘的形態變化,扭曲讀者印象而達致效果形變。《黑貓》中,黑貓普路托被吊死后又出現了另一只除了胸前的白斑、外形基本一樣的黑貓。相似的外表、白斑及火后墻上的貓形浮雕使普魯托的復活特顯神秘。兩只黑貓的形態變化讓讀者對隨后發生的殺人事件愈發感到神秘而恐怖,喚起讀者興趣,加劇了死亡這一恐怖效果。《門澤哲斯坦》中的黑馬及掛毯上的馬形圖案,伴隨火災出現,在毀滅中生成兇兆,預示著其致命的破壞力,也同樣有效聚合了統一效果。
其次,人體器官經過細描“放大”獲得形變。麗姬婭那雙眼睛出奇地又大又亮,成為具有窺視功能的工具,強化了其作為內心之眼透視人性的超能力。《貝蕾妮絲》《眼睛》以及《斯芬克司》中同樣強調眼睛的變形。《被用光的人》中的上校的肢體可以自由裝卸和拼接。《捧為名流》中“我”利用非凡的鼻子躋身上流社會。不同于卡夫卡《變形記》中人的整體形變,愛倫·坡關注具體部位形變,也使讀者感受到一種深切而具體的效果壓力。與繪畫藝術的現代主義類似,這種文學現代主義傾向有力推進了作品的效果營造。
最后,人物與動物互換形象。《跳蛙》壓根就未為男主人公命名,只言其兩腿長得畸形,走起路來一半像跳,一半像扭,但臂力無窮,跟松鼠猴崽不相上下。文中的“松鼠”“猴崽”“青蛙”及“猩猩”等稱呼更使人為事件變成動物事件,豐富了文本內涵,拓展了效果場域。《以比曼尼斯》的副標題就是“四獸合一”(“Four Beasts in One”)。這種轉換手法將人物與動物關聯,透視出人類內心的動物性,呈現出一種超現實主義圖景。
效果封固多依賴特定空間或氛圍的描寫。愛倫·坡一般會選擇封閉空間,壓迫讀者心理,封固預定效果。《厄舍府之倒塌》中古屋、《黑貓》和《一桶蒙蒂利亞白葡萄酒》中的地窖、《陷坑與鐘擺》中的地牢等都是封閉空間。它們排斥非效果成分,使其免受雜質干擾,影響預定效果。效果幻化主要是通過升華并賦能具象實體,使其超然于現實,成為一種形而上的存在,促成效果無障礙遷移,最大化預置效果。黑貓普路托被殺后,住所大火,但廢墟中白色的墻面上留有一幅貓形浮雕。黑貓的叫聲泄露藏尸地,將主人公送上絞刑架。在火災后被收留的馬與伯爵家中掛毯中的馬外形別無二致。弗雷德里克葬身火海后,在斷壁殘垣處“緩緩地,但清晰地形成一幅靜止的巨型馬形圖案”[16]。可見,愛倫·坡實際上在抽象化具體形態,使其作用于人的精神,由外而內實現效果的心理化塑形。
愛倫·坡小說從施動主體、空間場域以及形態升華三方面構建了效果話語,并從各自方面促進效果的增殖和聚合。施動主體的變形造成其身份分形,其行為能力將故事所能夠喚醒的認知理解進行形變和分化,多維度地拓展了事件的效能和文本的效果,并通過情節推動效果聚合。空間封固聚焦特定禁閉空間,構建主體行為的特定場所,也精確勘定了讀者信息接收的有效場域。此法能掃除與統一效果“違和”的因素,放大特定場域內的效果生成。形態幻化的實質是將效果轉換成微觀權力,如毛細血管遍布人體,不斷地滲透到讀者的靈魂,延伸效果的心理操控能力。言已盡,而意無窮,文本已盡,而效果無窮。可以說形態幻化是效果話語運作的最高層次,也是控制讀者心理的有效手段,可謂是愛倫·坡小說的心理恐怖根源之一。
總之,愛倫·坡在一定空間內進行物體形變與升華,提純并固化特定效果,促進效果聚合。它們在不同層次上集聚故事要素,在文本空間內發揮聚合作用。這是一種階段性成果,因為是文本內諸多因素重新組合后的結構。同時又不是最終結果,因為形變本身就影射了一種更高層次的形變,或者,一種超驗的聚合效果。
四、結語
愛倫·坡在小說創作中堅持效果賦予文本權力,展布并關聯相關因素,促進效果聚合。非理性被理性操控,并與之聯合構成效果運行的動力結構。物體形變、空間封固、形態幻化等手段則在操作層面推進了效果聚合。可以說,效果統一本質上是一效果聚合過程。以往學界雖普遍認為“效果統一”論“在于營造故事氛圍和情緒感染力,以達到某種預期效果”[17],“強調作品對讀者所能喚起的情緒和產生的效果”[18],但是缺乏對其效果統一所蘊含的效果聚合及其話語的分析,鮮有對具體手法的總結。本研究闡釋了愛倫·坡小說中的效果聚合意蘊,有助于深入理解其效果統一論的邏輯內涵、運作機理以及常用手法,從而可以清晰地認知愛倫·坡的相關創作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