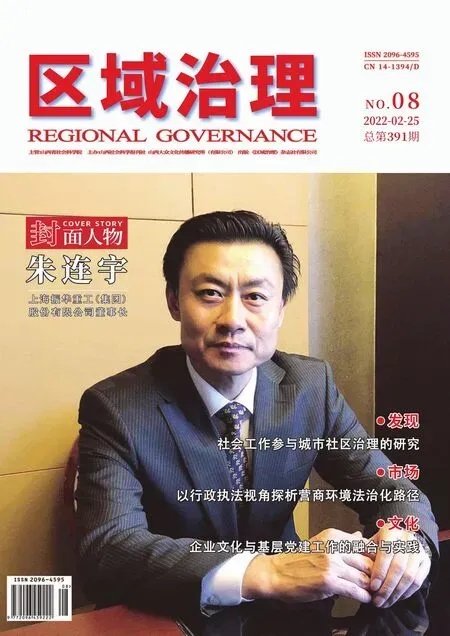刑期折抵規則適用的省市間裁判差異及進路研究
上海市閔行區人民法院 曹鈺
先行羈押折抵刑期已經是國際慣例,在立法上,我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國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其他法律法規中也明確了先行羈押折抵刑期的規則。但刑期折抵規則在立法上的明確并不意味著在實踐適用上的無差異化,實踐中各省市刑期折抵規則適用的差異普遍存在,筆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相關案例,發現刑期折抵規則的適法難以統一,為更加直觀地體現省市間適用刑期折抵規則的差異性,現筆者將引入數則案例。
一、案例對比
筆者通過中國裁判文書網搜索已經生效的刑事裁判文書,發現刑期折抵規則的差異化主要分為兩類情形,一種是將法定先行羈押手段的作出日期作為刑期折抵計算依據,如刑事拘留、逮捕等,而抓獲、傳喚、拘傳等期限均不算入刑期折抵范疇中;另一種則是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實際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間納入刑期折抵范疇,其中包含了抓獲、傳喚、拘傳、寄押、押解在途等期間。
(一)刑事拘留、逮捕作出日期作為刑期折抵起算依據
(1)被告人陳某成因多次盜竊他人財物,于2017年11月8日被公安機關抓獲歸案,同年11月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15日被逮捕。一審判決后,被告人陳某成提出上訴:認為抓獲當日被傳喚,應當折抵刑期。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認為:陳某成因本案于2017年11月8日16時接受傳喚,次日14時傳喚結束,傳喚的措施符合法律規定,且傳喚不屬于先行羈押,不應折抵刑期,故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被告人龔某俊因猥褻不滿十四周歲兒童,于2017年10月10日被口頭傳喚,同月1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20日被逮捕。一審判決被告人龔某俊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刑期自2017年10月10日至2021年4月9日止。同級人民檢察院針對龔某俊的刑期起算點提出抗訴:被告人龔某俊于2017年10月10日經公安機關口頭傳喚到案,同月11日被刑事拘留,刑期應當自2017年10月11日起算,一審法院判決將2017年10月10日作為龔某俊的刑期起算日,屬法律適用錯誤,導致刑期計算不當。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認為:關于龔某俊的刑期起算日問題,一審判決將公安機關口頭傳喚龔某俊的日期作為刑期起算日有誤,二審予以糾正,但刑事判決對被告人刑期計算有誤不屬于檢察機關的抗訴范圍,對抗訴機關的抗訴意見,本院不予支持。最后判決龔某俊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刑期自2017年10月11日至2020年8月10日止。[1]
除上述案例外,還有江蘇省淮安市中級人民法院、江西省南昌市中級人民法院、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四川省自貢市中級人民法院等多個二審法院因一審判決以傳喚或到案時間作為刑期折抵起算時間而作出二審裁定,將刑期折抵起算時間修改為刑事拘留或逮捕時間,未將傳喚或到案期間進行刑期折抵。
(二)以被告人被實際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間納入刑期折抵范疇
(1)以到案日期作為刑期折抵起算依據。被告人朱某生因詐騙他人財物,于2018年9月30日被羈押,同年10月31日被逮捕。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朱某生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二萬元。[2]后被告人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認為:朱某生于2018年9月30日按照公安人員要求到達指定地點,已在公安人員實際控制之下,當日應認定為被羈押時間。一審法院認定朱某生羈押日期有誤,本院依法予以糾正。故被告人刑期自2018年9月30日起至2019年12月29日止。[3](2)以抓獲日期作為刑期折抵起算依據。被告人魏某偉因故意毀壞公私財物于2016年8月23日被抓獲,同年9月2日被行政拘留,9月17日被刑事拘留,9月28日被逮捕。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魏某偉有期徒刑十個月。后被告人魏某偉上訴并提出:其于2016年8月23日被抓獲,由于手部受傷,被送至醫院治療,期間一直有派出所民警看守,同年9月2日,其又被行政拘留,到9月17日才被刑事拘留,這段時間應折抵刑期。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認定:對于上訴人魏某偉提出異議的這段時間應折抵刑期,原審判決未予折抵刑期不當,故魏某偉的刑期應自2016年8月23日起至2017年6月22日止。[4](3)將寄押期間計入刑期折抵范疇。被告人張某南因合同詐騙,于2014年2月26日被臨時寄押于濟南市看守所,同年3月14日被刑事拘留, 3月25日被取保候審;因涉嫌犯合同詐騙罪于2015年1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2月17日被取保候審,2016年4月15日再次取保候審。經莒縣人民法院決定于2017年8月24日被逮捕。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張某南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先行羈押41日折抵刑期41日,刑期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2024年7月6日止。后被告人張某南上訴并提出:其在濟南被羈押[5]沒有計入刑期。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認為:哈爾濱市公安局鐵西分局接到被害人報案后即電話傳喚上訴人張某南,并于2014年2月26日將張某南臨時寄押于濟南市看守所,后于2014年3月14日對張某南刑事拘留,可見應當將張某南臨時寄押于濟南市看守所的日期計入刑期。本院查清事實后對上訴人的刑期計算予以糾正,裁定上訴人張某南有期徒刑七年,先行羈押日期折抵刑期59日,即自2017年8月24日起至2024年6月22日止。[6](4)將傳喚期間計入刑期折抵范疇。被告人高某因故意傷害他人身體并致一人輕傷,于2015年2月4日至5日被傳喚,同年5月22日被刑事拘留,同年6月5日被逮捕。一審判決被告人高某有期徒刑一年二個月,刑期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2016年7月21日止。被告人上訴后,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裁定書,認為:原判對高某因本案被傳喚羈押的期間未折抵刑期,本院予以糾正。被告人高某的刑期自2015年5月22日起至2016年7月19日止。[7](5)以與后續羈押方式有持續性的傳喚日期作為刑期折抵起算依據。被告人楊某秘密竊取他人財物,于2015年5月9日被抓獲,到案后偵查機關以其吸毒為由進行強制戒毒兩年,期滿后其于2017年6月7日經偵查機關電話傳喚主動到案,同年6月9日被刑事拘留,6月29日被逮捕。一審法院判決被告人楊某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三千元。后被告人上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決書,認定:上訴人楊某于2015年5月10日因盜竊被傳喚到案,次日即被強戒,強戒期滿后回原籍,其在沒有任何強制措施的情況下,于2017年6月7日經電話傳喚主動到案,判處上訴人楊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個月,并處罰金一千元。刑期自2017年6月7日起至2017年12月6日止。[8]
上述5個案例的起算日期并不相同,折抵刑期的事由亦包括到案、抓獲、寄押、傳喚等多種方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3、4件案例實際刑期的起算日期仍是刑事拘留或逮捕日期,但將傳喚或寄押期間作為先行羈押日期予以折抵,其本質仍是將刑期折抵的范疇予以擴大。但在第5個案例中,實際刑期的起算日期是第二次傳喚之日,第二次傳喚與后續的刑事拘留及逮捕具有延續性,而第一次傳喚雖因本案作出,但因不具有延續性而未予以折抵刑期。綜合以上全部案例可以看出,刑期折抵規則在實踐中的適用具有較為明顯的差異化,且適用的規則間沖突明顯,導致相同法律規范在不同省市法院的裁判中體現出明顯的適法不一的現象。而這種適法不一的現象將如何統一,筆者在本文中將進一步探究。
二、兩種不同刑期折抵規則的博弈
上述兩種實踐做法的差異,實質就是對刑期折抵規則外延的區別化理解。將上述兩種刑期折抵規則進行對比,筆者認為可以將司法實踐中刑期折抵規則的適用區分為“法定說”與“實質說”。
“法定說”是指依照法律規定對先行羈押范疇進行界定,并嚴格依照先行羈押的內涵適用刑事折抵規則,即只有刑事拘留、逮捕及法律規定的可折抵刑期的先行羈押期限可以作為刑期折抵依據,此時的刑期折抵范疇不包含抓獲、寄押、傳喚等被告人已經實質到案的方式。以傳喚為例,傳喚本身是辦案單位所采取的一種通知的方式,被傳喚者并沒有被強制到案接受調查的義務,傳喚行為本身并不具有強力約束性。同理,到案、寄押等做法更不能納入先行羈押的范疇,這種非先行羈押行為的期限被排除于刑期折抵規則之外,亦應是法律推衍的必然結論。
但“法定說”的適用在司法實踐中顯現出明顯的缺陷。在司法實踐中,傳喚、拘傳等方式實質是為刑事拘留、逮捕等先行羈押的報批程序留足時間,為刑事案件的程序合法性打下基礎。實踐中如果拘傳、傳喚或者到案與后續的拘留、逮捕等羈押手段具有連續性,實質已經連續性地限制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實質說”是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質上被公安機關控制并被限制人身自由后,即視為刑期折抵計算期限的開始。此時對于喪失人身自由的判斷一般應依據先行羈押手段的性質及連續性進行判斷。通過判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被實質限制人身自由,可以更符合罪責刑相適應原則。但“實質說”的弊端在于在司法實踐中,實質限制人身自由的判斷標準在個案中難以統一。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后因不符合刑事拘留或逮捕條件而被采用取保候審措施,但法院判決主刑為實刑的,或者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同一強制措施間存在中斷情況,此時適用刑期折抵規則無法存在適法上的統一。如果將刑罰折抵規則的外延過于擴大化,是否會有矯枉過正之嫌也值得探討。
三、刑期折抵規則的適法統一進路
單純研判法律規定實質上并不會產生刑期折抵規則外延不明的情形,但實踐中不同地域判決時適法不一的現象卻切實存在且分歧較大。既然刑期折抵制度以“一事不二罰”為立法導向,我國刑事法律體系以保障人權和懲罰犯罪并重為理念,那么在適用刑罰折抵規則時就應當從規則設置的立法角度出發,綜合考量刑期折抵規則的適法統一進路。
筆者認為,雖然將刑期折抵規則根據實際適用的差異性區分為“法定說”和“實質說”,產生上述適法不一的問題癥結在于,立法與司法實踐對先行羈押的內涵認定不一致。先行羈押實質上是判決前羈押,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經審判不得定罪”,此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法律中即非戴罪之身。根據邏輯推演的結果,先行羈押實質是違背刑事法律原則的,這也是為何近年來羈押必要性審查愈發嚴格的原因所在。因此在先行羈押已經以犧牲未被定罪之人的人身自由為基礎換取司法程序的順利進行的前提下,應將先行羈押的范圍擴大至實質被限制人身自由之時。因此,就刑期折抵規則的理解和實踐,筆者認為本質上是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博弈。我們應該在形式基礎上追求實質,也不能脫離形式考慮實質。因此筆者認為,刑期折抵適用規則應當遵循以“法定說”為原則,以“實質說”為例外的“法益保障說”,也就是以刑法法益的保障為基礎,平衡法律的規定與實踐操作間的差異,實現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并重。
“法益保障說”的運用可以區分司法實踐進行討論。首先,在連續性羈押的案件中,應當以刑事拘留、逮捕作為刑期計算的起算日期,這是罪刑法定的必然內涵。但對于實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間,應當采取“實質說”予以補強,審慎、嚴格地審查公安機關對被告人采取限制人身自由措施的連續性和強制性,對于實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間通過適用刑期折抵規則予以抵扣,而非單純將抓獲日、到案日作為刑期羈押的起算日期。
其次,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取保候審的案件中,如判決的刑期為實刑的,應以“法定說”為基礎,以判決執行之日起算刑期。同時應當回溯確認在偵查起訴過程中是否存在連續性限制人身自由的行為,此時法官應當采取實質審查,確有超過必要訊問時間的羈押,應當視為被實質限制人身自由,不足一天的折抵刑期一天。如未超過必要訊問時間,如為配合案件調查而采用傳喚、拘傳等方式對罪犯進行訊問且訊問時間較短的,視為未被實質限制人身自由,此時不應將訊問時間計入刑期折抵期限。該種實質審查判斷應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一方面可以從程序審查的角度出發遏制公安機關超期羈押的現象,另一方面也體現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綜上,筆者認為立足我國國情和長期刑事司法實踐,從社會穩定性角度出發,采用“法益保障說”能夠更好地體現刑法規則的穩定性和明確性,同時也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實現懲罰與教育的刑罰目的。采用“法益保障說”側面也推動了公安機關對于羈押手段選擇的審慎性,促使公安機關依法、適時地變更羈押手段,有效解決長期羈押、普遍關押等問題,為有效緩和社會矛盾貢獻力量。
注釋
①參見湖北省宜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鄂05刑終227號刑事判決書。本案因二審中認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故予以改判,因篇幅限制,不再詳細載明。
②因未能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搜索到該案號的公開文書,且二審文書未載明一審判決書的刑期起止日期,故此處未能寫明該一審案件的刑期起止日期。
③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9)京01刑終495號刑事裁定書。
④參見湖南省長沙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湘01刑終330號刑事裁定書。
⑤此處裁判文書中使用的詞匯是“羈押”而非“寄押”,特此說明。
⑥參見山東省日照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魯11刑終12號刑事判決書。
⑦參見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1刑終189號刑事裁定書。
⑧參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新01刑終252號刑事判決書。本案亦因二審中認定被告人具有自首情節而予以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