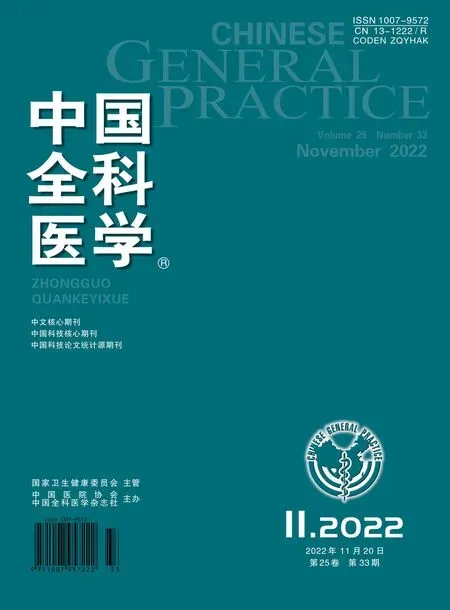正常尿白蛋白水平在多種疾病預測中的研究進展
孫珍珍,劉歡歡,陳開寧,樓青青
尿白蛋白水平已被確定為腎功能異常最敏感的標志物[1],在目前的臨床實踐中,有許多簡單的試紙檢測方法可以用來測量尿液中的蛋白質水平。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了尿白蛋白水平與其他疾病的關系,且參考范圍內的尿白蛋白作為疾病發生的預測因子也被許多研究發現。故本研究將圍繞正常尿白蛋白水平與不同疾病之間的關系,為確定正常尿白蛋白的疾病預測價值做一綜述。
1 尿白蛋白概述
白蛋白是一種主要由肝臟合成的帶負電荷的小分子蛋白質,占體內總蛋白質含量的10%[2]。腎小球是腎臟中一種復雜的血管結構,其限制了白蛋白從血液到尿液的運輸[3],受一些生理或病理因素的影響,腎小球的電荷和孔徑屏障作用遭到破壞,從而出現蛋白尿。從24 h尿樣中測量白蛋白水平是診斷尿白蛋白的“金標準”[4]。尿試紙條是檢測大量蛋白尿的最簡單、最快捷的方法,但對于定量尿白蛋白濃度來說,其是一種相當不靈敏的檢測方法[5]。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檢測方法較為方便,且與“金標準”的診斷價值相當[6]。有研究發現,相比于24 h尿白蛋白定量,UACR對糖尿病腎病(diabetic kidney disease,DKD)的預測價值更高[7],被推薦為糖尿病患者的篩查工具。按照UACR或24 h尿白蛋白排泄率(AER),將尿白蛋白水平分為以下3類:A1或正常尿白蛋白(<30 mg/g或<30 mg/24 h),A2或微量尿白蛋白(30~300 mg/g或30~300 mg/24 h),A3或大量尿白蛋白(>300 mg/g或 >300 mg/24 h)[8]。
2 正常尿白蛋白與糖尿病微血管并發癥
2.1 DKD DKD是糖尿病主要的微血管并發癥之一,其發病率呈明顯上升趨勢,在糖尿病患者中,DKD的患病率達20%~40%[9],已成為我國終末期腎病的第2位發病原因,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存質量。DKD患者最早的臨床表現多為持續性的微量尿白蛋白。然而,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部分DKD患者表現為正常尿白蛋白[10-12]。正常尿白蛋白型DKD的機制尚不明確,但這一發現引起了研究者對正常尿白蛋白與DKD關系的關注。2006年,英國前瞻性糖尿病研究(UKPDS)[13]就已發現:正常尿白蛋白水平升高與2型糖尿病患者DKD的發生獨立相關。隨后,日本的一項為期50個月、針對1 760例2型糖尿病患者的研究也證實:尿白蛋白即使在參考范圍內也會增加患者發生腎臟疾病的風險,當患者的基線UACR在7.5~30 mg/g范圍內時,其5年內發生大量尿白蛋白的風險就已增加至0.53%[14]。這兩項研究均為前瞻性研究,所納入的樣本量多、覆蓋人群較廣泛且隨訪時間長,所得出的結論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因此,參考范圍內的尿白蛋白水平對DKD的發生有一定的預測作用,但預測其發生的具體臨界值仍需進一步探討。HAYASHI[15]使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發現,預測DKD發生的UACR截斷值為6.1 mg/g,此時受試者工作特征曲線下面積(AUC)為0.75,檢測準確率為77.56%。此研究雖初步探討出UACR預測DKD的臨界值,但并未對此界值進行獨立外部驗證,故此界值的準確性和普適性仍有待商榷,未來還需多中心、大樣本的試驗來驗證。
2.2 糖尿病視網膜病變(diabetic retinopathy,DR) DR與DKD一樣,均為微血管病變,兩者之間存在相關性[16]。DR發生的細胞學機制為內皮細胞受損[17],而尿白蛋白水平為內皮細胞受損的早期標志物,現已有臨床研究證實尿白蛋白水平與DR的發生呈正相關[18-19],且DR與尿白蛋白的關聯性比與腎小球濾過率的關聯性要高[20-21]。已有部分研究者驗證了正常尿白蛋白水平與DR的關系。BENITEZ-AGUIRRE等[22]把參考范圍內的UACR值按三分位數分為3組,在校正混雜變量后發現第3組(12 mg/g<UACR<30 mg/g)與DR的發生獨立相關(HR=2.1,P=0.001)。LEE等[19]的一項橫斷面調查也證實了參考范圍內UACR是DR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預測DR發生的UACR截斷值為15.6 mg/g。中國學者CHEN等[23]對4 739例2型糖尿病患者進行橫斷面調查發現,尿白蛋白預測DR發生的截斷值為10.7 mg/24 h,其預測DR發生的尿白蛋白截斷值雖與LEE等[19]發現的15.6 mg/g這一截斷值不同,但均為臨床上所規定的正常尿白蛋白。這也預示著,即使糖尿病患者表現出正常UACR,也應常規篩查其視網膜病變。然而,這兩個橫斷面研究[19,23]并不能提供參考范圍UACR與DR之間的可靠因果關系,其探討出的截斷值也未進行外部驗證。由于DR發生的影響因素過多,若不能排除血糖、血脂、血壓及患者基礎疾病狀況等混雜因素的干擾,則其得出的結論可能存在較大偏倚,因此需要縝密設計的、更大規模的、前瞻性研究來進一步明確兩者的具體關系。
3 正常尿白蛋白與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CVD)
CVD已成為導致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約占全世界死亡人數的1/3[24]。及早發現CVD高危人群并進行隨后的健康教育或干預對預防這一全球性流行病和減輕相關的社會經濟負擔具有重要意義。微量尿白蛋白目前已被認定為高血壓[25-26]、糖尿病[27-28]患者乃至一般健康人群[29]罹患CVD風險的特異性標志物。尿白蛋白與心血管事件和全因死亡率獨立相關[30-31],完全調整了影響CVD的因素和其他潛在的混雜因素后,這種關聯仍然顯著。尿白蛋白增加是全身血管內皮細胞功能障礙的反映,而不是特定的腎臟損害[32]。白蛋白和其他大分子進入血管壁,導致血管炎性反應和基質紊亂,進一步引起血管擴張、功能喪失和動脈血壓升高,這不僅影響到大血管內膜功能,還會增加腎小球濾過壓。腎小球濾過壓升高可能會進一步增加尿白蛋白排泄,如此惡性循環,最終使患者容易發生CVD[33]。
早在2005年ARNL?V等[34]研究就已證實正常尿白蛋白與CVD的關系,在中年非高血壓、非糖尿病個體樣本中,尿白蛋白排泄水平遠低于當前規定的微量尿白蛋白閾值時仍可預測CVD的發生。但這項研究僅局限于白色人種中老年人群,其結果對其他種族和更年輕的人群的普適性有待考察;其后一項包含了105 872例研究對象的Meta分析也證實了UACR即使在參考范圍內也會增加患者因CVD而死亡的風險[35],UACR>10 mg/g就已是因心血管事件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以上兩項大型研究均是針對普通人群。ECKEL等[36]研究高危人群發現,其CVD風險在UACR水平為4.42 mg/g時就已增加,UACR水平每增加3.54 mg/g,主要心血管事件的發生率增加5.9%。此外,尿白蛋白對心血管結果的影響因種族而異[37],但目前針對亞洲人群的研究較少。LI等[31]針對32 650例無CVD且表現為正常尿白蛋白的中國成年人的多中心、前瞻性研究發現,正常尿白蛋白與10年內CVD發生風險相關[31]。然而,LIU等[38]研究并未發現這一相關性,其前瞻性研究結果顯示,參考范圍內UACR與患者的心血管事件沒有關聯〔HR=1.18,95%CI(0.95,1.46)〕。這兩項研究雖均為大型前瞻性研究,但LIU等[38]研究地點僅局限于上海地區,而LI等[31]研究則來自全國的7個中心,人群代表性更廣泛。因此,可認為正常尿白蛋白水平與CVD具有相關性。
然而,對于預測CVD發生的尿白蛋白截斷值,各個研究也尚未得出統一結論。WAHAB等[25]研究對150例患者進行了13個月的隨訪發現,預測發生高血壓的UACR截斷值為19.25 mg/g,靈敏度為62%,特異度為88%。XIE等[39]對317例UACR正常的糖尿病患者進行回顧性研究發現,UACR診斷糖尿病左心室肥厚的截斷值為10 mg/g。僅這兩項研究給出了具體的參照值,其余研究均只是給出CVD危險度上升時尿白蛋白的范圍,具體取值并未確定。但這兩項研究樣本量少且隨訪時間較短,其所發現的臨界值的普適性有待驗證。雖然目前尚無統一結論,但這些證據仍提示了目前正常尿白蛋白作為CVD預測因子的價值。這也提示在臨床工作中,即使患者沒有出現微量尿白蛋白也不應推遲CVD風險的篩查,尤其是已存在CVD危險因素的患者。
4 正常尿白蛋白與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MetS)
MetS是指與肥胖相關的心血管危險因素的集合,包括腹型肥胖、糖耐量減退、高三酰甘油血癥、高密度脂蛋白膽固醇降低和/或高血壓[40]。目前一致認為正常尿白蛋白與MetS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VYSSOULIS等[41]在6 650例高血壓患者中進行前瞻性研究發現,參考范圍尿蛋白與MetS患病率顯著相關。后來,幾項亞洲研究對兩者之間關系的證據進行了補充,在中國[42-44]、韓國[45-46]和日本[47]的成年人中,正常尿白蛋白與MetS呈正相關。SCHUTTE等[48]對202例非糖尿病非洲男性進行研究發現,正常尿白蛋白與高血壓呈正相關。但這項研究樣本量較小,關于黑色人種正常尿白蛋白與MetS之間的關系有待進一步研究。總之,正常尿白蛋白與MetS顯著相關,其可作為MetS及其組分發生、發展的預測因子。兩者之間這種關系的機制還不十分明確,可能與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激活[49]、胰島素抵抗[50]、內皮功能障礙[51]等機制有關。目前僅有一項關于正常尿白蛋白預測MetS發生截斷值的研究[45],其對9 650例韓國公民進行了橫斷面研究發現,預測MetS出現3個及以上代謝成分異常的UACR截斷值為4.8 mg/g,這一截斷值也未經過驗證,普適性仍有待確認。
5 既往研究局限性
關于正常尿白蛋白與以上疾病之間的關系目前基本上已經得出結論,但結合以往研究結果可以發現,正常尿白蛋白與相關疾病的關系不僅受性別、種族的影響,也受尿白蛋白升高因素(急性腎炎等)的影響。故今后的研究可能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分類討論。此外,關于正常尿白蛋白預測相關疾病發生的截斷值各個研究未得出統一結論,且關于最佳截斷值的研究較少。即使有研究找到了截斷值,但也未對此截斷值進行過外部驗證。所以,將這一截斷值進行推廣的可能性較小。
6 總結
綜上所述,目前諸多研究探討了正常尿白蛋白與相關疾病發生、發展的關系,這些越來越多的證據挑戰了UACR<30 mg/g表示正常尿白蛋白的概念,提示在臨床工作中即使患者的尿白蛋白水平在參考范圍內,臨床醫師也應加強對相關疾病的篩查。但囿于基礎及臨床研究的局限,UACR閾值設定多少為最佳,各個研究也未得出統一結論。因此,未來可能需對這些研究的數據進行定量綜合分析,以找出尿白蛋白預測相關疾病的截斷值并重新收集數據對此截斷值進行外部驗證,為今后正常尿白蛋白閾值的重新界定提供依據。本文僅對3種常見的慢性病進行了綜述,正常尿白蛋白水平與其他疾病(如慢性腎病、全因死亡率、妊娠期先兆子癇等)的關系未列入本綜述,未來可進一步補充討論。
作者貢獻:孫珍珍負責文章的構思與設計,文獻、資料的收集,進行論文撰寫;劉歡歡、陳開寧負責論文的修訂,文章質量的控制及審校;樓青青負責文章的可行性分析,最終版本修訂,對論文負責。
本文無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