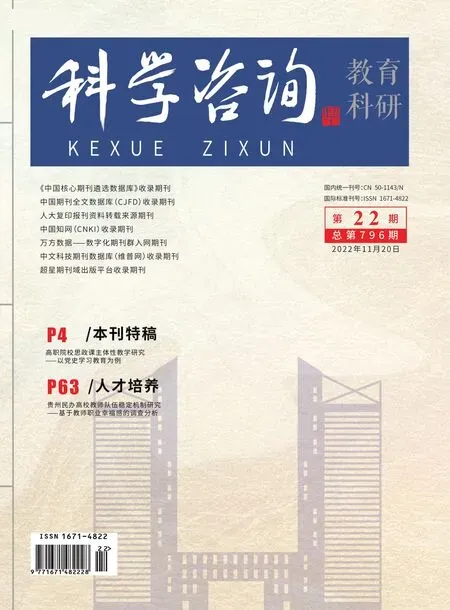流動兒童外顯群體偏愛與歧視知覺的關系
趙倩妤
(南京市江寧區湯山初級中學,江蘇南京 211131)
一、問題提出
隨著經濟迅速發展以及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發展機會增多,由于農村人口不斷涌入城市,其子女也從農村流入城市,成為“流動兒童”。國內對流動兒童本身所處群體以及感知到的歧視研究并不多。
歧視知覺是相對于客觀歧視知覺而言的主觀體驗,是人們知覺到由于自己所屬群體而受到有區別或不公平的對待[1]。在不同指向性特點的基礎上,分為個體歧視知覺和群體歧視知覺。個體歧視知覺指人們在生活工作中感受到的他人對自己的歧視,群體歧視知覺指人們感受到的在生活工作中他人對自己所在群體的歧視。
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與城市認同也有關,流動兒童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歧視,而這種歧視知覺影響他們對城市和城市居民的認同。小學高年級學生的歧視知覺顯著低于初中生,初三的流動兒童感受到更多的不公平對待[1]。將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的流動兒童進行對比,公立學校流動兒童很少受到別人的不公平對待或看法[3]。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社會文化適應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對適應城市也起負向作用,流動兒童的心理健康也受到歧視知覺的負向影響,且歧視知覺對心理健康問題具有顯著的直接影響[4]。同樣,個體和群體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主觀幸福感有顯著負向預測作用[5]。隨著時間的增加,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顯著降低、幸福感顯著增加[6]。在國內的研究中,將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與其所屬群體整合研究較少,因此這一問題值得探究。
群體指兩個或兩個以上相互依賴和作用的個體,為了某個相同目標而聯系在一起且彼此之間具有情感連接的人群。“內群體”是指人們所屬的群體,群體內成員擁有共同的群體身份并遵守一定的群體規范,“外群體”是相對內群體而言,指內群體以外的其他群體。在評價上和行為上明顯表現出對內群體偏好的傾向,稱為內群體偏愛(Ingroup Favoritism)。反之,則稱為外群體偏愛(Outgroup Favoritism)。弱勢群體成員有內群體偏愛和外群體偏愛,可能是由于弱勢群體成員將社會不平等性內化。共同內群體認同對總體群際幫助意愿存在積極的預測作用[7]。流動兒童作為一個群體,其相對剝奪感、團體歸屬感和認同整合三者之間均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8]。但國內對流動兒童這一弱勢群體的群體偏愛研究較少,這值得探討。
為進一步了解我國流動兒童在學校環境中心理融入與適應時歧視知覺和群體偏愛的現況,結合外顯測量及問卷等方法[9],探討歧視知覺與外顯群體偏愛的關系,為有流動兒童的學校對流動兒童的學習及生活上出現問題時的分析及原因探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能夠重視流動兒童在學校和社會上遇到歧視與偏見的現象。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初中流動兒童為調查對象,選取南京市某中學初一初二學生300名,初一學生150名,初二學生150名。有效數據包括283名被試(女生144名,男生139名),被試的平均年齡為14.45歲。
(二)研究工具
個體歧視知覺問卷:采用劉霞和申繼亮修訂的問卷,此問卷由流動兒童在學校等生活領域中經歷的典型歧視事件組成,共有20個條目,采用4點計分。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別1~4分。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7,信效度較高。
群體歧視知覺問卷:采用劉霞和申繼亮編制的問卷,研究流動兒童知覺到的本群體在與城市人互動過程中被歧視的嚴重程度。共有12個項目,采用5點計分,從“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別計1~5分。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77,信效度較高。在填寫該問卷前,要求被試先填寫自己所屬的群體,激活其所在群體,使得問卷填寫更有效。
語義差異量表:本研究根據通過開放式問卷對常州某大學150名學生進行調查,分別統計出形容流動兒童和城市兒童屬性詞頻數最高的10個詞語,由10個典型的消極詞匯和10個典型的積極詞匯組成,其中5個積極詞匯和5個消極詞匯形容城市兒童,另外5個積極詞匯和5個消極詞匯形容流動兒童。將其編制為語義分化量表,均為描述城市兒童群體及流動兒童群體的屬性詞,且為已配對的積極詞和消極詞,問卷最終共包含10個兩極對立的項目,采取7級等級評分,分別計-3~3分(分數越靠近-3代表該群體越符合左邊詞匯的描述;越靠近3,此群體越符合右邊詞匯的描述)。為防止一致性偏差,因此將各個項目的積極詞與消極詞左右隨機交替呈現。其中反向陳述的項目采取反向計分。
借鑒王麗麗關于大學生對農民工的外顯刻板印象的研究中所使用的方法,即采用D值的算法:分別計算對不同兒童群體評價分數的平均數(M城和M流),再計算出兩組得分的SD,最后用M城-M流,并除以SD得到D值。若D>0,表示被試存在外群體偏愛(偏愛“城市兒童”);若D<0,則表示被試存在內群體偏愛(偏愛“流動兒童”)。經檢驗,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系數為0.89,信效度較高。
(三)統計分析
經過初步數據處理,刪除問卷填寫有問題的數據,實際得到283份有效問卷。使用SPSS17.0進行數據處理和分析。本研究采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單樣本t檢驗、配對樣本t檢驗和相關分析。
三、結果
(一)流動兒童外顯群體偏愛研究結果
將被試對不同兒童群體與積極屬性詞、消極屬性詞的評價均分進行描述性統計,并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被試在城市、流動兒童群體語義分化量表中,對于形容城市、流動兒童的積極屬性詞和消極屬性詞的評價均具有極其顯著的差異,t(283)=7.34,p<0.001,t(283)=-9.79,p<0.001。被試在城市兒童群體積極詞語義分化量表的M=2.31,SD=0.77,被試在城市兒童群體消極詞語義分化量表的M=-0.36,SD=1.77。被試在流動兒童群體積極詞語義分化量表的M=-1.42,SD=1.84,被試在流動兒童群體消極詞語義分化量表的M=1.96,SD=1.11。

表1 流動兒童對城市、流動兒童群體語義分化量表評價的總體情況
(二)將相應項目反向計分后,將被試對流動兒童和城市兒童評價均分進行描述性統計,并進行單樣本t檢驗,計算D值。結果見表2。

表2 流動兒童對不同群體評價情況
由表2可知,被試在城市兒童群體語義分化量表的M=1.33,SD=1.04,對流動兒童群體語義分化量表的M=1.69,SD=0.99。將被試在兩個群體量表上的得分與量表中間分0對比,結果均達到顯著水平。
對外顯群體偏愛效應值D外顯進行單樣本t檢驗,與0作比較。發現流動兒童對城市兒童群體與流動兒童群體的評價差異顯著,D外顯<0,t(283)=-2.11,p<0.05。測量結果表明,流動兒童在外顯層面對內群體的偏愛程度顯著大于外群體,即流動兒童表現出內群體偏愛。
(三)流動兒童歧視知覺現狀
對流動兒童個體歧視知覺和群體歧視知覺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并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結果見表3。

表3 流動兒童歧視知覺的描述性統計
由表3可知,流動兒童個體歧視知覺均分為1.26,群體歧視知覺均分為1.08,都低于中值,說明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處于中等偏下水平。且兩者差異極其顯著(p<0.005),個體歧視知覺均值大于群體歧視知覺,即被試感受到的個體歧視知覺要比群體歧視知覺高。
(四)流動兒童外顯群體偏愛與歧視知覺的相關關系
將流動兒童的外顯群體偏愛和個體歧視知覺、群體歧視知覺做相關分析,結果見表4所示。

表4 流動兒童外顯群體偏愛與歧視知覺的相關分析
由表4可知,個體歧視知覺與外顯群體偏愛的相關系數為-0.38(p<0.05),顯著呈負相關。個體歧視知覺與群體歧視知覺的相關系數為0.52(p<0.01),呈顯著正相關。其他均無相關。
四、分析與討論
(一)群體偏愛存在性分析
外顯測量的結果表明,流動兒童在外顯層面對內群體的偏愛程度要著大于外群體,即流動兒童表現出內群體偏愛。這與以往的研究基本一致,群體服務偏向理論表明若個體把自己作為群體的一部分,就會形成群體服務偏向,且在被試正式填寫語義分化量表前,已通過問卷激活,要求其站在自己所屬群體一方對城市兒童群體及自己所屬群體做判斷。因此在外顯層面,流動兒童更偏愛內群體,即更偏向于流動兒童這一群體,體現為內群體偏愛。
(二)個體歧視知覺與群體歧視知覺的差異分析
本研究所得結果與國內研究的結論基本一致,發現流動兒童受到歧視的現象并不普遍。結果顯示,流動兒童個體歧視知覺均值為1.26,位于答案“有些不符合”附近,群體歧視知覺均數為1.08,低于中值2.50,流動兒童的歧視知覺都較低,但相比之下,個體歧視知覺要高于群體歧視知覺。說明流動兒童的歧視體驗在所屬群體中并不強烈,但個人本身受到的不良體驗或是感知到的歧視對比所屬群體要高些,但總體來講歧視的主觀體驗比較微弱。
(三)流動兒童外顯群體偏愛與歧視知覺的關系分析
本研究發現流動兒童外顯內群體偏愛與個體歧視知覺有顯著負相關,與群體歧視知覺沒有關系。對此結果,本研究可從以下幾點進行理解。首先,根據下行比較理論,個體在自我概念水平低時,需重新進行自我評估,外顯態度也易受到自我保護及其他外界條件的干擾,尤其是面對較敏感的問題時,個體容易隱藏自己的真實態度,因此,被試在作答時,表現出自己對所屬群體的偏愛。其次,公立學校的流動兒童逐漸脫離原有角色背景,轉換自己農村兒童的身份,已較好地融入城市,且在學校環境中心理融入程度較高,唯一無法改變的是自己真正屬于的是流動兒童這一群體,在感知到歧視的同時,也希望自己是城市兒童,這與社會認同理論的內容相符。因此,個體歧視知覺對流動兒童的外顯內群體偏愛有負向預測作用。
五、研究結論
流動兒童表現出顯著的外顯內群體偏愛,對語義分化量表選取的屬性詞基本能代表相應的群體;流動兒童的個體歧視知覺與群體歧視知覺存在差異,具體表現為個體歧視知覺高于群體歧視知覺;流動兒童的外顯群體偏愛與個體歧視知覺有顯著負相關,與群體歧視知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