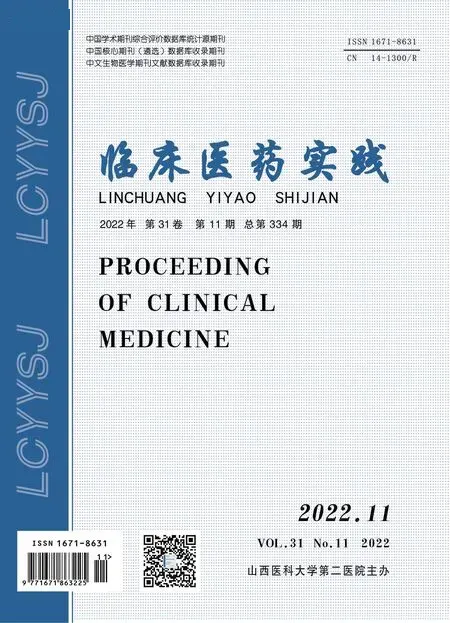醫教背景下教學反饋評價實施現狀的定性分析〔1〕
王言之,費嬌嬌
(1.南京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江蘇 南京 211166;2.江蘇省人民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隨著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取締傳統醫學模式的發展,人們對高質量醫療服務的需求日益凸顯。就醫學院校而言,輸送新一代醫護人才的社會責任也對醫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提出了一定要求。傳統的填鴨式教育存在重理論輕實踐、師生溝通度低等種種弊病,在此背景下,優化教學方法、提升教學效果成為醫學教育的重中之重。巴林特小組教學[1]、督導式教學[2]、以問題為導向的教學[3]等新的教學模式不斷被提出和實踐。教學反饋評價是指在教師與學生之間構建一套信息傳遞系統,學生對教學過程中接收的信息進行轉化、歸納及回授,教師則根據學生反饋的信息,判斷教學工作的狀態,進而修正、調整教學策略或教學方案[4]。近年來,教學反饋評價法已被用于臨床、護理、康復等各個醫學專業學生的帶教中,展現出較好效果。本文采用定性的方法分析國內醫學教育中教學反饋評價法的實施現狀及發展趨勢,為進一步優化教學效果提供一定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檢索策略
以2016年1月—2021年12月為檢索時限,以“教學反饋評價”“評價與反饋”“反饋式教育”及“teach-back”為主題檢索詞,系統檢索知網、萬方、維普等國內公開數據庫的研究論文。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教學區域為國內,論述語言為中文;教學內容為醫學相關主題;教學對象為臨床、護理、預防、康復等醫學專業在讀本科生及研究生,亦包括處于規范化培訓階段的住院醫師;有明確的實施效果、觀察指標及統計結果。
排除標準:教學主題與醫學不緊密相關,如大學物理、高等數學;教學對象非醫護專業,如來院患者及其家屬;文獻重復發表或不可獲取;文獻類型非實驗性研究,沒有明確的處理方法和統計結果,如綜述及述評等。
1.3 文獻篩選及質量評分
根據主題詞及納入排除標準,由2 名研究者分別獨立完成文獻的收集和歸類。應用Notexpress軟件進行查重,排除與醫學教育主題明顯不相關的文獻。對于納入與否存在分歧的文獻,借鑒所在科室高年資主任醫師的意見做出一致決定。初步篩選完成后,2 名研究者進行后續的信息提取和資料整理,并互相抽查準確性。確認無誤后,按以下標準對篩查的文獻進行質量評分。第一,教學模式:有明確的定義及實施細則記2 分,僅有其中一項記1 分,否則為0 分。第二,研究方法:設立對照組進行教學效果比較記1 分,未設立對照組記0 分。第三,教學對象:學員人數(含對照組)達30及以上記1 分,否則記0 分。第四,反饋時間:對反饋評價有明確時間表述記1 分,實施時間或頻率不詳記0 分。第五,實施效果觀察指標:包括考核成績、學生評價、學生滿意度等多項指標記2 分,僅含考核成績或學生評價一項指標記1 分,觀察指標表述不清記0 分。各項得分累加即為文獻對應的質量評分,總分為7 分。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梳理并歸納我國醫教背景下實施教學反饋評價法的典型項目、教學對象、反饋頻率及效果觀察指標,結合有關文獻分析其發展趨勢與存在的問題。
2 結 果
2.1 納入研究文獻的基本特征
初篩得到相關文獻868 篇,排除重復及無法獲取的文獻120篇,瀏覽題目及摘要后排除與醫學主題無緊密關聯的文獻389 篇,閱讀全文后排除綜述類文獻及其他不符合納入標準的文獻346 篇,進行質量評分后排除低質量文獻2 篇,最終納入研究文獻11 篇。其中,7 篇的教學對象為臨床專業學生或住院醫師(含中醫),4 篇教學對象為護理實習生/實習護士;采用教學反饋結合微課或視頻模擬教學模式者2 篇,其余為單一的教學反饋評價;納入文獻的質量評分均不低于5 分(見表1)。
2.2 教學反饋評價法教學模式的優勢
2.2.1 交互性
傳統填鴨式教學中,“教”的主導地位被過分強調,“學”的主體地位則被相對忽視。當教學被簡化為單方面的灌輸,教師與學生之間缺乏溝通理解,可導致學生厭學情緒的滋生和教師教學熱情的消減。而教學反饋評價法中的“反饋”即注重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信息傳遞,肯定了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能動性。以馬慧娜和劉潔[13]為代表的教學團隊開展師生雙向反饋評價教學實踐,在帶教過程中老師與學生就帶教理念和教學方式進行溝通,提升了配合度與理解度。教學反饋評價法構建了一種友善、和諧的新型師生關系,這種交互性對帶教老師和學生雙方都起到了正向激勵作用。
2.2.2 兼容性
有別于傳統的PPT講演,教學反饋評價法的信息傳遞可有多種表現方式。張德春等[7]、吳州麗等[15]將教學反饋評價法與微課及情景模擬結合,即體現出教學反饋評價法的兼容性。以骨科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為例,教研組預先為學員準備體格檢查及無菌術微課視頻,學員通過微課了解教學重點并回答相應問題。一方面,教師團隊可以及時通過學生的回答獲知其掌握水平,另一方面,學生可以重復播放微課視頻以便理解。教學反饋評價法與其他教學方法的組合具有協同效應,良好的教學設計可提高信息傳遞的效率,此外,引入新的教學方法亦能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更好地達到教學目的。
2.2.3 靈活性
為了調配任課人員,突出學習重點,各教研組往往在課程開始前明確教學進度表,對每個章節的課時分配作出固定安排。國內醫學課程普遍呈現內容多、課時少的教學困境,受課堂時間的限制,部分章節可能被劃分為自學內容不予講解,為學員日后的診療工作埋下隱患。而教學反饋評價法的反饋是動態反饋,學生提出疑點后教師可實時調整教學計劃,對教學的重難點進行二次整合,宏觀調控教學進度,使其與學生接納能力形成良好的匹配。
2.3 醫學教育中教學反饋評價法的發展趨勢
2.3.1 評價渠道多樣化
軟件技術的完善為教學反饋評價法提供了更多可能的渠道,除了傳統的紙質問卷和面對面訪談外,各院校自主研制的教學質量管理系統、微信小程序及問卷星App等均不斷被投入使用,后者相對前者而言更注重對學生信息的保護。將學生意見傳遞給教師也有多種路徑,可根據不同教學團隊的傾向性及個人習慣選擇短信、郵件[5]或專用系統。
2.3.2 評價主體多元化
一般概念上的教學評價在師生間雙向開展[13],而隨著國內醫學教育步入正軌,近年來全方位反饋評價法[11]被提出和應用。作為醫學教育的重要環節,規范化培訓具備一定的特殊性,實習護生或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訓過程需要參與的團隊相互協作,部門主管、上級醫師、同事及患者均是規范化培訓過程的見證者和參與者。以多元主體實施的評價取締單一的自我評價或師生互評,可綜合反映教學效果并增強師生的社會認同感。
2.3.3 評價指標系統化
為方便學生評價教學滿意度,教研組往往自制教學反饋評價量表,以問卷調查的形式開展教學評價。鑒于量表的科學性與評價的有效性存在明顯關聯,“設計”“內容”“方法”“特色”“效果”等多個指標被引入,以豐富評價維度。此外,以朱磊等[9]為代表的團隊將教員同行的評價得分與學生評分一致性采用組內相關系數(ICC)的方法檢驗,從統計學角度完善了實驗設計。
2.4 教學反饋評價法實際應用中存在的問題
2.4.1 教學雙方不重視,無效流程走形式
作為一種形成性評價方法,教學反饋評價法一般不與學生分數或教師績效直接掛鉤。因此,在實際授課過程中學生或忽視其重要性,與教師零交流,甚至參與問卷調查時存在一定的糊弄心理,不能反映真實的教學情況。此外,當教學團隊不能根據學生的反饋意見做出相應調整時,同樣也會打擊學生的學習熱情,降低教學模式的實施效果。鑒于教學反饋評價法的有效開展需要師生雙方的協作配合,院校在實施教學反饋評價模式前,應對其意義進行講解,營造良好的教學氛圍。
2.4.2 通道開放不及時,意見傳遞有遲滯
以南京醫科大學臨床醫學專業為例,其本科教育可分為三年的在校教育階段和兩年的在院教育階段,前三年包括高等數學、大學物理等通識課程及生理學、病理學等醫學基礎課程;后兩年則以見習和實習為主。通識課程是有固定的教師進行一對一的小班教學,而臨床課程的教學任務往往分配給各個見習醫院,由在職醫師輪流按課時開展授課活動。部分院校在教學進度全部完成后開展反饋評價,但由于學生存在回憶偏差,難以將各個課時與任課教師一一對號,導致評估反饋的準確性降低。相對而言,在授課過程中及每節課后開展的及時反饋評價[10]可規避此類問題,但對師生雙方的響應度都提出了一定要求。
2.4.3 評價系統不智能,信息篩選耗時間
一般而言,以問卷調查形式開展的教學反饋評價法最終由教學秘書進行匯總統計,雖然統計軟件及教學質量管理系統能實現對學生打分的數據處理,但對于文字形式傳遞的反饋意見,仍需教學督導逐條歸納核實。此外,部分學生與授課教師或存在個人矛盾,導致在評價階段惡意打分。為提升工作效率、排除個別干擾因素,抓取詞云、合并重復意見、剔除惡意評論的功能模塊有待添加。
3 討 論
教學反饋評價法既包括教學過程中的信息交流與動態調整,也包括師生雙方及其他主體的評分。“反饋”強調形成良好互動、優化教學的效果;“評價”則突出評估實施效果、建立多方認同。傳統的填鴨式教育中,學員或因接受度低、落后于教學進度而陷入越學越吃力的負反饋困境,而在教學反饋評價模式中,教師可根據學生表達的信息調整教學計劃,形成正向激勵機制。
教學模式迭變的背后是教學理念的更新,以教學反饋評價、巴特林小組模式、督導式教學等研究熱點為切入口,反觀全局,可見國內醫學教育從搭建框架的初級階段向提質增效的高級階段發展。此外,醫學教育的對象也不限于醫學專業學生,來院患者、患者家屬、社區居民等不同人群的健康宣教均可被納入醫學教育的宏觀范疇。郝娜等[16]采用教學反饋評價對炎癥性腸病患者進行干預,有效提高了患者的自我護理能力并可緩解其負面情緒。在確保實時性和有效性的前提下,教學反饋評價法在醫學教育中有較好的應用前景,隨著教學質量管理系統等軟件技術的更新,教學反饋評價的開展有望走向常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