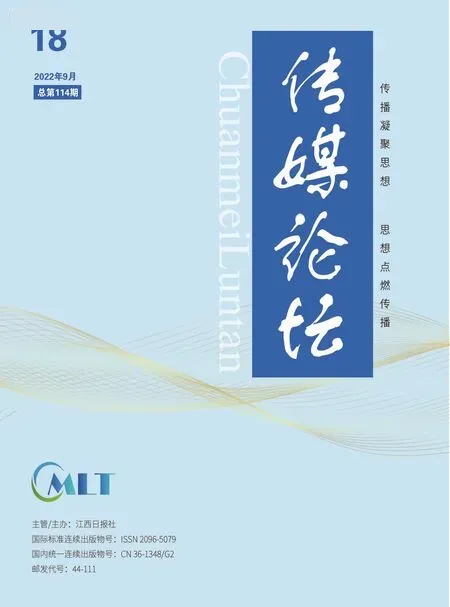數字時代城市獨居老人的生活風險與應對路徑探究
湯皓然 熊婕妤
在現代社會,雖然智能手機、移動通信等一類科學技術可謂是人類嘗試邁向精神世界的媒介之一,甚至可以說其產生的過程也是逐漸推動人類走進一個“數字時代”[1]。但數字時代一方面會給人類的日常生活帶來諸多的便利,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存在的弊端。結合現代社會的年齡結構分布,不難發現,老年群體,特別是城市獨居老年人表現出來的抗風險脆弱性特點,使其與當今社會形成了一道“數字鴻溝”[2],以致于其很可能受到數字時代帶來的隱性風險。
通過分析已有的文獻可以看出,目前針對城市獨居老人的研究主要分為兩類:一類主要涉及該群體家庭結構關系的平衡問題[3],另一類主要關注該群體養老方式的問題[4]。即便是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城市獨居老人的研究還是更偏向于精神情感層面的關懷反思[5],我們姑且將其歸為治療取向的微觀范疇。而城市獨居老人在數字時代下的生活適應和日常行動也是不容忽視的方面,同樣也需要我們從結構層面對上述情況做出社會反思效應。
基于此,本文將從風險社會理論的主要觀點出發,審視數字化服務的廣泛嵌入對于獨居老人來說是有益于提升其生活的質量還是區隔了他們與社會的交往和互動。其次,進一步思考數字時代的到來是否會對城市獨居老人的日常生活帶來一定的隱性風險。最后,試圖幫助城市獨居老人探尋一條緩解群體風險分配不公,使其與數字時代的產物形成合理性融合的應對路徑,以期構建該類群體與數字時代和諧共處的生活圖景。
一、出行與生計規訓:生活風險存在的一種可能
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談及社會風險的相關議題時,常常會牽絆出社會轉型等一類的現代性語匯[6]。同時,這類詞匯的背后也自然會催生各界人士對于“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對比性思考。聚焦主體的社會互動來看,傳統社會中,人們的交流較多以面對面的方式發生,其更注重主體在溝通過程中的動態體驗以及情感表達,同時也較少出現對行動群體的“偏見”[7]。而現代社會中,人們習慣于通過數字媒介為其快速的傳遞信息。可以說,這樣的轉變不僅能打破生活中時空層面的隔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數字時代的現實需求。但不得不說,“傳統”向“現代”的變遷多數情況是依靠科學技術作為支撐,實現數字系統對人類生活的服務,對于人口老齡化較為嚴重的中國來說,過度的數字化服務或數字生態的失衡也是不利于大多城市獨居老人正常生活的[8]。接下來,我們將以“城市獨居老人的生活出行”為分析場景,通過整理前期訪談對象的口述資料,系統地審視該類群體在數字時代的風險呈現。
(一)出行規訓下的風險分析
案例1:王奶奶,20年前隨老伴搬遷至城市,在城市生活8年后因老伴去世,子女也在外務工,最終只能選擇獨自一人生活。最近王奶奶面臨了兩大困難。其一是王奶奶平時習慣在社區樓下農貿市場買菜,但近年來農貿市場的支付方式基本轉變為移動支付。這樣的轉變使得王奶奶認為自己很快會被時代所淘汰。同時,由于自己生活在城市社區,鄰里之間不熟悉,也不愿多次麻煩鄰里,以致于其很難滿足生活基本需求;其二是王奶奶在老伴去世后,會偶爾與同伴去公園游玩,但受到疫情防控的有關規定,人員需掃健康碼、行程碼,才可進入園內。不同于過去的制度轉變,導致了王奶奶出行出現困難。
從上述的案例可以看出,數字時代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城市獨居老人的日常生活。而移動支付的廣泛普及對于人們來說是一種傳統行為的打破,從弱勢群體的角度來看,是社會環境對于其日常的規訓。同時,從城市獨居老人的生活世界出發來看,其過往的經驗是難以應對出行規訓的,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很可能長期受困于這類“枷鎖”之中或得不到合理的出行自由。因此,針對城市獨居老人,探尋一條緩解其生活出行方面的路徑有其現實意義。
(二)生計規訓下的風險分析
案例2:李爺爺,年老多病后無子女贍養,其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一直靠賣瓜果蔬菜謀生。近年來,受到掃碼支付的沖擊,導致很少有買家通過現金支付菜錢,或在支付菜錢時,只能給李爺爺大面額的現金,讓其退零。李爺爺每次遇到這樣的情況都很苦惱。一方面不想丟掉來之不易的生計機會,另一方面即使愿意掃碼支付,但在收到線上支付的金額后,又不能及時收到銀行卡的到賬信息。這樣一來,現代社會流行的掃碼支付就給李爺爺的生計帶來了無形的阻礙。
從上述案例不難發現,掃碼支付等數字科技的運用在某些情況下忽略了對于城市獨居老人實際困難的考慮,也使其與社會其他主體的互動表現出了“缺位” 的現象。而“缺位” 現象的緩解可能不能僅僅通過調整互動中的某一主體來實現,更多的需要考慮主體間關系的建立,以找到兩者的主體間性。因此,面對上述的風險呈現狀態,一方面需要思考如何從社會結構層面提升城市獨居老人在數字時代的生活福利;另一方面還需從社會行動層面反思其數字融入的實踐路徑。
二、智能與智人:城市獨居老人的一種生活應對路徑
上述從社會現象出發,集中論述了城市獨居老人在出行和生計方面的風險呈現。但僅僅從主體生活世界中反映風險對于該類群體的影響是遠遠不夠的。接下來,還需嘗試性地探尋符合城市獨居老人的一種生活應對路徑,為引導其與數字產物之間的關系從“區隔”轉向“融合”。
(一)媒介智能:風險應對的外部條件
風險的應對在很大程度上需進入風險所處的時代背景加以分析,同時需對風險產生的邏輯進行溯源[9],才能更好地為其提出不同思路。從時代背景出發,不難發現,當今社會對于信息的收集與利用已逐漸從傳統的紙質化方式轉向了無紙化的方式,這種慣習的打破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制于現代生活中人們對于時間的珍惜以及對于爆炸式信息的快速可知。雖然不可否認,數字化的行動的確滿足了年輕一代的需求,使其工作和生活變得更加高效。但社會活動不僅流動于上述群體之間,其同樣需要不同年齡階段的群體參與。特別在老齡化存在的中國,我們也需根據這類群體的特征以及其經濟、社會實際壓力的不同來為其提供差別化的服務與關懷[10]。其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和知識層度的阻礙,難免會與數字時代產生一定的區隔,而長期的區隔在多數情況下也會自然給其帶來隱性風險。因此,為緩解生活在數字時代的城市獨居老人之風險,我們試圖可以在多元共治的思路下展開思考。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風險社會的治理機制中,風險治理已不能僅僅依靠單一主體來承擔,很多時候需要政府、相關企業等合作治理的模式應對困境[11]。從風險產生的邏輯來看,數字風險之所以得以顯現且越來越受到關注,是因為其特征異于傳統的風險類型。一方面,大多高齡群體對時代的認知速度慢于社會變遷的速度,即認知滯后性。當該類群體在日常互動中還習慣于運用經驗性的認知來處理日常問題時,很容易遭遇一定的阻礙。屢次阻礙的形成過程我們也可將其視為一種風險產生的邏輯。另一方面,大多社會弱勢群體較缺乏適應數字時代的基本能力。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其因自身具備的適應能力有限,以至于當科技產物在日常生活中流行時,傳統的交流工具、媒介等就會面臨逐步的“失靈”,這樣一來,其日常行動就會受之牽絆,類似牽絆的情況越多,直接會使其陷入數字時代的“漩渦”中,亦是風險產生的另一種邏輯。
基于上述的分析,在生計風險的緩解層面,政府可充分發揮自身作為社會福利支持主體的作用。針對城市獨居老人制定人群生活困難度分級評定政策,以適應不同類型的老人需求。其次,聯動銀行主體開發城市獨居老人的支付結算系統,并附帶屬于每個等級的收款二維碼,以此保證城市獨居老人在謀求生計時,及時收到收入金額,這樣也便于老人在銀行網點當日取到生活所需的資金。上述過程既可以增強城市獨居老人在數字時代的融入,也能體現政府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差別化關注。在出行風險的規避層面,公園等場所可有效借助“刷臉技術”為其提供城市獨居老人的健康狀態檢測服務。這樣一來,不僅能緩解數字產物給城市獨居老人帶來的隱性風險,還能讓城市獨居老人感受到社會的溫暖,增強其數字社會融入的動力。
(二)主體智人:風險應對的內在選擇
在外部環境的優化性支持下,受風險影響的主體——城市獨居老人,也需要提高其應對生活風險的能力,因為數字產物多數情況下需要老人群體與外部社會的雙向建構,才能產生主體間的價值認同[12]。從社會志愿服務的層面來看,社區志愿者可以幫助城市獨居老人建立社區守望相助小組,引導鄰里之間相互幫助,特別是這類群體在遇到數字產物溝通困難時,積極幫助其弱化出行風險。除此之外,還可以鼓勵社區精英與一定數量的城市獨居老人結對,幫助其遠程化解生計風險。從社會專業服務的層面來看,首先,社會工作者可以在滿足“案主自決”的前提下,基于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的這對關系,幫助城市獨居老人轉變傳統的認知思維,逐漸引導其對數字時代和數字時代下的生活風險產生新的認知。一方面,使城市獨居老人相信社會環境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會影響一定的個人行為,而人們行為的改變也有可能會使其更加適應社會環境;另一方面,鼓勵城市獨居老人在社會工作者的專業服務下,建立認知改變的信心,以更好地應對生活風險。其次,社會工作者可結合社區工作的三大模式,通過扮演不同的角色,幫助城市社區的獨居老人緩解數字區隔。社會工作者在幫助城市獨居老人的同時,還可以發揮政策影響人的角色作用,幫助該類群體就普遍存在的需求或困難,提出相應的建議給政府相關部門,使其共同幫助城市獨居老人緩解數字時代的生活風險,同時在一定程度上溫暖其晚年生活。
三、結語
總而言之,探尋生活風險的應對路徑是為了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城市獨居老人打破時代區隔,使其更好地實現數字融入。本文首先對生活風險存在的可能形式進行了系統分析。其次,基于所提出的出行規訓和生計規訓,進行了風險產生的邏輯梳理與城市獨居老人的風險應對路徑探討,以期在數字時代為城市弱勢群體營造良好的生活空間。但由于該議題的思考目前處于理論探討和案例的前期分析階段,對于“刷臉技術”在城市獨居老人的生活風險應對上是否存在一定的不足之處以及如何形成一套更完備的多元共治機制來緩解城市獨居老人的生活風險,還需進一步的調研和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