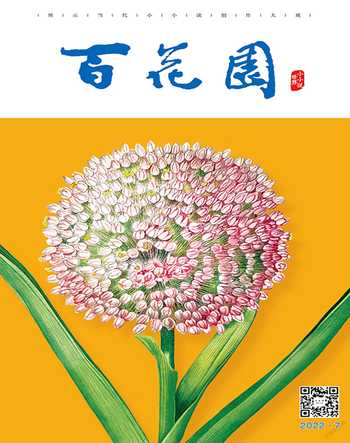董 工
齊川紅
董工到我們這兒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是我們請(qǐng)的第四個(gè)技術(shù)員了。
由于疫情的影響,公司承建的工程啟動(dòng)得很晚。勞務(wù)聘請(qǐng)的第一個(gè)技術(shù)員剛拿到圖紙,還沒(méi)細(xì)看,就告假說(shuō)外省的丈人剛剛?cè)ナ溃帽紗剩凰榻B的一個(gè)來(lái)了小半天就說(shuō)幾年沒(méi)干生疏了,也走了;又來(lái)了一個(gè),沒(méi)幾天就回了一個(gè)離家近的工地。工程還沒(méi)開(kāi)始就換了幾個(gè)技術(shù)員,老板很不爽。當(dāng)董工來(lái)的時(shí)候,老板有些疑惑——一則能否勝任,二則能否長(zhǎng)久。董工來(lái)自淅川,口音自然不太一樣,說(shuō)著土語(yǔ)式的普通話(huà)。他身材略高,胖瘦適中,紫銅色皮膚,像秋天田野里的紅高粱一樣樸實(shí);文質(zhì)彬彬,沒(méi)有多余的話(huà),一來(lái)就研究圖紙,做筆錄。老板對(duì)他第一眼的印象就很好。因?yàn)樗斩蠹叶冀兴岸ぁ保杏X(jué)叫著有點(diǎn)兒怪怪的。叫他的時(shí)候,他不應(yīng)答,只是抬頭看著你,有啥吩咐就照做,有問(wèn)題就解答。熟悉了,有人開(kāi)玩笑,喊他“東宮娘娘”。他訕訕一笑。原來(lái)他擔(dān)心的就是被這樣的稱(chēng)謂引出綽號(hào),終究還是被喊了出來(lái)。雖然不怎么愿意,他也沒(méi)表示過(guò)不悅。
他住在工地的辦公室里,一個(gè)人應(yīng)該是舒適安靜的。
閑聊時(shí)我問(wèn):“你知道我們這個(gè)地方不?”
他說(shuō):“不知道,第一次聽(tīng)說(shuō)。”
我說(shuō):“《三國(guó)演義》中‘火燒新野應(yīng)該知道吧?漢桑城,世界上最小的城。”
他搖搖頭,說(shuō)不喜歡文學(xué),也不喜歡文學(xué)作品。不過(guò)得知我時(shí)常寫(xiě)文章,他倒產(chǎn)生了一絲興趣。看到我的一篇有關(guān)齊大人齊慎的傳說(shuō),他覺(jué)得特有意思,一連幾天重復(fù)著文章中的幾句順口溜:“風(fēng)吹棋子落,摸住娘娘腳。犯下欺君罪,我命難逃脫。”“金頭銀頭,不如我爹的肉頭。”
董工是八○后,才三十來(lái)歲,媳婦在家照看兩個(gè)孩子。晚上他一個(gè)人難免寂寞,也不出去散心,唯一陪伴他的只有手機(jī)。有人問(wèn):“想老婆不?”他坦誠(chéng)地說(shuō):“肯定想了。”有人開(kāi)玩笑說(shuō):“遠(yuǎn)水解不了近渴,不如找一個(gè)情人,到外面風(fēng)流風(fēng)流。”他認(rèn)真地說(shuō):“我要背著她找,她也背著我找,怎么辦?”
一天早上我到工地,門(mén)衛(wèi)神秘地說(shuō)董工昨晚出去,剛剛回來(lái)。我愣了愣,這么說(shuō)董工夜里不是在工地住,莫非晚上真在外面……那就真應(yīng)了一句話(huà):“白天像教授,晚上是禽獸。”可是世上有多少正人君子、柳下惠,又有多少苦行僧、傳教士?不過(guò),如果真是這樣,也不算十惡不赦。食色,性也,也能理解,誰(shuí)也不能站著說(shuō)話(huà)不腰疼,站在道德的制高點(diǎn)評(píng)說(shuō)他人。我沖門(mén)衛(wèi)點(diǎn)點(diǎn)頭,意思說(shuō)知道了。董工像沒(méi)有什么事一樣,不過(guò)精神很好,竟然哼了幾句刀郎的《西海情歌》:“自你離開(kāi)以后,從此就丟了溫柔……”一連幾天,董工都是晚上出去,第二天早早回來(lái)。我也裝作不知道似的。
一天深夜,我正在夢(mèng)中,忽然被手機(jī)鈴聲驚醒,模糊中摸過(guò)手機(jī),手指一劃,問(wèn):“誰(shuí)呀?”聽(tīng)到一個(gè)熟悉的外地口音,吞吞吐吐:“齊哥,是我……董工……”我心想,深更半夜,有什么事?那邊說(shuō):“你能不能來(lái)一下?我……我……我在派出所……”我說(shuō):“怎么啦?”他說(shuō):“一句兩句說(shuō)不清楚。”
我暗自覺(jué)得好笑,他真是年少氣盛,血?dú)夥絼偅筒蛔〖拍3孕纫淮尉涂梢粤耍蛘呤彀朐乱淮危哪芤贿B幾天留戀風(fēng)塵?在派出所看到了紫著臉羞愧的董工,旁邊真有一個(gè)女的,垂著頭,披頭散發(fā),更是羞愧難當(dāng)?shù)臉幼印K┲肱f的衣服,用袖子邊遮掩邊擦淚,看起來(lái)也不像風(fēng)塵女子。一邊有兩個(gè)警察,似笑非笑,嘲諷的語(yǔ)氣中含著鄙夷,有著不易覺(jué)察的幸災(zāi)樂(lè)禍。
董工不住地辯解:“我們真的是夫妻。”
警察問(wèn):“結(jié)婚證呢?”
“沒(méi)帶,她來(lái)看我,我們住在賓館……”
“那怎么能證明不是賣(mài)淫嫖娼?”
“我們有身份證。”
“身份證上的住址怎么是兩個(gè)地方?”
“她的身份證是出嫁前在娘家辦的。”
“就算是一個(gè)村的,也不能證明你們是兩口子,偷情私奔出來(lái)快活的也不算少。我們見(jiàn)得多了。”
警察們“掃黃打非”也真不容易,不能正常作息,好容易逮到兩個(gè),如獲至寶。我解釋說(shuō)董工是我們勞務(wù)聘請(qǐng)的技術(shù)員,一直勤勤懇懇;至于他們的夫妻關(guān)系,就是沒(méi)有帶結(jié)婚證,也可通過(guò)別的方式證明,比如手機(jī)里存的照片、與子女的合影、聊天記錄等等都可以;要理解在外務(wù)工人員的艱辛,不是一般人能體會(huì)的。果然從董工的微信語(yǔ)音中聽(tīng)到這樣的對(duì)話(huà):

“媳婦,我好孤獨(dú),好寂寞,我想你。”
“我也想你。”
“那你來(lái)幾天。”
…………
當(dāng)我們從派出所出來(lái)時(shí)已是黎明時(shí)分。董工垂頭喪氣,他媳婦一言不發(fā),落后面很遠(yuǎn)。我安慰他們:“都過(guò)去了,不算啥。也許他們也看出你們是兩口子了,只是因?yàn)槟銈兪峭獾氐模肓P一筆錢(qián)而已。好了,天快亮了,你們休息一下,吃點(diǎn)兒早餐,還要上班呢。”
可是董工沒(méi)來(lái)上班,他辭工了。后來(lái)他跟我聯(lián)系說(shuō)回老家了,以后再也不出去了,一輩子就和老婆孩子守在一起。
[責(zé)任編輯 冬 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