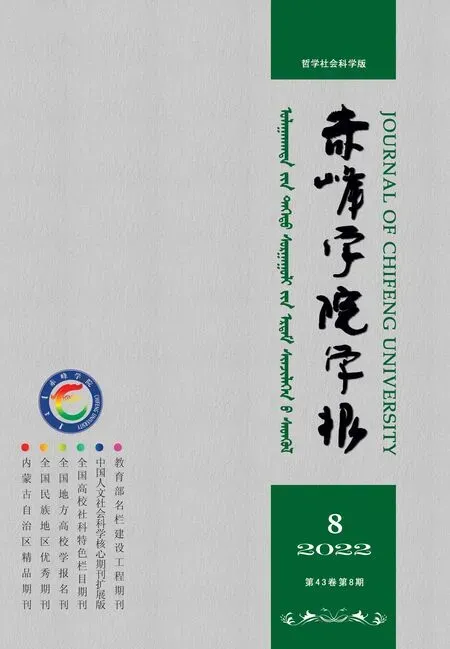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研究
楊 軍,徐 琦
(吉林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至梁啟超,其在《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中提出中華民族是由多元結合而來的一個大民族[1]。傅斯年進一步闡明該思想,1935年其發表《中華民族是整個的》一文,強調在大一統思想與大一統政治推動下,“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2]。之后傅斯年又對該理論進行補充,在強調整體的前提下,承認在中華民族中也存在各分民族[3]。顧頡剛在1939年發表《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引發激烈的學術爭論,同時也促進相關概念清晰化[4]。張博泉具體考察中華民族發展歷程,將其分為前天下一體、天下一體、前中華一體、中華一體等四個階段,重點研究北方民族政權與中華一體的關系,及北方民族政權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的貢獻[5]。上述研究主要是論證中華民族的整體性,對于北方民族如何參與構建中華民族則較少涉及。故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對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演變發展過程及其參與構建中華民族過程進行系統考察。
一、一體二元:秦漢時期
先秦時期已對“天下”有較為清晰的解釋,《禮·曲禮下》記載“君天下,曰天子”[6],鄭玄注“天下,謂外及四海也”[7],《爾雅·釋地》中將四海解釋為“九夷、八狄、七戎、六蠻”[8],可知天下這一概念由中國與四海構成,中國為海內華夏,四海為邊境四夷。包括華夏與四夷的“天下”也被認為是一個共同體,如子夏提出“四海之內,皆兄弟也”[9],荀子則更為明確地提出“天下一家”主張,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10]。可見“天下一家”“天下一體”思想在先秦時期已經出現。
秦漢建立起統一多民族國家以后,“天下一家”“天下一體”思想逐漸被認同。賈誼提出“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11],彭豐文據此認為,賈誼將天子與蠻夷比作身體的首、足以區分尊卑,但仍將二者放置于同一個整體當中,體現了賈誼夷夏一體、天下一家的觀念[12]。司馬遷《史記》體現出華夏與四夷同祖同源的思想,將四夷祖先追溯為黃帝后裔,從而將四夷與華夏都置于同一個以黃帝為始祖的血緣世系之中。如果說上述觀念仍屬于一家之言,那么西漢中期鹽鐵會議中士大夫與民間文人關于“天下一體”的討論則可以代表當時儒家知識分子的共識。雖然雙方關于如何解決邊境問題看法不一,但都將包含夷夏在內的“天下”視為一個整體,大夫一方提出“故王者之于天下,猶一室之中也”[13],文學一方也認為“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統”[14]。可見代表官方的士大夫與代表民間知識分子的文學都認同“天下一體”觀念。
漢朝統治集團也將“天下一體”觀念運用于處理其與匈奴的關系中,并在此過程中促進了匈奴共同體意識的覺醒。匈奴統治集團的共同體意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關于匈奴帝國內部共同體的構建,二是包括匈奴與漢在內的共同體的構建。
冒頓單于在給漢文帝的國書中提到,“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15]。樓蘭、烏孫等“國”“并為一家”,可見其存在高于“國”的共同體觀念。而匈奴統治西域,即是將其合并諸“國”為一體的政治觀念付諸實踐。匈奴采取定期朝會、和親、設置僮仆都尉、征收賦稅、納質、駐兵屯田、遣使監國、匈奴諸王駐牧西域等措施管理西域[16],表明匈奴在不斷推動共同體理念成為現實。而這一切的目的是“皆以為匈奴”,即打造包含多民族多國的匈奴草原帝國共同體。
漢文帝給單于的國書中說“漢與匈奴約為兄弟”[17],而在韓昌、張猛與呼韓邪單于簽訂的盟約中提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合為一家”[18],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構成了“一家”,漢匈雙方都認可這樣一個共同體,從中可見匈奴統治集團的共同體意識。值得注意的是,漢匈共同認可該共同體中存在漢匈“二元”。在漢文帝給匈奴單于的國書中提到“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19],漢朝方面認可匈奴是“一體”中的一元。在王莽干涉匈奴內部事務時,匈奴單于反駁:“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為作約束,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長城以北單于有之”[20]。可見匈奴方面也同樣認同自身是“一體”中的一元。
基于上述可知,雖然“天下一體”概念是漢朝人的一種政治理念,但在與匈奴交往過程中,漢朝人運用“天下一體”觀念處理漢匈關系,使得匈奴在此過程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共同體理念也逐漸植根于匈奴統治者心中。在“一體二元”形式之下,雙方通過戰爭、和親、互市等方式,增加民族互動頻率,推動民族融合。
二、一體多元:魏晉南北朝時期
魏晉南北朝時期,匈奴、鮮卑、羯、氐、羌等北方少數民族南下,先后在漢地建立以北方民族為統治民族、漢族為主體民族的多民族政權,北方民族地位發生變化,其共同體意識也發生了變化。出身氐族的前秦皇帝苻堅提出“方將混六合以一家”[21],北魏太尉長孫嵩及議郎博士等二百七十九人在討論吐谷渾問題時提到“四海咸泰,天下一家”[22],可見北方民族政權已經明確提出“一體”意識,并在構建與鞏固多民族共同體方面做出新實踐。
其一,繼承與發展儒學。匈奴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23]。鮮卑慕容皝“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24]。正是由于許多少數民族統治者有著較高儒學素養,他們也致力于興辦儒學教育,前趙劉曜設立太學、小學,選取13歲至25歲的一千五百人入學學習;前燕慕容皝“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25],可見其對于儒學教育的重視;后秦姚興時,太學已有數萬人的規模。北方民族統治者尊崇儒學,重用漢族士大夫,使儒學在北方得以存續和發展,北方民族與漢族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礎。
其二,運用天命觀證明“正統”。隨著北方少數民族統治的多民族政權的建立,北方民族的民族意識發生變化,開始對傳統華夷觀發出質疑,否定以華夷作為能否為帝王的標準,運用天命觀確立新標準。劉淵提出“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東夷,顧惟德所授耳”[26]。慕容廆在安撫降將高瞻時說:“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豈以殊俗不可降心乎”[27]。北方民族統治者打破了以往戎狄不可作天子的狹隘民族觀,進一步破除夷夏之別。
另外,采用“五德始終說”以及編造符瑞也是北方民族統治者塑造自身正統形象的重要方式。五德始終說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進入華夏歷史序列的重要方式,前趙開國君主劉淵自稱“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28]以延續漢朝的名義為其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爭取合法性。劉曜在稱帝后改變了劉淵延續漢朝、排斥魏晉的做法,確立前趙承晉為水德,石勒也以后趙為水德。前燕建立后則“承石季龍水為木德”[29],承認后趙的正統性。從此,“胡族政權納入到華夏歷史序列中,就成為既成事實,是歷史而不再僅僅是現實政治,這為北方胡族政權的華夏化,奠定了合法性方面的基礎”[30]。
其三,構建北方民族與華夏族的同祖同源。司馬遷《史記》構建“以黃帝為遠祖的世系相尋、血緣相通的五帝系統”[31],并將此系統與政權合法性掛鉤。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方民族從中得到啟發,為證明自身正統性,攀附黃帝世系,重新構建自身的族源傳說。《十六國春秋》中記載,劉淵“新興匈奴人,冒頓之后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32]。《晉書》中記載,慕容鮮卑“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號曰東胡”[33],《十六國春秋》則記載,“昔高辛氏游于海濱,留少子厭越以君北夷,邑于紫濛之野,世居遼左,號曰東胡”[34]。盡管《晉書》將慕容鮮卑記為黃帝苗裔,《十六國春秋》將其記為帝嚳后裔,但從本質上而言都將慕容鮮卑納入了黃帝世系之中,拓跋鮮卑則是昌意少子的后裔,昌意即黃帝之子。《晉書·符洪載記》提到,建立前秦的氐族“其先蓋有扈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35],建立后秦的羌族亦自稱為有虞氏之苗裔。由上述可知,匈奴、鮮卑、氐、羌等北方民族構建了與華夏族同祖同源的始祖神話,將本民族納入黃帝世系之中,以證明夷夏同為黃帝后裔,北方民族與漢族有了共同的心理認同。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在明確提出“天下一體”的前提下,通過繼承與發展儒學、運用天命說塑造正統形象、構建華夷同祖同源等方式,推動華夷之別的消除,進一步加強民族認同,為此后“天下一家”的實現奠定了共同的思想基礎以及共同的心理認同。
三、天下一家:從隋唐到遼金
唐朝統治者在“華夏一家”的基礎上,否定“先華夏而后夷狄”的民族不平等觀念,強調華夷平等,唐太宗明確提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冾,則四夷可使如一家”[36],后又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37],否定以往“貴中華,賤戎狄”的民族思想,承認夷狄與華夏為平等子民。正是由于隋唐統治者這種更為開放進步的民族思想,使得“天下一家”的政治理想成為現實。貞觀四年,“四夷君長詣闕,請帝為天可汗。帝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后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38]。唐太宗既是華夏之主也是夷狄之君,華夏與夷狄構成一個共同體。由契丹與女真等北方民族為統治民族的遼金則繼承與發展了唐代“天下一家”的格局。隋唐至遼金時期,北方民族不僅承認自身為該民族共同體中的一部分,還積極參與其建設,推動該共同體的發展與繁榮,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北方民族的民族思想發生變化。至隋唐時期,北方民族祖源追溯不再刻意追溯至黃帝世系,如記載突厥“蓋古匈奴北部也”[39],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40]。由此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民族統治者塑造“華夷同祖同源”的成功,“華夷同祖同源”已經成為華夷各民族的共識,北方民族在這一共識之下直述祖源,恰恰反映出北方民族承認自己與華夏民族處于一個共同體中,同為這個民族共同體中的一部分,已經不再需要攀附祖源來加以證明。
至遼金時期,構建該民族共同體的主導者由漢族轉為契丹與女真,契丹與女真都認同存在超越各自政權的多民族共同體即中國。一方面,遼金明確自稱為中國,完顏亮嫡母徒單氏在勸其不要伐宋時說:“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41],是以金朝為中國。另一方面,遼金同時也承認宋為中國,如,“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42],中國顯然指宋。在同為中國的前提下,遼金將自身與宋歸為中國這一共同體的兩部分。遼自稱為北朝,稱宋為南朝,如1052年遼遣使如宋,“其國書始去國號,而稱南、北朝”[43],“遼人無論是沿襲當時南北方位互稱南北并立政權為‘南北朝’的習慣,還是意欲提高自己以取得和北宋對等地位以及后來意欲凌駕于北宋之上而自稱‘北朝’,都具有強調‘南朝’、‘北朝’是一家的用意”[44]。金人更為明確地提出:“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45]。遼金統治者明確將自身與宋都納入“一家”這一民族共同體中,北方民族共同體意識得到進一步體現與發展。
二、北方民族在政治上積極參與建設民族共同體。唐王朝在北方建立多個羈縻府州用以管理少數民族,將原本的部落首領冊封為都督、刺史,北方民族通過這一特殊制度被納入一體統治,并參與建設這一民族共同體。另外,北方民族也為唐王朝的穩定繁榮輸出大量人才,如突厥處羅可汗之子阿史那社爾奉命征討龜茲,獲得勝利,西域諸國紛紛內屬,唐朝邊境得以西拓。另一方面,北方民族積極維護民族共同體的穩定。安史之亂爆發以后,“回紇遣其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余眾,助國討逆”[46],在平叛中發揮了重大作用。遼金則采用“因俗而治”的民族管理政策以及同化政策,使得遼金控制下的各民族成為一個實際意義上的民族共同體。同時,遼金政權所控制的各民族,也積極參與該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如遼征服渤海國以后,一批渤海國士人選擇入仕遼,尤其是在圣宗朝以“渤海舊族有勛勞材力者敘用”為原則[47],采取一系列用人政策后,進一步吸納渤海士人加入遼代官僚集團,為遼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在金對宋的戰爭中,也出現了耶律懷義、耶律涂山、耶律馬五等一批契丹族出身的將領擔任重要職位。
三、北方民族統治者通過與其他民族統治者構建親屬關系以維護民族共同體。“和親”一直以來被視為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通過構建姻親關系,使雙方統治者成為實質上的“一家”,同時也使得兩個民族共存于一個共同體之中。隋唐時期,北方民族早已具有“天下一體”的意識,并通過求親的方式使自身更好融入民族共同體。隋文帝時,突厥沙缽略可汗之妻,即北周千金公主,“自請改姓,乞為帝女”[48],隋文帝賜公主楊姓,并封為大義公主,沙缽略可汗與隋文帝形成翁婿關系,在沙缽略可汗致隋文帝的國書中提到:“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49]突厥沙缽略可汗希望通過構建姻親關系,使得隋與突厥形成彼此無異的一體。唐朝時,后突厥、薛延陀、回紇等北方民族也都曾主動向唐朝求親,與唐王室構建親屬關系,進而使民族共同體更為緊密。
遼金統治者與其他民族統治者構建親屬關系的形式主要分為真實與虛擬兩種。真實親屬關系構建主要是通過和親構成姻親關系,如遼曾三次與西夏和親,將遼朝公主嫁給西夏統治者,而金也曾將岐國公主嫁給成吉思汗。另一種則是構建虛擬的親屬關系,如遼金與宋約為兄弟之國、叔侄之國、伯侄之國,進而構建不存在血緣關系與姻親關系的虛擬親屬關系。隋唐至遼金時期,北方民族統治者積極與其他民族統治者構建或真實或虛擬的親屬關系,既表明北方民族對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可,也推動了北方民族更好地融入這一民族共同體。
四、多民族一體:元與清
元朝疆域遼闊,統一了北方草原地區與南方農耕地區,使身為游牧地區與農耕地區共主的元朝皇帝有著不同于以往君主的邊疆治理政策。元朝“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夷夏有別、內實外虛的傳統,采取了直接的更加積極的統治方式,將所謂羈縻關系實質化”[50]。一方面,在少數民族地區設立同內地一樣的行政制度,以宣政院、行省、宣慰司等機構對邊疆民族地區實行直接管理,當地戶籍需要上報中央,邊疆地區編戶也需要承擔賦稅徭役。在邊疆地區廣設驛站,使元朝中央對于邊疆民族地區的控制加強,同時為邊疆各民族之間往來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儒學成為各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礎。以忽必烈為代表的一批元朝統治集團成員對于儒學大力推崇,重用儒士、發展儒學教育、翻譯儒學經典、恢復科舉考試,使得儒學在元朝統治下的各族中廣泛傳播,儒學不再只被漢族掌握,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少數民族儒學大家,如畏兀兒人阿魯渾薩里、汪古人馬祖常等,儒學成為多民族的儒學。共同的政治制度以及共同的思想基礎使元朝得以構建出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共同體,遼金時期的“一家兩國”被統一為“一家一國”。
清朝強調“滿漢一家”“滿蒙一家”,進一步鞏固元朝所開創的統一中華民族。滿人入關之前,已經注意到建立多民族共同體的重要性,皇太極認為“滿漢之人,均屬一體,凡審擬罪犯、差徭、公務,毋致異同”[51]。滿人入關以后,滿漢民族矛盾尖銳,為解決更為復雜的民族問題,清朝統治者進一步宣揚“滿漢一體”觀念。順治皇帝明確說:“今欲聯滿漢為一體,使之同心合力,歡然無間”[52]。康熙繼承了“滿漢一體”思想,認為“朕于旗下漢人,視同一體,善則用之,不善則懲之”[53],“滿漢俱系朕之臣子,朕視同一體,并不分別”[54]。同時,康熙提出“中外一體”思想,認為“朕統御寰區,一切生民,皆朕赤子,中外并無異視”[55],并在康熙三十年宣布不再修理代表內外分界線的長城,進一步消除中外之別,鞏固了多民族共同體。
雍正朝上承康熙時期的繁榮景象,下啟乾隆時期的盛世,其大一統思想有著重要意義。雍正皇帝于《大義覺迷錄》中批判曾靜的“夷狄禽獸論”,認為“蓋識尊親之大義,明上下之定分,則謂之人;若淪喪天常,絕滅人紀,則謂之禽獸。此理之顯然者也”[56],強調應該以是否遵守倫理綱常來區分人禽,而不是以狹隘的民族觀念將夷狄視為禽獸。并以天命說反駁曾靜,提出:“皇天無親,惟德是輔”[57],強調德行才是能否為皇帝的唯一標準。并提出“天下一家,萬物一源,如何又有中華夷狄之分?”[58]打破夷夏之別。雍正十一年,雍正皇帝進一步對“中外一家”思想進行詳細闡釋:“中外者,地所畫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濱,統一諸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59]。雍正皇帝以一位少數民族統治者希望建立多民族共同體的角度出發,生動解釋“中外一家”觀念,提出了具有進步意義的民族觀念,這是千百年來眾多北方民族政權不斷努力的結果,是千百年來眾多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演變發展而來的思想結晶。
清朝統治者有著更為進步的民族觀念,并在施政中將“一體”觀念貫徹實施,“從思想文化上以‘儒化’促進‘一體’,用人制度上以‘共治’促進‘一體’,經濟生活上以‘互補’促進‘一體’,民族關系上以‘通婚’促進一體”,宗教信仰上以‘包容’促進‘一體’等方面入手,全方位地建構多民族‘一體化’體系”[60]。至清末,中華民族已然基本形成。
元與清建立了以北方民族為統治民族的全國范圍的大一統政權,這一時期的共同體意識更為成熟與包容,夷夏與內外徹底被打破,并且共同體意識得到了最為普遍且深入的認可,同時,這一時期共同體意識的實踐范圍包括了更為廣闊的疆域以及更多的民族,使得元與清所構建的“多民族一體”在思想上與實踐上超越了前期的“一體多元”與“天下一家”,為中華民族的最終形成奠定基礎。
結語
縱觀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演變發展過程,可以看出,北方民族共同體意識由模糊體現到明確自我表述,同時在將該意識付諸實踐方面,也由漢族主導、北方民族參與轉變為北方民族主導并主動構建民族共同體,這些轉變與北方民族歷史地位的變化及其文明程度的提高有著密切聯系。
透過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演變發展過程,可以看到我國古代北方政權積極參與及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構建,并在此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北方民族始終積極主動參與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北方民族通過多種途徑與多種方式與中原漢族交融,為中華民族的形成不斷注入新鮮血液。其二,北方民族破除了“內華夏而外夷狄”的狹隘民族思想,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其三,北方民族政權從多方面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首先,北方民族政權積極開發邊疆地區,同時在學習中原先進技術的基礎之上改進生產工具,使得邊疆地區生產力水平有了較大進步,極大地加強了邊疆地區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系。再者,北方民族文化極具本民族特色,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北方民族將本民族文化與中原漢族文化相結合,為中華文化增添活力。最后,北方民族在中外交流過程中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提出,我們遼闊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的,我們悠久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書寫的,我們燦爛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我們偉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61]。而對于我國古代北方民族政權共同體意識演變發展過程的探討,則更有助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使得各民族親如一家,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共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