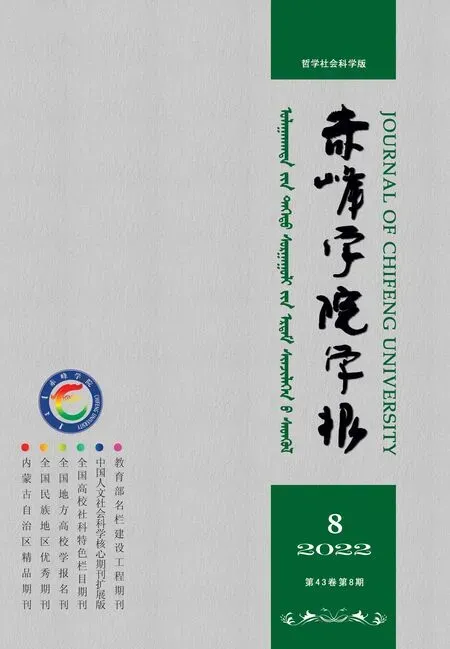清代中后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發展略論
秦 琴
(宿州學院 美術與設計學院,安徽 宿州 234000)
有清一代,安徽書院的發展達到鼎盛期且具有普及性,幾乎全省各州縣均設有書院。由于政治、經濟和地理因素導致安徽省書院出現區域發展及分布不均衡的現象,即皖南數量多且絕對發達,皖中次之,皖北最少且相對落后。就書院書法教育而言,皖北地區受淮河流域地區的傳統文化的影響,書法風格相對較為保守,多為古樸典雅。代表書院為:蕭縣的龍城書院、宿州正誼書院、靈璧正學書院。皖中地區以“桐城派書家”及梁巘為代表,書風多為二王一路的帖學,追求神韻。代表書院為:壽州循理書院、安慶敬敷書院。皖南地區書法發展呈現多樣性與包容性,一是以徽州地區曹文埴為代表,書風以帖學為主;二是受洪亮吉、包世臣等學者的影響,善篆隸者眾多,精篆刻者也甚眾。代表書院為:旌德縣毓文書院、碧陽書院、紫陽書院、竹山書院。
以歷史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清代中后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的情況,可以將其理解為超越地域的書院書法文化現象的廣泛存在。其原因在于安徽(江南省西部地區)、江蘇(江南省東部地區)早期同隸屬江南省,清康熙年間(1667),江南省分治,安徽單獨建省。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安徽省主要官員都駐安慶,自此不僅在實際上,而且在形式上也獨立成省。不過,終清一代,安徽、江蘇兩省的鄉試卻始終沒有分開[1]。正是這種歷史因素,也使得本文所論述的清代安徽書院書家分三大類,一類為皖籍且在安徽書院執教或求學的本地生徒,如姚鼐、梁巘、包世臣等;一類為流寓安徽的文人、士大夫、官員,如洪亮吉、沈曾植、吳德旋等;一類為籍貫在安徽,但基本生活工作在江浙地帶(原江南省)。本文以清代中后期為中心,擇取具有代表性的安徽書院對其書法教育的特征進行闡述。
一、清代中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
盛郎西在《中國書院制度》中云:“清之書院方式,大別為三:一為講求理學之書院,一為考試時文之書院,一為博習經史詞章之書院。”[2]需要提及的是,此一時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的論述主要分為講求理學之書院與以博習經史詞章為主的漢學書院。從乾隆到道光末年為中期。一方面,新安理學作為朱子學的重要分支之一,主要流傳于安徽,自南宋崛起至清前期終結,清代中期新安理學逐漸向皖派經學轉變,江永、程瑤、田既是這一轉變過程中的過渡人物,亦可視為新安理學的殿軍。安徽部分書院的教育既有新安理學傳統的烙印,又有著皖派經學學風的萌芽。表現在書法教育上便是在科舉的大背景下,為了給生徒科舉取士提供有益的幫助,教學以帖學為主,但又避免走向僵化,故尋求帖學內部的變革。最具代表性的書院是安慶敬敷書院、壽縣循理書院、還古書院。代表書家是梁巘(1710-1788),姚鼐(1731-1875)。另一方面,以婺源江永為先驅,休寧戴震為首的皖派經學在以漢學為主的安徽書院廣泛流傳,甚至突破地域限制,傳衍至全國其他范圍。戴震弟子段玉裁(江蘇金壇人)承其師未竟之志作《說文解字注》30卷,對清代安徽篆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表現在書法上便是篆書取得輝煌的成績。最具代表性的書院是洋川毓文書院,最具代表性的學者書家是朱筠、洪亮吉。
(一)傳統帖學的守護者:科舉背景下書院書法教育
在科舉取士的背景下,清代安徽許多書院增設字課教育,字跡工整規范、具有藝術美感,往往會影響科考成績的評定。基于此,清代中期以講授程朱理學為主的安徽書院部分執掌者和主講者為傳統帖學的守護者。他們受二王法帖及董趙書風的影響,擅長行書和楷書,尤以梁巘、姚鼐最具典型意義。
梁巘(安徽亳州人)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課徒春循理書院。在壽州的十余年,書寫碑版、教授弟子、獎掖后進,是清代中期安徽地域很有影響力的教育家和書法家。《承晉齋積聞錄》是梁巘在壽州講學期間所撰寫的,我們從中可以窺見他在壽州循理書院書法教學的理念。他在《承晉齋積聞錄·執筆論》中說:“吾課循理書院十余年矣。憶初至時,以執筆之法授人,無不謂為古人執筆不必盡如是,且誣以為欺人。及今得吾執筆法而字學長進者有數人,而人始息其譏而信之矣。是吾之不欺人已較然如是。然吾自掌教以來,教生徒之作時文者必先窮經,而人竟不之理,則又何也?”[3]可見,他在書院書法教學中極重執筆方法和力度的運用。
他在執掌書院期間不僅留下許多作品,“吾所書諸碑,以壽(縣)鳳(臺)《報恩寺碑》為最,《孫氏樂輪記》次之。《樂輪記》古厚結實,冠諸碑之上。”[4]且培養了大批書法人才,當地有“懷遠詩壽州字桐城文章”之說。壽州當地不少學生也精于書法,見于州縣志者不少,知州龔式谷《重修書院碑記》記載,當時書院董事議決:前院長梁先生巘,教諸生必以正,而尤長于書。今壽子弟之學書者,能通晉唐法,皆先生教也。先生手書摹勒及自為書尚存,請嵌之于壁以志景仰[5]。《壽州志》載部分書界名人,如余占鰲、黃令南、胡麟、劉兆岑、蕭景云、劉恬等皆受業于梁巘,以書名,其書風一脈相承,洋溢著文人的書卷氣息。
比梁巘稍晚幾年的姚鼐從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嘉慶二十年(1815)近四十年,輾轉講學于揚州梅花書院、安慶敬敷書院、歙縣紫陽書院、江寧鐘山書院,其中于安徽境內講學長達13年之久(1780-1788、1789、1801-1805),其書法教育思想、書法學術思想都是成績斐然。姚鼐主講書院期間書法教育思想主要有三點,其一:追求神似、崇尚自然的觀念。姚鼐書《論書絕句五首》(1785),主張書法不取形似,而求神似,無意于佳,“論書莫取形模似,教外傳方作祖師”[6]。他在講詩歌傳作時說:“若初學未能逼似,先求脫化,必全無成就。譬如學字而不臨帖,可乎?”姚鼐以學習書法做比喻,主張模擬,取法前賢,方可達到“兼體唐宋”的詩風[7]。姚鼐此意和書院的會規是一致的,《紫陽書院會規序》中講:“姚江復書,謂朱子《白鹿條規》蓋懼初學之靡所持循而然,誠恐學者不得其要,而徒依擬仿像于形似之間以為學,故私揭一‘心’字以為諸生告。”[8]此時書院會規也深受理學的影響,追求神似。其二:“勤于力”與“精于知”的教育觀念。《紫陽講堂會約》要求:“講論悉符于踐履,著述必本乎躬行,”[9]姚鼐在闡述自己的學書方法時說:“非無為書者也,勤于力者不能知,精于知者不能至也。”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書法教育思想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相融。其三:陰陽剛柔、中和為上的審美觀。我們從姚鼐任職書院期間的書法作品“為夢樓行書自作詩軸”也可以看出其書風受新安理學的影響,雅潔秀逸,深得中和之美,具有濃厚的書卷氣息,是傳統帖學的延續。
姚鼐近四十年的書院教學生涯,也培養了大批學術和書法人才,其弟子遍布江南各省,比較著名的有梅曾亮、管同、吳德旋、陳用光、李兆洛等,其中梅曾亮、管同曾主講安徽敬敷書院。管同的書作氣潔神清,深得姚鼐書風的神髓。吳德旋著有《初月樓論書隨筆》一文,主要的書法觀念為揚董抑趙、取徑唐人、崇尚晉韻,這也是姚鼐帖學思想的延續。此外,著名的書法家張栗庵和黃賓虹均曾為敬敷書院的生徒。
清代中期雖處科舉盛行時代,但以梁巘和姚鼐為代表的徽籍書家們能看到館閣書體的弊端,突破時風,極為重視書法藝術性,并告誡后人“學書勿惑俗議。俗人不愛,而后書學進”[10]。此類書院的書風雖然很難脫離清代中期帖學書法特定時代特點,但也未曾刻意跟隨潮流書風,而是在“法古”的同時呈現出自身對書法的理解與反思,書院掌教者和受教者也以高尚人品和脫俗書品的高度統一,構成其書院書法教育的典型特色。
(二)從“說文”學到篆書:皖派經學影響下的書院書法教育
清代中期以漢學為主的書院重視用考證的方法來從事研究,寓考訂于識字教育中,即:考訂經史,由識字而始。客觀上促進了篆書書法在書院教育中的傳播與發展。
就安徽而言,《說文》學在清代中期成為一門顯學,與江永、戴震等皖派經學家關系密切,“乾隆中葉,惠定宇著《讀說文記》十五卷,實清儒《說文》專書之首,而江慎修、戴東原往復討論六書甚詳盡。東原對于這部書,從十六七歲便用功起,雖沒有著作,然傳授他弟子段茂堂。自是《說文》學風起云涌,占了清學界最主要的位置”[11]。可見,清代《說文》學與皖派經學家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這一時期安徽書院也極為重視《說文》學,其書法教育具有濃厚的學術化色彩,以“為學先識字”為理念,講求字法與規范,開始教授生徒書寫篆書,《說文》成為識篆、習篆的工具書,書院的書法教育也逐漸形成了學術與創作互為滋養的優良傳統。此時對安徽書院產生重大影響的人物是朱筠(大興人,今屬北京市)及其弟子洪亮吉(祖籍徽州歙縣)。最具代表性的書院是洋川毓文書院。
乾隆辛卯年(1771),集官僚、學者于一身的朱筠任安徽學政期間曾《校刊毛本說文解字》三十卷刊行,且身體力行,書寫篆書,摹勒上石。他的本意是振撥漢學提倡樸學,但客觀上促進了書院學子對篆書興趣大增。清人張舜徽也曾評價道:“當時研精許學之風氣,尚未大開,筠倡導之功,為不可沒。”[12]這種“通經先識字”的學術氛圍在朱筠的倡導下,使得篆書的實用性及受眾群體在安徽大為增加,也為安徽書院培養了許多篆書大家。其弟子洪亮吉于嘉慶時期(1801)任洋川毓文書院山長長達五年之久,也依據《說文解字》來操觚作篆。他除了師法《說文》和“二李”之外,還取法古籀金文的奇字,“經學既大昌,籀法亦可窺。人摩一本日觀寫,豈數丞相東封碑”[13]。在任毓文書院山長期間其篆書達到成熟。他不僅不遺余力地推廣“說文學”,而且以學問帶動整個書院的書藝,“每有異才,必加將許,其尤邀欣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累累常盈幾案,至有數千里輾轉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不可勝計”[14]。洪亮吉在毓文書院培養了一批弟子,如呂培、譚正治、譚時治、潭貴治、呂璽、曹景先、汪賓、崔本化等,其弟子對洪氏的教學內容也多有記載,譚正治有云:“吾師尤在立名教,剪燭高談盡忠孝。教以研經知適從,先鄭后鄭當所宗。教以古篆心更恰,大徐小徐皆足法。”[15]洪亮吉也曾言:“九經四史孰淹貫,八體六書宜涉獵。”[16]這些都表明篆書書寫是毓文書院教育中的一部分。在此需要提及的是,清代中期毓文書院雖以漢學為主,教學也多以“字學”與“書學”并舉。但是并不排斥科舉,有著科舉應試和講究漢學的雙重目標,故書院生徒也善行楷,如洪亮吉弟子呂培著有《說文箋》,善行楷,工篆隸。
可以說這一時期,“說文學”以安徽、浙江、江蘇為中心,形成了一定的學術群體,書院也成為傳播漢學的中心并出現了空前繁榮的“說文學”家。雖“《說文》切于治經”,但其研究者多能作篆書,且成果也為篆書創作提供了基礎。安徽書院在此時篆書藝術取的輝煌成績正是賴于這批學者及他們的門生子輩才逐漸衍為潮流的。
二、清代后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
咸豐以后為清代后期。“西潮”的沖擊下,近代新學萌生和壯大。但此時的安徽書院書法有兩個方面的表現:一是書院書法教學受時代變化之影響,提倡經世致用,銳意改革,推陳出新。以毓文書院的包世臣為代表。二是書院書法教育思想深受理學的影響有著濃郁的“存古之風”。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理學大師程朝儀主講六安賡飏書院和敬敷書院,其弟子胡元吉在光緒二十二年(1896),任敬敷書院學長;沈曾植在安徽建立“存古學堂”。
包世臣(安徽涇縣人),22歲時曾在蕪湖中江書院學習,晚年曾任毓文書院山長(在院時間為:1844年-1850年),他的《安吳四種》就是在講學期間所寫,其中《藝舟雙楫》最能體現他的書學思想。他雖未曾直接受西學的影響,但處于西學東漸時代之中,加之與激進派人物林則徐、龔自珍、魏源等人有著較好的友誼,難免受其影響。包氏的書學觀是“以復古為解放”“借古開今”,以變革創新為其特點。具體而言,他推崇唐代以前的書風,對宋元明以來書法家使用的筆法提出質疑和否定,并結合自己的學書心得詳細指出了“逆入平出、萬毫齊力”的創作技巧、“篆分遺意”的審美標準和“五品九等”的品評體系。包世臣這些完整的技法原則和書法理論傳授給了大批的弟子。鐘明善先生曾經這樣認定包世臣:“包慎伯是優秀的書法教育家,而不是天才的書法家。”[17]筆者查看了《毓文書院志》和《毓文書院志續修》兩著作,但是到包世臣任山長期間的人物弟子一欄未被續寫,著實可惜。但是在當時毓文書院作為漢學人才的培養基地,其生徒數額肯定不在少數,書法方面的有才之士也應該濟濟一堂,在此姑且論述一下受包世臣書法風格和書學思想影響的徽籍書家,以窺其貌。如安徽旌德人姚配中為包世臣弟子,對包氏的《藝舟雙楫》深信不疑,稱其為“換骨金丹”,并受包世臣啟發著有《書學拾遺》。安徽合肥人沈用熙,一生精研包世臣書法。包世臣一直提倡碑學,但他在安徽毓文書院期間寫得最多的還是二王一系的法帖,這一點我們從安徽省博物館藏的《小倦游閣法帖》中也可以看出,包世臣及其弟子、友人所選的書作多為帖學范疇。
晚清安徽學林的重要人物沈曾植(浙江嘉興人),他曾任安徽提學、安徽布政使,特別推崇理學,“以道德為學界天職”,傾力興辦安徽存古學堂,辦學沿用中國傳統書院的日程和古學教法。沈曾植不僅在辦學上有著溝通中西的“世界眼光”,其書學思想也是融合南北書派,兼重碑帖的旨趣。在當時“尊碑抑帖”書壇背景下能夠注重師承“帖法”而又不失開放包容地面對“碑學”,是難能可貴的。其弟子王遽常在《沈寐叟年譜》中說,沈曾植出任安徽提學使,“先后招致耆儒桀士程抑齋、方倫叔博士(守彝)、常季、馬通伯主事(其昶)、鄧繩侯、胡季庵、徐鐵華、姚仲實(永樸)、姚叔節解元(永概),時時相從考論文學。人謂自曾文正公治軍駐皖以后,數十年賓客游從之盛,此其最矣”[18]。可見,當時皖中學人“時時相從考論”的,應不限于文學,也包括書法,王遽常本人也是章草大家。
上述兩個時期中,安徽書院書法教育的內容雖受書院性質及時代學風、書風的影響各有不同的側重。但是,清代中后期安徽書院書法教學重筆法,且教學內容多為晉唐法帖和秦漢篆隸,也涌現出一批通曉《說文》,熟悉篆文的書院學子。從具體書法實踐上講,帖學書風對書院學子影響較為深遠。
結語
清代中后期安徽書院書法教育歷史豐富多彩,本文僅就書院書法教育的發展過程和特點做了上述粗淺的探索,可以起到鑒往察今的作用。這對于我們今天的書法教育,特別是安徽高等院校的書法教育事業是有所裨益的。當然,清代書院書法教育有其歷史局限性,其教育觀念未脫離儒學教育“學而優則仕”的教育目的。但是客觀上清代安徽書院的書法教育培養了大批在學術和道德上具有高水準的士子,弘揚了書法藝術,傳播了學術思想,具有鮮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特色。我們不能以今天的書法教育標準來衡量清代的書法教育觀,只可吸收借鑒書院書法教育中的合理因素,進一步開闊書法教育的視野和思路,為未來書法文化的發展不斷注入時代的文化內涵,實現傳統書法文化的創造性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