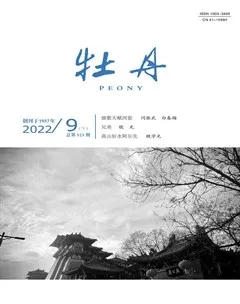《活著》與《巴里流浪記》的生死觀比較研究
生與死是文學創作中永恒的主題。中韓兩國地理位置相近,歷史文化不同,因而生死觀也有所差異。莫言稱余華為“中國當代文壇上的第一個清醒的說夢者”,創作過《許三觀賣血記》《活著》等現實主義作品。韓國作家黃皙暎被評價為“20世紀韓國最優秀的小說家”,《客地》《發財豬夢》《身邊的人》等都是描寫普通人民辛苦生活的現實主義作品。余華和黃皙暎在中韓兩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且都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候選人。在中國知網搜索相關論文,有《活著》作品生死觀的研究和中西、中日生死觀比較等,《巴里流浪記》的研究僅限于文化符號研究,還有王春煥關于余華與黃皙暎作品可比性的比較研究,但暫時未考察到兩部作品生死觀比較。本文通過比較文學中的平行研究方法和社會歷史批評方法把文章分成三部分,比較《活著》和《巴里流浪記》這兩篇長篇小說中出現的接二連三親人死亡事件。
一、余華《活著》中的生死觀
余華《活著》的主人公福貴經歷了在現實生活中幾乎不會發生的起起落落,但這些并沒有把福貴壓垮,反而每一次經歷都會使福貴成長,到最后,他坦然講述自己的經歷并微笑面對生活。“我爹死后,我像是染上了瘟疫一樣渾身無力,整日坐在茅屋前的地上,一會眼淚汪汪,一會唉聲嘆氣。”父親死亡后,接受不了父親死亡的福貴整天想不開,母親和妻子在家里都不敢大聲說話。家里因福貴破產加上父親死后,丈人氣沖沖地來把妻子接走,這是福貴人生的第一次落。沒過多久,妻子家珍遵守約定,生下兒子有慶后回到福貴身邊,一家人重新團聚使福貴人生又起了起來。
母親生病,福貴去城里請郎中時被國民黨抓去拉大炮,這段出現了小說中最多的對死亡的描寫。“有一次我跑著跑著,身邊一個人突然摔倒,我還以為是餓昏了,扭頭一看他是半個腦袋沒了,嚇得我腿一軟也差一點摔倒。”國軍的陣地逐漸縮小,福貴只能撲在坑道上看著陣地后方變成傷號的天下。“抬擔架的都貓著腰,跑到我們近前找一塊空地,喊一、二、三,喊到三時將擔架一翻,倒垃圾似的將傷號扔到地上就不管了。”看傷員看到麻木的福貴不但不會被嚇得腿軟,甚至感覺呻吟聲像是在唱歌。“只剩下一個聲音在嗚咽了,聲音低得像蚊蟲在叫,輕輕地在我臉上飛來飛去,聽著已經不像是在呻吟,倒像是在唱什么小調。”最后看淡生死的福貴開始擔心家人找不到自己會著急。“一個來月在槍炮里混下來后,我倒不怎么怕死,只是覺得自己這么死得不明不白實在是冤,我娘和家珍都不知道我死在何處。”這段經歷又是福貴人生的落。被解放軍救出的福貴雖然想參加解放軍來報答救命之恩,但由于對生的渴望,還是選擇回家和家人團圓。這使福貴人生又幸福起來。
回到家后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家珍什么也不說,就是淚汪汪地看著我,我也就知道娘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站在門口腦袋一垂,眼淚便刷刷地流了出來。”福貴人生又低落了起來。后來村里開始土地改革,從戰場上撿回一條命后又斃掉了替死鬼地主龍二,福貴感嘆大難不死必有后福,開始相信命運。福貴的人生又開始幸福起來。
日子越過越苦,家珍又患上軟骨病,干不了重活,還增加了家庭負擔,再加上有慶過度輸血死亡,作者對于福貴面對有慶死亡的反應描寫的篇幅最長,抱著兒子哭,對準醫生的臉打一圈,朝著縣長肚子蹬一腳,又笑又哭,這使福貴人生又黑暗起來。不久后家珍回光返照,竟可以自己坐起來,女兒鳳霞與靠譜的二喜結婚,黑暗中的福貴人生中又出現一束光芒。
鳳霞大出血死亡后,福貴比之前兒子死亡時冷靜許多,還可以安慰并照顧女婿二喜:“我的一雙兒女就這樣都去了,到了這種時候想哭都沒有了眼淚。”可以看出,福貴已經開始慢慢接受死亡,甚至在為即將死亡的妻子準備棺材。在后來回憶家珍死亡時說道:“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凈凈,死后一點是非都沒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還有人說閑話。”到二喜與苦根的死亡更是輕描淡寫,到最后因沒能阻止家人的死亡,所以救下待宰的牛來減少對家人死亡的痛苦。
二、黃皙暎《巴里流浪記》中的生死觀
黃皙暎的《巴里流浪記》是以韓國神話鼻祖《巴里公主》為母題創作的長篇小說。小說主人公巴里也面臨了無數的死亡事件,被迫從朝鮮到中國,再從中國到英國,巴里在移動過程中經歷了豐富的感情。
巴里從出生開始就伴隨著死亡。“媽媽一聲不吭地哭著坐下來,把我抱到屋外,走到離村子很遠的樹林里。媽媽把我扔到草叢中,然后把衣角蓋在我臉上。”如果巴里家的小白狗沒有救巴里,也不會有接下來的故事,但這種對死亡的恐懼從出生開始就伴隨著巴里的一生。隨著身邊家人死亡事件的故事發展,巴里對生死有了新的認識,承認并接受人必然會死亡、自己的死亡也遲早會發生的事實。第二次死亡描寫是巴里的姐姐賢兒。“那天晚上賢兒死了。因為身體過于虛弱,再加上無法忍受寒氣。但是爸爸、奶奶和我三個人都沒有流過一滴眼淚。”賢兒是六個姐姐中唯一一位陪伴在巴里身邊的姐姐,賢兒都沒有像樣的葬禮,父親拖著賢兒并大喊“不要跟著我”的樣子對巴里產生了巨大的傷害。13歲姐姐的非正常死亡對巴里來說是殘忍的,難以接受的。第三次死亡描寫是相依為命的奶奶。“我把頭靠在奶奶的胸前,試著把手指貼在鼻子底下,但她肯定已經死了。我坐在一旁嗚嗚哭了半天。過了很長時間之后,我在空林中聽到自己的哭聲,這才停止了哭泣。我呆呆地坐了幾個小時,然后開始用鋤頭刨地。”奶奶是巴里人生中最重要的親人,年幼的巴里把成年人處理起來都困難的埋葬奶奶尸體這件事處理得井井有條。奶奶的存在對巴里來說意義重大,所以小說中奶奶雖然在現實生活中消失,但依然以靈魂的方式默默守護著巴里,為巴里指明前進的方向。第四次是女兒順兒的死亡。“順兒像皺巴巴的布娃娃一樣被扔到了樓梯上。我趕緊抱起孩子。順兒,順兒!嬰兒的頭朝后耷拉下來。我又喊了幾聲,可家里還是空蕩蕩的。去醫院確認孩子已經死了,我還是不敢相信。”巴里花費很長時間才接受了女兒的死亡,只有為女兒報仇才能接受現實的巴里揚言要殺掉祥。雖然最終巴里沒有殺掉祥,但祥也自己終結了生命。
除此之外,巴里面對的死亡還有丈夫、弟弟、爸爸、媽媽和其他姐姐。住在英國的弟弟為了拯救陷入危機的祖國,冒著生命危險勇敢地決定和朋友一起去巴基斯坦,隨后丈夫也不顧危險去尋找弟弟。生病的爸爸在痊愈后便踏上尋找媽媽和姐姐的路,最終爸爸沒能遵守約定,和媽媽、姐姐都以死亡告終。身邊的家人接二連三地死亡和離開,使主人公巴里經歷了不安的一生。也正是這種一次次對死亡的不安,給了巴里在任何死亡面前都能堅強活下去的勇氣和信心。
三、生死觀的異同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是一種人生中的必然事件。文學作品中對新生命的誕生往往充滿希望和憧憬,但對于死亡的描寫卻讓人感到惋惜和傷心。讀者常常期待在文學作品中尋找現實中難以實現的歡樂和圓滿結局,所以創作時許多作者為了滿足讀者期待會對死亡輕描淡寫。《活著》和《巴里流浪記》中分別出現7次和8次周圍人死亡事件的描寫,這在小說中并不常見,在現實更是如此。創作源于生活,能把親人的死亡事件用不同的感情細膩描寫,要歸結于作者余華和黃皙暎的社會背景和人生經歷。
余華1960年出生,在余華的回憶里,小學時住在太平間對面,經常晚上聽著家屬凄慘的哭聲入眠,后來夏天熱的時候甚至跑到太平間里乘涼。非同常人的童年經歷使余華從小開始近距離接觸死亡,并且這種經歷對之后的創作產生很大影響。1943年出生的黃皙暎經歷過多個社會動蕩時期,并且親自參加過越南戰爭。不論是生活在戰亂年代還是親身經歷戰場的腥風血雨,都不可避免地與死亡擦肩而過。余華原本是牙科醫生,后來棄醫從文成為作家;黃皙暎參加過戰爭,當過僧人,1993年還入過監獄。因為兩位作家所處相似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有著相似的豐富的人生經歷,所以小說的題材、樣式、手法都呈現出多樣化。他們的作品中會出現多次死亡事件,平淡的死亡描寫讓讀者一邊驚訝于故事的發展,一邊又欣然接受。
如果把文學作品中人物的一生分為出生、人生、死亡三個部分,那么第一部分“出生”就是作者讓人物在作品中第一次展現在讀者面前。例如,《活著》中首先登場的在自己的田產上干活的傭戶都要恭敬叫老爺的爹,與父親相反的徐家的敗家子,從小就不可救藥的主人公福貴等,《巴里流浪記》中主人公巴里出生在上面有六位姐姐卻一心想要男孩的重男輕女的家庭。第二部分“人生”是指人物在作品中的經歷。《活著》中的主人公福貴年輕時拿著家里的錢去妓院、賭博,經歷家人接二連三的生離死別后慢慢成長。《巴里流浪記》中的主人公巴里雖然生下來就被父母拋棄,但為了生病的父親毅然決然踏上了尋找生命之水的路。最后一部分“死亡”就是人物在故事中的結局。《活著》和《巴里流浪記》中雖然出現大量死亡事件,但是兩位主人公的結局并沒有直接交代死亡,福貴和自己相似的老黃牛相依為命,無家可歸的巴里在發生恐怖襲擊的倫敦街頭結尾。
雖然兩部作品都出現除主人公以外大量親人死亡的事件,但比較兩部作品可以發現,《活著》以周圍親人的死亡來突出人生活著的意義。1997年意大利《共和國報》這樣評價《活著》:“這里講述的是關于死亡的故事,而要我們學會的是如何去不死。”每一次親人的離開都讓福貴更加珍惜還陪在身邊的人和還活著的日子,不再為死去的人和事感到惋惜和悲傷。《巴里流浪記》則以親人的相繼離開讓巴里學會更加堅強地面對困難,在困境中重生,找到生命的意義。剛出生就被丟棄的巴里被小狗救回來獲得重生,創業失敗后從中國偷渡到英國的船里聽著各種哭聲和忍受各種虐待艱難度過地獄般的四十天,到達倫敦后再次重生。尋找生命之水也是為了重生,巴里跋山涉水去尋找的生命之水不光是救父親的水,更是支撐自己在艱難旅途中繼續活下去的水。名字代表對一個人的期望,從主人公的名字中也可以看到這種傾向。《活著》主人公“徐福貴”寓意人生既有福,又可以遇到貴人。《巴里流浪記》中的巴里從出生開始就擁有通過腳來觀察他人命運的能力,所以“巴里”是“被拋棄”加“腳”的韓語合起來的發音。通過名字可以看出,福貴是余華希望主人公看淡生死、珍惜眼前的福和貴而起的名字,而巴里是黃皙暎希望主人公被拋棄后通過其他姐姐沒有的能力來改變命運、勇敢活下去而起的名字。
四、結語
本文通過《活著》中主人公福貴和《巴里流浪記》中巴里經歷的一系列親人死亡事件,分析在兩位作者相似的社會歷史背景和豐富的人生經歷下兩部作品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比較得出如下結論:在兩部出現大量死亡事件的長篇小說中,《活著》以主人公身邊親人起起落落的生死事件來使福貴更加珍惜在世的親人和活在世上的每一天,強調經歷親人死亡是為了突出還活在世上的意義;《巴里流浪記》中一系列家人死亡事件使巴里從單純的小女孩變成堅強的女人,這些經歷不但沒有擊垮她,反而使她變得更加勇敢,堅定地在殘酷的世界尋找生命之水獲得重生繼續活下去的信念,強調死是為了突出生的意義。如果說《活著》是越經歷死亡越平淡,那么《巴里流浪記》則是越經歷死亡越勇敢,兩部作品以不同的生死觀,從不同角度體會了不同的生死意義。
(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