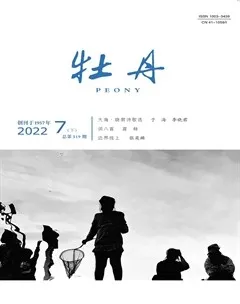到不了的遠方
作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就已經成名的“先鋒作家”,余華素來注重使用敘事的結構和暴力美學風格的構建表達對社會不良現象的憤怒,到90年代的文學創作開始逐漸將注意力轉向情節等傳統小說因素,并通過敘事抨擊社會不良現象。2000年后,余華的小說創作在講故事的同時表現出對現代性甚至哲學層面的探討。《文城》沿襲20世紀80年代后新歷史小說的創作理念與方法,在保持個人風格的基礎上傾向哲學甚至宗教的思考,以情節豐滿的故事滿足大眾的閱讀興趣。
一、新歷史小說的余韻
《文城》講述的是北洋政府末年期間的故事。當時北洋軍閥之間的混戰、北洋軍閥與國民革命軍的混戰使得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北方地主林祥福與南方來的“兄妹”阿強與紀小美(實為夫妻)結識,紀小美留在林祥福家與他發生感情,兩人生有一女后紀小美離開了林祥福。林祥福發覺小美離去,決定帶著女兒去南方尋找小美,在南方溪鎮定居用木匠的身份創業成功,在溪鎮購置田產落戶,后在與土匪的斡旋過程中不幸被殺害。紀小美在溪鎮因為封建迷信的祭拜活動受凍而死,兩人自在林祥福家鄉分別后終究沒有重逢,只是在將林祥福的墳遷回故鄉時與小美的墳偶然相遇。林祥福用一生的時間尋找小美,最終兩人卻在死后以墓碑和棺材的形式“相見”,讓讀者讀后不禁悵惘。完整豐滿的情節吸引著讀者,溪鎮與土匪幫派的較量與故事主人公死亡的偶然性使讀者在享受情節帶來的快感時不禁反思戰爭對人民群眾的迫害之深。
與《第七天》的新世紀都市時代背景大不相同,《文城》故事的時代背景顯示了余華對以往新歷史主義范疇創作興趣的延續。當時代主題為戰爭與和平時,文學創作的社會功利性價值增強,創作內容往往表現當下社會現實或歷史重大事件;當時代主題為和平與發展時,人們的物質生活得到改善,文學創作的社會功利性價值減弱,娛樂消遣功能增強,作者與讀者將閱讀審美興趣投向不同的歷史時空。故事發生在北洋軍閥與國民革命軍戰爭時期,卻并沒有涉及任何相關史實的陳述,它跳出了革命歷史小說的二元對立模式,以民間愛情故事和村鎮民團與土匪的較量為主要內容來挖掘人性,反映背后深層次的社會秩序的混亂。反映歷史真實是作者創作《文城》的目的之一。
《文城》中的人物往往帶有模糊化特點。地主階級的林祥福這個人物形象在《文城》中并沒有得到立體化的塑造,與其將他定義為主要人物,倒不如將他定義為一個符號或是行動元,僅僅是推動情節的工具。身為地主的林祥福并沒有被農民、軍閥殺死,反而被土匪殺死,側面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閉塞的社會環境中部分農民人性的惡。正如《文城》六十五章所描述的:“張一斧左手揪住林祥福的頭發,右手的尖刀往林祥福的左耳根處戳了進去,又使勁擰了一圈,林祥福的鮮血噴涌而出,抓住林祥福的幾個土匪叫著跳開去,用手胡亂抹去噴在臉上的鮮血。”無論在封建王朝末期的中國近代社會處于什么位置,人的健康甚至生命都不僅僅被外部帝國主義勢力所侵害,而更多地被社會內部的動蕩所削弱。
對于人的死,亞里士多德在《詩學》中闡釋道:“引起我們憐憫的只有那不應分遭受的災難,而引起我們的恐懼的卻是由于遭難者和我們之間有些相似。”黑格爾在《美學》中運用辯證法否定其觀點,并得出結論:“對于亞里士多德的說法,我們必不能死守著恐懼和哀憐這兩種單純的情感,而是站在內容原則的立場上,要注意內容的藝術表現才能凈化這些情感……所以悲劇人物的災禍如果要引起同情,他就必須本身有豐富內容意蘊和美好品質,正如他的遭到破壞的倫理理想的力量使我們感到恐懼一樣,只有真實的內容意蘊才能打動高尚心靈的深處。”站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立場上,小說、戲劇中人物的死帶來的又比恐懼和哀憐復雜得多。這就好比集體無意識是中性詞,但是特定時代的集體無意識所導致的意外死亡使人憤怒。無論小說中的人物是否擁有豐富內容意蘊和美好品質,當代人都可以意識到不良制度對人的迫害。
二、一如既往的暴力美學
揭露不同時代的混亂現實、批判不良社會現象成為當代嚴肅文學作家筆下必然出現的內容。不同的作家運用不同的方式進行著這項工作:莫言運用魔幻現實主義方法塑造生命力異常的人物,以此來打破不良政策對人的束縛;劉震云使用新寫實主義的方法描寫小人物的庸常人生,以此來拒絕主流意識形態的過載;余華使用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方法描寫種種極端暴力、血腥的場面,以此來表現集體無意識、批判社會不良現象。對暴力血腥的零度描述成為余華作品獨特的文學風格。
《十八歲出門遠行》中村民在搶劫壞車零件時對少年的毆打,《在細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家與王躍進家的斗毆,《第七天》中種種爆炸、車禍、暴力拆遷,《文城》中也一如既往承載著余華對暴力的敘述:
起先徐鐵匠還能看清,當他眼球被打出來以后,就不清楚了,他覺得有什么東西掛在眼睛上,就問孫鳳三:
“我眼睛上掛著什么?”
孫鳳三看了看說:“師父,你眼睛上掛著眼睛。”
溪鎮民團與當地土匪戰爭的暴力敘述在《文城》的比重比以往大大減少,但是余華依舊能夠使用暴力美學恰到好處地展現戰爭的殘酷,體現戰爭中平民所遭受的真實創傷,闡明一個真理:無論戰爭最后勝利的是何方軍隊,民眾永遠是被傷害最深的群體。《文城》中的鎮長顧益民和地主林祥福也并未因為財富逃過張一斧土匪幫的凌虐,人物的意外死亡是余華暴力美學風格的又一特征。構成人物意外死亡的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暴力,還有各種偶然事件與自然的力量。《文城》中的小美就是在城隍閣拜蒼天儀式時因為氣溫過低而被凍死:“這時候小美看見了女兒,女兒張開嘴對她嘻嘻而笑,女兒嘴里有兩個白點,門牙生長出來了。小美淚流而出,這兩行眼淚是她身上最后的熱量。”
對于普通人來說,暴力、血腥、死亡等種種概念過于黑暗而無法接受。但對于余華來說,這或許又是一種工具。父母都是醫生的余華自童年就在醫院度過大部分時間,對于太平間、尸體及其親人的哭聲早已司空見慣,成年后的余華成為作家前有過做牙醫的職業經歷。余華自然使用很多醫學的思維角度看待這個世界。對于平常人過于黑暗而無法接受的事物是余華習以為常的,于是他可以從容地描述暴力與死亡。
三、難以言喻的荒誕
封建制度與戰爭對人的迫害在《文城》中顯露無疑。喚醒讀者主體意識體現著該小說的意義所在。文城是不存在的,這個地方來源于小美的謊言。換句話說,林祥福用了后半生所追尋的地方是不存在的。西西弗斯無法逃離與石頭做伴的命運,林祥福注定一生追尋小美未果。
西方現代文學中的荒誕性在余華的文字中顯現。仔細思考可以發現,余華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文集中都隱藏著荒誕主義、虛無主義哲學的色彩。以余華短篇小說《河邊的錯誤》為例,讀者可以意識到現代社會中基層民眾生活意義的虛無、人與人關系的疏遠和人的異化。余華的雜文集《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中有一篇《語文與文學之間》,余華在其中展現了一堂中學語文課堂實錄,真實呈現了老師、學生關于《十八歲出門遠行》的對話和自己的真實想法,而老師、學生與自己對于作品的認識大相徑庭,荒誕意味也自然顯現出來。
與其說是林祥福選擇了小美,倒不如說是小美和阿強利用計謀選擇了林祥福。小美和阿強因為這次選擇而以不正當的方式獲得了活下去的資本,林祥福也獲得了自己的女兒,但這選擇不能說明林祥福和小美的人生是有主體意識的。兩個人如同設定好的機器一樣履行著自己的社會義務,對于法律的踐踏則是以宗教式自殺進行懺悔,這些故事內容側面反映了現代文明的虛無與荒誕意味。盡管《文城》是一部相對趨向迎合讀者心理的長篇小說,但是不能完全否定故事中作者形而上學式的哲學思考。這種深刻的哲學思考又通過余華獨特的文學風格在《文城》中展現出來。
四、向傳統形式的回歸
《文城》的思想內容依舊具有后現代性。隨著歲月的推移,小說結構的先鋒色彩由20世紀80年代末至今逐漸褪色。閱讀《兄弟》《第七天》《文城》等作品可以發現,小說敘事結構是封閉的,故事情節是豐滿的,20世紀80年代末的《十八歲出門遠行》《鮮血梅花》等作品中,作者追逐小說結構的標新立異而不注重故事情節的完整,對比可知,這兩類作品截然相反。閱讀《十八歲出門遠行》《在細雨中呼喊》等作品可以發現,作者正是以小說的結構表達自己的思想,然而《文城》的封閉結構更像是環形結構的古典小說,仔細交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這體現了21世紀以來余華的文學創作由注重小說形式轉向注重故事內容的變化。
《文城》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文城”,第二部分是“文城補”。“文城補”其實是在補述“文城”部分沒有交代的重要情節,解答讀者心中的疑惑,將故事的原委娓娓道來。盡管余華在創作的三十多年中不停地改變講故事的方法,但是講故事的敘事語調一直沒有改變。《文城》的敘事語調一如既往的冷靜、客觀,不帶有任何主觀感情色彩。
從詞句的形式上讀者可以發現,余華講故事的手法可以歸結為“極簡主義”。不像許多作家用許多細節和心理活動甚至是意識流來描寫人物,余華僅僅用名字來代表一個人物,用人物的對話、行為構成故事的主要內容。不像現當代的蕭紅、沈從文、汪曾祺等許多文體作家使小說散文化,《文城》中的風景描寫未幾,就更不必談及意境、意象的開拓。如同人們對窗外景色的不經意一瞥,余華描寫景物的語言是洗練的,比如“文城”部分最后一段話:“道路旁曾經富裕的村莊如今蕭條凋敝,田地里沒有勞作的人,遠遠看見的是一些老弱的身影;曾經是稻谷、棉花、油菜花茂盛生長的田地,如今雜草叢生一片荒蕪;曾經是清澈見底的河水,如今混濁之后散發出陣陣腥臭。”
洗練的語言將戰后荒村的凄涼景象一筆帶過,整段話仿佛一幅簡筆畫,讀者看不出任何作者的感情色彩。同是寫景,余華是站在故事情節之外描述景色,又使人不禁聯系起宋代詞人姜夔的《揚州慢·淮左名都》:“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夜無聲。念橋邊紅藥,年年知為誰生。”
五、結語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同時期的作品反映了歲月帶給余華創作思想的洗禮與沉淀。2021年3月出版的《文城》講述了一個北洋軍閥末年戰爭年代的凄美民間愛情故事,本文從新歷史主義小說特征、難以言喻的荒誕主題、暴力美學風格和向傳統形式回歸的文本結構四方面分析《文城》的思想主題和藝術價值。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城》的文學價值并沒有超過余華之前的作品。然而,作為成功的大眾文化作品,該作品以豐滿的情節和獨到的敘事風格再次滿足了不同社會階層人群的閱讀興趣。
(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作者簡介:孔捷夫(1989—),男,山東濟南人,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中國語言文學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