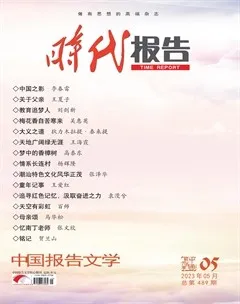關于父親


母親還健在,但父親已逝久矣。
關于父親的那些事兒,一直想記,想寫,想表達。但不敢著筆,懼怕的是兒躺在父親肩膀上的那幅畫被凌亂的筆力給戳碎了。父親于兒子的恩德是叢林著筆、溪水著墨也寫不完的。我寫了好多作品,但關于兒的父親卻是第一次著墨文字。
本市作協主席田永華先生和文聯主席曹其華先生一直催促我寫我的那份鄉愁。我說,我在京華客居太久,在江湖漂泊久矣,我有些麻木了,不想寫。其實,那都是幌子,兒是不想觸動兒對父親深深思念的那管神經。23年前,兒掩埋了父親,兒在父親的墳頭立誓:兒一定要讓父親在九泉含笑,在陰曹地府有用不完的錢糧,這些兒子都似乎做到了。但做為父親的兒子,兒年經時就有一種宏愿,那就是:要為社會的公平、正義而奮斗,直到社會公平、正義。但這一點,兒子沒能做到,兒子自覺沒臉向父親訴說,也就不想寫關于父親的回憶文章。但這一次,文友一再催促我寫我的那份鄉愁,從接到命題作文通知至今,我就不得安生了……
我因此回到我的家鄉,在母親身邊久居數月。有時摸一摸母親的銀發,有時給母親剪一剪指甲,甚至渴望再吮一吮母親的乳汁;有時夜半三更,悄悄爬起走到母親的床頭,看著母親微弱地呼吸著,想著:就是這位94歲高齡的老太在年輕時用她的豐體孕育了自己,用她的甘乳哺育了自己……而這時,就在她的身體里尋找父親的影子。我想:這位老太一定是融合了父親的精髓和魂魄。兒的父親,你的靈魂在哪?你化作了何物?是高山獵豹,還是河里小妖,或許還在虛空浮游……兒的父親,你在哪?寂空冥冥,只有兒子身上奔突著父親的精血在沸騰……兒一次次不能自己,掀開房門,沖上樓頂,而這時,母親似乎從無覺中驚起,“狗兒”“狗兒”地連聲喚起(狗兒是兒的乳名),兒子又從樓頂跑到母親床邊,輕輕地讓母親復歸平靜……
我的出生地是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鎮獅子咀村一組。童年、少年乃至青年時期,那里叫南海區木天河公社青嶺大隊一生產隊。僅從行政區劃的改變就蘊藏著歷史的滄桑。而在鄉人的心里、嘴里,那塊土地就叫“對罵沖”。從洪荒以墾,這個不到兩平方公里的田園內,就住著兩大姓人家,一戶姓趙,一戶姓金,姓趙的擁有一半多的土地,自恃家大。姓金的也不甘示弱,經常為爭水對罵。一條驛道從田疇中穿過,往來路人聽到金趙兩姓的對罵,故而,一傳十,十傳百,“對罵沖”就出了名。我們王姓本支從曾祖一代敗落,便至此“對罵沖”居住,在后山支沖里租著另一戶雷氏小地主的兩間茅屋,佃了雷氏二畝薄地,一直熬過了祖父一輩,四個姑母都是在雷氏茅屋里出嫁。
父親最小,到他成人,就租了趙姓地主的一間瓦房,佃種趙氏地主的一畝多地,并娶了母親楊氏。父親嚴格地講不是莊稼人,而是手藝人,以篾工為生。父親因家貧,爺爺沒讓他上一天學,不識一個字。但父親很聰明,記憶力特別好。他因踩百家門,常常聽到讀書人講故事,什么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桃園三結義,諸葛亮唱空城計,岳飛精忠報國,金兀術敗走黃天蕩……好多好多歷史和戲曲故事,他都能講得脈絡清晰,繪聲繪色。
父親做手藝有三大絕活:一是能打“榨籃子”,這個“榨籃子”可是20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南方貧窮的產物與歷史見證。在鄉村,無數佃農與地主,家家都有。因為糧食嚴重不足,米飯里面必須夾雜大量的菜葉,有時甚至是九成菜一成米。“榨籃子”就是把菜葉的苦汁榨干的一種工具,用竹篾制成。使用時,把底部固定在地面,用力向上拉頂部的環,直到把它拉到半人以上高度,形成巨大的空間,然后把一籮籮的菜葉裝進去,再封頂。兩個壯漢用木杠使勁壓,反復多次,直到把各種野菜的苦汁榨干。夜晚,再放上一塊巨石壓一晚。次日,取出菜葉,半干半濕。需干藏的,將菜葉鋪在地上,一日陽光,可至冬藏。需急用的,則拿進廚房交給廚娘……這樣一種民間使用頻率頗高的竹器,因為需要很好的韌性和很強的張力,對于竹篾的“薄”度與質的“韌”度及編織的細密要求至精至高,一是一般的篾工匠不會做,二是一般的篾工匠不敢做,也做不成器,三是即便能形成器具,可用上一二次,那竹篾、那“筋骨”便斷了破了,就會穿幾個窟隆,菜葉就漏出來了,或壓不嚴實,榨不出苦汁而失去功用。父親在木天河一帶十里八鄉,是唯一能打“榨籃子”的篾工匠。父親是怎樣練就這一手好工藝的,至死父親也不給兒子講,當我好奇地問起父親這門手藝時,父親說:兒子,都過去了,誰還想那個窮啊,不提它,不提它……但愿八百年后也不要再有它,讓它斷種吧。可以說,父親是中國南方“榨籃子”這種竹器具滅種與斷代的最好也是最后的一位工匠,他的內心既有對這種竹器工藝傳承的本能希冀,也有將它藏身歷史的興奮,他的內心也是極其矛盾而苦澀的。他沒有將編制“榨籃子”的絕活傳給他任何一個徒弟,父親一生帶了十三個徒弟,沒有一個會打“榨籃子”,是為證。
父親手藝的第二種絕活是打“貓兒哼”。所謂“貓兒哼”是一種“曬魚”的工具,聽其名便知,把魚裝在籠子里,掛在三叉竹架上,或掛在門前樹杈上,太陽靜靜地曬著,陽光穿透亮篾和漏隙,把熱力直刺在魚上,一只或數只乃至一群虎貓圍著它哼哼直叫,虎貓們看得見魚就在眼前足下,卻怎么也抓不出來,那種吹胡子、瞪眼睛、跳墻爬樹、氣急敗壞的樣子,逗樂得玩童直撒尿泡……打“貓兒哼”的絕活還是有別于打“榨籃子”的。“榨籃子”是沒有筋骨,沒有硬篾,落在地上如一張餅,拉起來如一只巨盆,吞吐量特別大,容積越大,裝的菜葉越多,越見工藝。“貓兒哼”有筋骨,有硬篾,它要對付群貓的爪抓齒咬,它要有大面積的陽光照射,又要有最小的縫隙。父親說,縫隙大了,蚊子、蒼蠅飛進去,就爛了魚身,曬出的魚就有苦味。也就是說,“貓兒哼”甭說貓們不能取出一翅一骨,連蚊子、蒼蠅也甭想樂享腥味。試想,一只蚊蟲都飛不進去的竹籠子,而又要借太陽的光熱把魚肉曬干,可想那竹篾薄到什么程度,那重過二斤的篾刀又是怎樣劃出此等亮篾的?那碩大的粗手又是怎樣細巧地將其編織得連麻蚊都飛不進去的。
父親的第三種絕活是打“蓋籃子”或打“蓋籃子”上面的字。20世紀上溯,女兒婚嫁,必有一種叫“蓋籃子”的陪嫁物,那是伴著女兒終身的。出嫁時裝上滿滿的三升米或一些雜糧,以期婆家再窮,娘家可維持女兒夫妻三天生計(隱喻能保證傳宗接代),當女兒熬成了外婆,便將這“蓋籃子”裝上三升米和油條麻貨之類,提著送“祝米”(暗示為女兒婆家再窮也能讓女兒喝上半月稀粥,保證外甥孫有奶吃),這“蓋籃子”年深月久,呈黃褐色,只有篾蓋上的字粗黑發亮。我見過父親制作這打字的細篾,每匹篾約一尺半長,2.5毫米寬,0.5毫米厚,父親借著黑夜燃燈,有意把燈花撥大,現出濃煙,然后一根根把細篾放在焰火上薰,一節節慢慢薰,直到竹篾把黑煙吸進去,黑碳在竹篾上放出光亮,一根篾大約需要5分鐘才能烤成,在“蓋籃子”上打一個人的名字或“萬代千秋”字樣大約需要50根碳篾。而父親令我欽佩的地方還不是劃篾打籃,而是那篾蓋上的文字,父親不識字,應當不知道文字的結構,但只要讀書人工工整整將名字和吉祥語寫給他,他就能打出標準的字來,這是最不簡單的,他怎么知道這一橫一豎一撇一捺怎么安放得體,對于一個目不識丁的匠人,那是一種工夫的磨礪。雖然對讀書人來說,不值一提。可我的父親那種與生俱來的悟性是常人不及的,或許兒子僅傳承了那么一丁點兒,就有了謀生的本領。在中華民族的演進史上,有魯班一樣的巨匠,那是載入千秋史上的,但中華民族的演進史上,也有如我父親一般的能工巧匠,他們也是應該載入歷史的,而無論如何是不應該消逝的。
父親的本名叫王澤斌,乳名“和尚”,民國十四年(1923年)七月初十生人,篾工匠,終生布藝于木天河一帶十里八鄉。父親身高1.72左右,不胖不瘦,筋骨強壯,臉圓形,晚年有輪廓,大鼻,濃眉,大耳墜,大眼睛,亮額頭。父親一輩子上工時,不穿鞋,赤足而行,總是把布鞋、棉鞋、球鞋夾在腋下,到了工地(農戶家)再穿上。父親說,穿鞋走路會把鞋磨破……這種儉行時刻鞭笞著兒子的奢侈無度。兒每每放浪,父親如臨,雖慈祥和藹,無斥責之言,但崇高的道德之山還是仿佛壓了過來,讓兒警醒,以至花山錢海,兒不墮崖,兒不溺亡。父親的勤善功德,蔭庇了兒這一生一世……兒在與父親的35年的交集中,最深記憶的是仿佛永遠躺在父親的肩膀上。父親背著14歲的兒子去上工,那一顛一簸中,兒便在父親的肩膀上睡著了。有一次,月黑風高,父親背著兒子到趙家坡一袁姓家偷偷地買糧食(一段時間政府禁止糧食私人買賣),父親背著兒,胸前抱著50斤谷子,道路泥濘,山高路滑,一失足,父親甩了糧食,救護了兒。兒說讓兒自己走,父親不干,堅持把谷子擁在前面,讓兒躺在他那碩大的肩頭上……冬天,父親總是把兒擁在他胸前暖和;夏天,父親總是在竹床上給兒打扇驅熱趕蚊,讓兒沐日月精華、山川風露,呵護著兒慢慢長成……
今天,兒也年邁,父親逝世23年了,恰是這23年,兒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與發展。兒不再羸弱,脊骨和胸骨不再嶙峋,這是父親常常用手撫摸和最擔心的,問兒:什么時候才能長壯一些、長厚一些?今天兒長壯了,長厚了;父親最擔心兒在單位與領導遭遇矛盾,兒在1997年停薪留職離崗,兒單位的領導,那些懼才的領導都走下了領導崗位,淹沒在平凡中了;父親最擔心兒的妻兒,那朱氏早已隨人去了,孫子還行,仁慈如您,慧心如兒,想必自會成才;那早年兒離婚時判歸王氏監護的孫女,因兒的努力,將其送往大西洋外,在曼哈頓求學后謀得一職,年薪頗豐,父女關系還行;兒又娶了媳婦郭氏,賢慧萬婦莫及,伴兒南下北漂,已苦盡甘來。兒還建造了“王府”,巍峨華貴,供奉著您的老伴兒的母親,供其錦衣玉食,使女有之。自您離世,23年里,兒一時一刻也未忘卻您對兒的希望與叮囑:做正派人,不坑人,不害人,做忠厚人,不貪意外之財。23年里,與兒同時生發的好多物事都已消亡或正在消亡,滄海桑田,世事沉浮,而兒卻愈風光,愈精彩……
兒是在父親的肩膀上度過了冥頑的童年,也是在父親的目送中趟出了青嶺山鄉,兒是在父親的希冀中走向了天南地北……兒是父親心中綻放的花蕾,理想中放飛的鷹鷂,是父親在冥府中寄望守護王氏家族前行不敗的家丁……兒是父親做人一世的生命延續,融入萬千世界,構成人類生生不息的漢民族之種族繁衍。做為父親的兒子,或者說作為兒子的父親,兒精彩紛呈,沒有羞赧。而這一世,兒鄉音未改,童心未泯,正派不已,都源自于父親對兒的遺傳與教誨,比較起父親,無論兒的文化有多高,和父親比都如滄海一粟。因為在兒的心目中,父親就是一座巍峨不可攀頂的大山,那基于平凡的偉大,兒身上缺失了。父親那人性中的慈善與博愛,愈是經過教化點綴就愈易消失的東西,在兒身上所存無幾。如此綿延,王氏的子孫還是父親的子孫嗎?
我的鄉愁,除了以“思念父親”為最神圣的鄉愁,其余可以淡定從容。至于母親,她是和父親結伴而行的活著的歷史人物,早年在《母親》一文中已表述至深,業已收入梁曉聲先生主編的《中國百位文化名人寫母親》一書,供大眾閱讀,傳播甚廣。也許是母親尚且健在的緣故,母親乳汁的原香沒有比兒躺在父親肩膀上的睡香更馨更濃,即使母親乳汁的原香是兒躺在父親肩膀上的酣睡之本,那種回味仍然沒有兒對躺在父親肩膀上沉睡而獲得的體香與思念更濃更澀……
兒平生思念不已的父親,兒終究會躺在您的身旁。而下一輩子,再下下輩子,兒愿在您的胯下重生,做您永世永代的孝兒。此心為誠,天公可見,昭昭赤子,托起你生命的光榮。
鄉人曰:王篾匠后繼有人。而僅此一句,是對冥冥中的父親最踏實的安慰。
我想,父親定會抿唇而笑,含笑九泉的……
作者簡介:
王夏子,男,1956年出生于湖北省松滋市木天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名作家。曾任《中國作家》雜志編務總監;現任《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雜志常務副社長。發表小說、散文、報告文學、文學評論逾500萬字。
責任編輯/孫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