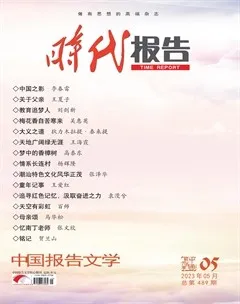天道


一
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后,中國工農紅軍經歷了一段迷茫的日子。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軍隊的領導地位后,紅軍一改撤離蘇區以來消極避戰、被動挨打的局面,在川、滇、黔邊地區穿插于敵人重兵之間,先后取得遵義戰役、四渡赤水的勝利,繳獲了大批軍用物資,取得了長征以來的最大勝利,士氣大振。
國民黨派遣大量部隊圍追堵截。為擺脫追兵,更好實現戰略轉移,紅軍四渡赤水之后,又“調虎離山”,才實現了紅軍佯攻貴陽,分兵黔東,調出滇軍,西進云南的“聲東擊西”目標。
元代新開辟一條連接湖廣,經貴州至云南、東南亞、南亞的一條官道及其支線,全長近三千里,涵蓋了云貴高原大部分地區,學界稱為“苗疆走廊”。清水江(黔南貴定段稱獨木河)渡口曾是古代官道上一處重要的軍事關口,稱清江關,俗稱清江坳,是東西古驛道西去貴陽的一個重要渡口。
為制造中央紅軍東進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假象,達到誘敵的目的。中央紅軍假戲真做,佯攻息烽,主力進至扎佐,前鋒直達貴陽城郊烏當白泥(百宜),威逼貴陽。一路則放棄由清鎮衛城、貴陽一線西進的部署,改向東南運動。紅一軍團則進至龍里縣老巴鄉、洗馬河,渡過開陽縣腳渡河到羊場、高寨、狗場壩(今久長)一帶,再渡清水江,往平越縣(今福泉市)方向運動。這個大手筆完全迷惑了蔣介石,蔣介石認為紅軍會往東運動和二、六軍團會合,電命大軍趕往黔東。
1935年4月2日上午,紅一軍團二師六團經開陽底窩壩,挺進到羊場龍崗鎮、杠寨、高寨、平寨一帶待命。偵查員聯系上向導以后,團長朱水秋和政委王集成即刻帶領200多名紅軍戰士,快速趕到清水江谷汪深新渡口西岸,大張旗鼓地開架浮橋,天上敵偵察機隨即尾隨而至。
時值中午,艷陽高照。朱水秋望著奔流而去的清水江水,抬頭仰望敵人偵察機,想起強渡湘江時戰友鮮血染紅湘江的慘痛情景,不禁潸然落淚。然而時間才過去幾個月,局勢接連發生絕對逆轉,朱團長望著天上張狂的“飛鳥”,譏笑道:蔣軍兄弟,看清楚點啊!看清楚了好給老蔣匯報。
嗡嗡聲由遠而近,“飛鳥”在天上飛來飛去,朱團長命令戰士們把動靜再弄大一點。戰士們即刻把老鄉支援的大木桌子排列起來,用粗大的棕繩串起來放入江中,再把兩端拉緊固定在大樹樁上,桌面上鋪上木板,砰砰之聲不絕于耳。3個多小時以后,一座長約30米、寬約1米、簡單、輕便的浮橋架起來了。
18時左右,大隊紅軍腳踏浮橋,浩浩蕩蕩地跨過清水江,進入谷汪深村,急速向江邊和大谷賓挺進。這時天已黑盡,敵人偵察機仍然盤旋在紅軍的頭頂。紅軍指揮員生怕偵察機看不清楚,又在新渡口通往谷汪深的山路上燃起篝火,戰士們把火把舉得高高的,有意暴露目標,引誘敵機上當。為讓敵人確信無疑,又于4月6日派出一個營在開陽、龍里和平越三縣交界的清水江兩岔河牛渡架設浮橋,再造聲勢,敵偵察機看得真切,信以為真,掉轉頭向他們上級報告去了。
蔣介石得知紅軍西進貴州后,坐臥不安,于1935年3月24日,帶著夫人宋美齡以及親信智囊們乘專機飛抵貴陽,督剿紅軍,坐鎮毛公館。毛公館是貴陽民國時期的四大建筑之一,是典型的中西合璧式洋樓。青磚灰瓦,寬走廊深屋檐,大圓拱門,鑲五彩玻璃窗,木質扶手和地板,非常舒適,但蔣公卻如坐針氈,夜夜驚魂,難以成眠,在得知飛機偵察的報告后,他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其實蔣總統心里很清楚,國軍一路剿來都沒有把紅軍消滅,反而越剿越壯大。貴州圍剿,成敗如何,難以預料。盡管希望渺茫,他還是命滇軍速進貴定、龍里,企圖在馬場坪到黔東南之間,擺一道攔截防線,然而還是被紅軍擺了一道,撲了個大空。
二
且說紅一軍團完成“聲東”任務后,突然調頭南下,進入貴定縣新巴,再往龍里觀音山至谷腳,通過湘黔公路,跳出了敵軍包圍圈。至此,中央紅軍實現了佯裝東渡、實施西進的戰略轉移。新巴地處貴定縣北部,民國三年(1914年)屬貴定縣第九區,乃區署所在地,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屬第六區,交通便利,四通八達,東西古驛道橫穿其間,北上南下,東進西出,均可自由來去。由于鄉腳寬,新巴是一個集市貿易重鎮,物品豐富,商賈活躍,很早就有客棧、飯店、酒肆,市場十分繁榮。上貴陽、下黔東的馬幫都在這里打幺站,人口流動大,馬廄業十分發達。
1935年4月,中央紅軍左路大軍到達新巴,紅軍先頭部隊到達谷兵時,偌大一個寨子,竟然成為空心村。面對如此窘境,紅軍指揮員意識到群眾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即刻下令部隊野外休息,免驚百姓,同時發動政治攻勢,派出有經驗的政工人員進村了解情況,放手宣傳發動群眾,消除老百姓的心理障礙。但由于谷兵群眾平時聽反動宣傳多了,見到紅軍就躲,一時難以溝通。
進退維谷之際,一個穿著靛青短衣的中年人,牽著馬從松毛林里走來,邊走邊唱:紅軍哥呀紅軍哥,不怕涉水和爬坡。打富救貧為乾人,馬幫將過好生活。政工人員聽到歌聲,判斷此人對紅軍了解,便主動搭訕。趕馬哥發現搭訕人頭上的紅五星那是紅軍的標志,驚異道:你們是紅軍嘎!怎么不進寨呀!布依族熱情得很呢!我們有紀律,不能叨擾老鄉的,紅軍戰士說。咦!趕馬哥錯愕。這時過來一個紅軍干部,微笑著問他:寨子里的人躲起來他為何不躲。趕馬哥幽默地說:他們怕你們,我不怕。說完開懷大笑,把紅軍們給逗樂了。
說話間,紅軍干部看到不遠處的人家炊煙裊裊,望山錢經風一吹,飛曳起來,像翩翩欲飛的風箏。紅軍干部問:趕馬哥那家人在做什么。趕馬哥說:老人死了,在辦喪事。啊!老人過世,死者為大,紅軍干部說,我們尊重地方風俗,不能打擾人家。趕馬哥說:死的人姓羅,是他姨父,沒關系的。紅軍干部說:不可以,不能壞了風俗。
此時正是農村吃晌午飯的時候,院壩中央擺了桌凳,菜已經上了,只是很簡單,一缽南瓜湯,一碗清炒紅蘿卜,一碗回鍋肉,一碗酸菜豆米。平時是難得吃到豬肉的,因為是白喜事,羅家再窮也得有幾片肉打發幫忙的。
四月的冷風呼呼地吹,大甄子苞谷飯,眼看就冷了,幫忙的人還沒有坐攏來,主人家十分焦急。紅軍從羅家門前小路大踏步前進,飯香撲鼻,戰士們吞咽著口水,可他們連看都不看一眼,一路絕塵而去。
慘慘淡淡的太陽被云紗纏繞著,像泡在米湯里的白雞蛋。紅軍離開谷兵寨,幫忙的村民陸續鉆出洞窟,走出山林,聚攏羅家。羅家人感慨地說:紅軍不擾民,連擺在露天壩的飯菜都不動一筷,真是天下的好軍隊啊!要是遇上國民黨軍,哪還有飯菜給大伙吃,早被黃狗子消滅了。
人死飯甄開。農村一有白喜事,全寨人都來幫忙,吃“大鍋飯”。主人家不會嫌棄,圖個吉利和熱鬧。總管來催干活,見他們仍在嘰嘰喳喳,催他們快吃,吃完該干啥干啥去。寨佬陳朝齊披著破棉衣走過來,寨佬是一寨最有威信的人,總結式地說:大家說半天都沒說在點子上,我們谷兵人最大的悲哀是聽信了反動謠言,不辨是非,怠慢紅軍兄弟。他們不進孝家門,不拿孝家的東西。這樣的軍隊,下次遇到,一定要請進寨子來,用最好的米酒招待他們。
紅軍先頭部隊沒在谷兵休息,留下了宣傳標語,打開民心之門。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們訪問耄耋老人陳廣亭時,他說布依族本來就是好客民族,紅軍是貴人,貴人來了要敬酒的,不但酒沒敬成,反倒把紅軍拒之門外,不是布依族的待客之道。十多年以后,紅軍改編成解放軍,解放軍土改工作隊進駐新巴,新巴人民敲鑼打鼓迎接他們。老人把沒有唱給紅軍的山歌唱給了解放軍:客從遠方遠路來,布依鄉親樂開懷,客你要是不嫌棄,喝杯米酒表心懷。
三
清水江日夜流淌著,寂寥平靜的日子猶如粗茶淡飯。1936年1月,紅二、六軍團分路進入平越縣,再次打破山川溝壑的寧靜。
紅2軍團以一個團兵力南下馬場坪,阻擊來敵,主力擊潰縣城守軍后,經巴巴箐進入仙橋。紅6軍團自牛場走云頂進入巴巴箐。會師仙橋后,首長觀察地形,當機立斷下達命令搭浮橋!
搭浮橋先得解決材料問題,江水滔滔,兩岸空曠,唯有河邊的破廟門庭冷落,紅軍只好拆了破廟,拆下來的木頭、椽皮、枋子、行挑,用作搭橋材料,又就近砍了一些樹木,才混合搭成一座簡易浮橋,然橋面太窄,影響行軍速度。戰士們又在清水江渡口附近村寨向老百姓借了一些桌椅、門板、木板、木料,砍了一些原木,搭建了另一座浮橋。
1936年1月28日,大部隊跨過浮橋。敵人追兵到來時,紅軍早已不知去向,只好望江興嘆。
新年初三,紅二、六軍團途經谷兵,鄉親們認識五角星和領章,他們把自家最好吃的東西拿出來送給紅軍,紅軍說不能拿群眾一針一線。鄉親們也有理由,說:紅軍是人民軍隊,人民送給自己的軍隊,有什么不可以?盛情猶如暖流流進紅軍戰士的心田。
紅軍戰士的腳被草鞋磨出水泡,布依族人們用繡花針燒紅給他們挑破,又用自制的特效藥敷上。新巴紫皮大蒜有消毒功效,為了使紅軍能健康行軍,他們自發地把大蒜送給紅軍。有些人家還把自己舍不得吃的小米、核桃拿出來送給紅軍。紅軍給他們錢,他們不要,紅軍就送一些可用的物件給他們。有的送漱口缸,有的送瓷盆。有個戰士為了感激大土陳姓老人接待他們,送他一口銅鍋。陳姓老人一高興,順口編一首布依山歌唱給紅軍:紅軍哥喲紅軍哥,長征你來我家坐。我家住的茅草房,你送一口銅小鍋。
中央紅軍到黃土寨那天正好清明節,陳燦衡說他在打清明粑。紅軍進寨子,他以為是土匪,拔腿就跑,跑了一段路,沒看到后面有追兵,他就停下腳步遠遠偷看,看到有紅軍幫他打粑粑。放哨的紅軍喊他不要怕,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會打擾他的,他就轉回了寨子。清明粑打好后,他拽了一坨遞給紅軍戰士,紅軍戰士堅決不要,陳燦衡強行揣在了他的兜里。戰士不好推辭,就把隨身帶的一支煙斗給了陳燦衡,以示交換。并說煙斗是他班長的,班長犧牲時送給他作紀念。陳燦衡感動得差點淌眼淚。
四
新巴是布依族聚居地,紅軍在這里開展革命活動時,留下許多民間傳頌的故事。
陳朝海是甘塘寨人。大年剛過,他就聽說紅軍要打福泉縣城,生怕紅軍到新巴自己遭殃,一直憂心忡忡。初三晚上,夜色朦朧,甘塘寨很靜,一只貓從房擋頭跑過時,把陳朝海從睡夢中驚醒。醒來后就聽見噼里啪啦的聲響,他以為是哪家大年放早炮仗。可仔細一聽,是槍聲。槍聲劃破天際,從河的那面傳到河的這面。
大冷天他該睡個懶覺的,對門河動靜太大了,攪得他無法安眠。彎月沉下去的時候,槍聲停了,然殘兵敗將的暴行就要開始了。他木然地望著昏暗的天宆,嘴里念念有詞,祈禱天亮后是一個平靜的白天。
剛祈禱完畢,青崗老方向又傳來突突突的槍聲。槍聲沉悶,像炒黃豆一樣啵啵啵地響。緊接著有保安團的人從山腳跑過來,他們是羅善之的保安兵,都是一伙好吃懶做的地痞流氓和無賴。說起來是村民養活他們,他們應該保境安民,可這些家伙不干正事,專門欺壓鄉鄰,禍害同胞,鄉親們敢怒不敢言。陳朝海看到他們往寨子里走來,心里倒抽一口涼氣,心想這回完了。
那伙人走到他家門口,靠著圍墻抽煙,嘴里說著粗話。有個吊著手臂的團丁說:羅團總說紅軍沒有重武器。他咂一口卷煙,煙霧混合進灰色中,又向地上呸一口,說:“卵子!盡他媽忽悠我們。老子連人都沒看清楚,子彈就像下冰雹一樣漫過來了,打得樹葉簌簌落地,穿透好幾棵青杠樹。要不是老子跑得快呀,早命喪黃泉了。”拄著槍走路的團丁接著他的話說:“我說搞不得,他非說上邊有命令,不堵不行。結果咋樣,被老子說中了吧,槍一響他比兔子跑得還快,拿老子當替死鬼。”團丁們你一言我一語地說:媽的,守一夜就守得這樣一個結果。以后吃槍子兒的事他自個兒吃去,老子可不奉陪。大不了,撂下這棵燒火棍!
團丁們罵罵咧咧地走遠了,陳朝海心頭的石頭暫時落了地。可一聽到“紅軍”二字,心里不覺又是一激靈。這些年他聽得多了,就是從來沒見過紅軍長什么樣,共產黨長什么樣,他還真想認識一下他們。準備反身進屋,隔壁家的黃狗突然狂吠起來,嚇了他一跳。他不由得罵一句,畜生!
狗吠聲越來越急促,又跳又吼。往常狗們不會叫得這樣兇的,今日狂吠不止,肯定嗅到什么異味了。不一會兒,他聽到唰唰唰的腳步聲,由遠而近,黃狗愈發叫得狂暴了,像要跳出圍墻的樣子,被他喝住了。一狗引來百狗聲,寨子里的狗跟著叫,一時間整個寨子像狗吵架一樣。
他踮著腳往圍墻外看,一支隊伍奔寨子而來,狗們吠得更歡了。他不自覺地摸了摸門閂,看閂好沒有。忽然又覺得多余,心想,如果他們真想進門,這薄門是擋不住的,一腳就能踢開,閂和不閂一個樣。
紅軍?他腦際劃過這個念頭的時候并沒有慌亂,他拉了拉肩頭的破棉襖,轉身進了屋。他不想讓他們看到自己,可又忍不住透過窗欞方孔朝他們看。隊伍走近寨子并沒進寨,而是在離寨門口兩丈遠的地方停了下來,領頭的在講話,隔得不遠,夜間又靜,說話聲清晰可聽。領頭講的是外鄉話,后來換了個人,瘦削,高個,講官話,他讀過幾天私塾,聽得懂官話。
彎月很快躲起來了,夜色如攪拌的灰漿,稠糊糊的一團。他側耳細聽,聲音清晰得像是在屋檐下對著他說的。高個說他們是人民的隊伍,要保持寨民的安寧。告誡戰士們,宿營的是布依族寨子,民族工作很重要,絕不能擾民。最后用低沉的聲音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記住了嗎?
記住了!
他一顆懸著的心算是放下了。
部隊三三兩兩散去,找了一些適當的地方躺下了,有些戰士干脆睡在老井邊的古樹下。陳朝海忽然覺得這些人像走親訪友的寨鄰和朋友,不但可親而且可敬。他叔伯哥陳朝亮屋檐腳睡了一些戰士。陳朝亮醫術精湛,是甘塘寨不可或缺的郎中。
狗吠聲停了,黑夜恢復了原狀,甘塘寨突然間像睡著一樣。他覺得有點失落,心緒亂亂的。剛想回屋躺會兒,就聽得門外有腳步聲。他猶豫著開不開門的時候,腳步聲從院墻邊過去了。他冷靜下來,心里覺得過意不去,悄悄地打開一條門縫偷窺,門外闃寂無聲。他又悔又恨,心想,如果他們是好人,戰士們凍病了,豈不是我罪過?可事情已無法挽回,他很頹喪。忽然感到疲乏,想睡個回籠覺,就鉆進了被窩,可怎么也睡不著,那些兵們究竟去哪里了?
五
睡不著躺著難受,天剛蒙蒙亮,陳朝海起來了。老習慣,他清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喂牛。一年到頭為他賣命的牛,是一條上年紀的老牛,他得對它好點。老牛聽著他的腳步,親切地打著響鼻,還沒走近牛圈,就被牛圈邊的一幕驚呆了。
沒有太陽,頭天下的雪被霧靄籠罩著,屋檐吊著冰柱。牛圈背風地方有塊干燥地,地上睡著十多個士兵。兵們闔衣或躺或靠,雙手筒在袖子里。側躺著,蜷縮身子,像彎曲一團的毛毛蟲。牛圈相隔正房十多米遠,住房要避開臭氣,牛圈一般都安排在正房擋頭。戰士們衣衫不一,色道各異,睡著的姿勢也不一樣,鼾聲輕微。
睡這兒?陳朝海驚訝之余,嚇得倒退一步,踩到屋檐下的鋤頭,一個大趔趄。他定了定神,索性站著不動,他不想吵醒他們。看著面前這些疲憊不堪的軍人,陳朝海心里忽然有了隱痛,早知這樣,不如讓他們進屋里休息呢,無論睡哪里,也比這外面強呀!
有個紅軍警惕地坐了起來,見是房東老鄉,揉揉惺忪的睡眼,歉意地說:老鄉,叨擾您了!他怔了一下,沒答話。那人倏地站起來,清瘦的臉頰有谷草印。對,他就是昨晚那個站在石墩上講話的人。不,不!陳朝海一時慌亂,說話不成句:“你,你們咋睡這里?這可是雪天呀!”
那人胡子拉碴,面色蠟黃,斜挎駁殼槍,領口綴著的紅布條已經褪色了,帽子上的紅五星也失去鮮艷。他主動自我介紹,說是紅軍先遣連尖刀排排長。陳朝海不知道尖刀排,木愣愣地傻笑。當他的手被對方捉住的時候,他感覺那只手有很厚的老繭,比他的還厚。“可是莊稼人?”他問。“人民子弟兵嘛,當然是莊稼人。”排長笑答。他仿佛一下子有好多話要說,卻又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像啞巴一樣,打著手勢,“冷不冷?”
“冷,比起睡山坡,暖和多了。”排長說。
“你們真是紅軍?”
“真是紅軍。”
陳朝海牽著他進了屋,請他坐在火籠坎邊的凳子上,將火鉗撥開蕹著的炭火,茶罐就墩在火邊,他準備給他熱茶。排長叫他別忙了,他們馬上就出發了。
陳朝海說不急不急,茶熱了喝一碗再走。排長朝外看看天色,說:沒時間了老鄉,謝謝!排長趁機給他講了一些革命道理,他理解不了,什么“革命”啦,“共產黨”啦,天外來客般陌生,他只覺得這些詞與改變命運有關。聊了十多分鐘,排長說該整理內務了,就朝戰士們輕喚一聲,集合!戰士們齊刷刷地站成一排,精神抖擻的樣子好威風。
排長又下命令,把谷草收拾干凈,恢復原狀。一班挑水,二班劈柴,三班打掃衛生。戰士們七手八腳忙起來,陳朝海阻止,可沒人聽他的。
他第一次見到這樣的軍隊,竟發自內心哼起了自編的山歌,他久已不唱山歌了,今兒個不知咋的,那幾句歌詞順口就出來了:紅軍貴客來我鄉,甘塘到處喜洋洋。挑水劈柴搶著做,軍民友誼萬年長。
隊伍開拔,他像丟了什么東西一樣,心里空落落的。忽然看到排長腰間插一桿煙袋,就給他摘了一把葉子煙。排長堅決不收。他急,硬往他懷里揣。排長把口袋捂得死死的。陳朝海不禁感嘆,這樣的隊伍不打勝仗才怪呢!部隊走了,家寂靜起來。陳朝海站在路邊,目送遠去的隊伍,忽然有了失落感。
“老鄉”,背后傳來問話聲,“請問這是甘塘寨嗎?”“是。”陳朝海一看又是紅五星,紅軍戰士個個扎著綁腿,穿著草鞋,也有穿布鞋的,不過腳趾已經露出來了,像一雙窺探的眼睛。問話軍人見他爽快,突然問,老鄉,我們有個小同志受傷了,借住你家可以嗎?
“可以“可以。陳朝海答應干脆,他不想再失去表現的機會。他邀他進屋,說:不要再住外面了,貴州天氣冷得很。軍人說:他們還是住外面,小傷員傷重,屋里給個地方就行。擔架抬過來了,小傷員翻下擔架,想站起來卻倒了下去,令人心疼。小傷員名叫唐炎純,1919年生于湖南石門縣,紅二軍團四師十二團戰士。唐炎純說話還沒完全變聲,帶有濃濃的少年味兒。陳朝海很震撼。小傷員一瘸一拐進了屋,他才悄聲問他多大年紀。小傷員說17歲。
昏暗的月光褪去,天開始放亮了。陳朝海放不下小戰士,一直關注著他房間的動靜。忽聽一聲嫩嫩的聲音從屋里躥出來:“班長,我能走!班長,別丟下我!”聲音凄凄的,嚇了他一跳。
這間屋原本是他日常睡覺的地方,為騰出來給小戰士養傷,他只好睡樓板。白天他發現小戰士發冷,身體一直顫抖,他給他加蓋了一床秧被,加蓋秧被也無濟于事,唐炎純一直高燒不退說著胡話。
他輕推門扉,想一探究竟,只見小戰士側睡著,小戰士說的是夢話。
集合!一個背著駁殼槍的干部喊著口令:“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稍息。”
部隊就要出發了,喊口令的軍人站在石坎上,嚴肅地對戰士們說:“同志們,唐炎純同志傷勢太重,不能隨大部隊行軍了,我們給他敬個軍禮吧!”唐炎純拖著傷腿奔出門來,哀求他:“連長,我能走,不會拖累戰友們的。”
戰士們哽咽著請求連長帶他走,說哪怕背也要把他背到目的地。連長強忍淚水,說:“唐炎純同志留在老鄉家養傷,這是黨組織的決定,我相信他會像火種一樣發揮作用的。唐炎純說:“連長……”連長打斷他:“服從命令!”又見他的腿腫得粗大,眼睛一下潮濕起來,但他盡力地掩飾悲傷,故作瀟灑地說:“我命令你早日康復!”
天已大亮,連長把陳朝海拉到僻靜處,悄聲說:老鄉,他的傷不能再等了,拜托找個郎中診治吧!他從懷里摸出兩塊大洋遞給陳朝海,囑咐他一定要治好他的傷。
后來陳朝海聽到風聲,說團丁要來他家抓人,他就把唐炎純藏在朝天洞里。朝天洞陰濕,對有傷的人來說,無異雪上加霜,藏了十多天。傷口大面積潰爛,土郎中的藥也不管火了。兩兄弟想了許多辦法,就是沒有效果。二月中旬的某天,唐炎純病情惡化,處于昏迷狀態。傍晚時分,忽然回光返照,遞給陳朝海一枚紅布剪成的五角星,流著淚對他說:“哥,承蒙照顧這么多天,我沒什么報答你的,這枚五角星是我參軍時連長親自給我的,送你做個紀念吧!你們的恩情,只等來世報了,說完就閉上了眼睛。”
據查證,湖南籍的紅軍戰士在貴定縣犧牲的一共9位。當時不敢說埋的是紅軍,隨意蕹一些泥巴,壘個小墳頭。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當地老百姓自發地重新給他們包了墳,擴大了墳的范圍。他們的真名當時也沒人知道,但“紅軍”這個光榮稱謂是抹不掉的。她像一面紅色的旗幟,引領著新巴人民向著美好的生活奮斗。每逢清明,機關干部、青年學生、普通百姓都要為他們添一抷黃土,獻一束鮮花。誰說烈士只是碑,他們的名字永遠刻在人民的心碑上。
六
一個在黃土寨游玩的客人,在讀了陳斗賢寫給爺爺的家書之后,深情寫道:“我對您的思念,溢于家書之外。雖不曾見過您,雖不知您的名……可我們時常相見在夢里。只是哪一個是你,哪一個是他,哪一個是親人?”
一封普通家書,能使游人如此感動,這封家書一定是蘸著眼淚寫成的,是一個親人對另一個親人的渴望和期盼。
貴定縣新巴鎮,青山郁郁,紫蒜彌香。紅色基因在這里發芽、生長,紅色文化在這里熠熠生輝。新巴鎮的紅軍墓,埋葬著當年“投身革命即為家,血灑異鄉為祖國”的英烈。熱血不知流何處,永不知名踐春秋。我們只能用無名來代替他們的信仰。這些未名烈士其實早已銘在民心。他們的青春一如星辰,高遠而閃亮。他們用未名傳遞光明,他們用未名堅守信仰,他們用未名傳遞使命。
“敬愛的爺爺:您離開黃土寨已經整整86年了,大山隔開了您和祖母、父親的聯系,卻加深了我們的思念。父親在世時,常聽他提起您的故事,在那個歲月動蕩的年代,祖母和父親想方設法尋找過您,但是都杳無音訊。在您離開的第二年,祖母去世了,彌留之際還念著您的名字。父親吃著百家飯長大,后來成家立業、生兒育女。
父親時常教誨后輩,我們能有安穩的今天,是用無數革命先輩的鮮血換來的。他也曾驕傲地告訴我:他為有您這樣的父親感到非常光榮。現在,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安定富裕,家家戶戶都能吃飽飯穿暖衣,我們家還蓋上兩層的新房子。您留下的老房還在,算是留個念想,我打算還要在上面放一顆閃閃的紅星,讓后人謹記我們是革命先烈的后代,把紅軍長征精神傳承下去……”
全文錄下的這封家書,是一個紅軍后人埋藏在心底的對失蹤親人的深切思念。他叫陳斗賢,紅軍陳燦坤的孫子。他在57歲那年清明,提筆寫下了對爺爺的思念,行間字里,傾注著對爺爺的崇敬和悼念之情,讀來宛如一抹陽光乍現,令人激動萬分。那段歷史像滾滾而來的潮水,把陳斗賢給淹沒了。那是一個細雨紛紛的日子,紅軍戰士們披著蓑衣,戴著竹笠,從大土翻山進入黃土寨,一路風塵,顯得極為疲憊。疲憊的身影在訪貧問苦中穿梭,人民懂得了革命道理。躲避的鄉親安心回了家。他們幫鄉親們打掃衛生,打柴挑水,鄉親們則做好飯,把好吃的東西送到他們駐地。軍愛民,民擁軍,壯觀的場面感染著青年陳燦坤,他決定自告奮勇地為紅軍帶路,結果他成了紅軍。
陳燦坤走時匆忙,沒來得及知會家里。妻子陳羅氏四處打聽他的下落,牽著年幼的兒子一路乞討一路追。追到龍里時已精疲力盡,丈夫不知往何方,真可謂:“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
七
四月的風是熱的,四月的太陽是溫暖的,布依族人開始了一年一度的農作。突然,紅軍吹響集結號,指戰員們爭著為老鄉打掃院子,挑滿水缸,準備著臨行的告別。鄉親們一聽軍號響,預感親人要遠離,紛紛從田間地頭奔回寨里,他們要送親人一程。
紅軍宿營于新巴36個村寨,和當地百姓結下了深情厚誼,共同耕耘著幸福的日子。舍不得啊!山歌仿佛火鳥的深情挽留:紅軍今早離寨門,滿寨相送好傷心。哪歇再得紅軍轉,滿酒膾肉接你們。
陳燦衡的歌聲,仿佛一束暗香茉莉,頓時香飄在紅軍心頭。他一生愛唱山歌,見花唱花,見鳥唱鳥,見人唱人,隨唱隨有,隨有隨唱,像清水江的水長流不斷。他唱一輩子山歌,沒有此時唱出來的歌有氣勢有力度有內涵。
他握著排長的手,排長說:要是能一道走,那是多好的事呀!他歉意地笑笑,想唱一首歉意歌。正值鄉親端著酒碗,請紅軍喝壯行酒,陳燦衡奪過他們手中的酒碗,一碗遞給排長,一碗留給自己,唱道:紅軍今天要啟程,乾人相送不落心。水酒一碗表心意,哪歇轉來幫乾人?酒干情濃,陳燦衡終于滾出一滴熱淚,歌聲蘸著眼淚,從他喉嚨里顫抖地發出。兄弟!排長緊緊地擁抱著他,說: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大部隊昂首闊步往前走了。陳燦衡望著漸漸遠去的背影,落淚唱道:紅軍乾人心連心,今天開拔要啟程。心頭難過淌眼淚,曉得哪歇轉回程?
此時的尖坡又是另一番情景。
一位尖坡大嫂挽著紅軍軍醫的手臂,戀戀不舍。大嫂的夫君一個月前被土匪打死在大麻窩,無比悲傷,是紅軍軍醫開導她,說:人死不能復生,要堅強。土匪造孽,這個賬要算在國民黨身上,只有徹底打倒國民黨,窮人才能翻身。她像吃了靈丹妙藥,頓時心情好了許多。接下來的時間,她帶著紅軍妹妹走遍整個村寨,認識村子里的窮婦女。紅軍妹妹的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她生銹的鎖芯。紅軍妹妹出發了,她深情唱道:紅軍妹妹慢慢走,姐送妹妹到路口。妹去何時才能歸,一碗酒水送到頭。時間太短,妹妹說走就走了,如果不是拖著嫩娃崽,她也會和妹妹一樣去革命,心中無形中有了牽掛:紅軍妹妹要遠征,姐我今天像丟魂。此去不知何時轉,姐妹同是一胞親。
紅軍妹妹聽罷,甚是內心激蕩。她聽老鄉說,新巴大蒜能治病,拿來試了一下,果然對一些輕傷有療效,于是靈感一來,和了她一首:布依姐姐情意長,紫皮大蒜醫我傷。地方太多難記住,我叫紫皮大蒜鄉。
山歌此起彼伏,這是水乳交融之情,這是患難知己的蛩音。戰士們感激老鄉的熱情和幫助,唱了一首回謝歌:紅軍革命走四方,冒雨頂風打豺狼。掛彩傷口缺了藥,紫皮大蒜洗膿瘡。
山歌越唱越想唱,紅軍越遠情越濃。這一場難得的送別,是新巴歷史上一次大送別,以后再也沒有過。新巴人民的斗志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念念不忘此次送別的情景。新巴解放后,解放軍來到新巴,幫助新巴搞土地改革。原來的紅軍已經改編成中國人民解放軍,他們用歌聲再次唱出心聲:桂花生在桂石崖,桂花要等貴人來,桂花要等貴客到,貴客來到花才開。
時光蹉跎,青春也揉碎了歲月。紅軍筑牢軍民友誼,譜寫一曲民族團結之歌,留下民族共融、軍民團結的寶貴遺產。革命活動早已沉入歷史,但他們經歷的點點滴滴,依然甜潤著現代人的心,永遠活躍在人們的記憶里。“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精神是民族之魂,永遠是鮮艷的紅色。進入新時代后,共產黨人依然堅守長征精神,踐行宗旨,初心未改,為民謀福。
進入二十一世紀,中國工農紅軍用鮮血澆灌的祖國大地,早已春風習習,鮮花盛開。昔日紅軍搭浮橋的清水江,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貴黃高速公路開通,貴陽到新巴,只需40分鐘,新巴達仙橋,只要6分鐘。這樣的交通環境,迎來了新巴人民改變窮困的契機。
烈士的血沒有白流。當年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宿營的36個村寨,經過3年脫貧攻堅,早已消除貧困,過上了幸福生活。2022年,新巴鎮脫貧人口人均純收入約為12087.9元,村民戶擁有機車輛約占75%,擁有摩托車輛約占90%,擁有智能手機的人數約占93%,家家戶戶有智能電視機,新巴人民的好日子——芝麻開花節節高。不久的將來,新巴人民一定會全面進入小康社會。
作者簡介:
王安平,曾服役于總后勤部某部。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散文詩作家協會會員。貴定作家協會主席,《麥溪文藝》主編。先后在《解放軍文藝》《神劍》《萌芽》《北方文學》《朔方》《星星》《散文詩》《貴州日報》等報刊發表作品。出版長篇作品有《風流貴子街》《宋思一將軍跌宕人生》《何必當初》《凌霄》等。
責任編輯/袁士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