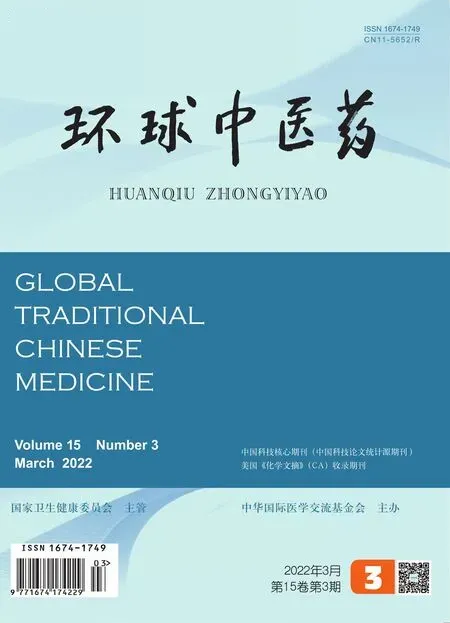從風論治紫癜性腎炎的無證、寡證患者
孫超凡 謝璇 郭曉媛 蔡倩 王暴魁
紫癜性腎炎是由過敏性紫癜導致的腎臟損害,是一種常見的繼發性腎病,臨床上除表現蛋白尿、血尿外,部分患者還可出現不同程度的水腫、腎功能不全等。隨著生活環境及飲食方面等變化,兒童及成人過敏性紫癜性腎炎的發病機率日趨增高。西醫主要以對癥治療為主,患者極易出現病情反復、遷延不愈等情況。中醫藥經過長期的臨床實踐總結,在控制皮膚紫癜,減少蛋白尿、血尿,保護腎功能等方面療效顯著,具有獨特優勢。在治療上,多數醫家基于臨床經驗,提出本病當“從風論治”的思想,并經過臨床實踐總結,使得“風邪入腎”這一理論逐步成熟。筆者前期從外風傷腎、內風擾腎、腎病治風等方面論述了風與腎病的相關性[1],在對風邪與腎病的認識上已初具雛形。在治療膜性腎病上,自擬扶正祛風方已經過臨床與實驗驗證,療效確切,說明腎病“從風論治”這一治法是有據可循的[2-6]。而臨床上筆者在對無明顯癥狀而確診為“紫癜性腎炎”患者的治療觀察中發現,應用祛風之法,療效亦顯。故試從風邪的角度,在中醫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全面探討無證可辨下紫癜性腎炎的治療方法。
1 中醫對本病與風邪相關性的認識
1.1 病起于風
“風為百病之長”,早在《內經》中就有關于風邪襲腎的論述,如《素問·水熱穴論篇》:“勇而勞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于風,內不得入于臟腑, 外不得越于皮膚,客于玄府,行于皮里,傳為腑腫,本之于腎,名曰風水。”歷代醫家在對本病的病機認識上往往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如明代醫家陳實功《外科正宗·葡萄疫》:“葡萄疫,其患多生小兒,感受四時不正之氣郁于皮膚。”《幼科金針》言:“葡萄疫乃不正之氣使然”,均指出外感不正之氣可導致本病發生,而此不正之氣多可能為風邪所致,因《素問》中提出:“風氣藏于皮膚之間,變化多端,無孔不入。”此外,《圣濟總錄·清熱門》認為紫癜風“此因風濕夾熱邪,客在膝理,營衛奎滯,不得宣流,蘊疲皮膚,故令色紫”。明代醫家王肯堂在《證治準繩·瘍醫》:“夫紫癜風者……此皆風濕邪氣客于腠理,氣血相搏,致榮衛否澀,風冷在肌肉間,故令色紫也。”《景岳全書》曰:“血之妄行,又火者多,然未必盡由于火者也。故于火證之外,則有風邪結于陰分而為便血者。”國醫大師呂仁和、著名腎病專家王耀獻亦認為紫癜性腎炎起病緣自于“風”,將本病命名為“紫癜性腎風”,二者共認為風邪貫穿疾病始終[7]。
1.2 癥隨風性
“風邪善行而數變”,患者起病時常表現為皮疹忽隱忽現、關節疼痛游走不定、皮膚瘙癢等癥,具有發病時作時止,病情變化迅速等特點;“風性開泄”,臨床上泡沫尿的出現多為風邪侵襲腎絡,腎失封藏,開闔失司,精微外邪所致;風為陽邪,主升主動,久羈于腎,入里化熱而絡破血溢,發為血尿;風熱相搏,擾動血絡,破血妄行,血液溢于皮膚發為肌衄;“傷于風者,上先受之”,發病初期常有咽喉部干癢疼痛、皮膚紫癜等表證、熱證,亦符合“風為陽邪,易襲陽位”的致病特點。此外,本病好發于冬春季節,而冬春乃氣候交替之機、陽氣生發之時,冬春季節多風,故發為此病。根據發病特點及臨床表現,可以看出“風邪”與本病密切相關。
1.3 從風論治
在治療上,多數醫家倡導從風論治,如王耀獻等[7]在論治此病時常分為祛風除濕、疏風解表、搜風通絡、活血滅風等四法;陳以平認為外感風邪熱毒可導致本病的發生,治療上宜祛風散邪,偏風寒者消風散加減,風熱者施以金蟬蛻湯[8]。于俊生亦認為風邪乃紫癜性腎炎發病的主因,初期常因外感風熱毒邪或接觸致敏原性物質誘發,而過敏因素亦屬于風邪致病的范疇,故在發作期、恢復期重視風藥的應用,常應用過敏煎以祛風抗過敏[9]。江順奎在治療本病上倡導的“御風扶正”法亦體現了祛除外風的思想[10]。丁櫻在論治此病時,認為急性期多以風熱傷絡為主,患者發病時常有發熱、咽痛等外感之候,常施以疏風清熱、涼血安絡之法[11],均取得了不錯的臨床療效。
2 無證可辨,不離“祛風”
基于患者發病特點與風邪致病的相關性,“從風論治”這一治法已得到多數醫家的廣泛認可。然部分患者發病中除蛋白尿、血尿等外無明顯不適,醫家在面對“無證可辨”的情形下常出現誤診、漏診等失誤。筆者在繼承前人醫家學術思想的基礎上,結合臨床實踐,認為本病在“無證可辨”的情況下,治病之法仍不離“祛風”二字,試將其從病證相參、寡證辨證、微觀辨證等角度,進一步闡明從風論治紫癜性腎炎無證、寡證患者的理論根據與方藥應用。
2.1 病證相參,祛風扶正
在臨床診療中,辨病與辨證常作為診治疾病的兩種基本思路與方法,二者相輔相成。“辨病”,即是對疾病一般規律的把握,代表了疾病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而“辨證”是對疾病發展過程中某一階段的病理狀況進行概括與分析。在對疾病的認識及診治中,往往二者相參。然在臨床實踐中,多數醫家往往重視辨證的異同而忽略辨病的重要性,且在紫癜性腎炎的進展過程中,很多患者多有血尿、蛋白尿等實驗室檢查異常情況,在證候上并無特殊表現,常可出現“無證可辨”的情形;亦或患者臨床表現較為復雜,疾病的證候要素過多時,極易影響醫者對疾病的整體把握。如在對本病進行辨證的過程中,患者若出現舌脈不符的情況,或受其認知水平、表達能力等影響,使得癥狀的證候群與疾病本質呈“不相符狀態”,辨證常不能體現疾病的本質,故臨證中“辨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以“辨病”為主導,抓住疾病的主要矛盾,把握治療的基本規律,彌補“辨證”的不足,做到馭繁就簡。以“辨病”為主,結合“辨證”,兼而有之,方能取效。“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風邪乘虛而入擾動腎絡,故臨床上出現蛋白尿、血尿等,本病患者多以“整體虛,局部實”為主要病機特點。考慮本病的固有特點,究其病因,不離“風邪”二字,故治療上以“祛風”之法論治此病,辨病論治。同時兼以扶正清熱,以祛邪為主,扶正為輔,治法為祛風清熱兼扶正。
筆者臨床上治療本病時多應用當歸飲子合過敏煎加減。當歸飲子出自《重訂嚴氏濟生方》,是治療過敏性皮膚病的經驗方。方中荊芥、防風、白蒺藜等疏風散邪以預防或減少紫癜性腎炎的發作;四物湯聯合何首烏滋陰養血以熄風。而過敏煎由名醫祝諶予所創,全方由銀柴胡、防風、烏梅、五味子、甘草等具有抗過敏功效的藥物組成,在治療各種過敏性疾病方面具有顯著療效[12],體現了“辨病論治”“辨病與辨證相結合”的治療思路[13]。此外,配伍穿山龍、青風藤、豨薟草等祛風通絡之品以加強疏風之力。現代藥理學研究證實,祛風類藥物具有抗炎、抗免疫損傷、改善微循環、促進腎小球修復、改善腎功能等作用,對于減輕紫癜性腎炎炎癥和免疫損傷具有重要意義[14-15]。“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疾病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正氣虧虛。《靈樞·師傳》有“脾主為衛”“腎主為外”之說,此二臟乃先后天之本,人體的氣血精津、臟腑經絡、四肢百骸皆賴于此才能發揮正常的生理功能。故在臨證過程中宜從健脾益腎著手,常以黨參、白術、黃芪、仙鶴草等健脾益氣,六味地黃丸之山萸肉、山藥,加枸杞子以補益肝腎。其中,黃芪經藥理研究證實具有顯著改善蛋白尿、水腫等作用,一般初始應用時劑量宜大,常50~60 g起步,同時加用知母、仙鶴草等涼藥反佐,以制約其火熱之性[16]。
2.2 寡證辨證,疏風清熱
在面對無證可辨的情形下,亦可從“寡證辨證”的角度進行思考。《說文解字》云:“寡,少也,從宀從頒,分賦也,故為少。”寡證,是患者沒有或者少有不適的主訴或體征,從傳統中醫四診合參的角度很難獲取患者完整的病情信息來辨證。在診療過程中,過敏性紫癜性腎炎患者往往起病時僅有蛋白尿、血尿等實驗室檢查異常,無明顯的癥狀或體征,很難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進行辨證,即為“寡證”。而同一種疾病的發生發展過程往往有其獨特規律,故對于癥狀不明顯的過敏性紫癜性腎炎患者,可以通過“以有測無、以多測少”的原則進行辨證施治[17]。針對本病,多通過疾病發展到一定階段時出現的癥狀來推測“寡證”時期的證候,如患者常在上呼吸道感染后出現血尿、蛋白尿增加等情況,使得病情加重或反復。而上呼吸道感染常表現為咽喉干癢疼痛、扁桃體腫大、咽后壁充血等風熱侵襲之候,故推測此種疾病存在“風熱”之候,在治療尚未出現咽喉部干癢疼痛等風熱之證,也要注意清熱祛風。此外,任繼學教授在慢性腎風時的基礎上提出了“喉腎相關”理論[18],認為腎風初起,毒邪最易循咽喉而入,故在診療中,尤注意望其咽喉以辨證施治。
“喉應天氣乃肺之系也”,咽喉為肺衛之門戶,故外風侵襲每多犯于肺,現于咽。《靈樞·經脈》云:“腎足少陰之脈,……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喉乃少陰腎經所主,肺腎相合,經脈相通,故風邪從咽喉循經直抵入腎,使得腎失封藏而見蛋白尿。同時,風邪久羈于腎,入里化熱,邪熱耗傷腎陰,陰虛相火妄動,咽喉失于濡養且虛火上灼,《靈樞·經脈》曰:“是主腎所生病者……咽腫上氣,隘干及痛。”故在臨證中必察咽喉,若患者出現咽部干癢不適,伴上呼吸道感染、扁桃體腫大,咽后壁及兩側紅腫、增生等風熱之候時,除應用青果、玉蝴蝶、板藍根等清熱利咽之品外,常配伍金銀花、連翹、牛蒡子等以疏風散熱。
2.3 微觀辨證,臟腑論治
微觀辨證是在中醫理論的指導下,運用現代影像學檢查、實驗室檢查、病理組織檢查等技術,從器官、細胞、分子水平等進行更深層次的辨證,為臨床診療疾病提供更多的辨證思路。隨著現代醫學診療技術的發展,腎活檢病理檢查已成為腎臟病診斷的“金標準”。基于“天人相應”整體觀的指導下,各個醫家運用比類取象法、司外揣內法等對微觀辨證提出了新的看法,如陳以平[19]將免疫介導的腎臟細胞增殖、間質炎細胞浸潤、細胞性新月體形成等病理改變辨證為外邪擾絡,治當以祛風化濕、清熱解毒。眾多醫家認為,系膜細胞增生、內皮細胞增生等具有“生長”的屬性,屬“陽”。其來勢急、變化快等特點與“風邪”善行而數變的致病特點相似[20]。
筆者在總結臨床診療經驗的基礎上,基于腎臟組織結構,生理功能及病理狀態的相似性,結合中醫哲學思想,比類取象,從微觀辨證的角度,提出了對腎臟病微觀結構及病因病機的個人認識[21]。一方面,從腎臟結構的微觀辨證來看,過敏性紫癜性腎炎的病理表現一般是以IgA沉積為主的系膜增生性腎小球腎炎,其病理改變以系膜病變為主,可見腎小球局灶性、節段性或彌漫性系膜增生,電鏡亦可見系膜細胞增生,基質增加。《素問·痿論篇》言“肝主身之筋膜”;《素問·六節臟象論篇》云“肝者,罷極之本,其充在筋”,而系膜細胞中大量的肌動蛋白與肌球蛋白有類似平滑肌的收縮與舒張功能,故能通過其收縮、舒張功能來改變腎小球毛細血管的濾過面積和壓力通透性。而系膜這種聯結、舒縮的功能與筋、膜類似,故有關系膜細胞的疾病可從“肝”來論治。“肝為風臟,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榮,故肝陽偏亢,內風時起”。肝木失榮,內風時起。同時,肝為風木之臟,經云“風氣通于肝”,故祛風之法,當從“肝”來論治。故論治此病時,在運用當歸飲子的基礎上常配伍防風、川芎、羌活、柴胡等疏肝散風之品。大量研究表明,應用祛風之品能減少腎組織系膜區IgA沉積,減輕系膜細胞及系膜基質增生,從而減少尿蛋白,保護腎功能[22];另一方面,從腎臟病因病機及臨床表現來看,部分患者多表現為咽喉紅腫熱痛,皮膚發熱、發斑等營血分證,起病較急,病情變化迅速。葉天士云:“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素問·五臟生成篇》云:“諸血者,皆屬于心。”《素問·痿論篇》云“心主身之血脈。”此類病理狀態與“火” “血脈”相關,與心相應,故在治療時亦可采用清心、涼血之品,如生地、丹皮、梔子等以涼血散血。
3 結語
“風者,百病之始也”,風邪與紫癜性腎炎的發病具有密切關系,多數醫家據此提出了“從風論治”的經驗思考。然在臨床中患者易出現“無證可辨”的情況,給臨床診療帶來了挑戰。本文在中醫整體觀的指導下,從辨病與辨證相參、寡證辨證、微觀辨證等方面闡述了紫癜性腎炎無證、寡證患者“從風論治”的理論依據與治則治法,充分發揮中醫學傳統診療的優勢,彌補了本病臨床中無證、寡證患者診療上的缺陷,為本病論治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