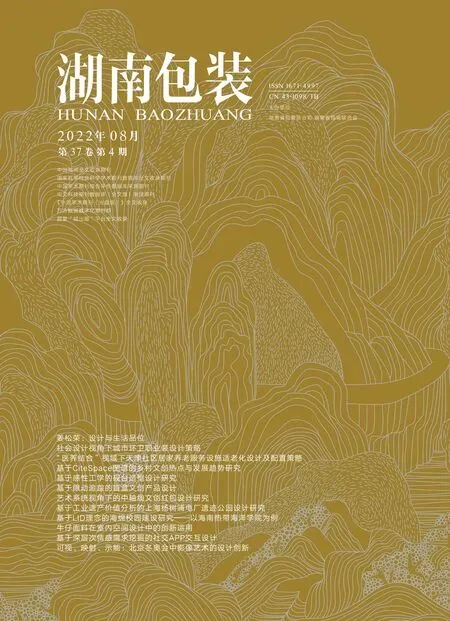技術景觀視野下大理扎染的發展研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中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定義是指被各社區、群體或個人,視其為文化遺產組成部分的各種社會實踐、觀念表達、表現形式、知識、技能及相關的工具、實物、手工藝品和文化場所[1]。手工藝作為非遺中較為特殊的一類,它不僅呈現了非物質的創造過程,還需要物質載體將其呈現出來。在工藝世代相傳至今的時間中,它們滿足著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和精神需求的慰藉。在獨屬于它們的歷史長河中,工藝的制作方式隨著社會的更迭,幾經變遷。從創造初期的純手工制作到工業革命之后的機械化生產,再到信息時代的數字化生產,手工藝的呈現與不同技術的運用息息相關。工藝的改良隨著技術的進步孕育出不一樣的制品,在信息時代的今天,手工藝的屬性已經偶爾不需要實體的存在。阿帕杜萊全球化理論中的“技術景觀”將手工藝的生產技術分為手工技術、機械技術、信息技術3類,以阿帕杜萊“技術景觀”的三種技術背景分析傳統非遺手工藝的續存邏輯,可突破時空的局限,更加清晰地展示其變遷過程,以技術的革新為突破口,可以更深入地探析手工藝改變背后的原因,從對物、對工藝的描寫上升至對社會流變的思考。同時,文化的保存、保護只有在活生生的生活實踐與文化傳統相融合中才能實現[2],手工藝的發展與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息息相關,以技術景觀為視野分析非遺手工藝的發展現狀,對于在實踐中促進傳統手工藝與新興技術的融合以及在技術雜糅的時代下非遺手工藝未來的發展趨勢有著較好的推動意義。
1 從技術景觀到手工藝
阿帕杜萊的“技術景觀”是以其嶄新的全球文化經濟新秩序為背景提出的,他提出了5種全球文化流動的維度來探究全球經濟文化的復雜性,它們分別是:族群景觀、技術景觀、金融景觀、媒體景觀和意識形態景觀。其中,阿帕杜萊[3]44對“技術景觀”的定義是:“全球技術的流動形態。”他強調的是以技術為核心所引發的一種流動性的狀態,無論高低,不論是機械技術、手工技術還是信息技術,它們現在都呈現出高速跨越曾經不可滲透的邊界的運動狀態。在“全球文化經濟中的散裂與差異”[3]45中阿帕杜萊分析:驅使其發生的動力不再是任何明顯的規模經濟、政治控制的經濟或市場理性下的經濟,而是貨幣流動、政治機遇以及非成熟勞工和熟練勞工等因素之間的日益復雜的關系。阿帕杜萊的技術景觀強調的是一種流動的狀態,不同技術的古怪分配形成了技術景觀的奇特之處,他將“技術”分為手工技術、機械技術、信息技術,囊括了自人類誕生以來因4次工業革命而延伸出的3種技術。一次又一次更新了人類“手”的替代品,技術與手工藝之間一直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從人類真正的手到第一次、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再到第三次、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信息化,技術的革新也會帶來手工藝的變遷。以技術景觀這一視野看扎染的發展現狀是以技術的流變看社會,從對物、對工藝的描寫上升至整個社會的分析,研究在技術流變的背后,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之間的互動。
在身處技術雜糅時代的今天,學術界對大理扎染這項傳統手工藝有過不少研究,針對扎染藝術的研究十分豐富,從扎染的詳細制作技藝描述到其技法的研究[4],再到扎染圖案、色彩、題材的藝術特征美學分析[5],再到扎染這項手工藝的變遷探索研究[6]。除了藝術本體的探索,學者們關于大理扎染的深入分析也隨著時代的變遷從藝術本體轉向它的傳承、綜合運用等方面,學者們更落腳于它的未來發展,有與市場、旅游、數字化相結合的發展路徑研究[7-9],也有探尋扎染保護傳承方式的研究[10]。通過上述概述,可以看到學者們從多角度,運用多個領域、學科相結合的方式對扎染研究各抒己見,但對其傳承方式的討論大多針對市場或是與設計、數字化結合的新路徑給出看法、意見,很少有從技術的角度探尋扎染的發展趨勢。下文便以扎染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在這項技藝原生主體處——大理,扎染作為手工藝在手工技術、機械技術、信息技術視野下的存續邏輯[11]。
2 手工技術下的扎染
“手工技術”是指依靠手工勞動,使用簡單的手工工具從事小規模生產的加工活動。中國的手工技術業歷史悠久,它最初與農業密切聯系,屬于個人副業性質的家庭手工業,每個民族的手工技術技法不一,幾經更迭流傳至今。在如今技術雜糅的社會,手工技術作為手工藝中最傳統、最本真的技術,它在與機械技術、信息技術相抗衡的時間里,展現了它獨一無二的魅力,也形成獨屬于它的生命之路。扎染是中國一種十分古老的印染技法,它作為大理人民最為熟悉的手工技術,幾乎每家每戶的女性都會制作,扎染制品早已成為他們的生活日用品。以“手”為直接參與其中的扎染,藍白之間不僅是傳統手工技術的呈現,更是其中人情、溫度的傳遞[12]。在如今3種技術雜糅的時代,手工技術下的扎染不僅以村民生活中日用品的形式存在,更可以突破時空的局限,讓外地游客親手嘗試他們不曾了解的傳統手工技術。
扎染從畫板、打板、印刷、扎花、脫漿、染色、拆花到晾曬,一個個步驟組成了扎染這項獨有的手工技藝,其中“針法”“扎法”“染法”作為扎染核心的三大技法,是幾乎每家每戶的媽媽輩、奶奶輩的婦女都十分熟悉的手工技術。扎染于她們而言,是孩童時期的一次幫忙、一次玩樂。在當地,家里會用板藍根的莖和葉子泡在水中進行蒸煮制成簡易的染料,或是直接到專門的染坊中請專業的師傅幫忙進行染色,成品一般作為家用,制成頭巾、臺布、圍腰、床單、窗簾等。在她們眼中,扎染所得也是家中的生計、補貼,當地的扎染工場為了遵循古法制作的原則,在人手不夠的時候會將印好花的布料分發給當地會技術的村民,按件計費,支付相應的報酬。在當地村落中,尤其是午飯、晚飯之后,會看見一些老一輩的白族村民坐在自家門口扎花、拆線。在扎染上百年的歷史中,手工技術在大理人民的手中傳承、流轉,默默地對抗著機械化市場的沖擊,同樣,在信息通暢的今天它也開辟出另一番蓬勃發展之路。
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當地開設了很多扎染體驗館,手工技術得以超越時間與空間的界限,讓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體驗到手工技術的魅力。在周城村的璞真扎染博物館中就有這樣一項體驗,游客可以體驗扎染手工技術的每一個步驟,由有經驗的手工藝人帶領著,一步步領略傳統扎染的制作過程。從紋樣的選擇、顏色的搭配、“三法”的嘗試與學習到最后的拆線、晾曬,切身體驗整個手工技術的魅力,到最后,拿到一件純手工制作的扎染制品。至此,手工技術突破地域的限制,不僅存在于這項技術原生主體的手中,更是將人群擴展至其他地區。
手工技術是扎染作為一項手工藝的核心,也是一代代手藝人堅持傳承下來的工匠精神,就其傳承而言,它也面臨著諸多困境,最突出的現象便是,無論在當地工場中打工的手藝人,還是工場外制作訂單的散戶,基本上都是年齡偏大的中老年婦女。老齡化、勞動力流失、手工藝人受教育低等問題在當地越演越烈,這些問題也不是手工技術下扎染的個例,更是手工藝以手工技術發展到現在呈現的普遍問題。
3 機械技術下的扎染
有純手工制作的扎染制品,就一定會有機械化生產出來的流水線制品。“機械技術”便是運用大型的、復雜的機器代替手工進行生產的技術,機械不同于工具,機械更多強調的是以多數人工和很大力量而達成效果的。相較于純手工制作,有了機械技術的參與,效率會大大提高,因此工廠流水線的生產方式迅速普及。由于扎染技法的特殊性,大理當地的工廠并沒有采取純機械化的流水線,以半機械化的生產方式進行生產、運營,巍山三彝扎染公司從建廠至今的30多年里,集生產銷售于一體,以批發為主要的出售方式,從外銷走到如今的內銷,在機械化浪潮為洪流的時代中,敢于創新,以發展、融合的方式傳承手工藝。
巍山自古就有染布匠,有將土布染成包頭布,銷售給周邊少數民族并隨茶馬古道遠銷的歷史,但都不成規模。真正把染布這一工藝收集、整理、流程化加工,打造成商品,遠銷國外,是在巍寶彝族扎染廠創建后逐漸才有的事情。扎染廠隸屬于巍山三彝扎染公司,年生產系列扎染制品達到100余萬件,主要經營出口扎染布及其系列產品。扎染廠是一個半機械化的工廠,在保留了手工扎布的同時輔之以機械化流水線模式。工廠廠房分工明確,有質檢部和整燙車間;整燙車間主要負責后期的熨燙、成品打包成袋、裝箱等工作。有銷售部和縫制車間,縫制車間負責縫制成品。染色車間設有植物染提取鍋、草木染色池、板藍根土染缸、靛藍染缸、漂洗池、卷染機、甩干機等機器用于染布。當地市場上買賣的扎染制品,無論是大件成品還是小件周邊、文創產品都在堅持核心技術的運用。從印花到縫制,完整的制作工藝是人工與機械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完成的,這是當地工廠對機械技術的態度,積極與新時代、新技術融合以提高效率、擴大市場,但絕不丟失手工藝的核心,堅持以手工扎、植物染的核心。
自19世紀工業革命爆發以來,手工業受到了機械化的極大沖擊,但機械化的進程從不停歇腳步,如何與之融合是每項工藝都需要思考的問題。在如今文化消費的時代,“文創”成了文化消費的一大路徑,那何為“文”,何為“創”,學術界更多的是從不同角度對其界定。巍山當地的扎染工廠順應時代的選擇,創新性地開發出極具特色的文創周邊,很好地將傳統融入其中,傳承下去。
4 信息技術下的扎染
“信息技術”指的是用于管理和處理信息所采用的各種技術的總稱,在第三、第四次工業革命爆發之后,以互聯網為基點,全球趨于數字化,世上所有的物質不僅僅以實物的方式存在,在信息技術面前,都是一串串數字。中國對于非遺數字化的保護從2010年10月正式啟動“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工程”,旨在利用科技更有效地保護、傳承、發揚我國非遺。古法扎染作為第一批國家級非遺,也已經以數字化的方式進入中國非遺數據庫。除了數字化的保護,隨著中國進入了工業革命4.0——信息技術促進產業變革的時代,網絡的力量隨之展現,人們變為了信息的產出者和傳播者,同時也是接受者,兼有多重身份[13]。在“萬物互聯”的時代,手工藝緊跟信息時代的洪流,利用信息技術擴大受眾群體,讓自己被世界認識,大理當地的扎染也開始擴展數字化業務,網購、線上教學等模式都已初見雛形。
璞真扎染博物館除了有線下的體驗點、展覽、商鋪,它在微信上也有針對線上的扎染小程序——大理白族扎染,小程序中對大理的歷史、扎染一系列的信息做出詳細說明,如有關扎染材料、圖案的特點、扎染所需要使用的工具等。扎染的工藝步驟從畫板到晾曬都向大眾做出詳細的介紹,圖文并茂,同時還附有扎染的成品以及對應地址。除了這款有普及性質的小程序,璞真的老師制作一系列扎染技法的視頻,其目的一方面是針對非專業的人群,用于擴大受眾人群;另一方面是想通過網絡這一平臺,讓更多的人認識扎染,給愿意傳承這項技藝的人有更專業的學習機會。
除了當地官方的一些小程序以及相關視頻的制作,當地時常也會有一些自媒體的博主光顧。他們以旅游、非遺、手工藝等關鍵詞拍攝VOLG放到自己的社交平臺上供大眾點擊、瀏覽,這種形式在增加博主點擊量的同時也在為當地旅游、文化打廣告、做宣傳,達到一舉多得的效果。來大理旅游的游客也表示,他們很多是通過網絡的推薦來這邊感受少數民族的文化,體驗最傳統的非遺手工藝制作。這種以網絡為基礎的宣傳方式效率大大高于傳統的口口相傳,提高了當地經濟收入,宣傳了當地的文化。
信息技術下的非遺手工藝除了以網絡為基礎的宣傳,更有當下很火熱的直播與網購。無論是周城還是巍山,目前還沒有官方的賬號進行直播,而針對網購,璞真還處在起步階段,沒有一個穩定的網店訂單,更多的是通過微信好友的方式與當地商鋪的老板建立聯系,接受批發、定制等多種方式。在巍山,網店的訂單則較為穩定,有兩家合作較好的商家,他們拍照上傳,有訂單就發貨,一開始是公司支持他們,現在網店生意逐漸變好,一款的銷量可以達到上百件,開始反哺公司,形成一種良性循環。在大理當地,無論信息技術被怎樣運用,無論扎染以哪種數字化的形式出現在大眾視野中,他們傳播的內容都是手工技術,信息技術的運用是一種呈現方式,更是一種為了高效傳播手工技術的手段。
從2019年底持續至今的疫情不僅加速了信息技術的發展與運用,更加快了信息技術與人們生活的聯系與相融,在后疫情時代的今天,數字化的優勢更加凸顯,但在拓寬受眾人群與市場的同時,弊端也隨之展現。原本極具民族特色的圖案容易被西方審美的思想影響,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圖案被隨意嫁接,脫離原生主體語境進行錯誤解釋的現象頻發。信息技術更應該作為手工技術與信息時代的融合、延伸,創造更真實的信息環境,更好地幫助手工技術的傳播與傳承才是運用信息技術引流的落腳點[14]。
5 結語
現代全球化背景下手工藝的技術景觀是手工技術、機械技術、信息技術相融合的視野,3種技術相互牽拌、各司其職,形成了一幅完整的技術景觀圖景。手工技術作為手工藝最為傳統、核心的技術,以手為器,承載了幾百年來手工藝的傳承與變遷,而老齡化、年輕勞動力流失嚴重等問題是手工藝面臨的現實困境。機械技術、信息技術在對手工技術帶來強烈沖擊的情況下,卻也給它帶來了全新的呈現方式。在手工藝的傳承與傳播途中,更應該利用好機械技術與信息技術,堅持以手工技術為基礎點、核心點,更高效地保護、傳承、發揚手工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