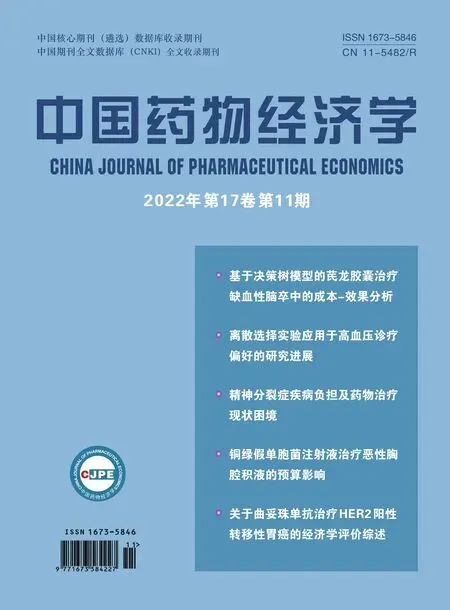精神分裂癥疾病負擔及藥物治療現狀困境
黃 兢 唐 慧 伍海姍 向 慧 劉 晶 李樂華 吳仁容* 陳晉東*
精神分裂癥是一組常見的病因未明的嚴重精神疾病,多起病于青壯年,常有知覺、思維、情感和行為等方面的障礙。其全球患病率近1%,已成為全球十大殘疾病因之一[1-2]。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發病年齡相對較小,大多數患者初次發病年齡在青春期至30 歲。該病屬于腦功能失調的神經發育性障礙,致病原因涉及復雜的遺傳因素、生物因素及環境因素[1]。病程通常多遷延,約50%患者最終結局為出現精神殘疾,給社會及患者和家屬帶來了多方面的沉重負擔[2]。
精神分裂癥的主要治療方式為藥物治療,而現有的治療選擇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針對陰性癥狀、殘留陽性癥狀和認知功能等方面的有效治療方法缺乏,藥物不良反應和依從性差等問題,仍是該病臨床治療面臨的重大挑戰[3]。近年來,非典型抗精神病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典型抗精神病藥的局限性,并逐漸取而代之,但未來仍需要更多新的藥物選擇和方案優化,以滿足更多患者的需求。
1 精神分裂癥的疾病負擔
1.1 流行病學負擔
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報告顯示,全世界約有超過2 000 萬人正在經受精神分裂癥的影響[4]。該病全球年發病率為0.22‰左右,終身患病率為0.38%~0.84%,美國報道的終身患病率高達1.3%[2]。目前國內仍缺乏大規模的精神分裂癥發病率研究,2018 年一項針對北京市某地區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調查結果顯示,2015 年精神分裂癥患者發病率為0.079%[4]。2019 年一項橫斷面流行病學研究,調查了31 個省(市區)的157 個全國代表性人群疾病監測點的成年人樣本,結果顯示中國精神分裂癥的終身患病率及12 個月加權患病率均為0.6%[5]。
精神分裂癥患者過早死亡風險是一般人群的2~3 倍,預期壽命比一般人群低約20 年[6]。一項瑞典前瞻性研究納入了29 823 例精神分裂癥患者,在5.7 年的平均隨訪期間,約8.4%患者死亡,平均年死亡率為1.47%[7]。2020 年公布的一項基于中國臺灣人民醫療保險數據庫的研究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的10 年累計死亡率為11.67%,顯著高于其他精神類疾病,如情感障礙(10.67%)、焦慮癥(6.32%)和物質使用障礙(8.69%)等[8]。整體來看,目前中國精神分裂癥的發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現狀均不容樂觀。
精神分裂癥患者易并發其他疾病,其中心血管疾病是最需關注的并發癥之一,也是導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9]。QT/QTc 間隔延長、肥胖、代謝綜合征等合并癥的存在均可增加心血管事件風險[10]。研究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發生心血管疾病風險是其他精神疾病患者的1.53 倍。并發癥的存在也嚴重影響患者生存,一項中國調查研究顯示,在精神分裂癥死亡患者中,因并發癥死亡比例占總體患者的5.94%,占死亡患者的84.2%。此外,長期未經治療的精神分裂癥也可能與認知功能減退有關[11],已有薈萃分析表明代謝綜合征、糖尿病和高血壓等合并癥與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功能障礙顯著相關[12],進一步加重了疾病負擔。
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服藥依從性較差,一項來自世界衛生組織、針對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患者的調查顯示,超過69%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13]。早期研究報道的依從性差的精神分裂癥患者比例約為32%(16/50)[14],近年來發表的CATIE 試驗中,洞察力受損的患者用藥不依從者可達43%[15]。中國一項2018 年的報道顯示,農村社區精神分裂癥藥物治療依從性差的患者比例為41%~88%[16]。造成患者依從性差的主要原因包括藥物治療不良反應和并發癥的發生。在我國,自我感覺療效欠佳、生命質量和社會功能的減退是影響精神分裂癥患者依從性的重要因素[17]。服藥依從性差是導致患者復發率升高的主要風險因素之一。
國內近年來報道的精神分裂癥的兩年復發率在26.2%~45.3%[18-20],可導致患者的再次入院。而各種原因所致的反復住院進一步增加了醫療和經濟負擔。一項歐洲多中心真實世界研究顯示,在隨訪期間71.7%患者出現因治療失敗而復發的情況,43.7%患者經歷了再入院治療[21]。在國內兩項調查報道中,精神分裂癥患者經歷≥1 次和≥2 次住院比例也分別達60.8%和61.3%;其中住院患者藥物治療費用僅占11.1%,而因住院所產生的非藥物治療費和床位費等占比超過60%,明顯增加了患者的經濟負擔[22-23]。
1.2 經濟和社會負擔
1.2.1 經濟學評估研究不同國家報道的數據雖有所差異,但總體上精神分裂癥造成的成本費用是較高的(表1)。有報道顯示其中藥物治療的直接費用占比不足25%,而住院費成為大多數國家醫療費用的最大組成部分(可達66%)[24-25]。疾病復發會導致反復住院和增加額外治療費用,一項針對精神分裂癥復發患者的系統性綜述顯示,歐洲國家報告的患者治療后6~12 個月因疾病復發產生的額外費用為8 665~18 676 美元,美國報告的12~15 個月的額外費用為16 000~33 000 美元[26]。在新近的報道中,2020 年丹麥的一項調查表明,精神分裂癥患者每年的直接成本(醫療費用)和間接成本(生產力損失)總和為43 561 歐元[27]。另一項韓國的回顧性研究顯示,2006 年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總直接醫療費用約為4 510 億韓元,至2016 年已上升至8 680 億韓元,同時總間接費用也從3.09 萬億韓元增加到5.79 萬億韓元[28]。
在中國精神分裂癥患者中,這種經濟負擔同樣不容樂觀。精神分裂癥相關經濟總負擔占中國衛生總費用的0.35%[29]。與國外現狀相似,國內報道的精神分裂癥住院費用也仍然是總醫療費用的主要組成部分,研究顯示住院患者相關費用是未住院患者的11 倍[23,30]。一項2020 年的疾病負擔分析顯示,與年齡和性別匹配的一般人群相比,中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總生存率降低了20.6 年,質量調整生命年(QALYs)降低18.4 QALYs,且平均直接醫療費用增加了約3倍[31]。
1.2.2 社會生產力損失精神分裂癥患者發病年齡較小,因此造成的社會生產力損失也較大(表1)。有研究顯示該病帶來的生產力損失成本在各國為每年4 260~62 431 美元/人,社會負擔成本在30 405~94 229 美元,分別可達當年該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的37%~214%[33]。中國的報道也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中無法工作者的比例超出28%,造成生產力損失[37]。精神分裂癥同時也造成照護者生產力損失和加重家庭經濟負擔。一項基于中國農村地區精神分裂癥患者分析得出,患者家庭年平均總收入約為12 108 元,而因該病造成的年平均直接和間接家庭經濟負擔分別達963 元和11 724 元[38]。丹麥的調查研究顯示,精神分裂癥患者配偶的醫療和生產力損失費總和高出非精神分裂癥患者配偶約21 888 歐元/年[27]。

表1 不同國家精神分裂癥經濟負擔研究報道
總體來看,精神分裂癥給患者、家屬及社會均帶來了多方面的沉重負擔,而有效的治療和干預,將有助于改善患者癥狀、提高生命質量和減輕疾病負擔。
2 精神分裂癥的藥物治療現狀
精神分裂癥的管理包括藥物治療、心理干預、物理治療和代謝綜合征管理等。其中藥物治療仍是主要的治療方式,藥物治療的原則是早期、足量、足療程、單一、個體化用藥[2]。
2.1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又稱第一代抗精神病藥)的主要作用機制為通過阻斷大腦中的多巴胺D2受體而發揮作用[39]。其中最大的一類為吩噻嗪類,其他還包括硫雜蒽類、丁酰苯類和苯甲酰胺類等,相關代表性藥物見表2。
2.2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
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又稱第二代抗精神病藥物)相對于阻斷多巴胺D2受體,具有更強的阻斷5-羥色胺受體的能力[39]。基于其對D2受體的拮抗作用相比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弱,同時也更有可能阻斷皮質和邊緣區域的多巴胺受體,因此表現為錐體外系副作用發生率較低[40]。目前,已批準用于臨床的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包括5-羥色胺和多巴胺受體拮抗劑類、選擇性多巴胺受體拮抗劑類、多巴胺受體部分激動劑類、苯基吡啶類和苯異噻唑類。見表2。

表2 常見的典型和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39]
研究表明,新型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布南色林與安慰劑或典型類的氟哌啶醇相比,對陰性癥狀的療效更好。同時,該藥耐受性良好,尤其在催乳素升高和錐體外系反應發生率等安全性獲益方面也優于氟哌啶醇[41]。該藥在中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治療中也被證明與利培酮同樣有效,且總體安全性相當[42]。另一個新型藥物代表為苯異噻唑類的魯拉西酮,其在中國精神分裂癥患者的治療中也顯示出不劣于利培酮的療效,并對體重、代謝參數或催乳素水平的影響較小[43]。
2.3 其他機制藥物
近年來,針對精神病治療的其他非經典作用機制藥物也仍在研發中,如代謝型谷氨酸受體和磷酸二酯酶抑制劑等,或有望用于改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認知癥狀等[39,44]。
2.4 臨床治療指導建議
國內外治療規范均推薦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作為一線藥物選用[2]。而目前在國內,仍有部分地區和醫療機構將傳統的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如氯丙嗪、奮乃靜、氟哌啶醇和舒必利)作為首選治療藥[2]。例如北京市某精神病托管中心,抗精神病藥物中使用頻率排名第1、3 和5 位分別是典型的氯丙嗪(25.0%)、氟哌啶醇(12.0%)和舒必利(10.2%)[45]。非典型的氯氮平在國內應用廣泛,雖有獲益,但不良反應多見;基于代謝綜合征問題,目前部分國外指南不再將其作為首選,在中國《精神分裂癥防治指南》[2]也建議謹慎作為首選。在治療評估方面,除考慮療效外,在椎體外系反應、催乳素升高、體重增加及心血管風險等方面的安全性獲益,也需進行考慮。
3 藥物治療現狀的困境
3.1 現有藥物治療的局限性
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對緩解陽性癥狀具有明顯療效,但對陰性癥狀和認知功能損害的改善效果欠佳。從藥物作用機制來看,其對中樞神經系統中多巴胺通路的作用不具有選擇性,導致了一系列副作用[39]。盡管過去幾十年中典型抗精神病藥物為患者帶來了癥狀改善,然其應用仍然受到嚴重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2,39]:1)不能改善認知功能,包括不能改善執行功能、工作記憶、言語記憶、視覺運動、精細運動功能等,但有時可改善注意力的某些指標,相關藥物的抗膽堿能作用也可能會使記憶惡化;2)對原發的陰性癥狀療效微小,有時可產生繼發性陰性癥狀與抑郁癥狀;3)約30%患者的陽性癥狀不能有效緩解;4)引發錐體外系癥狀、升高催乳素,以及造成遲發性運動障礙的比例較高;5)因不良反應等因素導致患者用藥依從性較差;6)藥物對患者的社會功能和自我照料能力的改善作用較小。
典型抗精神病藥已逐漸被非典型抗精神病藥所取代,后者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這些限制。然而Leucht 等[46]的薈萃分析顯示,只有部分藥物顯示出更好的整體療效。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也同時存在自身的局限性,如易發生體重增加、代謝異常、心血管事件風險增加等。Saucedo 等[47]的薈萃分析表明,典型與非典型長效注射抗精神分裂癥藥物在長期管理的癥狀控制和依從性方面同樣有效,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降低了使用抗帕金森病藥物的風險,但可增加血清催乳素水平、體重和體重指數(BMI)。
3.2 疾病帶來的困難
一方面,抗精神病藥物的局限性進一步增加了疾病治療困難。藥物治療帶來的副作用可造成患者服藥依從性差,致使療效降低,復發率升高,進而增加醫療負擔和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從疾病特點來看,精神分裂癥患者常伴有較高的心血管疾病風險,并常見合并代謝疾病和其他精神疾病等[10-12],意味著患者可能需要多種藥物治療,也為臨床治療增加了難度。同時,精神分裂癥患者存在較高的自殺和傷殘風險,2019 年中國研究報道的精神分裂癥患者自殺死亡發生率和傷殘率分別約為 0.85%和0.38%[48-49],也會影響治療依從性,并降低生命質量和預期壽命。此外,從人文角度來看,精神分裂癥患者及家屬常具有病恥感,生命質量差[50]。患者子女身心健康也可能受到影響,如出現情緒不穩定或執行功能障礙等,從而加重家庭負擔[51-52]。這些因素帶來的疾病、經濟或人文負擔均會對臨床治療決策產生影響。
3.3 相關政策現狀和需求
國內常用的治療藥物中,已被納入國家醫保目錄的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包括氯丙嗪、硫利達嗪、奮乃靜、氟奮乃靜、三氟拉嗪、氯哌噻噸、氟哌啶醇、五氟利多和舒必利等,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包括利培酮、奧氮平、奎硫平、齊拉西酮、氯氮平、氨磺必利、阿立哌唑、布南色林、魯拉西酮等。然而精神分裂癥治療領域的新藥有限,仍未滿足患者對藥物可及性的臨床需求。非典型抗精神分裂癥新藥布南色林和魯拉西酮已被證明具有顯著臨床療效和安全性優勢,可降低不良反應,提高患者用藥依從性。布南色林不引起催乳素水平升高、體重增加和體位性低血壓,且錐體外系反應發生率低[41];魯拉西酮治療帶來的體重增加發生率也較低,近年來還被報道對血脂和心血管風險指數顯示出有利的影響[53-54]。此外,中國首個自主研發的精神分裂癥藥物注射用利培酮微球(Ⅱ)近期也已在國內獲批上市,這些新藥也將為臨床醫生和精神分裂癥患者治療帶來更多的選擇。
4 總結
精神分裂癥在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臨床、經濟、社會和人文等多個維度的沉重疾病負擔,改善患者臨床癥狀、提高生命質量是該病的重要治療目標。由于精神分裂癥疾病的特殊性,許多患者需要長期甚至終生服藥,而使用藥物改善癥狀的同時,也可能會引起各種不良反應,影響患者用藥依從性,嚴重影響患者的治療效果和生命質量。因此,選擇更有效、安全和更具成本-效益的藥物仍然是臨床迫切所需。治療藥物醫保政策的完善及社區精神衛生服務水平等方面的提高,也對改善精神分裂癥具有重要意義。非典型抗精神病藥物的發展近年來已取得重大進展,未來也期待更多新的藥物或優化治療方案研究的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