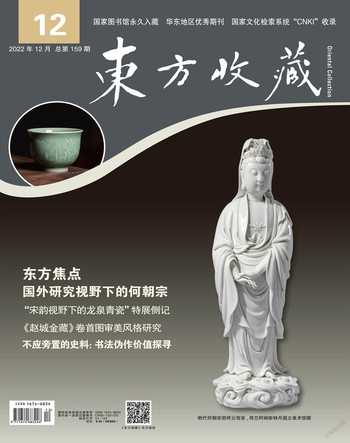論唐代書法屏風的發展與藝術功能


摘要:唐代書法成為繼六朝書法蓬勃發展后的又一座高峰,建立起十分完整的書法理論體系。書法創作除題壁、石刻等形式之外,書屏也盛行一時。書法屏風是唐代書法作品的重要形制之一,獲得帝王貴戚、文人墨士以及庶民百姓各個階層的喜愛。李白《草書歌行》云:“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體現出唐代家家戶戶都有擺放書法屏障的習慣。從唐代書法屏風的發展過程中,不僅能看到唐人的審美趣味,還能反映唐人的生活細節。處在這一特殊時期的書法屏風,其藝術功能多元化,展示出唐代書法藝術的無限魅力。
關鍵詞:書法;屏風;發展;功能
一、唐以前的書法屏風
有關屏風的記載最早始于西周,專為帝王所設,是古代天子座后的屏障。古人稱其為“邸”或“扆”,上面繪有黼形紋,出現在各種重要的禮儀活動之中,屬于皇權的象征。
“屏風”之名在漢代已經出現,東漢劉熙《釋名·釋床帳》謂:“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古代房屋的密封性不佳,屏風作為遮蔽、擋風的器物在古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從考古文物來看,漢代出現了具有實用功能的座屏、圍屏,且屏風裝飾多為彩繪,尚未出現書法屏風,至少在當時未能流行。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戰亂頻繁、社會動蕩,但這并不阻礙文化的繁榮,書法藝術的發展進入自覺階段。屏風作為書寫媒介被廣泛使用,書法屏風開始流行,出現曹毗、宗炳、庾元威等書屏名家。此時,在文獻中可以找到諸多對于書法屏風的記錄,且屏風的書法內容頗為豐富。例如東晉曹毗《詩敘》中云:“余為黃門,在直多懷。遂作詩,書屏風。”梁代王琰《宋春秋》曰:“明帝性多忌諱,禁制回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宜代之。”另外還包括著錄經文、表彰功臣、記功政事等內容。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書法屏風除內容多樣外,書體更是多變,宗炳曾“于屏風上作雜體篆二十四種,寫凡百名。將恐一筆鄣子,凡百屏風,傳者逾謬,并懷嘆息。”梁簡文帝《答蕭子云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縑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太平御覽》記梁庾元威《論書》云:“余為書十牒屏風,書作十體,間以彩墨,當時眾所驚異,自爾絕筆,唯留草本而已。”甚至當時有人以能夠在一面屏風上表現多種書體為榮。諸多文獻資料證明了書法屏風在魏晉時期的普遍流行,這一現象促使書法屏風成為一種獨特的圖像,這種圖像在隋代時又被描繪在維摩詰畫像中。
隋代的書法藝術成就雖然不及魏晉南北朝,但對唐代書法發展也起到先導作用。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記載:“殿內東壁,孫尚子畫《維摩詰》,其后屏風臨古跡帖,亦妙。”可以將此看作維摩詰像與書法屏風二者組合的重要文字資料,且盛唐時期開鑿的莫高窟第103窟中出現了維摩詰像(圖1)與書法屏風結合的珍貴畫面。巫鴻《重屏》中涉及書法屏風的相關內容,對此類潦草墨跡解釋為模仿某一書法家的創作風格。雖書法內容無法辨別,但可看出書法屏風在發展過程中逐漸成為一種文化象征。
二、唐代書法屏風的繁榮
唐代屏風廣為流行,獲得上至帝王貴族、下至平民百姓的普遍喜愛。東漢李尤的《屏風銘》明確闡釋了屏風的使用方法和主要功能:“舍則潛辟,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坑。奉上蔽下,不失其常。”唐代室內的家具陳設基本沒有固定位置,往往需按照不同的禮俗場合隨宜安排。作為活動家具,屏風可用來區隔空間、遮蔽視線、烘托氣氛。受起居生活習慣的影響,屏風成為唐人室內陳設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初唐家具以席地而坐的低矮型家具為主,后來受佛教的高型坐具和西北少數民族胡床等外來文化的影響,逐漸出現適應垂足而坐的高型坐具。因此,隨著家具形制的變化發展,屏風原本的實用功能變得含蓄,審美功能則逐漸凸顯。屏風在唐代獲得鼎盛發展,其樣式較前朝也多有突破。裝飾內容的豐富多樣,使得屏風與書法藝術的結合越發緊密。隨著唐代社會開放、經濟繁榮,文化藝術空前發展,唐代書法達到鼎盛階段。屏風作為一種便于展示書法藝術的理想創作載體,受到大量書法名家的青睞。除此之外,唐代詩人們也樂于書屏,留下很多書法屏風的詩篇。王梵志《紙屏風》云:“家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事有益,且得耳根熱。白紙書屏風,客來即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白居易曾借屏風抒發對摯友元稹的思念之情:“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李白有不少有關書屏的詩句,如“家有寒山詩,勝汝看經卷。書放屏風上,時時看一遍” “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遍”。劉禹錫有詩:“雖陪三品散班中,資歷從來事不同。名姓也曾鐫石柱,詩篇未得上屏風。”另外還有題屏風詩,例如白居易的《題詩屏風絕句》《題海圖屏風》、宜芳公主的《虛池驛題屏風》、溫庭筠的《題李相公敕賜錦屏風》、貫休的《觀懷素草書歌》、許謠的《題懷素上人草書》、魯牧的《懷素上人草書歌》、劉坦的《書從事廳屏上》,還有竇冀、蘇渙、錢起等人的詩歌,舉不勝舉。由此可以看出唐代詩人書屏是普遍現象,體現出唐代詩歌創作與書法活動的空前繁榮。
三、唐代書法屏風的藝術功能
(一)審美功能
屏風作為一種獨特的藝術審美形式,獲得唐代社會上層的青睞與追逐。收藏家、鑒賞家對于書畫作品的名氣和品質要求很高,唐代以前由于長時期的戰亂以及人為因素,對藝術品造成巨大毀壞,使得具有收藏價值的書畫作品數量極其有限。供需關系的緊張,促使唐代藝術交易市場繁榮,藏品價值不菲。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記敘:“則董伯仁、展子虔、鄭法士、楊子華、孫尚子、閻立本、吳道玄,屏風一片,值金二萬。次者售一萬五千自隋以前多畫屏風,未知有畫障,故以屏風為準也。其楊契丹、田僧亮、鄭法輪、乙僧、閻立德,一扇值金一萬。”
唐人以書法作屏風的裝飾,體現以書法為美的審美取向,最典型的就是將名家書法作品裝成屏風欣賞,以此顯示自己的審美品位。徐浩《古跡記》中記載:“至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奏事承恩,乃乞大小二王真跡,敕賜十二卷,大小各十軸,楚客遂裝作十二扇屏風,以褚遂良《閑居賦》《枯樹賦》為腳,因大會貴要,張以示之。”記錄了唐中宗時期,因中書令宗楚客辦事得力,而蒙受帝王恩澤,于是向朝堂討要大小“二王”的書法真跡,朝廷賞賜他“二王”的真跡作品有十二卷,大小共計各十軸,宗楚客受賞后就將這十二卷真跡裝裱成十二扇屏風,就算是褚遂良的書法作品《閑居賦》《枯樹賦》也僅僅作為腳注映襯。因此宗楚客借此機會,會聚尊貴顯要之人前來欣賞“二王”真跡。在此,將屏風作為書法欣賞的載體,提供的不僅僅是視覺感官上的愉悅,更多的是個人的審美趣味以及社會的流行趨勢。
(二)教化功能
唐人的書法屏風不僅用于裝飾欣賞,還起到教誨勸誡的作用。漢代后,屏風作為規誡性韻文的載體成為道德和政治上訓誡的媒介。至唐代,帝王內殿的御座旁,多陳設書寫治國要義的屏風,如唐太宗時的“戒奢屏”。貞觀之初,唐太宗“抑損嗜欲,躬行節儉”,那時政通人和、國泰民安,長治久安的局面卻導致李世民逐漸滋長驕奢情緒。貞觀十三年(639),魏征書《十漸不克終疏》,勸諫唐太宗治國理政要崇尚儉約杜絕奢靡。李世民讀完“深覺詞強理直”(《貞觀政要》),下旨將此奏章謄寫于自己起居室內的屏風上,以便“朝夕瞻仰”,后人將此屏風稱為“戒奢屏”。李世民以屏風上的諫疏為鑒戒,時刻提醒自己要以古為鑒,一改奢侈驕縱之錯,克勤克儉,以天下為己任,繼續保持執政之初的治國之風。房玄齡曾集古今家訓書于屏風之上,用來提醒、訓誡子孫,以防驕奢。《新唐書·房玄齡傳》載:“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侈,集古今家誡書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于,足以保躬矣!”《新唐書》中對唐代書法家徐浩的論述:“始,浩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八體皆備,草隸尤工。”《宣和書譜》記載司空圖之父司空輿曾得到徐浩的書法屏風真跡,屏面題寫:“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司空輿稱贊徐浩的書法屏風曰:“人之格狀或峻,則其心必勁,視其筆跡,可以見其人。”并以此為家族戒圖,贊曰:“儒家之寶,莫逾于此屏。”由此可以看出唐代書法屏風在當時擁有極高的藝術品格和教誨勸誡作用。
唐太宗李世民對書法極為鐘愛和推崇,據《唐朝敘書錄》載:“貞觀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太宗自為真草書屏風以示群臣,筆力遒健,為一時之絕。”唐太宗不僅親自書寫屏風,還下令讓虞世南寫書法來裝飾屏風,《舊唐書》記載:“(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風。”此外,高宗、玄宗、憲宗等也多喜好書法,據《舊唐書》記載,元和四年(809)七月,唐憲宗李純曰:“御制《前代君臣事跡》十四篇,書于六扇屏風,是月,出書屏以示宰臣。”統治階級自書屏風,一方面出于對書法的喜愛,書屏以展示自己的書法藝術;另一方面統治者深諳文字的教化功能,其政教觀念也從書法的內容上反映出來。
(三)抒情功能
書法的抒情觀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隨著思想的解放、藝術的自覺,書法家極力尋求個性的張揚,抒情觀體現在書體的多樣性上。南齊王僧虔在《筆意贊》中提出“心手達情”,認為書法創作的主體應當注重表現自我,體現書者本人的情感價值,這為唐代藝術的繁榮提供了一個相對寬松的思想環境,也為唐代書法發展的多元化打下基礎。盛唐時期審美思潮變遷,逐漸由六朝時的“妙”轉向空前的“狂”。特別是在屏風上的書寫形式,對草書家的影響最大,也促成唐代狂草藝術的成熟。與桌面上的紙箋絹素相比,尺幅巨大的屏風所提供的書寫空間,自然而然使書家的創作心態和方法產生轉變。
唐代詩人白居易《素屏謠》中提到:“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可見得當時張旭的狂草是屏風的絕妙裝飾之一。張旭嗜酒,酒酣之時,寫草書受酒精催化,創作靈感沖破理性束縛,在墻壁或屏風上隨處揮灑,盡情宣泄,抒胸中逸氣,書法自然飄逸而神韻超常(圖2)。施宿編纂《嘉泰會稽志》記載張旭與其好友賀知章二人出游,“凡見人家廳館好墻壁,以及屏障,往往忘機興發,落筆數行,如蟲穿飛走,古之張、索難能及也。”
張旭之后,涌現出眾多的狂草書家,據記載有懷素、鄭虔、釋亞棲、釋高閑等,其中以懷素最為著名(圖3)。“草圣”懷素常寫屏風,唐代多有品評懷素屏風書法的詩篇。韓偓曾作《草書屏風》曰:“何處一屏風,分明懷素蹤。雖多塵色染,猶見墨痕濃。怪石奔秋澗,寒藤掛古松。若教臨水畔,字字恐成龍。”此詩乃詠書法屏風上懷素的草書作品,最后四句以“怪石”“寒藤”“古松”這樣的山水景色來比喻懷素草書飛動的筆力氣勢與蒼勁的書法字跡,看出詩人對于此書法屏風的用心體會。馬云奇有詩《懷素師草書歌》云:“一昨江南投亞相,盡日花堂書草障。”任華《懷素上人草書歌》曰:“誰不造素屏?誰不涂粉壁?粉壁搖晴光,素屏凝曉霜,待君揮灑兮不可彌忘。”且此詩中有對懷素醉后興發、提筆忘我、縱情書寫的癲狂狀態描寫:“駿馬迎來坐堂中,金盆盛酒竹葉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顛狂。一顛一狂多意氣,大叫一聲起攘臂。揮毫倏忽千萬字,有時一字兩字長丈二。”懷素《自敘帖》也記錄了他的創作狀態:“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唐人戴叔倫曾詠道:“詭形怪狀翻合宜。”狂草的表現形式突出情感的宣泄,這種“癲狂”狀態下創作的書法藝術,不僅是一種時代的產物,也是一場視覺上的革命。
盛唐時期流行張揚個性、不拘法度的浪漫主義精神,憑借藝術形式創造出自我感性的藝術境界,賦予筆墨線條更多的人格情感,此時屏風成為即興式創作的重要載體。
四、結語
唐代書屏風氣很濃,形成一種獨特的書法藝術品類,為唐代書法增添光彩。由于受屏風材質的自然屬性所限制,唐代書法屏風至今一無所存,雖不能目睹唐代書家屏風的書跡真容,但通過品讀古人的詩文,也能從中發現無限玄妙。
參考文獻:
[1][唐]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全譯(修訂版)[M].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9.
[2][清]彭定求編.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3]金學智.中國書法美學[M]. 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4.
[4][美]巫鴻著,文丹譯.重屏:中國繪畫中的媒材與再現[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5]沃興華.應當重視書法展示空間的變化[J].中國書畫,2003(01):36-40.
作者簡介:
石楊(1992—),女,漢族,山東威海人。山東大學(威海)藝術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 研究方向:藝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