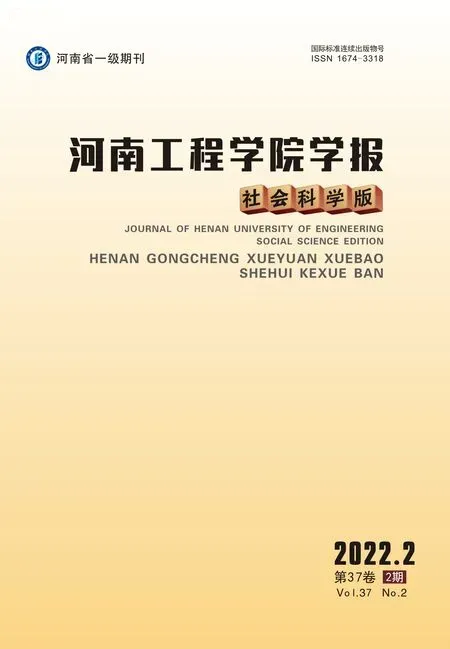狹義著作權視角下游戲玩家操作行為的性質分析
李 昊
(華東政法大學 知識產權學院,上海200042)
玩家的操作是一種創作、表演,還是僅為一種娛樂行為,著作權法領域仍未形成一致結論。然而,厘清游戲玩家操作行為的著作權法律屬性對爭議的解決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操作行為的法律屬性將直接決定游戲玩家在著作權法上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它還會影響游戲畫面的版權歸屬及合理使用的認定問題。既然爭議的源頭是玩家的操作行為,那么只有明確操作行為的法律屬性才能成功解決有關網絡游戲的著作權糾紛。《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以下簡稱《著作權法》)參照大陸法系的立法模式,在狹義著作權之外還設立了鄰接權。因此,玩家操作行為的著作權法律屬性存在兩種可能:創作和表演。其中,關于創作屬性的爭議點主要集中在認定標準及適用思路兩個方面。本研究僅從狹義著作權角度按照“明確獨創性標準-分析獨創性來源-判斷獨創性貢獻”的邏輯,主張從內容生成和畫面拍攝兩個角度對玩家操作是否屬于創作行為進行討論。
一、創作作品的認定堅持獨創性的客觀效果標準
當下,學術界與實務界關于玩家操作是否創作了作品主要立足于主觀意圖和客觀行為兩個角度進行考慮。不可否認,游戲畫面的形成與玩家的操作密切相關,但如果據此認定玩家的操作屬于創作,恐有適用“額頭流汗”原則之嫌疑,有違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同時,創作作為一種事實行為,它的認定與玩家的操作意圖無關。正確的做法是堅持客觀效果標準,操作行為只有在做出獨創性貢獻的情況下才可以被認定為創作。
(一)采取行為標準認定創作存在困境
從現實情況來看,基于行為本身來判斷玩家是否參與了創作存在一定的困境,大多呈現為一種見仁見智的局面。例如,在“奇跡MU”案(1)參見(2015)浦民三(知)初字第529號民事判決書。的一審判決中,被告就曾表示,“畫面是由玩家借助網絡游戲提供的各類工具獨創而成”。質言之,被告認為,玩家的操作是在創作作品。一審法院對此并不認同,法院認為,“游戲畫面由游戲引擎按照既定規則調取開發商預先創作的游戲素材自動生成”“玩家的行為并不具備作品創作的特征”。以《我的世界》等沙盒游戲為例。一些學者[1-2]認為,在此類游戲中,游戲開發商只是單純地為玩家提供創作工具,游戲畫面的生成取決于玩家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在這種情況下,玩家的操作無異于在創作美術作品。因此,這種操作行為可以被認定為一種獨立的創作。然而,在“《我的世界》訴《迷你世界》侵犯著作權”一案(2)參見(2019)粵03民初2157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玩家的操作實質上是在調用開發商事先預設的各種游戲元素,與創作作品相差甚遠。
由是觀之,認為玩家的操作行為構成創作的觀點有法律和理論依據,而認為玩家的操作不構成創作的觀點也有充分的理由。如此僵持下去,并不會對學術研究帶來任何幫助,而且也不會改變司法實踐是基于政策背景做出裁判的現狀。因此,不能淺嘗輒止地從客觀角度談論創作行為本身,而應該對游戲畫面的構成要素及其來源進行實質剖析。否則,“玩家的操作行為是否屬于創作”仍舊是一道無解命題。
(二)創作的認定與玩家的主觀心態無關
有學者表示,玩家的操作“不具有創作所特有的個人思想和獨特表達”[3]。其邏輯在于,操作行為主要是技巧和經驗的運用,由此產生的整體畫面并不具有獨創性[4]。在他看來,雖然創作是一種事實行為,但是仍然需要行為人具有創作的主觀意思,考慮到玩家的操作目的是競技而非創作,故操作行為不可能產生作品[5]。然而,上述觀點是經不起推敲的。如果把創作意圖作為必備要件,此舉無異于要求玩家具有創作的效果意思。但事實行為是無關于心理的行為,它不以表現內心的意思內容為必要。小孩在黑板上亂涂亂抹的行為之所以不會產生作品,并不是因為他缺乏創作的主觀意思,而是因為這寥寥幾筆缺乏最起碼的藝術美感和智力創造成分。也就是說,有無創作意圖并不會影響創作行為的認定。只要創作成果具有獨創性,即便是“神來之筆”也應當屬于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創作。
事實上,玩家的主觀心態只能決定操作行為屬于何種類型的創作。在《著作權法》中,創作可以表現為多種行為方式,包括獨創、合作、即興表演及演繹等。其中,合作作品與演繹作品存在本質區別,前者不但要求合作雙方都實質參與作品的創作過程,而且要求雙方具有共同創作的意愿。由此可見,玩家的操作意圖僅影響創作的行為類型,而不涉及創作行為的認定。
(三)創作的認定標準是操作效果具有獨創性
創作行為的認定應摒棄客觀行為標準與主觀意圖標準,轉而采用客觀效果標準。
《著作權法》(2020年修訂)第十一條第二款規定,“創作作品的自然人是作者”。由此得知,玩家必須滿足兩項法定要件才能成為作者:一是玩家實施了創作行為,二是該行為產生了具有獨創性的智力成果即作品。這兩項要件之間是“因”與“果”的關系,作品是創作行為的結果。
生活中的創作與法律上的創作有所不同。就前者來說,創造性成果的有無與創作過程無關。換言之,生活中的創作不必然也不要求產生作品。與之不同,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創作行為是一個法律問題,唯有創作行為產生獨創性的客觀效果即作品才能從法律上得到認可。因此,與其討論操作行為是否構成著作權法意義上的創作,不如探討玩家是否對游戲畫面的形成做出了獨創性貢獻。獨創性既是作品的構成要件,又是對行為結果的客觀評價。只有勞動成果具有獨創性,產生作品的行為才可以被稱為“創作”。由是觀之,操作行為是否屬于創作,關鍵在于其是否對畫面的形成做出了獨創性貢獻。
二、游戲畫面的作品屬性及其獨創性來源
學術界與實務界存在一種想當然的觀點,即單純的交互式操作并不足以認定玩家對畫面的形成做出了獨創性貢獻。這一觀點主要是基于游戲畫面的作品歸屬及漠視視聽作品的獨創性構成得出的。要澄清上述誤區就必須回歸到對游戲畫面獨創性來源的分析上。
(一)游戲畫面屬于視聽作品
游戲畫面屬于視聽作品。鑒于已經有學者[6]從正面對這一結論詳盡闡述,本研究僅就部分代表性爭議予以回應。
第一項爭議,游戲畫面的“雙向交互”與電影作品的“單項播放”存在本質不同。游戲畫面不是被動欣賞的作品,玩家不是“看游戲”,而是“玩游戲”。這種體驗方式的不同對游戲畫面產生的影響無非有兩點:其一,它包含了玩家與其他玩家之間的互動交流;其二,它無法離開玩家的操作行為而單獨存在。那么,這些差異能否成為游戲畫面構成視聽作品的阻礙?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類電影作品的實質是靜止畫面的集合和連續播放(3)參見(2020)京73民終189號民事判決書。。連續畫面是否具有單向性并不是認定類電影作品的法定要求(4)參見(2020)粵知法著民初字第16號民事判決書。。簡言之,只要畫面具有連續性就可以構成視聽作品。而“連續動態性”恰好是游戲畫面最突出的特征[7]。種種跡象表明,游戲畫面劃歸于視聽作品不存在問題。當然,不能否認游戲畫面與傳統視聽作品相比存有明顯差異,但是當我們試圖用著作權法去保護一個新的對象時,往往更為看重的是,新對象與在先保護的對象之間是否存在相似性[8]。因此,“雙向交互”不應該成為影響游戲畫面構成視聽作品的理由。
第二項爭議,游戲畫面不具有“可固定性”。因“可固定性”引起的質疑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游戲畫面不可固定,二是游戲畫面不可窮盡[9]。第一項質疑實際上是對“固定”的理解存在偏差,即“可以固定”與“實際固定”之爭。這樣的爭論在網絡游戲的問題上毫無必要。無論是基于《著作權法》,還是基于現實的市場需求,如果游戲畫面沒有被固定,那么一切關于游戲畫面是否構成視聽作品的討論都不具有合理性[10]。這就好比口述作品沒有被固定在載體上,不但在發生侵權糾紛時難以舉證,而且許多國家甚至不會對其給予著作權法上的保護。在實際發生的多數案例中,游戲畫面要么已經被實際錄制,要么已經成為直播畫面的一部分被取證。也就是說,涉案游戲畫面從一開始就已經被固定。在這種情況下,游戲畫面是否需要被固定的討論已經失去了意義。第二項質疑與游戲畫面是否屬于視聽作品不存在任何關系。一方面,“攝制在一定介質上”并不要求游戲畫面表達的內容具有“唯一確定性”。另一方面,關于“畫面的不可窮盡會給開發商帶來無期限保護”[11]的疑慮,與其說質疑點在于游戲畫面不可窮盡,不如說質疑者更為關注的是玩家是否可以對這些畫面主張權利。正如質疑者所說:“如果真能獲得任何的權利,至少應由該游戲的設計人、制作者與所有的玩家共同享有。”[11]換言之,該質疑并不是在討論作品是否適格,以及作品的類型是什么,而是在分析誰更有資格成為權利的主體。因此,游戲畫面是否具有“可固定性”其實是一個假命題。如果非要說有爭議存在,也應當是游戲畫面權利歸屬的問題,與作品屬性無關。
綜合上述分析,游戲畫面被劃歸為視聽作品并不違背著作權法的基本原理。
(二)游戲畫面的版權歸屬與其獨創性來源無關
網絡游戲的構成主要包括游戲引擎和游戲資料庫兩個部分。游戲引擎是一種計算機軟件程序,包括主引擎、輔助代碼、插件、執行命令等;游戲資料庫則主要由音頻因素和視頻因素構成,具體包括圖片、動畫、音效、文檔等。在產業界,游戲引擎和游戲資料庫一般被統稱為游戲的靜態數據。而本研究所說的游戲畫面指在玩家操作運行程序后,通過電腦屏幕以“連續動態圖像”的方式呈現的文字元素、靜態畫面、背景音樂及過場動畫等整體內容[12]。
眾所周知,游戲開發商為游戲畫面的生成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因此,有學者[13]指出,按照《著作權法》的規定,游戲開發商應獨自對游戲畫面享有著作權,玩家不能對畫面本身主張權利。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游戲畫面屬于視聽作品,但這并不代表畫面的獨創性全部源于開發商的貢獻。暫且不議游戲畫面的版權分割問題,當初立法者只是出于電影制片人的巨額投資和電影作品的商業運作等方面的考慮,才將制片人作為視聽作品著作權人的第一順位,而只允許編劇、導演、攝影、作詞、作曲等作者保留署名權:理論上講這是一種著作權的法定轉讓[14]。此舉與游戲畫面的獨創性來源不存在關聯。即便可以由此認定游戲開發商可以享有與電影制片人同等的地位,這一結論的得出也與游戲畫面的獨創性來源不存在任何關聯。
(三)玩家操作可能為游戲畫面帶來獨創性
玩家操作是否為游戲畫面做出了獨創性貢獻需從內容生成和畫面拍攝兩個角度進行考慮。長期以來,版權領域內一直存在著一種觀點,即玩家單純的操作行為不會為游戲畫面帶來獨創性。事實是否如此,我們可以從視聽作品的獨創性來源入手一窺究竟。此前,游戲畫面的獨創性分析存在一種隱藏的慣性思維,即畫面中各種元素的個性化設計決定了畫面本身的獨創性。由于畫面中的內容是由游戲開發商提前預設好的,因而游戲玩家只是從游戲提供的有限方案中進行選擇(5)Midway Mfg. Co. v. Ar′1., Inc., 704 F. 2d 1009,1011-1012 (S.D.N.Y. 1983)。。最終有部分學者據此也得出了游戲玩家的操作行為無法提供獨創性貢獻的結論。這種聚焦于畫面元素的分析過程其實是對視聽作品獨創性構成的誤解和漠視。首先,畫面內容的獨創性取決于元素的選擇,但這種選擇不只是元素自身的設計,還包括各類元素的篩選與編排。其次,視聽作品的獨創性不只來源于畫面內容的選擇,對素材的選擇、對素材的拍攝、對拍攝畫面的選擇及編排都能夠體現其獨創性[15]。其中,對拍攝畫面的選擇及編排主要發生在電影的后期剪輯及視頻制作環節。顯然,單純的游戲操作并不涉及這方面的問題。因此,玩家操作體現獨創性貢獻的地方只可能存在于對素材的選擇和對素材的拍攝兩個方面。從理論上講,對素材的選擇主要是看玩家如何對開發商預設的內容進行選擇和運用,重點是考察操作行為是否生成了具有獨創性的新內容;對素材的拍攝主要是分析玩家是以何種角度和手法拍攝被選定的內容,亦即玩家操作是否對畫面的拍攝做出了獨創性貢獻。綜上所述,玩家操作有可能為游戲畫面帶來獨創性。下文將從內容生成和畫面拍攝兩個角度對玩家操作的行為進行具體分析。
三、玩家操作行為生成獨創性內容的分析
操作行為是否創作出了具有獨創性的新內容,需要從“獨”和“創”兩個角度分別討論。現階段,著作權法領域更熱衷于直接分析游戲畫面的獨創性,從而再對操作行為是否生成了獨創性效果進行回應[16]。這種通過外顯特征進行判斷的做法最終會在獨創性效果的歸屬問題上產生爭議。從玩家角度進行分析,在一些非競技類游戲中,玩家的操作行為屬于在已有作品上再創作,可能會生成具有創造性的新內容。
(一)“獨”的角度:操作行為屬于“用戶衍生內容”
“獨創性”中的“獨”指“獨立創作,源于本人”,共包含兩種情況:一是行為人從無到有進行獨立創作,二是行為人以已有作品為基礎進行再創作[17]20。換言之,第一種情況屬于“用戶原創內容”,勞動成果完全由自己獨立完成;第二種情況屬于“用戶衍生內容”,會涉及使用他人作品的問題。那么,玩家的操作行為屬于哪一種創作模式?
本研究認為,在網絡游戲中難以出現“用戶原創內容”的情況,原因有三點。第一,從形式上來看,用戶操作行為不符合“用戶原創內容”的創作模式。以時間為序,開發商預設的靜態數據經過玩家的操作行為生成游戲畫面,這一過程更貼合“用戶衍生內容”的創作模式。第二,從實質內容出發,操作行為所生成的內容必然利用了原有游戲作品里的素材。玩家的操作行為固然會導致游戲畫面最終呈現的內容難以確定,但是正如美國法院所言,無論玩家如何操作,游戲畫面所呈現的不同內容中依然存在實質不變的影像和重復序列(6)Williams Elecs. v. Artic Int′1, Inc., 685 F.2d 874 (3th Cir.1982). Stern Electronic, Inc. v. Kaufman, 669 F.2d 856 (2th Cir.1982)。。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玩家只是借助操作行為對靜態數據中的視聽素材進行了“再拼湊”“再組合”[18]。第三,即便是給予玩家超高自由度的沙盒游戲,也難以存在“用戶原創內容”的情況。“給他們一個沙盒,他們就會建出城堡”[19]是沙盒游戲的設計理念。這句話具有極強的迷惑性,會讓人誤以為此類游戲是通過設計游戲元素與游戲材料來向玩家提供自行創作的工具。事實上,在沙盒游戲中,玩家能夠使用的材料已被存儲在游戲開發商預設的靜態數據里,房屋的樣式、磚塊、顏色等材料種類都是玩家無法決定的,玩家唯一能做的是對上述材料進行選擇和編排。由此來看,沙盒游戲的開發者并沒有放棄對游戲世界的控制權,玩家仍是在其設計的游戲框架內進行操作。質言之,沙盒游戲提供的不是一支畫筆,而是一些創作素材,部分學者把游戲材料比喻為玩家的創作工具并不合適。綜上所述,從“獨”的角度來看,玩家操作行為更接近于“用戶衍生內容”這種創作模式。
(二)“創”的角度:“用戶衍生內容”的創造性需具體分析
玩家的操作行為是否產生了獨創性內容還需從“創”的角度對其勞動成果進行分析。“獨創性”中的“創”指具有創造性,要求勞動成果具有一定的智力創造水準。如上文所述,玩家在操作過程中必然涉及對靜態數據的使用,故玩家的操作行為首先是一種復制行為。當然,游戲開發商推銷游戲的目的就是為了吸引玩家參與游戲。可以說,這種“復制”已經得到了開發商的默示許可,并且如果“用戶衍生內容”符合“創”的要求,玩家的操作行為就應當是一種演繹行為。因此,“用戶衍生內容”是否具有創造性決定了操作行為是“復制”還是“演繹”。本研究認為,這一問題需要從創造高度及創造空間兩個方面予以考慮。
首先,玩家操作行為輸出的內容需要具有一定的創作高度。此前,有美國法院認為,玩家的操作行為就好像是“在電視上更換頻道”(7)Midway Mfg. Co. v. Artic Int′1, Inc., 704 F.2d 1012 (7th Cir.1983)。。換言之,此種觀點認為,游戲畫面是開發者預先設計的,玩家的操作行為是一種單純調取游戲靜態數據的過程[20]。從游戲運行的原理出發,崔國斌[21]則指出,靜態數據是開發商事先固定的內容,而動態圖像是因玩家操作而臨時呈現的內容。在“額頭流汗”原則已經被著作權法普遍放棄的情況下,上述兩種對游戲操作行為的分析顯然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因此,玩家操作行為是否會實際參與游戲畫面的生成過程是解題的關鍵。在當今的游戲世界,游戲程序文本與游戲畫面文本理應被一分為二地看待。游戲程序文本主要包括靜態數據的設置及游戲畫面運算的方式。游戲畫面的生成通常需要經歷建模和實時渲染兩個步驟:建模指用點、線、面、貼圖、材質等元素構建逼真的物體和場景,實時渲染是把模型在視點、光線、運動軌跡等因素作用下的畫面邊計算邊輸出顯示的過程[22]。上述工作都是通過游戲引擎來完成的。換言之,游戲引擎具有自主建模和實時渲染的能力。這意味著游戲畫面的生成具有臨時性,并非開發商提前預設的。質言之,隨著電子游戲產業的高速發展,游戲畫面的生成已經不再是一種公式化的輸入和輸出,游戲玩家存在參與到游戲畫面創作過程的可能性。
其次,網絡游戲還要為玩家留下充足的智力創造空間。在已有作品的基礎上進行再創作要求操作效果必須與游戲本身存在的內容具有明顯的區分度,只有這樣才能認為其符合創造性的要求。根據自由度的高低,網絡游戲可以簡單地分為兩大陣營:第一類是以沙盒游戲為代表的給予玩家超高自由度的非競技類游戲,第二類是除第一類游戲以外的其他類型的游戲。通常情況下,只有在第一類游戲中,玩家的操作行為才可能是一種創作。這是因為在沙盒游戲中,玩家可以對道具、材料等進行選擇和編排,從而在游戲中建造出一些虛擬的建筑,這一過程完全有可能發揮玩家的創造力。只要玩家在沙盒游戲中的生成物具有創造性,操作行為就是一種創作。有人會覺得為什么在一些角色扮演類游戲(第二類游戲)中,玩家的操作行為必然是一種復制而不可能是演繹?這種疑問是有道理的,畢竟按照上述理解,所有的游戲畫面都是在玩家的操作下臨時生成的。那么,為何同樣的依據卻可以產生不同的結論?眾所周知,一般的角色扮演類游戲自由度較低,玩家在既定規則下自由發揮的空間甚少,而且水平相近的玩家基本上可以產生相同的游戲畫面,即便是不同水平的玩家也可以通過學習其他玩家的操作技巧而獲得同樣的戰術效果。一般來說,除去思想本身,任何對于思想的表達都可以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但是,即便游戲畫面毫無爭議地是一種表達,由于角色扮演類游戲的操作效果實際上只存在一種或極為有限的表達方式,因而在這種情況下,“思想”與“表達”之間已經沒有明確的界限。依據著作權法中的“混同原則”,不宜將角色扮演類游戲畫面的專有權賦予玩家。相應地,玩家的操作行為也不能被稱為“創作”。
最后,仍需注意,游戲類型的劃分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它只是為法官提供了一種快速審查的思路,不能取代獨創性成為認定“創作”的標準。其一,在形式上為玩家留出創作空間的第一類游戲,操作的過程并不必然產生作品。以一款網絡游戲內部設置的“捏臉系統”為例,法院認為,玩家“捏出”的臉型和五官與初始人物形象相比,只具有無法客觀識別的細微差異,不符合獨創性的要求(8)參見(2020)浙01民終1426號民事判決書。。其二,任何游戲都為玩家留下了自由發揮的機會,只是程度高低不同,即便是在第二類游戲中,玩家也仍然存在創作的可能性。例如,在規則允許的范圍之內,一盤棋怎么下都可以,黑白雙方相互配合從而制造出具有美感的圖片并非沒有可能性(9)例如,有用戶總結了13種五子棋規則下的“心型”擺法。[23]。因此,是否創作出作品,最終仍要落腳在操作效果的獨創性判斷上。
四、玩家操作拍攝獨創性畫面的分析
如前所述,此前研究忽視了從拍攝角度分析游戲畫面的獨創性。游戲畫面的形成過程與電影拍攝相似,在電影作品中,真正反映劇本作者獨創性的是情節與結構,而攝影師的獨創性貢獻通常體現在如何更好地“拍出”劇本情節。玩家拍攝自制劇本,可以認為其操作行為對畫面的拍攝做出了獨創性貢獻。
(一)游戲情節的來源
在“太極熊貓”一案(10)參見(2015)蘇中知民初字第201號民事判決書。中,法院認為,ARPG類電子游戲中,角色的選擇、成長、戰斗等玩法設置本身具有敘事性,依托游戲界面呈現的詳盡的游戲玩法規則,類似于詳細的電影情節。由此來看,網絡游戲的情節與游戲規則具有難以分割的混同性。游戲開發者預設的游戲規則、游戲地圖、人物技能等各種游戲資源共同完成了游戲情節的配置,相當于為網絡游戲的運行提供了一個“劇本”,而玩家只有按照游戲規則的要求進行操作才能不斷推動游戲劇情的發展。因此,游戲開發者相當于“劇本作者”,玩家的一切操作都是在靜態數據預設的規則框架內完成。
網絡游戲也可以用來敘述一個游戲規則以外的故事。近年來,游戲玩家已經不再滿足于追逐游戲的勝利,而是將網絡游戲作為自己創作作品的工具,用來制造一些游戲視頻。以《絕地求生》為例,該游戲已經誕生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視頻,例如此前火爆網絡的“用《絕地求生》還原《亮劍》”[24]“用《絕地求生》拍攝感人動畫”[25]等。上述視頻足以表明,靜態數據既是一個可讀的文本,又是一個可寫的文本:盡管它提供了不可變更的游戲框架,但也為玩家留出了自由“書寫”的空間。因此,靜態數據預設的劇本不是游戲情節的唯一來源,玩家同樣可以成為劇本的作者。
(二)游戲情節的拍攝
在具有自制劇本的情況下,玩家當然可以憑借其獨創的游戲劇本受到《著作權法》的保護,甚至還可以控制由此產生的游戲畫面的進一步傳播,但是這都不足以證明操作行為本身對畫面的獨創性做出了貢獻。當然,如果操作行為實際參與了劇本的拍攝,則可以認為畫面的部分獨創性是源于玩家的貢獻。如前所述,游戲畫面是由游戲引擎臨時生成的。這意味著,對于網絡游戲來說,游戲開發商決定畫面如何展現,但是這并不代表玩家沒有機會參與畫面生成的過程。考慮到電影的拍攝與攝影具有相似性,本研究將二者進行類比。攝影過程中的獨創性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拍攝技能,包括對拍攝角度、距離、光線和明暗等進行選擇;二是拍攝時機,包括對時間和場景的把握;三是拍攝對象,包括對被拍攝者的姿勢、表情、服裝及拍攝現場進行設計和布置[17]100。對于游戲畫面的生成來說也是如此。只要玩家的操作能夠在上述三個方面之一做出獨創性貢獻,其操作行為就屬于創作的范疇。
那么,玩家能否控制開發商預設在游戲里的攝像鏡頭?與拍攝電影相似,游戲開發商在每一個游戲場景內都設置了多個鏡頭,即時捕捉游戲場景發生的變化。除此之外,與電影拍攝不同的是,網絡游戲通常會在游戲角色身上設置一個“行走的鏡頭”,以帶給玩家最好的視覺體驗[26]。這表明玩家可以憑借其操作行為帶動鏡頭的轉換。
通常,玩家在規則的指引下進行操作。換言之,操作行為完全是出于游戲的目的,玩家對于游戲畫面的生成無暇顧及。相應地,游戲畫面的生成順序也是按照開發商設定的游戲劇本層層遞進。如果說在體育賽事直播中不同的人擔任導播畫面會存在差異,這尚存些許的個性因素,那么不同的玩家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操作呈現的畫面大同小異,可以說毫無獨創性可言,而且從生成過程上看,這種情況下畫面的產生與機器自動攝錄照片并無二致。由于機器拍攝不涉及人工干預和選擇,因之形成的照片普遍被認為不具有獨創性[27]。類比來看,在正常操作下,玩家同樣不會對游戲畫面的拍攝做出獨創性貢獻。
如果玩家是按照自制劇本進行操作,則情況會不同。一方面,玩家的心態已經從游戲轉變為創作,不會按照游戲規則按部就班地操作;另一方面,為實現劇本中的情節,玩家會通過自身的操作對拍攝的手法、時機乃至場景或人物的安排做出個性化的選擇,具體包括各個人物的出場、戰斗及場景變換等。如此一來,上述過程能夠體現出玩家富有個性化的選擇是一種創作。
綜上所述,只有玩家利用網絡游戲拍攝自己的劇本情節時,才可以認為其對畫面的拍攝做出了獨創性貢獻。
五、結語
網絡游戲引發的著作權糾紛之所以復雜,主要原因在于對于玩家操作行為的法律屬性仍未有清晰的界定。著作權形成于作品的創作行為,其權利類型的確定與適用范圍的劃分也是以行為方式為標準。因此,明晰玩家操作行為的法律屬性對于解決與著作權有關的網絡游戲問題至關重要。
對于游戲玩家操作行為的定性不能一概而論,能夠產生獨創性效果的操作行為屬于創作的范疇。本研究從狹義著作權角度入手,對游戲玩家的操作效果進行了分析。從內容生成來看,在一些自由度較高的非競技類游戲中,玩家的操作行為更可能產生具有獨創性的新作品。從畫面拍攝來看,只有玩家在落實自己的劇本時,才能認為其操作行為對畫面的拍攝做出了獨創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