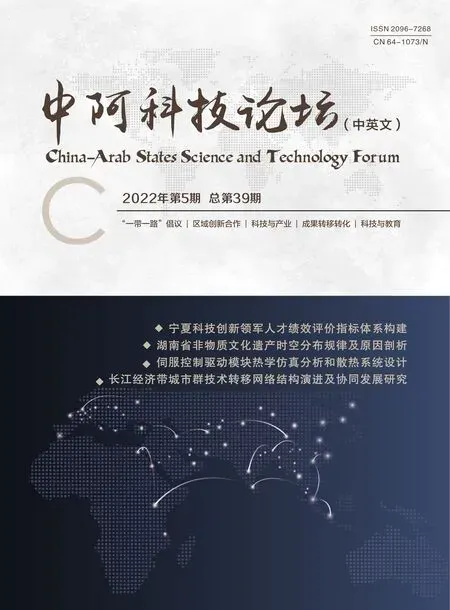“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問題分析
蔣卓強
(浙江警官職業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發揮民航重要的戰略產業作用,推進民航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設“空中絲綢之路”,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組成部分。截至2021年9月,與我國簽署航空運輸協定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已達103個,強力推動了區域經濟發展與民航強國建設[1]。研究民航管理部門、民航企業、民航機場等在應急管理中的共性問題,對于貫徹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建設好“空中絲綢之路”、促進區域經濟復蘇具有重要意義。
1 “一帶一路”背景下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問題
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工作,主要是在減緩、準備、響應、恢復的應急管理四階段中建設民航應急管理預案、體制、機制、法制。應急管理不僅僅是突發事件發生后的應急響應,還包括事前預防、事中控制、事后處理。突發事件不僅僅指飛行危險事件、空管不安全事件、機務維修不安全事件、機場地面故障事件等自然屬性的安全生產事故,也包括擾亂行為與非法干擾行為等社會屬性的公共安全事件。比如機械的不安全狀態導致的機艙內煙霧、起落架故障、客艙失壓等,人的不安全行為引起的沖出跑道、機尾擦地、重著陸等,環境的不安全條件引發的湍流、跑道異物、鳥擊等,空管設備故障導致的跑道侵入,機場施工事故、油庫失火、無人機干擾引起的臨時停航等,還有尋釁滋事、妨礙機組成員履行職責、毀壞使用中的航空器等擾亂航空器良好秩序、危害航空安全的事件等。
國際民用航空組織(ICAO)對各國開展安全監督審計(USOAP),主要審計國際民用航空公約以及附件實施等情況,比如從航空立法和民航規章、國家航空體系和安全監督職能、附件1《人員執照系統》、附件6《航空器的運行》、附件8《航空器適航性》、附件11《空中交通服務》、附件13《航空器事故和事件調查》、附件14《機場》共8個方面檢驗各國民航產業是否符合標準,也從側面反映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航產業應急管理現狀。其中,審計主要要素有效實施得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柬埔寨0項,馬爾代夫4項,俄羅斯3項,老撾4項,烏茲別克斯坦3項,格魯吉亞6項,土庫曼斯坦0項,加納8項,緬甸2項,吉爾吉斯斯坦5項,埃塞俄比亞0項,盧旺達7項[2]。總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航產業應急管理能力還有待提升。
防患于未然是最好的應急管理,是本質安全理念的體現。把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降到最低,避免次生危機,只是除患于已然。梳理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問題,需更加聚焦預防、預測、預警機制建設。本文通過國際民航組織網、航空安全網數據庫(The Aviation Safety Network)、中國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統中的國際和地區事故信息與國際事故調查跟蹤模塊,梳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工作中的共性問題。
1.1 各國民航標準不一致,應急能力建設不平衡,航班事件易升級為外交事件
截至2022年3月23日,已經有149個國家和32個國際組織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其中非洲52個,亞洲38個,歐洲27個,大洋洲11個,南美洲9個,北美洲12個[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存在差異,民航建設標準不一致,應急能力建設不平衡,部分旅客之間小范圍的航班事件也容易外溢升級為外交事件。比如2015年尼泊爾機場發生事故,由于缺乏應急專用的大型起重機和拖拽設備,導致大面積航班延誤,我國數千名旅客滯留尼泊爾[4];2021年希臘飛立陶宛的航班因非法干擾行為威脅迫降白俄羅斯,引發外交事件[5];甚至部分國家允許帶打火機上飛機。國際民用航空公約以及附件1至19,是各國通過法律法規、規章和管理行動予以執行的最低標準,尤其是附件6《航空器的運行》、附件11《空中交通服務》、附件12《搜尋與救援》、附件14《機場》、附件15《航空情報服務》、附件17《安保:保護國際民用航空免遭非法干擾行為》、附件18《危險品的安全航空運輸》、附件19《安全管理》。然而,并非所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都簽署加入并執行應急能力要求更高、安全標準更嚴的《東京公約》(1963年)、《海牙公約》(1970年)、《蒙特利爾公約》(1971年)、《蒙特利爾議定書》(1988年)、《蒙特利爾公約》(1991年)、《北京公約》(2010年)、《北京議定書》(2010年)、《蒙特利爾議定書》(2014年)等。
1.2 難預測的民航外部破壞威脅大于規律性較強的內部運行風險,應急重救援
根據航空安全網數據庫1942—2021年的民航事故統計數據,來自民航外部破壞威脅與內部運行風險的民航事故都是呈下降的趨勢。雖然內部運行風險導致的民航事故多于外部破壞威脅引起的民航事故,但隨著對民航安全飛行、安全生產運行規律的把握,以及民航產業科技化水平、本質安全理念的提升,民航安全管理體系(SMS)和航空安保管理體系(SeMS)建設的推進,規律性較強的內部運行風險是總體可控的[6]。不過可預測性較低的民航外部破壞威脅大于規律性較強的內部運行風險,前者層出不窮、不斷變化的人為故意破壞的風險來源十分不可控、不確定、不穩定。民航產業的致災因子還是較多,脆弱性還是較高,一個惡作劇式的虛假恐怖信息就會擾亂民航運輸秩序。“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航應急隊伍只能被動地防守,主動出擊、主動防范、主動化解的預防措施較少,只能偏重應急救援,在突發事件發生后盡可能地減少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如果花更多功夫在應急管理中的減緩、準備階段,則可以用1美元的預防成本避免未來4美元的響應與恢復損失[7]。比如美國東方航空401號班機價值20美分的前起落架指示燈燈泡因為技術和設計上的缺陷引發故障,直接導致了民航事故[8];俄羅斯航空593號班機機長不嚴格遵守民航安全規章制度,讓孩子進入飛行中的駕駛艙,導致飛機解除自動駕駛模式失速發生事故[9]。所以從事故原因“4M”因素源頭上避免人的不安全行為(Men)、機的不安全狀態(Machine)、環境的不安全條件(Medium)、管理的混亂缺位(Management),從而消除民航事故隱患風險,顯得尤為重要。
1.3 民航應急預案形式化,動態應急規劃不足,演練輕實戰,應急溝通滯后化
民航應急管理中的準備階段主要包括應急規劃與應急保障體系建設。應急規劃強調應急預案的制定、演練、修訂過程,具有動態持續性。部分國家的民航安全檢查活動中,只片面強調有無靜態的民航應急預案。如果民航應急預案只是用來應付檢查,就會產生麻痹效果,讓民航應急隊伍誤以為有備無患,等到發生突發事件,才發現未全面溝通協調區域內外各方應急資源,未在應急演練中磨合各方應急隊伍,缺乏針對性和實用性。突發事件有時會復合交織疊加,初期情報信息失真,沖突混亂,完全拘泥于靜態的應急預案,有時也容易適得其反。所以過于強調靜態形式化的民航應急預案,忽視應急規劃中分析民航系統脆弱性、協調各方資源、不斷培訓演練修訂的動態過程,是需要反思的。同時部分民航專項應急預案與現場處置方案還過于具體化、煩瑣化,片面強調快速響應而忽視正確響應。尤其是針對2010年的《北京公約》中提到的生物、化學、核放射等危險物質,正確響應比快速響應更重要。民航應急演練可以檢驗應急規劃的有效性與磨合應急隊伍,但程式化的演練輕實戰,缺少無劇本、隨機化和對抗性。應急溝通包括風險溝通與危機溝通,當前發達的網絡媒體片面追求民航負面新聞以獲取眼球經濟的網絡流量,而忽視了對公眾的民航應急文化宣傳教育的職責。民航應急溝通略顯滯后化,直接影響公眾對民航產業的信心。
2 “一帶一路”背景下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對策建議
2.1 校企多方共建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合力提升民航應急隊伍的水平
航空安全員或機上安保員(Flight security officer),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航空器中的專業應急力量,是空中保衛民航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線。專門防范與控制擾亂行為與非法干擾行為,類似機上尋釁滋事、妨礙機組成員履行職責、毀壞使用中的航空器等擾亂航空器良好秩序、危害航空安全的突發事件等。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錘煉學生體能技能,就業方向主要為“空中反”的航空安全員崗位,也可以為“地面防”的民航安檢員崗位。開設的主要課程有“機艙防衛與控制”“機艙突發性事件處置”“異常行為識別與處置”“兩擾行為防控”“民航安保法律法規”“航空安全員職業體能訓練”“航空安保英語”“航空禮儀與形體訓練”“犯罪預防”“治安管理”“航空乘務”“民航概論”等。全國開設有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的院校由2014年的3所上升至2022年的44所,側面反映了民航產業應急管理隊伍的需求增長。新設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的大部分院校并非直屬民航系統,人才培養工作缺少民航業合作基礎,亟須校企多方共建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推進民航產業應急管理訂單班學徒制實習,合力提升民航應急隊伍的水平。
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沿線國家應加強民航產業鏈應急人才聯合培養交流合作,在共同體理念的啟示下,各國校企雙方應避免“學校熱航空公司冷”的現象,擺脫利益、效率等市場準則觀念的束縛。加強課程思政引領,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厚植愛國情懷,堅守保衛國家民航安全的使命和立場,鍛造民航產業應急管理鐵軍。發揮中國民航“一帶一路”合作平臺作用,共建“一帶一路”民航產業應急管理教學資源庫。航空安全員人才培養的主渠道是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從源頭上培養更多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實戰型人才,是合力提升民航應急隊伍水平的關鍵之舉。
2.2 完善各國民航應急法律法規體系,源頭上加強公眾的民航應急文化教育
我國民航產業“飛出去”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輸出民航產業建設標準、擴大國產客機訂單、援建國際機場、推進民航基建產能合作、民航產業鏈應急人才培養、國際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協作等,是民航產業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有效性舉措。加強《北京公約》與《北京議定書》的宣傳和推廣,邀請更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簽署加入[10]。在歷經奧運會、亞運會、世博會、G20峰會等國際性重大活動執勤后,積累的大量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工作經驗可以通過立法的方式固定下來。完善各國民航應急法律法規體系,相關的民航產業應急管理規范性文件也可以上升為部門規章,設置處罰措施。如2014年文萊修訂民航規例,2017年老撾修訂民航法,2018年緬甸修訂飛機規則[11]。對于非法干擾行為的行政處罰過輕,缺少應有的威懾力。各國類似《治安管理處罰法》也需更新完善危害民航安全與擾亂秩序的行為,加大對吸煙、違規使用電子設備、擅開應急艙門等擾亂行為的處罰力度。
在深化民航系統自身安全文化建設的同時,加強社會公眾的民航應急文化教育,也是十分必要的。應急文化是在從事危機管理的活動中逐漸形成的行為方式、思維模式和安全價值觀,決定著關于危機與風險的知識、態度和行為準則。當前公眾過于注重個人現實利益,公共安全意識和集體觀念有待強化,缺少對法律法規的敬畏,“機鬧”行為屢見不鮮。對于鐵路公路延誤,公眾通常都會理解忍耐。對于航班延誤或其他客艙沖突,公眾卻認為民航運輸價格更貴,應有更好的服務,在配合機組人員履行職責前提下的旅客維權意識還需善加引導。同時鼓勵旅客勇于指出并糾正航班中的不正常現象,共同維護客艙秩序和飛行安全。民航應急文化氛圍的營造離不開民航管理部門、民航企業、民航機場的培育推動。媒體是把“雙刃劍”,引導得當能夠讓公眾廣受教育,若引導不當,只會迎合公眾情緒,片面追求“新聞價值”,刻意強化某些敏感因素。因此,在每一起擾亂客艙秩序的新聞報道中,媒體需要強調不同國家法律的不同準則,讓社會公眾更加了解非法干擾行為的刑事責任。
2.3 推進民航應急管理動態規劃協同,精密智控,提升風險識別處置能力
推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航應急管理動態規劃協同,精密智控,提升風險識別處置能力的交流合作還有較大空間。隨著恐怖組織、極端宗教組織和反政府組織等對民航的威脅日益增大,加上民航客艙空中Wi-Fi業務的大規模普及應用,新型毒品、新型爆炸物、電子脈沖爆炸裝置、核生化武器等高科技物品和犯罪手段的威脅越來越復雜,迫切需要更多的技術和方法來應對。在法律法規允許的前提下,應在公共安全部門、民航管理部門、民航企業、民航機場之間開展大范圍的情報信息共享,強化風險共擔意識,或者將公共安全部門大數據研判分析后的航班風險、安全情勢、暴恐密報等情報發送至民航應急管理各部門,讓民航應急人員對機上旅客的背景資料有更多了解,從而可以實現重點監控和精密智控。加大對應急預防技術設備的研發,改善客艙與駕駛艙間的通話報警裝置,改進能更準確識別危險物品的機場安全檢查儀器和微量炸藥探測設備,應用身份識別技術,研發更適應客艙環境的航空安保器械武器裝備,配齊客艙監控設施。總結危險旅客乘機特征,嚴格安檢交接班流程,避免早晚航班安檢疏忽。同時深挖大數據分析應用,通過“AI+異常行為識別”引入安防主動預警技術,如以色列的“可預測旅客過濾法”民航安全檢查措施,運用先進的安全檢查技術自動識別出潛在的異常行為旅客。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在民航動態規劃與應急演練交流合作中發現民航系統技術和設計上的缺陷,彌補民航應急隊伍教育培訓不夠的短板,杜絕應急現場缺乏檢查或指導錯誤的漏洞,避免缺少安全操作規程或不健全的隱患,排除民航應急組織不合理不協調的風險。民航應急管理關口前移與重心上移,完善應急管理中的減緩、準備階段工作。評估民航系統風險,削減航空安全與航空安保致災因子,降低民航系統脆弱性,完善全天預測預警機制建設,兼顧突發事件發生后的業務持續性管理,做好民航應急溝通,疏導民航危機網絡輿情,與軍隊開展應急與應戰一體化合作。中國民用航空安全信息系統中的調查報告模塊公布了我國2018年5月—2021年7月合計39個月間的通用航空55起事故,平均每月1.41起[12]。“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更加關注比民航商業客機事故率更高的通用航空監管。
3 結語
“空中絲綢之路”的建設,是國家“十四五”規劃的重要舉措,是推動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載體,需要“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完善協同開放的合作機制。“一帶一路”背景下民航產業應急管理存在共性問題,需要在減緩、準備、響應、恢復的應急管理四階段中建設民航應急管理預案、體制、機制、法制。校企多方共建民航空中安全保衛專業,合力提升民航應急隊伍的水平;完善各國民航應急法律法規體系,源頭上加強公眾的民航應急文化教育;推進民航應急管理動態規劃協同,精密智控,提升風險識別處置能力。從而提高“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民航的安全性,提升沿線國家航空安全和航空安保監管能力,合力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民航產業與經濟社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