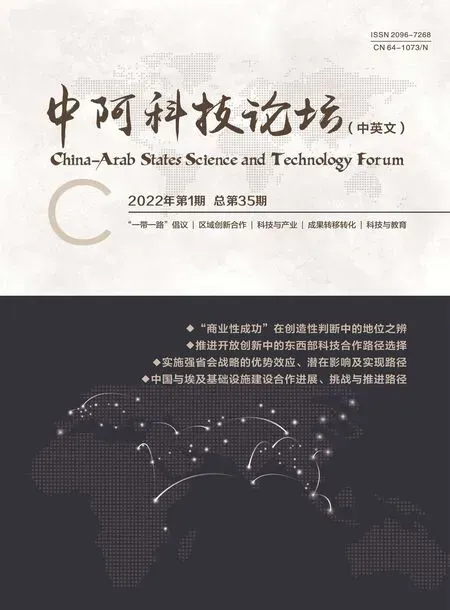“商業(yè)性成功”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地位之辨
馬舒文
(華東政法大學(xué),上海 201620)
1 問題的提出
根據(jù)我國《專利審查指南》的規(guī)定,“發(fā)明在商業(yè)上獲得成功”是判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性時需考慮的其他因素①。基于此,在實踐中當事人常通過主張“商業(yè)性成功”以支持對其發(fā)明的創(chuàng)造性判斷,但得到成功適用的概率微乎其微,其一大成因正在于當前對“商業(yè)性成功”與創(chuàng)造性主要判斷方法間的適用順序尚缺乏統(tǒng)一的認知。
從一般邏輯來看,在討論“商業(yè)性成功”與“三步法”②間的關(guān)系上,大體包括兩種可能:(1)運用“三步法”足以肯定或否定技術(shù)特征的創(chuàng)造性,進而適用“商業(yè)性成功”加以分析,即兩者間乃先后適用的關(guān)系;(2)運用“三步法”尚不能明確是否具有創(chuàng)造性,通過“商業(yè)性成功”的平行適用以輔助結(jié)論的得出。考量我國當前實踐,上述不同邏輯均有所體現(xiàn)。如在“國家知識產(chǎn)權(quán)局專利復(fù)審委員會與胡穎、深圳市恩普電子技術(shù)有限公司實用新型專利權(quán)無效行政糾紛”一案中,最高院指出:“當采取‘三步法’……得出技術(shù)方案無創(chuàng)造性的評價時”,即當“技術(shù)方案本身與現(xiàn)有技術(shù)的區(qū)別在構(gòu)成可授予專利權(quán)的程度上有所欠缺時”……“從社會經(jīng)濟的激勵作用角度出發(fā),商業(yè)上的成功就會被納入創(chuàng)造性判斷的考量因素”③。這一觀點亦得到了實踐中的較多支持④。相反,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一般在采取‘三步法’難以判斷技術(shù)方案的創(chuàng)造性時,才將商業(yè)上的成功納入創(chuàng)造性判斷的考慮范圍”⑤。對比兩種觀點,看似僅有細微的差異,但對創(chuàng)造性結(jié)論的得出卻產(chǎn)生了至關(guān)重要的影響。更進一步來看,這兩種觀點的背后系對“商業(yè)性成功”,乃至輔助判斷要素本質(zhì)認識的差異,反映了對專利激勵理論認識的不同:當立足于上述前一觀點的視角,某一技術(shù)特征對社會經(jīng)濟的激勵作用可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技術(shù)貢獻的不足;而若基于后一觀點,商業(yè)上的成功應(yīng)被認為系針對技術(shù)進步的側(cè)面證明,其在本質(zhì)上并未突破對發(fā)明的技術(shù)評價范疇。
綜觀我國當前實踐,可以發(fā)現(xiàn)“商業(yè)性成功”作為輔助性判斷因素被主張的概率卻非常之高,乃至有美國學(xué)者認為其為最重要的輔助性判斷因素⑥。那么,我國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應(yīng)采何種邏輯?尤其當已得出“無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時,是否可基于“經(jīng)濟激勵”的理論,運用“商業(yè)性成功”對該結(jié)論加以突破?本文擬加以探究。
2 “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和“無創(chuàng)造性”間的內(nèi)涵界分
在探討“商業(yè)性成功”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地位之時,首先應(yīng)明確“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和“無創(chuàng)造性”的內(nèi)涵及兩者間的本質(zhì)界分,否則后續(xù)討論將失去意義。
對此,存在意見主張并不存在“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的狀態(tài),其主要認為:首先,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主觀性源于其法律適用過程的性質(zhì),“大可不必因存在主觀活動就認為這一判斷是一個模糊不清的過程”;其次,若“不能通過‘三步法’對某一技術(shù)方案作出否定評價或者找不到可以使用‘三步法’對某技術(shù)方案作出否定性評價的文獻或其他事實依據(jù)”,在實踐中通常“推定具備創(chuàng)造性”[1]。這一觀點系站在結(jié)果的角度,認為不論過程如何,對創(chuàng)造性的判斷最終都將得到明確的結(jié)果。但問題的關(guān)鍵在于,結(jié)果的確定性并不必然等于結(jié)果的正確性,因?qū)@麑彶榻K將產(chǎn)生確定結(jié)果而否認判斷過程的不確定性并不合理。
首先,正如上述意見所述,適用“三步法”的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主觀性,尤其對于“三步法”中的“判斷要求保護的發(fā)明對本領(lǐng)域一般技術(shù)人員而言是否顯而易見”,其中對“本領(lǐng)域一般技術(shù)人員”標準的尺度把握、技術(shù)啟示的確定等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判斷主體主觀意志的影響,當這些因素最終疊加到一起時,在諸多復(fù)雜的案例中,專利的創(chuàng)造性都將成為不確定的命題。在實踐中,除了在個別情形下因發(fā)明的創(chuàng)造性程度很高或很低(例如在所涉區(qū)別特征為公知常識,或系對兩種現(xiàn)有技術(shù)手段的簡單組合等),可直接得出確切結(jié)論外,在多數(shù)情況下,對創(chuàng)造性的判斷系介于有和無之間的模糊地帶,更涉及一種主觀上對程度的衡量,這就導(dǎo)致不同的判斷主體在面對同一客體時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結(jié)論。因此,即便如意見所指,在無法確認時通常應(yīng)當采取推定的態(tài)度,但判斷者可能已在推定前得出了關(guān)于創(chuàng)造性的錯誤結(jié)論。
其次,按照上述意見,推定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前提是找不到否定的事實依據(jù)或無法“作出否定評價”,即在客觀的事實判斷層面或主觀的價值評價層面無法得到否定性的結(jié)論。但一定創(chuàng)造性高度的要求決定了主觀評判的模糊性,因此在大量案件的判斷過程中均無法直接得出確切的否定性結(jié)論。若依照推定具備創(chuàng)造性的邏輯,那么輔助判斷要素將失去存在的意義。根據(jù)《專利審查指南》,當申請存在輔助判斷要素時,審查員“不應(yīng)輕易作出發(fā)明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⑦,可見其意義在于輔助肯定發(fā)明的創(chuàng)造性,但既然當無法得到確切結(jié)論時可以推定發(fā)明的創(chuàng)造性,那么即意味著無論輔助判斷因素存在與否,得出的結(jié)論都是一樣的。
由此,“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系建立在判斷過程的視角上,而“無創(chuàng)造性”則關(guān)乎創(chuàng)造性的判斷結(jié)果,單純從某一視角出發(fā)否定另一視角的論斷缺乏合理性。
3 對基于“經(jīng)濟激勵理論”的“突破說”立場之證否
“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和“無創(chuàng)造性”概念均有其存在的意義且并非同一概念,由此,對“商業(yè)性成功”與“三步法”間適用順序的討論確有必要。在當前關(guān)于“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的爭議背后,反映著對專利制度“經(jīng)濟激勵說”與技術(shù)激勵間的不同態(tài)度。
綜觀目前實踐及理論,關(guān)于“商業(yè)性成功”可在一定程度上突破創(chuàng)造性不足的論斷(以下簡稱“突破說”)均系基于對社會經(jīng)濟的激勵角度。基于“經(jīng)濟激勵說”,專利制度的價值除在于促進科學(xué)技術(shù)進步以外,還在于“作為經(jīng)濟激勵的政策性手段推動社會發(fā)展”,故對發(fā)明應(yīng)予以經(jīng)濟評價,“商業(yè)上的成功正是發(fā)明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價值的直接體現(xiàn)”[2];對此,學(xué)界亦有意見認為“商業(yè)成功的判斷邏輯……并非基于技術(shù)上是否構(gòu)成貢獻來考慮”,根據(jù)該說,“商業(yè)性成功”并非對發(fā)明技術(shù)貢獻的證明,而是在經(jīng)濟范疇內(nèi)的評價。相比之下,認為“商業(yè)性成功”系在根據(jù)“三步法”難以判斷創(chuàng)造性時始得適用的觀點則并未突破技術(shù)評價的范疇(以下簡稱“輔助證明說”),正如美國法院所指,輔助判斷要素應(yīng)被認為屬于“事實調(diào)查(factual inquiry)”的范疇,即“間接證據(jù)”,其作用在于防止法院陷入“事后諸葛亮”的主觀判斷⑧,就“商業(yè)性成功”而言,其意在說明“在消費需求相當大的情況下”,若發(fā)明顯而易見,則競爭對手應(yīng)早已“成功取得該發(fā)明”[3]。可見,兩種觀點背后存在著對理論理解的根本沖突。
在專利審查過程中側(cè)重于在技術(shù)層面上對“三性”的判定,由此,當基于“經(jīng)濟激勵理論”意圖對此加以突破時,應(yīng)存在相應(yīng)的正當性基礎(chǔ)。那么,何為“經(jīng)濟激勵理論”?對其內(nèi)涵及其在專利制度中的意義應(yīng)作何理解?當基于該理論,又是否可必然推導(dǎo)得出“突破說”?本文擬回歸專利制度的本源,通過對“經(jīng)濟激勵理論”的討論,以期厘清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過程中經(jīng)濟因素、技術(shù)貢獻等考量因素間的關(guān)系。
3.1 “經(jīng)濟激勵理論”的內(nèi)涵及意義之析
對于專利制度下的“經(jīng)濟激勵理論”,首先應(yīng)明確其并非意味著基于一項創(chuàng)造活動在經(jīng)濟上的成功而應(yīng)對其進行激勵。否則商業(yè)秘密同樣可以取得經(jīng)濟上的巨大成功,但其并未通過公開技術(shù)方案等方式作為對價,無須在制度框架內(nèi)予以激勵。
無論是基于洛克的勞動財產(chǎn)理論,還是以黑格爾為代表的財產(chǎn)論,抑或是功利主義學(xué)說,“經(jīng)濟激勵理論”均應(yīng)被理解為通過經(jīng)濟上的收益以激勵知識產(chǎn)權(quán)創(chuàng)造、運用等相關(guān)活動。而在“突破說”關(guān)于經(jīng)濟激勵理論的主張與論斷中,其更立足于結(jié)果的角度,側(cè)重于專利制度對社會經(jīng)濟的價值,即通過創(chuàng)造、運用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活動促進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進而認為“商業(yè)性成功”正體現(xiàn)如此,故應(yīng)予以認可。該觀點并非不無道理,正如有學(xué)者所指,“專利制度所激勵的,是通過專利將技術(shù)成果市場化的商業(yè)行為。不考慮市場的專利行為,是對專利與專利激勵作用的誤解”[4],在技術(shù)價值以外,對專利整體價值的評判不應(yīng)遺漏商業(yè)價值,完善的專利制度在激勵發(fā)明創(chuàng)造產(chǎn)生的同時,更應(yīng)促進其推廣運用,進而推動社會整體經(jīng)濟的進步。
“經(jīng)濟激勵理論”有其存在的價值,但并不意味著據(jù)此即可肯定某一技術(shù)特征在商業(yè)上的價值可彌補技術(shù)上的不足,兩者并不存在直接必然聯(lián)系。當基于該理論肯定“突破說”的成立,仍應(yīng)經(jīng)過邏輯上的層層推導(dǎo)。
3.2 “經(jīng)濟激勵理論”對“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的影響與限制
關(guān)于“經(jīng)濟激勵理論”對證明“突破說”的意義,筆者認為:一方面,“經(jīng)濟激勵說”的價值并不意味著需通過包括創(chuàng)造性判斷在內(nèi)的整個專利制度加以滿足,這不僅不具備現(xiàn)實性、還將導(dǎo)致專利制度體系上的混亂;另一方面,在專利整體制度內(nèi),經(jīng)濟激勵理論不應(yīng)優(yōu)先于對發(fā)明的技術(shù)評價以適用。
首先,在專利授權(quán)過程中,對新穎性、創(chuàng)造性的評判均系與現(xiàn)有技術(shù)相比較而言的技術(shù)性評價,即便對于實用性,也僅強調(diào)在產(chǎn)業(yè)中具備能夠被制造或使用的“可能性”⑨。至于對發(fā)明實施、運用的激勵,可通過授權(quán)后的年費、強制許可等機制予以實現(xiàn)。由此,“經(jīng)濟激勵說”與“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間也并不一定存在著必然聯(lián)系,而若基于“經(jīng)濟激勵”說簡單認可“突破說”,將可能導(dǎo)致在專利授權(quán)審查階段和獲得授權(quán)后的復(fù)審、無效階段中對同一技術(shù)方案創(chuàng)造性水平的認定標準、結(jié)果的不同。基于新穎性的要求,技術(shù)特征可能通過使用等方式公開,因此對于實踐中的大量技術(shù)方案而言,其在申請專利前并未投入市場,這就導(dǎo)致其在申請過程中尚未取得商業(yè)上的成功,而在獲得授權(quán)后的復(fù)審、無效制度在本質(zhì)上均系對技術(shù)方案的再次審查,其審查的基礎(chǔ)、標準應(yīng)與授權(quán)審查時具有一致性。若某一技術(shù)方案與現(xiàn)有技術(shù)相比,系對部分現(xiàn)有技術(shù)特征的簡單替換,若因其之后商業(yè)上的成功即對授權(quán)審查時的錯誤予以認可,將造成對公有領(lǐng)域內(nèi)技術(shù)或他人技術(shù)的吞噬,并不合理。
其次,“經(jīng)濟激勵說”下技術(shù)成果市場化實現(xiàn)的前提應(yīng)為技術(shù)成果的“創(chuàng)造”,因此,脫離技術(shù)層面對商業(yè)價值的強調(diào)將成為“空中樓閣”,技術(shù)判斷相比于經(jīng)濟判斷應(yīng)具有優(yōu)先性。正如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第一條的規(guī)定,“鼓勵發(fā)明創(chuàng)造,推動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應(yīng)用”對于社會經(jīng)濟的發(fā)展均至關(guān)重要,若因經(jīng)濟評價而對創(chuàng)造性水平較低的技術(shù)方案賦予壟斷權(quán)的保護,并不利于提高發(fā)明人的創(chuàng)造積極性,反而不利于專利制度目的的達成。
綜上,“經(jīng)濟激勵理論”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與“技術(shù)激勵說”存在先后的順位關(guān)系,更不得基于“經(jīng)濟激勵說”突破發(fā)明的基本屬性。由此,“商業(yè)性成功”似乎更像是在“三步法”判斷過程中的一個證明要素,能夠證明技術(shù)方案本身的創(chuàng)造性水平,當某一技術(shù)特征導(dǎo)致商業(yè)上的成功時,基于“經(jīng)濟激勵理論”應(yīng)予以周密慎重的考量與論證,不宜輕易作出發(fā)明不具創(chuàng)造性的論斷,但不得因此直接肯定技術(shù)方案的創(chuàng)造性水平。
3.3 “突破說”所致的可能不利后果
此外,正是因為我國目前在司法實踐中普遍認同建立在“經(jīng)濟激勵說”上的適用框架,導(dǎo)致了“商業(yè)性成功”條款如同空中樓閣一般極少被成功適用。在筆者檢索的判決及審查決定中,幾乎所有均是在運用“三步法”明確得出技術(shù)特征不具創(chuàng)造性結(jié)論的前提下,再進一步分析“商業(yè)性成功”的主張能否成立。在此種情況下,裁判機關(guān)已經(jīng)在邏輯上接受了發(fā)明實質(zhì)上未對現(xiàn)有技術(shù)做出貢獻,此時無疑難以再通過輔助性判斷因素推翻既有結(jié)論,這在一定程度上將導(dǎo)致最終幾乎所有的案件均認定發(fā)明沒有取得“商業(yè)性成功”或“商業(yè)性成功”與技術(shù)特征間不存在直接關(guān)系。
綜上,無論從“經(jīng)濟激勵理論”與“商業(yè)性成功”間的關(guān)系出發(fā),抑或從“突破說”可能帶來的不利后果來看,當前實踐中普遍關(guān)于“突破說”的立場均不具有合理性。基于此,本文擬進一步分析對于“商業(yè)性成功”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應(yīng)有地位。
4 對“輔助證明說”之理論與實踐證明
4.1 “商業(yè)性成功”作為輔助判斷要素的起源及發(fā)展
對于“商業(yè)性成功”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適用地位之析,仍應(yīng)回歸其作為輔助判斷要素的產(chǎn)生及在各國的發(fā)展路徑,借此可在我國現(xiàn)行《專利審查指南》關(guān)于輔助判斷因素適用地位的規(guī)定尚不明確的情況下,厘清其本源及在適用過程中的應(yīng)有態(tài)度。
一般認為輔助判斷要素的提出源于美國,在美國早期漢德法官的諸多判決中,其將輔助因素“看作專利性的鑒定性證明,沒有這些證據(jù),法院僅僅能夠依靠朦朧的‘發(fā)明’標準”[5];之后在著名的“Graham”案中,法院明確指出商業(yè)性成功、長期存在但未能解決的需求、他人的失敗等輔助判斷因素可以被用于解釋想要尋求專利保護的客體創(chuàng)造性的一些情況。作為顯而易見或非顯而易見性的指征,這些探尋可能具有相關(guān)性⑩。在“Graham”標準確立之后,在眾多判決中又進一步深化了該認識,如在“Stratoflex”案中,法院指出:“事實上輔助性因素常常是最具證明力和最令人信服的證據(jù)……它應(yīng)被視為所有證據(jù)的一部分,而不只是當裁判者在審查后仍然有疑問時適用。”?由此可見,在美國的實踐發(fā)展過程中,輔助性判斷因素是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過程中的證明,如上文所述,其是在專利創(chuàng)造性判斷中的“間接證據(jù)”。在歐洲,輔助性因素則被認為是對創(chuàng)造性主要判斷標準的補充,如根據(jù)歐洲專利局上訴委員會的觀點,“只有在利用‘問題—解決方法(Problem and solution approach)’等評價專利創(chuàng)造性存疑(對現(xiàn)有技術(shù)是否給予教導(dǎo)的客觀評價尚未明晰)的情況下,輔助判斷因素才是重要的”[6]。
可以發(fā)現(xiàn),不同國家地區(qū)對輔助判斷要素的適用順序存在著些微不同。單純從邏輯來看,在美國“證據(jù)說”的觀點下,輔助判斷要素作為證據(jù)的一部分,只要當事人提出,即應(yīng)在創(chuàng)造性判斷的整體過程中加以考量;而在歐洲“補充說”的背景下,只有在無法明確得出創(chuàng)造性結(jié)論時,輔助判斷要素才會被納入考慮,在技術(shù)方案創(chuàng)造性極高或極低的情況下,即便輔助判斷要素被提出,也沒有考量的必要。
但問題的關(guān)鍵點在于,當聚焦于實踐中的適用,兩者是否還存在顯著的差異?以我國對創(chuàng)造性的判斷過程為例,“三步法”作為主要的判斷方法,其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較大的主觀性,例如對最接近現(xiàn)有技術(shù)的確定過程中,涉及與現(xiàn)有技術(shù)領(lǐng)域的遠近、技術(shù)特征的復(fù)雜程度等多方面的要素;在確定區(qū)別特征及其實際解決的問題中,也涉及對某一特征在發(fā)明中事實上起到的效果的認定;而在對顯而易見的判斷過程中,主觀因素將具有更大的影響,對各種因素的確定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審查員主觀意志的影響。在此情形下,即便秉持美國的“證據(jù)說”,其本質(zhì)亦在于認為專利創(chuàng)造性判斷過程中得出的結(jié)論可能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而外在的輔助證據(jù)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判斷的客觀性,正如在美國的“Washburn”案中所提出的,“專利發(fā)明的優(yōu)劣不應(yīng)該在所有周圍環(huán)境真空的情況下確定,而應(yīng)該在行業(yè)內(nèi)周圍環(huán)境的背景下進行評估”?。從這一角度來看,以美國為代表的“證據(jù)說”和以歐洲為代表的“補充說”都是建立在創(chuàng)造性的主觀判斷可能是模糊不清的基礎(chǔ)之上,而輔助判斷因素的介入雖然在邏輯上存在先后的差異,但其本質(zhì)上都是借助外在環(huán)境的因素為最終創(chuàng)造性結(jié)論的得出提供客觀性的證據(jù),在實踐中并不存在順序的差異。
由此可見,各國實踐中關(guān)于輔助性判斷要素的適用順序正是建立在運用“三步法”得出有關(guān)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可能模糊不清的基礎(chǔ)之上,這對我國“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的判斷具有啟示意義:若從輔助判斷要素的產(chǎn)生及其在各國的發(fā)展來看,均持此觀點,那么我國實踐中關(guān)于“突破說”立場的合理性也將受到懷疑。正如《專利審查指南》中所指出,當出現(xiàn)輔助判斷要素時,“審查員應(yīng)當予以考慮,不應(yīng)輕易作出發(fā)明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可以認為輔助判斷要素是“三步法”判斷過程中的組成部分,其在本質(zhì)上即是對于創(chuàng)造性要求的具體表現(xiàn),而通過將“商業(yè)性成功”等典型表現(xiàn)列為輔助判斷要素,在有助于實現(xiàn)判斷相對客觀化的同時,也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4.2 我國實踐發(fā)展中對“商業(yè)性成功”態(tài)度之梳理
基于上述對輔助判斷要素從產(chǎn)生到在各國發(fā)展的梳理,筆者擬通過對《專利審查指南》歷次修改的版本進行比較,以考量我國在實踐發(fā)展中對“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態(tài)度的變化,以期幫助厘清對“商業(yè)性成功”適用的應(yīng)有地位。
通過梳理,可以發(fā)現(xiàn)在輔助性判斷因素的表述上各不相同:除卻上文所述的我國現(xiàn)行《專利審查指南》中的表述,在1993年版本中,其規(guī)定“評定發(fā)明有無創(chuàng)造性,應(yīng)當以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三款為基準。為有助于正確掌握該基準,下面給出一些參考性判斷基準。應(yīng)當注意的是,這些判斷基準僅是參考性的,審查員在審查具體的案子時,不要生搬硬套,而要根據(jù)每項發(fā)明的具體情況,公正地做出判斷”?;而在2001年版本中,其規(guī)定“發(fā)明是否具備創(chuàng)造性,通常應(yīng)當依據(jù)本章第3.2節(jié)所述審查基準進行審查。為了有助于創(chuàng)造性的判斷,下面給出一些特定情況下的輔助性判斷基準”?;而在此之后的修改中,相關(guān)表述與當前《專利審查指南》中的表述趨同。單從輔助性判斷要素相關(guān)規(guī)定的字面來看,我國的態(tài)度似乎較為偏向于上文中歐洲的代表觀點,即認為輔助判斷要素系對于較為復(fù)雜的創(chuàng)造性主觀判斷的補充,當運用“三步法”無法得出確切結(jié)論時,輔助判斷要素的存在可幫助其結(jié)論相對客觀。
4.3 小結(jié)
總結(jié)而言,當討論輔助性判斷要素的適用地位時,不論是美國的“證據(jù)說”,抑或是歐洲的“補充說”,其均是建立在創(chuàng)造性主要判斷方法的主觀性基礎(chǔ)之上,畢竟技術(shù)特征的創(chuàng)造性并非絕對有或絕對無,其更多情況下是處于0~1間的一種程度的衡量。也正因此,上述兩種學(xué)說的本質(zhì)均是運用輔助判斷因素為創(chuàng)造性判斷提供一定的客觀證據(jù),至于與“三步法”間適用順序的差異則更多屬于邏輯層面。但與此同時,輔助判斷因素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其僅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切不可因某一因素的出現(xiàn)而斷然肯定某一絕對不具創(chuàng)造性的技術(shù)特征,而“商業(yè)性成功”也并未脫離這一適用框架。通過對“商業(yè)性成功”適用地位的厘清,將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目前的適用困境,當運用“三步法”能夠確定得出一個特征不具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時,顯然“商業(yè)性成功”沒有適用的必要,而這正是目前我國司法實踐中普遍存在的認識誤區(qū),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拉低了這一規(guī)定適用的成功率,也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更重要的是,這一適用順序可能會影響到有關(guān)最終“創(chuàng)造性”正確結(jié)論的得出。
5 結(jié)語與討論
目前我國成功主張“商業(yè)性成功”的比例非常之低,盡管這一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系基于多種原因,如對于商業(yè)成功、商業(yè)成功與技術(shù)特征間相關(guān)性等問題的舉證困難等,但也應(yīng)認識到,目前實踐中普遍認為只有在運用“三步法”否定創(chuàng)造性之后才有“商業(yè)性成功”的適用可能性,而正是這一觀點,從根本上切斷了“商業(yè)性成功”得到成功主張的道路。盡管“商業(yè)性成功”背后確有“經(jīng)濟激勵”的考量,但該考量也絕不可突破專利的技術(shù)本質(zhì)。而當在技術(shù)層面否定專利創(chuàng)造性乃至新穎性后,始得適用“商業(yè)性成功”顯然難以突破這一結(jié)論。
“商業(yè)性成功”雖然在浩瀚的專利制度中如同滄海一粟,但其與專利制度的本質(zhì)密不可分;同時,創(chuàng)造性判斷作為專利法中的重要命題,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主觀性,而通過對“商業(yè)性成功”等輔助判斷要素的厘清和正確理解或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創(chuàng)造性判斷過程中的“事后諸葛亮”問題。
注釋:
①參見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節(jié)判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性時需考慮的其他因素:“發(fā)明是否具備創(chuàng)造性,通常應(yīng)當根據(jù)本章第3.2節(jié)所述的審查基準進行審查。應(yīng)當強調(diào)的是,當申請屬于以下情形時,審查員應(yīng)當予以考慮,不應(yīng)輕易作出發(fā)明不具備創(chuàng)造性的結(jié)論。”“5.4 發(fā)明在商業(yè)上獲得成功”。
②根據(jù)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中的3.2.1.1判斷方法,“判斷要求保護的發(fā)明相對于現(xiàn)有技術(shù)是否顯而易見,通常可按照以下三個步驟進行:(1)確定最接近的現(xiàn)有技術(shù);(2)確定發(fā)明的區(qū)別特征和發(fā)明實際解決的技術(shù)問題;(3)判斷要求保護的發(fā)明對本領(lǐng)域的技術(shù)人員來說是否顯而易見”。此為對創(chuàng)造性判斷的主體方法,筆者在本文中將其稱為“三步法”。
③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8號行政判決書。
④如在實踐中的大量法院直接指出“商業(yè)性成功”乃當采取“三步法”難以判斷技術(shù)方案的創(chuàng)造性或者得出技術(shù)方案無創(chuàng)造性的評價時適用,參見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6)京73行初2509號行政判決書、北京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7)京73行初2940號行政判決書等。同時,大量判決雖未明確指出,但判斷的邏輯順序亦是首先運用“三步法”認定某一技術(shù)特征不具創(chuàng)造性,再進一步分析“商業(yè)性成功”的要素,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2)行提字第20號行政判決書、北京高級法院(2017)京行終5610號行政判決書等。
⑤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知行終237號行政判決書。
⑥See Robert P.Merges,“Commercial Success and Patent Standards: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Innovation”76(4)California Law Review 816(1988).
⑦參見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節(jié)。
⑧See Vandenberg v.Dairy Equip.Co.,740 F.2d 1560.
⑨參見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第5.3節(jié)。
⑩Graham v.John Deere Co.,383 U.S.1.
?Stratoflex,Inc.v.Aeroquip Corp.713 F.2d 1530.
?George M.Sirilla,“35 U.S.C.§103:From Hotchkiss to Hand to Rich,The Obvious Patent Law Hall-of-Famers”,32 J.Marshall L.Rev.437(1999).
?參見2020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5節(jié)。
?參見1993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2節(jié)。
?參見2001年《專利審查指南》第二部分第四章第3.3節(ji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