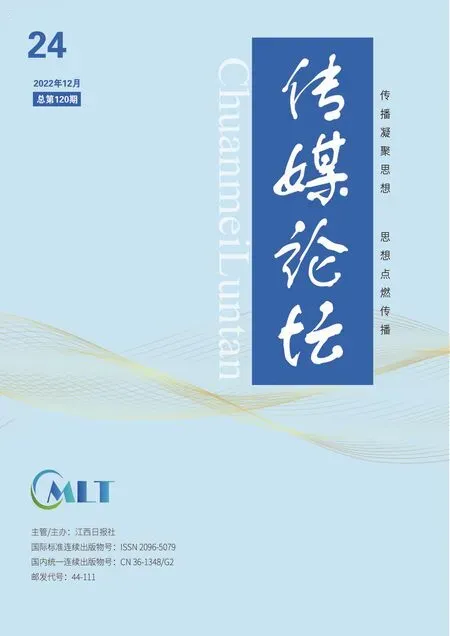多維學科視野下信息變異圖景深描與傳播治理創新
——《UGC媒體語境下信息變異與治理研究》評介
羅 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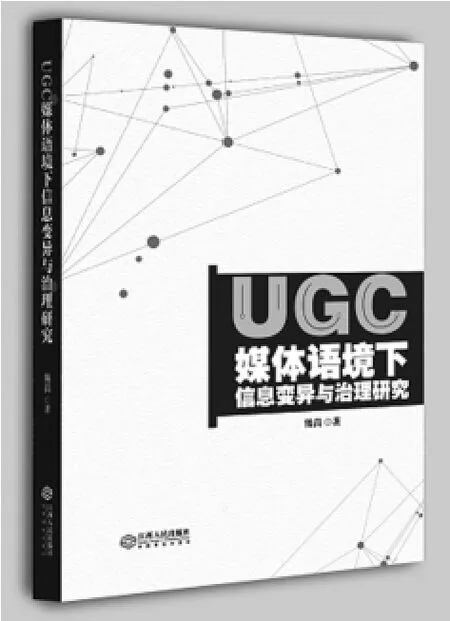
信息變異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生物進化過程中存在物種變異,其背后是基因信息變異;在通信過程中,信號收到噪音干擾出現變形,信息變異成為信息科學的重要命題;在文學或者翻譯文學中,由于文本的開放性或文本的跨文化轉譯,信息所蘊含的意義也常常發生改變;在日常生活中,人際交流,媒體傳播、官民互動等,或多或少存在各種形式的信息變異,例如口耳相傳的流言、失實的新聞、偽裝的知識等等。盡管有學者從修辭學角度提出“合法偏離”[1]的積極作用,但是一旦超越“合法閾值”,“偏離”將會成為表達和理解的阻礙。如是觀之,超越了“合法閾值”的信息變異將會對傳播造成干擾,進而對社會整體運行帶來不良影響。正是基于這樣的問題意識,江西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熊茵教授論作《UGC媒體語境下信息變異與治理研究》開啟了系統深入、頗具啟發的研究。熊茵教授自讀博至今,多年深耕媒介技術與社會發展的學術領域,相關的科研產出頗豐,主持過兩個國家社科基金、發表多篇高質量論文,出版《突發事件信息變異與應對策略研究》、《江西黨政新媒體傳播力藍皮書》(2017、2018、2019)、《江西教育輿情藍皮書》(2020、2021)藍皮書等多部論著,她已成長為該領域的青年專家。此次新出版的論著結合新媒介技術背景,詳盡地描摹UGC媒體語境中信息變異的生成圖景, 并應運用管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提出頗富洞見的信息變異綜合治理方案。細細讀來,本書有三點內容令人耳目一新,顯示了作者的扎實功底和深刻洞見。
一、新媒體語境下信息變異復雜圖景的深度描摹
去中心化技術來臨后,互聯網發生根本意義上的范式變革,傳播格局發生顛覆性變化。克萊·舍基將其描述為“人人時代”以及“大規模的業余化時代”,以“專業者”為中心的格局被打破,技術賦權和賦能普通民眾,大量“非專業”的普通民眾和組織機構參與到信息生產與傳播之中。他們信息行為異常復雜,他們各有理念、各有標準,信息的個性化生產與關系化傳播成為常態,大眾傳媒語境中的制式化信息符號和統攝性信息意義消逝,信息形式和意義也呈現參差多態,UGC媒體語境充滿了各式各樣的信息變異。不得不說,對于這一史無前例復雜語境的描述和研究對作者而言是極大挑戰和考驗。
為了清晰描摹UGC語境中紛繁復雜的信息變異圖景,熊茵教授科學地借鑒了麻省理工學院集體智能中心主任管理學者Thomas W. Malone研究互聯網集體智能行為(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分析框架。Malone通過對Google,Wikipedia,Threadless,Linux,YouTube,Digg等近250個“集體智能”組織平臺上的深度觀察與分析,從信息生產傳播的主客體邏輯出發,提出兩組關聯性追問,在此基礎上提煉出Who、What、Why、How四元維度并構建分析框架。在該書的第二章中,論著從行動主體、內容、動因、過程四個層面,展現了UGC媒體語境中復雜多態的信息變異全景圖、揭示了信息變異的深層動因和內生機制。為了厘清多元行動主體的類型,研究頗具巧思地以“職業-專業”雙重維度為依據,交叉架構了四類象限,分別對應了職業性和專業性俱佳的“傳統范式”型傳播主體、職業性和專業性皆弱的“訴說沖動”型傳播主體、職業性強但專業性弱的“利益偏向”型傳播主體以及職業性弱但專業性強的“創新突破”型傳播主體。以此劃分標準觀照當下UGC語境中的多元傳播主體,不僅將UGC媒體生態中的主流媒體、“公民記者”、組織機構類媒體、經營類自媒體等各色傳播主體涵蓋在其中,更將他們之間紛繁復雜、交錯纏繞的邊界和內涵厘定得清清楚楚,可謂十分準確恰當;至于哪些信息發生了何種形式的變異,該書也頗有洞見地分析了人類社會傳播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四類信息分別是是事實類信息、觀點類信息、知識類信息以及娛樂類信息,及其超出“合理閾值”的變異形式。在對UGC媒體語境信息變異的動因檢視中,熊茵教授在研究中指出社會性因素和技術性因素的互動互推,不斷放大信息變異規模和程度;而在信息變異過程考察中,研究也頗有洞見地指出信息變異的兩類行動模式,即基于“內容加工”的信息變異模式和基于“關系改寫”的信息變異模式。通過四元維度分析,熊茵教授將UGC媒體語境中極度復雜的信息變異圖景清晰呈現,這遠非是簡單的描述性研究,而是針對復雜事物的類型研究(Genre Study)。眾所周知,條理清晰的類型研究有賴于研究者對研究對象及相關材料的持續觀察與積累,敏銳的體悟與洞察、對相關理論深刻把握以及對現實的強烈反思。由此可見,作者對該研究主題的長期關注與深耕,也反映了一名學者應有的嚴謹治學態度。
二、新媒體語境信息變異的理論闡釋和理論創新
該書不僅對信息變異發生圖景進行了細致而深入的描摹,更從相關理論層面對信息變異現象及發生規律進行了學理闡釋與分析。信息變異是具有多種學科意涵的概念,生物科學、信息科學、管理科學甚至社會學、文學等都對之有或清晰或曖昧的界定。但傳播學研究中,尚無共識。該書結合傳播學范疇,并融通多學科知識對概念界定進行了探索。研究指出傳播學視野下的信息變異指“受主客觀原因的影響,傳播主體在編碼、譯碼等傳播環節出現行為偏差,從而導致信息的符號變形及意義偏離”。這個概念立足人類傳播行為,涵蓋和融合了社會學、信息學以及語言學知識,提出信息變異的概念,具有嚴謹性、較好的包容性和較強的闡釋力,為后期研究設定了科學正確的研究起點。
UGC媒體語境中,信息變異生成交錯糾纏、延綿不絕且有愈演愈烈之勢。這與德勒茲的“塊莖”理論所表達之意何其相似。在該書第一、二章中,作者用德勒茲“塊莖”“生成”“逃逸”“解域”等經典概念對UGC媒體語境中信息變異的生成進行哲學闡釋。眾所周知,吉爾·德勒茲被譽為互聯網的思想“先哲”,他的理論切中互聯網本質,極具闡釋力。該書將德勒茲相關理論和概念創造性地用于闡釋UGC媒體語境信息變異生成。這不僅恰如其分,而且有力地拓展了“塊莖”理論闡釋空間和范圍,是對該理論的豐富與完善。
在繪制UGC媒體語境多元傳播主體的共生圖景時,該書的研究聚焦了多元傳播主體共生的“動態性”,頗有新意地借用管理學“演化博弈”(Evolutionary Game)理論進行理論闡釋:多元類主體逐漸構成了當下新聞傳播主體的新生態,構成了一副錯綜復雜、充滿角力的動態圖景:各主體在新聞資源、采寫技巧、話語地位、用戶市場、廣告份額等諸多方面展開激烈競爭博弈。他們都努力尋求各自的發展進路,力圖壯大自身、搶占主流和主導地位,并指出四大傳播主體的博弈戰術與策略,包括了“平衡范式”傳播主體的“社會化”策略、“利益偏向”型傳播主體的“媒體化”轉向、“創新突破”型傳播主體的“職業化”趨近、“訴說沖動”型傳播主體的多重進路等。對“演化博弈”理論拓展應用,有力地闡釋多元主體格局的動態演進過程,并通過規律指明未來演進發展的方向。
在學理闡釋與分析之外,本書開展了諸多頗有見地的理論創新。例如在第三章中,作者對“自組織”進行否思,提出了“有組織的自組織”的新概念,強調了自組織并非絕對,它仍存在一定的內生組織機制,否則將會陷入混沌無序,那么自組織也將不復存在。又如在第六章研究認為需要確立以“利益相關者”思路,立足中國具體國情、結合中國實際,提出黨政領導下多元協同的信息變異治理模式構想,這無疑是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的豐富與充實。
從理論應用程度看,該書科學應用了豐富的理論資源,較好地闡釋現象、揭示規律及未來趨勢。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在拓展理論維度上做出大膽而嚴謹的探索,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又切中本質的新概念、新提法和新論述。這些都反映出作者不僅具備扎實的理論功底,更具有向縱深推進理論研究和銳意求新的學術探索精神。
三、新媒體語境下信息變異治理創新構想
媒介技術變遷帶來信息生成模式變化,信息變異也呈現不同特征,治理模式也應有相應的創新。在傳統媒體“中心化”語境中,對信息變異等傳播失范行為的規制多以政府部門為主導和主要力量,自上而下開展垂直科層管理,管理對象主要是媒體單位。一般情況下,政府通過政治、經濟、法律等手段進行集中調控,信息變異會在較短時間內得以明顯改善。然而,這種組織對組織的管理模式在“去中心”化的時代已經失靈。在人人參與信息生產與傳播,信息變異也就成為高度個體化的行動,這意味著被規制對象從有限的組織機構擴展成為無限的個體單位,管理模式亟待創新轉型。2013年,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標志著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進程的全面開啟和深入推進。[2]對信息變異的治理也應從一元、垂直、單向的模式轉變為多元、扁平、協同的模式。該書正是對信息變異的多元治理模式的前沿探索和思考。書中第六章中指出,政府、大眾媒體、商業技術公司、社會力量等對“治理”達成基本共識,也開展了相應的治理實踐,多元參與、齊抓共管的“眾治”格局初現。研究也對“眾治”模式進行了審慎思考和追問,由于“眾治” 模式是牽涉各方的復雜模式, 更需要有效地協同運行,那么必然需要回答“誰來協同”“如何協同”“何以協同”三大問題,也即協同主體、協同形式以及協同機制的問題。書中引入了管理學的“利益相關者”理論(stakeholder),對信息變異多元協同治理的未來發展進路開展建構探索,包括確定哪些是利益相關者、核心利益相關者以及外圍利益相關者如何厘定,各自的利益相關點為何、各自行動策略為何、協同行動機制和驅力為何,規范保障機制為何等。研究指出,唯有凝聚各方共識、切中各方利害、達成共同方案,信息變異的多元治理模式才能持續有效地運行下去。近年來,對傳播失范的治理研究逐漸成為熱點,但始終沒有有力地回應“多元何以協同”的關鍵性問題。不回答這個問題,立足各自立場和利益的多元主體就無法真正地達成協同,多元協同治理將會是空中樓閣,難以落地。本書研究開創性地用“利益相關者”作為治理邏輯起點,逐層推進、縝密搭建了多元協同的治理體系,探索了切實可行的運行機制, 為UGC媒體語境信息變異治理提供有效的整體方案, 具有極強的實踐價值和現實意義。
媒介技術迭代不斷造就新傳播語境,信息變異生成也將更加錯綜復雜,由此帶來的風險也將日益放大,給社會治理帶來新難題與挑戰。與時俱進地思考和審視風險、創新有效治理模式將是社科學者的使命與責任。熊茵教授及論著《UGC媒體語境下信息變異與治理研究》積極回應了新時代的需求與召喚,不僅在新聞傳播學術理論中國化道路上積極探索,更為新媒體語境的傳播治理提供科學有效、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具有寶貴的學術和實踐雙重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