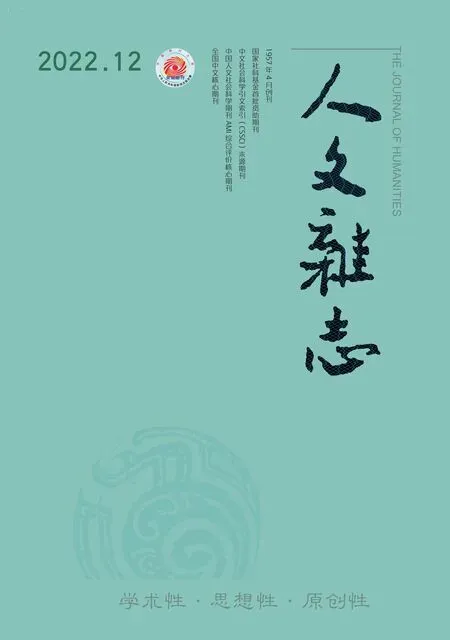“實事求是”之學及其問題*
——以《論語正義》為中心
鄺其立
內容提要 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集中體現了“實事求是”的學術風格,表現有三:重禮、考史與“事實至上”。但檢尋劉疏,會發現他未能貫徹“實事求是”的要求,所以引證材料時有“求同略異”“斷章取義”的嫌疑,甚至會牽合材料以證成先入之見,且“實事求是”之學亦有其內在問題。劉氏所援引的歷代《論語》注疏,與“實事求是”的解釋方案并不同質,這將招致一個悖論:“實事求是”的要求,反倒使劉寶楠無法實事求是地運用材料,追索經義。最后,“實事求是”之學作為一種解讀方案,與結構松散的《論語》并不相適。集合眾多零散“思想點”的《論語》,需要整全的背景或一貫的立場,這便需要“實事求是”之外的“決斷”。藉由對《論語正義》的反思,可管窺清代實學之深層問題。
劉寶楠撰寫的《論語正義》,是清代《論語》學的代表作,集中反映了清代經學尤其是揚州學派的學術風格。這部經典的誕生,源自一段學術史佳話:道光八年(1828年),劉寶楠應省試,與同級生劉文淇、梅植之、包慎言、柳興恩、陳立相約各治一經,加以疏證。劉寶楠抽中《論語》,自此專精致思,以之為終身志業。最終,該書歷劉寶楠、劉恭冕兩代人的努力方成。
但是,歷代《論語》注本堪稱繁多,劉寶楠再作新疏的用意何在?劉恭冕述先君著書之法云:“依焦氏作《孟子正義》之法,先為長編,得數十巨冊,次乃薈萃而折衷之,不為專己之學,亦不欲分漢、宋門戶之見,凡以發揮圣道,證明典禮,期于實事求是而已。”(1)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798、797頁。劉寶楠廣搜歷代注解,后乃薈萃折衷之,旨在“實事求是而已”。“實事求是”,正是一眾乾嘉學者所追求的目標,劉恭冕又云:“我朝崇尚實學,經術昌明,諸家說《論語》者彬彬可觀,而于疏義之作,尚未遑也。”(2)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798、797頁。清代經學崇尚“實學”,實學即是求真征實、實事求是之學。錢大昕即云“俾知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3)陳文和主編:《嘉定錢大昕全集》,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3頁。故反觀歷代注疏,雖各有可觀,但就實事求是的標準來看,則猶未愜人意。所謂“實事求是”,即是通過考證、訓詁等方式追尋經典本義。(4)郭院林:《試論乾嘉時期“實事求是”觀念——以戴震與阮元為中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以之為指導原則的《論語正義》,集中展現了實學的風貌。
過往的研究,多集中于通過《論語正義》來展現寶應劉氏家族、揚州學派乃至有清一代的學術特征。(5)李曉明:《清代寶應劉氏家學考述》,博士學位論文,華中師范大學,2016年;馮曉斌:《清代揚州學派〈論語〉詮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揚州大學,2017年;唐明貴:《劉寶楠〈論語正義〉的注釋特色》,《歷史文獻研究》2012年(總第31輯),等等。其中《劉寶楠〈論語正義〉的得與失》一文最富啟發。參見陳壁生:《劉寶楠〈論語正義〉的得與失》,《國際儒學》2021年第4期。本文則試圖將《論語正義》作為反思清代實學的切入點,進而揭示“實事求是”之學內含解構經學的傾向。考察其所沖擊者為何,俾能反觀經學之邊界所在。
一、禮制、歷史與“事實至上”
通觀全書,《論語正義》的“實事求是”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重禮、考史與“事實至上”。以劉疏“哀公問社于宰我”章為例明之:
哀公問社于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八佾》)
哀公請教宰我,應以何樹作為社神所依附的“社主”。宰我答云:夏人以松樹,殷人以柏樹,周人以栗樹。而周人以栗為田主的寓意,在于使民畏懼戰栗。孔子對弟子的應答相當不滿,遂深斥之。
劉寶楠先考經文所涉之禮制,廣引眾說,辨明“社”意。在魯《論》的版本中,“社”作“主”,二者字異而意同。“主”即宗廟之主,為祖先神靈所依附者,故可引申為社神所依附之樹。后者亦謂之“社主”或“田主”,此即哀公所問之“社”。因牽涉社稷之神,故劉寶楠又引述論及“社稷”的文獻,如《禮記·祭法》《周禮》《左傳》等,辨析社稷之禮及其方位;繼而羅列涉及三代之主異制的文獻以澄清社樹之制,遂得出“不定是一木,亦當以其土所宜爾”(6)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797、2頁。的結論;最后,考證后代社主以木還是以石為材質的問題。可見劉寶楠尤其著意于澄清禮制原貌。劉恭冕《后敘》云:
漢人注者,惟康成最善言禮,又其就《魯論》,兼考《齊》、《古》而為之注,知其所擇善矣。魏人《集解》,于鄭注多所刪佚,而偽孔、王肅之說,反籍以存,此其失也。梁皇侃依《集解》為疏,所載魏、晉諸儒講義,多涉清玄,于宮室、衣服諸禮闕而不言。宋邢昺又本皇氏,別為之疏,依文衍義,益無足取。(7)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797、2頁。
首先,劉寶楠激賞鄭注,因為“康成最善言禮”,在重視禮學這一點上,二者相契。正因劉寶楠如此重視禮學,所以對何晏《集解》刪削鄭注的做法,十分不滿。(8)喬秀巖、葉純芳:《學術史讀書記》,三聯書店,2019年,第62~103頁。且他對于多涉清玄而略于言禮的六朝義疏,頗有微詞,此其重禮的表現。其次,劉寶楠并非對歷代注解一視同仁,而是有“崇古”傾向。《論語正義·凡例》云:“漢人解義,存者無幾,必當詳載,至皇氏《疏》、陸氏《音義》所載魏、晉人以后各說,精駁互見,不敢備引。唐、宋后著述益多,尤宜擇取。”(9)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797、2頁。考察劉疏所引的歷代解說,非常顯著地體現出“愈古愈真”的優先級。譬如,劉疏雖漢宋兼采,但未曾以宋人的解釋取代《集解》的說法。(10)劉寶楠引范祖禹的說法,并以為雖“與鄭、孔注義異”但“范說亦通”,卻仍“主鄭、孔而以范說附之”。參見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28頁。是仍以漢學為主,吸納宋人解義。他在面對《集解》與鄭注的齟齬時,優先采納鄭說;(11)針對《為政》“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的解釋,鄭、何異趣。在矛盾的兩說之間,劉疏從鄭。參見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64頁。甚至在發現鄭注有誤時,亦曲為回護,疑為記者錯錄。(12)劉寶楠:“則《釋文》所稱‘鄭讀’恐誤記也”。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87頁。其尊鄭學、崇古注,可見一斑。
不過,雖秉有好古傾向,但獨鐘鄭注的劉寶楠也并非一味從鄭。在自認確鑿的情況下,仍不妨憑據事實,駁正鄭說。譬如,針對“哀公問社于宰我”章所涉及的社主材質問題,鄭注《小宗伯》云“社主蓋用石”,俞樾從之。惠士奇則辨正云:“若后世五尺之石主,埋其半于地,即不便于載,亦不可抱而持”,惠氏依據常理推定,隨行軍而遷移的軍社不可能是石制,因過于沉重,“不便于載”。(13)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劉疏從惠說,謂鄭玄、俞樾的“軍社用石主”說“與惠氏石主不便于載之說異,當以惠說為然”。可見劉寶楠據常理、事實為斷,而不盲從鄭玄。“事實至上”,是“實事求是”之學的第二個表現。
“實事求是”的第三個表現,在于劉疏對歷史背景的注重,意在將經文置于具體情境之中,以求索隱微的原意。仍以“哀公問社”為例,劉疏引方觀旭《偶記》云:“此時哀公與三桓有惡,觀《左傳》記公出孫之前,‘游于陵坂,遇武伯,呼余及死乎?’至于三問,是其杌隉不安,欲去三桓之心,已非一日。則此社主之問與宰我之對,君臣密語,隱衷可想。”(14)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據《左傳》,哀公之時,三桓僭越。哀公深感芒刺在背,惴惴不安。發生于暗流潛動的背景中,這番對話別有深味。劉寶楠認為,哀公與宰我的問答為“君臣隱語”。宰我對曰“使民戰栗”,或即暗示哀公應殺伐決斷,以免陷入太阿倒持的危險境地。不僅如此,劉寶楠更對孔子斥語作細致解讀,以為其指代了具體事件。劉疏“既往”云:“竊疑‘既往’指平子言。平子不臣,致使昭公出亡,哀公當時必援平子往事以為禍本,而欲聲罪致討,所謂既往咎之者也。”(15)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劉疏歷史化、具體化的理解方式,由此可見。
重禮、考史與“事實至上”,貫穿于劉疏全書,亦為“實事求是”之學的應有之義。那么,劉寶楠是否能完全貫徹“實事求是”的主旨?此“實事求是”的解經法,又有何弊病?
二、不充分的“實事求是”
劉疏效法焦循之《孟子正義》,窮畢生精力,網羅眾說,并折衷選材、稍下己意。《論語正義》的主體部分,便是由劉寶楠所薈萃的眾多材料所構成。若細檢疏文,就會發現劉氏選材時或不審。這表現在兩方面:相關度不足的“求同略異”與嚴謹性不足的“斷章取義”。
先看“求同略異”的問題,以《為政》篇“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句為例。何晏《集解》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也。”(16)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21頁。通過引述皇疏、邢疏,劉寶楠解何注云:
皇疏申此注云:“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一也。”又云:“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于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邢疏云:“異端之書,則或秕糠堯、舜,戕毀仁義,是不同歸也。”(17)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
劉寶楠認為,何注與皇、邢兩疏可通。若細繹之,則可知三者各有所指,未必兼通。“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警語意在表明,沉溺“異端”,貽害無窮。但皇疏則轉換了焦點,從申言異端之害,變為強調學經之重要。若經文旨在勸人學經,則凡與“五經正典”“為教”無涉之“雜書”,即為“異端”。此意未見于何注,實屬皇侃的“孤明先發”。至于邢昺,則將“異端”理解為與儒家齟齬的老莊之學,遂有“秕糠堯、舜,戕毀仁義”的說法,這也未必是何注本意。鑒于何晏深諳老、莊、《易》三玄,是兼綜儒道的開風氣之先者,其所謂“殊途同歸”或有融通二家的用意在焉。畢竟,經文明謂異端有害,何晏則反其道而解之,提醒讀者除了“異端”之外,仍有可以并行不悖的“殊途”可同歸于大道。欲以皇疏、邢疏佐證何注,實為不得要領。
除了強合諸說,劉寶楠引文也時有斷章取義之嫌。劉疏《學而》篇“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句中的“觀”之字義時,援引《榖梁傳》隱公五年的說法云:“常視曰視,非常曰觀。”(18)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但是,《榖梁》傳文明為指斥隱公觀魚非禮的特殊筆法。劉寶楠隱沒“公觀魚于棠”的語境而節選傳文,消解《榖梁》筆法和寓意之后,引為字義訓詁的旁證,其實難以成立。
又,《八佾》篇載孔子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這段話的關鍵問題在于,孔子為何征考二代舊禮。劉寶楠認為,此句“因修《春秋》而發,《春秋》亦本周禮也。”(19)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120、122、123、59、27、92頁。所以,孔子是本于三代之禮而修《春秋》之史。劉疏又引戴望《論語注》佐證云:“王者存二王之后,杞、宋于周,皆得郊天,以天子禮樂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備其典章文物”云云。(20)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56、56、57頁。若檢尋戴注原文,則可知劉疏有意刪節。戴望先云:“如使子夏等適周求百二十國寶書以作《春秋》也”,(21)郭曉東:《戴氏注論語小疏》,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2頁。爾后方有劉疏引文。可見,以《公羊傳》解《論語》的戴望,以孔子為作《春秋》之素王,旨在為后世立法。此說與劉疏“修《春秋》”之論相左,故被有意抹去。
進而言之,如果劉寶楠引證的相關度與嚴謹性不足,則受材料引導的劉疏,或將產生超離于經文本身的斷言。譬如,《為政》篇有“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從之。’”句,劉疏因注意到《禮記·緇衣》也論及言行問題,遂引之作解:“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22)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56、56、57頁。但劉寶楠并未忠實援引,而是截去了“以成其信”之后的“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句,不惜割斷貫通的文脈。這是因為,《緇衣》的言說對象分明是人君,意在勸其以信德孚民。探討人君化民之德與功,乃為《緇衣》主旨。遂與論“君子”的《論語》此章無法嚴絲合縫。但劉寶楠仍因循《緇衣》而推闡云:“小人言不顧行,行不顧言,故易致多言。”(23)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56、56、57頁。《緇衣》謂君子需言行相顧,故而寡言。由此反推,可知小人言行不相顧,故不慎言。這一理解無法從《論語》經文推知,是劉氏基于引文的推補。嚴格地說,若佐證材料與經文未必相合,則其闡發便難以稱得上穩健可靠、實事求是。
不過,劉疏雖以材料鋪陳與立基于材料的闡釋為主,但也不完全為材料牽引或憑據“事實”、材料作疏。其中亦不乏劉氏帶著明確的論證目標而“排布”材料,以證成先入之見。如在“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句的疏解中,劉寶楠謹遵孔安國“忠信為周”的注解,意欲勾聯“周”與“忠信”兩個意項。通過引用材料,劉寶楠“鋪出”了兩條論證思路:其一,先引《毛詩》《國語》等材料證明“周”有親、密、合之意,又據王引之之言,論證“周”即“以義合者”,并斷言:“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24)劉疏引《經義述聞》云:“王氏云:‘以義合者,周也;以利合者,比也。’既以義合,得非忠信耶?”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57頁。劉疏的邏輯,是將“以義合者”作為關聯“周”與“忠信”的中項,并由此打通二者。其二,劉寶楠引據《爾雅釋詁》《國語》韋昭注,證明“比”有“阿黨”之意。又認為,“周”與“比”相對,故“周”即“不阿黨”,進而自下己意道:“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如兄弟,故能周也。周則忠信之謂,若非忠信,而但引黨以封己,是即阿黨為比矣。”(25)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56、56、57頁。劉氏將“周”落實為“不阿黨”之意,并認為非忠信者必阿黨自封,忠信者則必“不阿黨”。所以,“忠信”與“周”可互訓。這顯然是基于預定目標,借助于材料和解說來補足、完成“論證鏈”。與其說是中立客觀地依據材料,毋寧說是頗顯生硬地利用材料而已。
綜上,劉疏未能貫徹實事求是的要求,遂有“求同略異”或“斷章取義”之嫌。且基于不夠準確的引文,便難以推出牢靠的結論。而借助材料來證成先入之見,也稍顯獨斷。但是,劉寶楠之所以無法充分地“實事求是”,亦有其不得已處。
三、“實事求是”的悖論
除卻劉疏未能力求客觀的疏失,“實事求是”的難以貫徹,一定程度上是實學本身所招致的結果。因此,亦應考察“實事求是”之學所蘊涵的內在問題。
劉寶楠引用材料,時或斷章取義。吊詭的是,為了實事求是,斷章取義亦常為不得已之舉。譬如,劉寶楠不信公羊家說,故在引述公羊家戴望的注解時,刻意刪去孔子“作《春秋》”的內容。對戴望注而言,誠為斷章取義,但對解讀經文而言,似無可厚非。因為孔子的身份問題,難有定論,言人人殊。刪選可疑之論,無可厚非。又,對《八佾》篇“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句,為了得到更確切的理解,劉寶楠引據《公羊傳》與何休說作為考證材料,試圖落實“夷狄”與“諸夏”的具體指代。其疏云:
包氏慎言《溫故錄》:“夷狄謂楚與吳,《春秋》‘內諸夏,外夷狄’。成、襄以后,楚與晉爭衡,南方小國,皆役屬焉。宋、魯亦奔走其庭。定、哀時,楚衰而吳橫,黃池之會,諸侯畢至,故言此以抑之。襄七年,鄬之會,‘陳侯逃歸’,何氏云:‘加逃者,抑陳侯也。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言不當背也。’又哀十三年‘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吳何以稱子?主會也。吳主會,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何氏云:‘明其寔以夷狄之強會諸侯爾,不行禮義,故序晉于上。’主書者,惡諸侯之君夷狄。”案,包說是也。(26)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84、7~8、10頁。
依據“鄬之會”與“黃池之會”,包慎言斷定“夷狄”指代楚、吳,“諸夏”則為宋、魯、晉,劉寶楠許之。但如此解讀《公羊傳》與何注,顯然未能充分尊重材料本身的邏輯。因為傳文旨在借事明義,是將歷史中的具體指代,抽象化為便于講述道理的符號。意即以吳、楚象征“夷狄”,并通過隱微書法貶斥“夷狄主中國”,以表達“內諸夏,外夷狄”之微言大義。這屬于“借事明義”的思路。包、劉則“反其道而行之”,將紬繹義理的公羊家說,作為考證、落實經文具體指代的歷史材料,是由抽象而具體的歷史化思路,實乃背道而馳。但對劉寶楠而言,這是為了“實事求是”而不得已的削足適履,因為他無意引入可疑的義理。
朱子《論語集注》也是劉寶楠采擷引證的對象之一。但劉疏甚少全面采納朱注,而是“避重就輕”地有所去取。所選內容往往繞開朱子思想的要害。《學而》篇中,有子論仁孝關系云:“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劉疏“為仁”曰:
“為仁”猶言行仁,所謂利仁強仁者也……“仁”者何?下篇“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仁”字本訓。《說文》“仁”字從二人,會意,言己與人相親愛也。善于父母,善于兄弟,亦由愛敬之心。(27)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84、7~8、10頁。
有子此語,素稱難解,主要有兩種解釋:其一為“孝弟是仁之本”,其二為“孝弟是行仁之本”。歧解的關鍵,在于如何落實“為仁”。朱子釋為“行仁”,劉寶楠從之。若檢尋朱注,則可知其背后有精細的考量。朱注云:“本,猶根也。仁者,愛之理,心之德也。為仁,猶曰行仁。”(28)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8年,第70、71頁。仁是內在的“愛之理,心之德”,孝是外在的言行表現。基于仁內孝外的理解,便無法解為“孝是仁之本”,遂有“行仁”說。劉寶楠不欲牽涉理學家所建構的仁學孝論,故在隱去“愛之理,心之德”等內容后,引用此說。只是,脫離朱子提供的論證前提與理論背景,則“行仁”說在何種意義上仍得成立,便成問題。
又,《學而》篇有曾子自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注家聚訟于“傳不習乎”句。何晏注云:“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29)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4頁。是以曾子為人師,通過聚徒教學,將夫子之道向下傳衍不息。朱子則云:“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自治誠切如此,可謂得為學之本矣。而三者之序,則又以忠信為傳習之本也。”(30)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書社,2008年,第70、71頁。朱注以曾子為修身之學者,而非教授之人師,又將忠、信與傳習理解為“自治”的修身功夫,進而以忠、信為“傳習之本”,是用內、外區分“忠信”之本與“傳習”之末。于是,曾子“三省”之言,乃為勸人修行的寄語。在此基礎上,本章的言說對象,被落實為修德之學人。劉寶楠從朱注,認為“傳習”乃好學之事。其疏云:“今曾子三省,既以忠信自勉,又以師之所傳,恐有不習,則其好學可知。”(31)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84、7~8、10頁。但劉疏只取其局部論斷,而略過背后一整套圍繞修身而闡發的解讀。(32)至于其他,如皇侃義疏,劉寶楠亦多有引述。但也同樣經過謹慎、細心的“選材”,著意剔除其中涉及清玄的“雜質”。此不贅引。
對劉寶楠而言,“斷章取義”有其必然性。因為引文或《論語》諸解,或多或少都雜有注家的一己之見,不得不予以“清理”。劉疏由此陷入兩難:若不借助前人成果,便如撤去求索經義的階梯,無處借力;若通過材料鋪陳以展開論述,則必須“裁剪”。左支而右絀,捉襟則見肘,此為“實事求是”之學的困難。不過,該困難只如征顯出來的“病癥”,其“病根”在于:以皇疏、朱注為代表的傳統《論語》學解釋,與以追尋原意的實事求是之學,是兩種不同質的詮釋方案。
解釋與原意之間,皆存在或遠或近的距離。橫亙于其間者,可能是解釋者的建構目標、思想預設或理論偏好等,不一而足。換言之,我們總能從各種解讀中,離析出額外的信息。實事求是的追求,可能導向對所有注解的否棄。劉寶楠已經邁出了一步,所以時或通過批判眾說而自下己意。這也意味著,選擇借助于材料的引證、鋪陳來疏解經、注,注定難以“實事求是”。此為劉疏的內在張力。斷章取義、利用材料,也就在所難免。究其因,乃在于不存在一種單純以澄清原意為目標的客觀解釋,可供劉寶楠參考。誠然,追尋本意為解釋的目標,但這并不妨礙一切解釋都或隱或顯地含有建構性、時代性與個人性的色彩。
此為實事求是之學的悖論:因為不存在一種絕對意義上的“實事求是”之解。所以“實事求是”的追求,正是劉寶楠無法“實事求是”地運用材料、求索經義的根本原因。此悖論所揭示的是,實學與傳統解釋學是兩種不同質的解讀方案。重禮與考史的“實事求是”之學,旨在回到經文誕生的原語境中追尋本意。這種解釋方案,預設了封閉的原意,或將導致可以容納、生發豐富可能性的“經典”,扁平化為存在“唯一解”的原典。即便“最優解”難有定論,但在理論上只能有一種理解。諸說之間,完全互斥。
純粹的“實事求是”之學,缺乏或刻意摒除明確的建構意圖,將導向只以澄清為目標的解釋活動。而鄭注、皇疏或朱注等更為傳統、典型的《論語》學解釋,則呈現更強的現實性,并不排斥思想建構。這種解釋,符合“經典、經師與現實”的三元互動結構:解釋經典的活動,本質上是帶有“當代”思想觀念的經師根據現實需要,重返經典,尋找回應現實問題的理論資源。譬如,鄭玄身處“經學中衰時代”,(33)皮錫瑞:《經學歷史》,中華書局,2008年,第141頁。彼時之今古文經學分庭抗禮、互攻若訾。鄭注群經,參合眾學,從而建構以古學為宗、兼采今學的新經學,經學暫歸一統,學者有所歸趨。皇侃兼綜儒玄,援引體無論、本跡論等玄理解讀《論語》,其中不無融通諸教的用意。(34)谷繼明:《“同物示衰”:南朝〈論語注〉中的圣人形象》,《人文雜志》2018年第1期;皮迷迷:《“隱圣同凡”:〈論語義疏〉中的孔子形象》,《哲學研究》2020第5期。至于朱子,則以修身為主旨,將《論語》理解為成圣指南,旨在通過添入、豐盈內圣之維,回應佛老挑戰,并為外王理想重新奠基。
由此觀之,思想建構與追尋原意之間,交織難以離析,遂能筑起蔚為大觀、異彩紛呈的經典世界。傳統的解釋活動,是經師通過切己、適時的方式,對經義予以新理解、新表述,以煥發經典的活力。與之相比,實學雖也反映了一代學風,但其現實指向性則受到抑制。在這一意義上,“實事求是”之學近于求真的知識活動。傳統解釋學與實學的不同質——前者認為澄清與建構可并行不悖,后者惟愿澄清原意——導致了“實事求是”之學的悖論,讓既追求“實事求是”,又必須依靠歷代解釋史為基礎的劉疏,陷入兩難。
耐人尋味的是,如果“實事求是”之學所要求的無非是回到原語境中揣摩本意,從而避免過度發揮。那么,過往的《論語》學何以未能依循這種看似合理的訴求?解題的關鍵,不在《論語》的解讀者,而在《論語》本身。
四、“實事求是”之外
解經方法不是絕對中性的工具,故存在方法與對象之間相適與否的問題。《論語》自身的特質,決定了“實事求是”之學無法成為最佳方案。那么,《論語》本身有何顯著特點?
皇侃對《論語》有一精準的把握:“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35)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第12頁。首先,《論語》所載,多為夫子的隨疾與藥、應機行教,是根據不同言說對象所施予的教誨,在應答之際演繹出豐富道理。其次,謂夫子之教為“應機適會”或“隨須而與”,揭示出《論語》一書所具有的隨機與松散特質。夫子為教,感而遂通,靈活圓轉。義旨妙理,由不同請益或偶然事件所觸發,篇、章之間未必呈現嚴謹的邏輯性或規律性。所以,《論語》一書就是孔門行教之集合,因隨機而松散。《論語》這一特點,造就其詮釋的開放性。帶有不同思想背景的人,都能于這片義理繁富的詮釋場域中,找到共鳴且自圓其說。反之,這部“松散”的經典,需要并等待著一個整全的思想背景為之奠基。這個思想背景的核心,便是對于孔子的理解。因為《論語》的主角,無疑就是夫子。有一種孔子形象,便有一種理解《論語》的方式。
鄭玄、皇侃與朱子等傳統注疏家,于此頗為自覺,遂借助于先在的背景與零碎的“材料”,構建風格迥異的《論語》學。鄭玄認為,三代政教已窮盡所有的政治經驗,夫子并無制作之必要,故為綜匯三代經驗的整理者而已。(36)鄭注“十世可知也”章云:“自周之后,雖百世,制度猶可知,以為變易損益之極,極于三王,亦不是過。”王素:《唐寫本論語鄭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4頁。因此,鄭注尤其關注《論語》與五經的關聯。皇侃則以夫子不得為政而行教,乃為有德無位之圣師。(37)《自序》:“但圣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游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返魯,刪詩定禮于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第1頁。所以皇疏重在還原孔門的行教現場。若朱子,將圣人標榜為修身模范,于是《論語》便為后學的修身指南。(38)朱子在《論語章句集注》的序言中,引述程子之語云:“讀書者當觀圣人所以作經之意,與圣人所以用心。圣人之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朱熹:《四書章句集注》,岳麓出版社,2008年,第67頁。所以說,一種圣人觀對應一種《論語》學。諸家皆為解讀《論語》提供完整的背景。
劉寶楠則不然,他并未能將零散的思想組織起來,以形成一貫而完整的《論語》學。這就表現在,他對諸如圣人觀等前提性問題的認識,十分含混。比如,《八佾》“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句中,劉寶楠論及“孔子何為”的問題,先云“夫子學二代禮樂,欲斟酌損益,以為世制”,次引《漢書·藝文志》曰“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圣之業,乃稱曰‘夏禮吾能言之’云云”。(39)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135頁。若據前說,則夫子損益三代之禮,是為了制作一代大法,創為“世制”。若如《藝文志》所言,則夫子僅為“存前圣之業”的述而不作者。兩說分別對應今文經學的素王說與古文經學的傳述說,判若冰炭。劉寶楠卻混而言之,可見他未對圣人觀問題有足夠清晰的判斷。又,《八佾》篇載有一則故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喪乎?天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
現已無從得知儀封人與孔子交談的內容,但儀封人顯然大受震撼,慨嘆不已,預言夫子將為“天之木鐸”。問題是,“木鐸”何謂?換言之,孔子何為?《集解》引孔安國注云:“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于天下”。(40)何晏注,邢昺疏:《論語注疏》,中國致公出版社,2016年,第49頁。皇侃雖以《集解》為底本,卻悄然改易其意,其疏曰:“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41)皇侃:《論語義疏》,中華書局,2013年,第79頁。皇疏隱蔽地將“制作法度”“號令天下”的王者之姿,變換成周游施教的人師形象。所以,對于本段經文,有為君或為師、行政或行教兩種解讀思路。但原文提供的信息,實不足以斷定或排除任何一種解釋。只能認為,兩種解釋分別對應了兩種圣人觀和《論語》學。由此可知,注疏家必須先選取一種圣人觀或立場之后,方能落實“木鐸”的寓意。劉寶楠卻未能或拒絕作出“決斷”,故含混其詞云:“夫子不得位行政,退而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是亦制作法度也。”(42)劉寶楠:《論語正義》,中華書局,1990年,第92、135頁。劉疏仍想居中調停,故有“是亦制作法度”的兩可之辭:一方面,并未完全排拒制作之意;另一方面,卻用“亦”來提示讀者,這并非是今文經學意義上的制作,而是傳經、修史意義上的“制作”。是仍在“作”與“述”之間游移不定。所以,在碰到涉及孔子形象的問題時,劉疏顯得捉襟見肘。
究其因,仍在于“實事求是”之學的局限。“實事求是”的目標,將劉寶楠的注意力吸引到禮制和歷史的考證之中。正如劉疏在解釋“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句時,將主要精力放在考證“木鐸”的形制、“儀”的方位和夫子是第幾次適衛的歷史背景中,卻對經文的根本性問題——“木鐸”的寓意與孔子身份問題,閃爍其詞。一方面,“實事求是”之學企圖通過考證禮制與歷史,回到原語境中,這自然有助于增進對于某句經文的理解,卻無法為《論語》提供一個完整的圖景,讓諸“思想點”呈現出一貫性與系統性。因為劉寶楠苦心澄清的原語境,不過是孔子“應機行教”的場景。而隨機、偶然情況觸發的語境之間,無法呈現關聯性。劉疏常將人陷入瑣碎的失焦感,蓋因于此。另一方面,對于“孔子何為”的圣人觀問題,是理解《論語》的前提。若不先作出判斷,則難以提供清晰切要的解讀。只是這一前提性問題,更像是立場的選擇。因為很難認為鄭、皇、朱等經師間的歧見有絕對意義上的高下之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對《論語》的具體經文做實事求是的探究。但在解讀《論語》之前,所必須面對的立場性、前提性問題,并無法通過“實事求是”的方式,確定一個穩健的、完美的答案,而是需要一個“決斷”。這是“實事求是”之學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也是“實事求是”之外的問題。
五、“實事求是”之后
劉疏不夠且難以“實事求是”的表現,已如上述。如果發揚實證精神,貫徹“實事求是”的思路,又將如何?“實事求是”之學有兩個關鍵——歷史化的理解方式與純學術的中立客觀,這正是醞釀、觸發經學危機的兩個因素。
先看歷史化的問題。華喆先生認為:“乾嘉學者以考據作為研究經書的基本途徑,力圖通過考據的方式,求得思想無誤的文本,從而進行了對于經書的古典重構。然而這種研究方法也使得經典之中的內在邏輯遭到破壞,使經學走上了史學化或小學化的道路。”(43)華喆:《〈儀禮·士冠禮〉“鄉大夫”“卿大夫”辨正——兼議乾嘉考據學對經書文本的古典重構》,《文史》2020年第4期。藉由考證歷史背景與禮制細節的方式,乾嘉學者意欲還原經文的背景,同時也將孔子及其言教限定于原初語境之中,化作與當下現實“失聯”的歷史陳跡。經難以自立,而漸淪為史,是為經學退出歷史舞臺的先聲。
次及“純學術”的問題。首先,前提性的問題往往難以確證,卻又偏偏是解經的管鑰。這就導致對立場性問題的排拒警惕而不置可否,看似穩健,實則有其代價。回避問題并不等于問題被解決,反倒會造成“實事求是”者與經典本身、解釋傳統的疏離與隔閡。對于每個要進入經典世界的人而言,或早或遲、有意無意間,“決斷”都無所逃遁。其次,如果說近于“純學術”的“實事求是”之學與現實感更強的傳統經學,是兩種不同質的解釋方案,正說明,推崇考據的“實學”,也不過是一種深具時代性的研究方式而已。正如對“無立場”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旗幟鮮明的立場。“實事求是”,只如一個自負卻事與愿違的口號。它不過表明了經典解釋的一次轉向:從經典、經師與現實三元互動的傳統經學,轉而為經典與解釋者之間的考證“游戲”。要言之,對實學的無限推崇,將日益削弱經典、經學的教化之維與現實意義。
由是觀之,劉寶楠“點到為止”的“實事求是”之學,是介于傳統學問與現代學術之間的“中間狀態”,亦為古、今之學的“轉折點”。正因如此,行將越出傳統經學邊界并反噬其獨立性的實學,恰好為觀察經學的本質與外延提供了外部視角。一言以蔽之,因全然學術化、歷史化而失去現實感的經學,終將失去力量而萎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