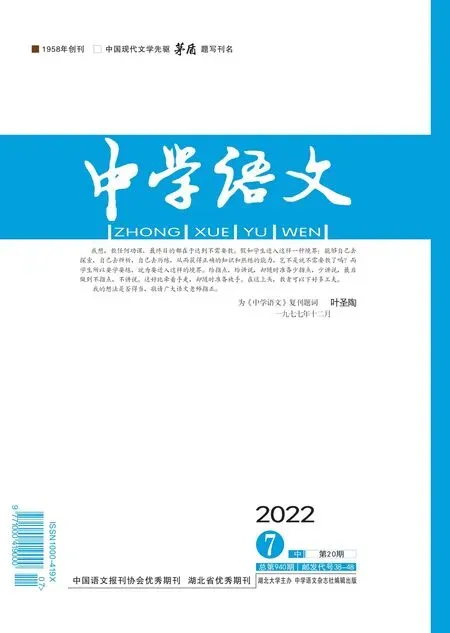由“抑”轉“揚”背后的三個深層原因
——《阿長與〈山海經〉》的互文解意
朱慧 楊兆君
《阿長與〈山海經〉》是入選統編初中語文教材的魯迅名篇,也是散文集《朝花夕拾》十篇文章中的一例。文章在寫到阿長為小魯迅買來《山海經》的事情時,敘述的筆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先前直言對這位勉強稱得上稱職的保姆的不耐煩、厭惡,此處急轉為真誠的敬意和贊揚,微微戲謔和淡淡嘲諷也隨之消解,乃至文末處產生濃厚的懷念與抒情。準確把握文中此處情感轉折的原因,是深入認識阿長形象和阿長對魯迅意義的關鍵。若僅局限于單篇文本內部解讀該關鍵問題過于單薄,將《阿長與〈山海經〉》中產生從“抑”到“揚”突轉的問題,放置到整部散文集《朝花夕拾》的視野之中,著眼“整”字聯讀其他文章,在互文解意中能更為深入地挖掘到轉折背后的三個深層原因。
一、成長:繪圖“嗜好”的啟蒙與發展
如果只是將魯迅對阿長的情感轉折完全歸因于小魯迅對一本喜好之書的獲得,或兒童好奇心的簡單滿足,是不夠準確的。這不足以構成小魯迅千方百計地去得到這本書的理由,也不能有力地解釋他拿到《山海經》時“似乎遇著一個霹靂,全身都震悚起來”[1]的狂喜,甚至長大后的魯迅明知這是一部“十分粗拙”的書,卻依舊將其視為“最為心愛的寶書”。《山海經》對小魯迅的吸引力無疑是巨大的,那么小魯迅對此書的執念之處到底是什么?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山海經》是一部關于繪圖的書,令小魯迅最為著迷的是書中的“繪圖”而不是其他,這在文本中有跡可循。小魯迅在遠房叔祖的宅子內只閱讀《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等有畫圖的書,最愛看畫了許多圖的《花鏡》,兒童對圖畫的偏愛和小魯迅的興趣可見一斑,后遠房叔祖惹起我對畫有很多奇特人獸的《山海經》的渴望。可見繪圖才是小魯迅對此書的真正興趣所在。那么為何這本圖畫書讓小魯迅如此鐘情?竟到了顛覆對阿長的情感的地步。解惑這一深層疑問不僅要從單篇文本出發,更要勾連《朝花夕拾》中小魯迅繪圖“嗜好”的成長線索。
放眼整本《朝花夕拾》,能梳理出一條魯迅繪圖“嗜好”的發展軌跡。小魯迅最先所得的圖畫本子是《二十四孝圖》,他在讀前十分期待,閱讀時卻因其僵硬虛假而萬分掃興。但到《阿長與〈山海經〉》一文中兒時《山海經》等繪圖讀物啟發小魯迅的藝術興趣,并正面陶冶其繪畫情志。《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所記小魯迅在三味書屋學習時,就用“荊川紙”細細地描摹圖像,竟形成一大本《西游記》和《蕩寇志》的繡像,這儼然是興趣發展中長期主動實踐并沉淀的過程,直至《無常》一文中小魯迅對《玉歷鈔傳》上“活無常”畫像的豐富想象和生動描述,表明他已然能夠自覺地關注并評析日常所見的圖畫。最后,成年魯迅在《后記》中以個人的繪畫審美評點各類插畫,并一一提出修正意見,魯迅的繪畫“嗜好”此時已經成熟。在《朝花夕拾》整本書的關照下,我們能看到“繪畫”是魯迅的人生意趣,繪畫愛好的啟蒙、發展、成熟的過程貫穿了小魯迅到大魯迅的成長史,成為他認識世界的窗口和自我完善的方式。縱觀魯迅先生的一生,繪畫也是他除語言藝術外用力最多、成就最高的藝術活動。
在魯迅繪畫興趣發展的脈絡中,審視阿長買來《山海經》的行為,更能體會其對小魯迅繪畫興趣啟蒙的重要意義。阿長此舉讓小魯迅在閱讀畫有神異世界的《山海經》中,見識了與現實迥異的、想象力豐富的傳說世界,既是對兒童好奇天性的滿足,也是小魯迅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返回過程,因此“我”獲得了與《二十四孝圖》之類截然不同的讀畫體驗,發現了繪畫藝術的魅力與真正喜愛的繪圖樣式,同時點燃了魯迅追求繪畫愛好的激情,文中寫道:“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繪圖的書,于是有了石印版的《爾雅音圖》《毛詩品物圖考》,又有了《點石齋叢畫》和《詩畫舫》。”[2]《山海經》實在太具啟發性,極大地鼓舞了兒時的魯迅積極發展繪圖興趣。可以說,阿長在魯迅繪畫“嗜好”的終生活動中,主動給予其《山海經》這樣一個關鍵啟蒙點,小到使小魯迅獲得興趣發展中的高峰體驗,大到賦予魯迅追求生命另一種意義的可能,為其人生增添了深刻的價值。我們可以認為,這是《阿長與〈山海經〉》中產生情感拐點的重要原因。
二、反思:兒童教育的批判與認同
《朝花夕拾》不僅是魯迅的成長史和求學史,也是魯迅以成年視角通過自述孩童時期的經歷,批判非人性化的兒童教育、反思兒童教育應有之義的思想發展史。魯迅的兒時回憶中充斥著大量兒童教育的反例,大致可分為三類:《五猖會》中父親忽視“我”作為兒童渴望參加五猖會的急切心理,壽鏡吾先生回避并怒目“我”對“怪哉蟲”的求知發問,以及三味書屋灌輸式的教學方式,都體現成人世界對兒童心理的誤讀和漠視;蒙學教材《二十四孝圖》里“老萊娛親”“郭巨埋兒”折射出封建孝道的虛偽及其對人性的摧殘,阿長執意遵行的迷信禮節也令“我”反感厭倦,衍太太要求“我”遵照某種禮制對著垂死的父親高聲喊叫,此類是封建禮教、禮節、思想對孩童心靈的束縛和毒害;最后一類則是“大人”自身惡劣行徑對兒童造成的極重負面影響,以心術不正、卑鄙下流、兩面三刀的衍太太為代表,魯迅對其深惡痛絕。上述是魯迅在整本書中所批評的兒童教育,歸根到底就是一點,即以權威專制控制兒童的身心,剝奪兒童主體自由純真的天性,這完全扭曲了兒童教育的真諦和本義。
魯迅認為父母與子女間是平等的,“對于子女,義務思想須加多,而權利思想卻大可切實核減,以準備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3]。在整部散文集中不難發現,魯迅犀利地嘲諷《二十四孝圖》中罔顧兒童生命、天性的孝子事件,深刻地反思《鑒略》、制藝和試帖詩之類把孩子當作木頭人的封建教育書籍。在當時很多兒童讀物與兒童身心健康發展完全相悖的情況下,《山海經》一書歸還孩子天真、解放孩子天性,著實可貴,魯迅對此類“以兒童為本位”的書籍是大為認同的。將這本寶書送給“我”的不是別人,正是長媽媽,她為還是孩童的魯迅買來心心念念的奇書《山海經》,相較于《朝花夕拾》中魯迅兒童時期經受的大部分教育,長媽媽為“我”這個孩童的個性發展創造了條件,實在是整部散文集中難得的正面教育之舉。
再將長媽媽與《阿長與〈山海經〉》中的“別人”進行對比,就更能理解魯迅情感急轉的原因。小魯迅曾竭盡所能地想要買到《山海經》,但“問別人呢,誰也不肯告訴我”[4],買《山海經》更是“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5],重復出現的“別人”一詞值得深思。聯系整本書中小魯迅生活的人際環境,可推測這里的“別人”可能是同為孩童的同窗、大家長父親、和善的母親、板正枯燥的壽鏡吾先生、甚至是玩弄兒童的衍太太等,除去不能做的人,那些在小魯迅多番懇求下卻“不肯告訴我”“不肯做”的人,魯迅是暗含深深的不滿和批評的,這些大人不愿回應孩童的苦苦訴求,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漠視兒童真切的需要。
在“別人”的襯托下,阿長為“我”送來《山海經》的小小教育行為就顯得彌足珍貴。這位“我”未曾抱有希望的、很是討厭的保姆卻以平等的態度正視作為兒童的“我”,她不像“別人”那般對“我”的需求毫不關注、敷衍推脫,而是設身處地地體貼“我”內心強烈的渴求,體察我的“心理”,或許她所做的只是不經意間的行為,卻給予“我”探索興趣、自我成長的天地,讓“我”能舒展地成長,這儼然是長媽媽兒童教育的“壯舉”,也是整本書中多次被提及的長媽媽最高光的時刻。此時魯迅毫不猶豫地肯定并褒揚阿長具有“偉大的神力”,對她萌發了最為真誠的敬意。基于大魯迅對阿長兒童教育行為的認同與贊賞,他的筆觸就此產生了轉折,先前與阿長之間隱隱對抗的隔閡便徹底消失了。
三、回望:個體記憶的“幻化”與再造
魯迅在其作品中經常表達對中國底層人性的批判,流露“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憤懣與悲哀。而《阿長與〈山海經〉》中的阿長盡管有非議人事、愛告小狀、粗俗迷信、愚昧無知的缺點,但魯迅并沒有嚴肅尖銳地批判其身上的“農民性”,反而以詼諧的語調進行調侃,甚至在文章末段表達對這位保姆的懷念與祝愿。其實,回憶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魯迅筆下的絕大部分人物,除去毫無優點的衍太太外,在魯迅對記憶的回望中都籠罩著一層淡淡的暖色,連古板無趣的壽鏡吾先生,在拗頭讀書的時候也顯得格外可愛動人,這與魯迅基于回憶視角創作整本散文集運用的藝術手法有直接關系。
《小引》里寫道“便是現在心目中的離奇和蕪雜,我也還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轉成離奇和荒蕪的文章。”[6]將記憶材料進行“幻化”,可以理解為魯迅在創作散文集時出于一定的考量,對記憶材料進行加工處理的再造過程。有學者也指出:“《朝花夕拾》是魯迅先生回憶自己過去生活的散文,既有濃濃的苦澀,也有絲絲的甜美,其中的一部分正面形象,融入了魯迅對他所堅持的‘最理想的人性’形象的塑造。”[7]這于魯迅對阿長形象的塑造有所印證。魯迅在《自言自語》里提到:“啊! 我的老乳母,你并無惡意,卻教我犯了大錯,擾亂我父親的死亡。”[8]這在《朝花夕拾》內分明是《父親的病》一篇中,衍太太慫恿“我”在父親死前高聲叫喊令父親不得安寧的過失,就阿長保姆的身份和《自言自語》中更為真切的直述而言,這“對于父親最大的錯處”[9]是魯迅在阿長的誘導下所犯較為可信,但魯迅卻將之轉移到衍太太身上,阿長的形象從而得以“美化”。無獨有偶,同樣是回憶性寫人散文的《藤野先生》,魯迅也有意隱去藤野先生就是那位多次勸說“我”另尋住處、幫了倒忙的先生的事實,而將敘述重點放在表現其“偉大”性格的事件上。整本書層面“幻化”手法的運用,可以為作者對阿長從“貶”轉“褒”的突轉提供一定的解釋,這正是散文集整體創作和語調的回響。
在對藝術形象“幻化”和再造的背后,是中年魯迅回憶兒童時期經歷時自我情感的個性化表達,還原了兒時孩童的生活感受與體驗,又傾注了中年感慨、自省及些許寬慰的情緒。回憶性視角在時空距離中產生情感再視的可能,這位連書名都未識得的底層保姆為她的雇主尋得他人都無能為力的《山海經》,可以想象其中幾番周折,也可體察其中樸拙的愛護。這童年時期所受的誠摯關愛,對中年時期的彷徨的魯迅何嘗不是一種安慰和激勵?盡管她不懂得民間禮節的緣由和缺陷,但卻真誠地相信只要“我”遵行就可避災獲福,在成年魯迅的視閾中,何嘗不透露著底層的純善?書中那位貌似僅是恪守教職、認真負責、關愛學生的藤野先生何以在魯迅眼中“偉大”?或許是他回首不甚滿意的求學經歷和弱國子民的屈辱的過往間,這位先生曾給予少年真誠的教導和超越性的尊重。在充滿個體記憶、彌散個人情緒的《朝花夕拾》中,魯迅以回望的姿態書寫那些曾給予他善待與愛意的人,筆端自然地流露內心的溫情。或許通過對記憶的“幻化”和再造,能實現“記憶哄騙我一生,使我時時反顧”[10]的情感目的。
在整本書視野下,探究《阿長與〈山海經〉》一文中阿長形象由“抑”轉“揚”的深層原因,可以讓我們讀到不少從單篇文章中較難讀出的新元素,深化了我們對魯迅童年成長經歷、終生興趣發展、兒童教育思想的理解,也深掘到《朝花夕拾》基于回憶視角個性化創作的特點及背后的情感因素,在作品集的內部關聯和整體統照中,抵達對單篇散文更具高度和廣度的理解,以期對名篇《阿長與〈山海經〉》和名著《朝花夕拾》的教學有所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