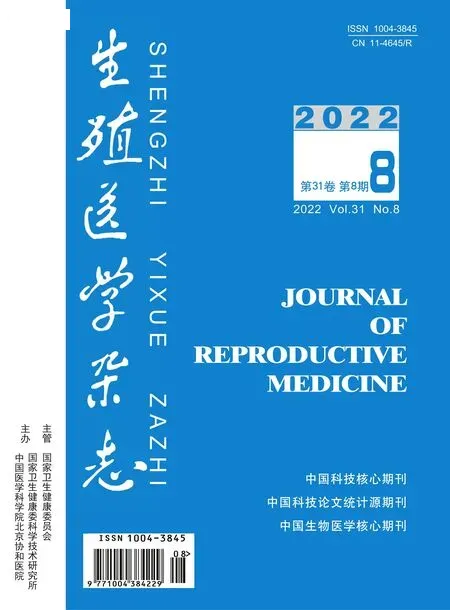大動脈炎患者的生育力和妊娠風險
代倩文,鄧姍
(中國醫學科學院 北京協和醫學院 北京協和醫院婦科內分泌與生殖中心,國家婦產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北京 100730)
大動脈炎不孕病例
患者,女,33歲,已婚,G0,因“未避孕不孕及發現卵巢囊腫2年”于2021年10月25日入院。
患者既往月經規律,5~7 d/28 d,量中,痛經(-)。2017年2月于我院診斷大動脈炎(廣泛型),影像學評估雙側頸總動脈、腹主動脈及肺動脈受累,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環磷酰胺(CTX)]治療效果不佳;2017年5月行右頸部無名動脈支架植入術,術后定期監測病情穩定。目前用藥:甲潑尼龍片、羥氯喹(紛樂)、螺內酯、呋塞米、阿司匹林。我院免疫科評估無妊娠禁忌。自服用激素后月經不規律,表現為月經周期及經期延長,5~30+d/30~90 d。2018年當地醫院行婦科超聲發現雙附件囊腫,直徑2 cm,定期觀察。2019年起備孕,予芬嗎通1片/d后月經正常,超聲監測有排卵,排卵試紙自測弱陽性。2019年9月22日當地婦科超聲示右附件探及多個囊性無回聲,最大約2.5 cm×2.6 cm、2.6 cm×2.6 cm,左附件探及大小4.2 cm×3.2 cm無回聲,邊界清。2020年8月4日檢測FSH 8.11 U/L、E2(Ⅱ) 78 pg/ml(285.5 pmol/L)、AMH 0.85 ng/ml。2021年8月查男方精液正常,2021年7月外院輸卵管造影示雙側通暢。患者未避孕未孕2年,有生育需求,擬行宮腹腔鏡手術入院。
入院后復查AMH 0.39 ng/ml、FSH 3.93 U/L、E2(Ⅱ) 83 pg/ml(303.8 pmol/L);血清腫瘤標志物均陰性。超聲提示左附件區見無回聲,7.5 cm×7.4 cm×6.6 cm,邊界清;右側附件區見兩個無回聲,大小分別為2.9 cm×2.1 cm、3.1 cm×2.8 cm,均邊界清,透聲可;彩色多普勒血流顯像(CDFI)均未見明確血流信號。考慮患者卵巢儲備功能下降,而盆腔囊腫無惡性征象,建議先行超聲引導下囊腫穿刺。后在超聲引導下左側囊腫穿刺引流220 ml清亮液,右側囊腫兩囊分別穿刺出15 ml和7 ml黃色清亮液,病理細胞學檢查均未見瘤細胞。出院后轉生殖中心助孕。
大動脈炎妊娠病例
患者,女,27歲,已婚,G1P0,主因“宮內孕34周,胎兒進行性偏小近3月”入院。
平素月經規律,6 d/31~35 d,末次月經(LMP):2018年3月19日。2013年4月于我院診斷大動脈炎,2017年11月8日于阜外醫院行胸主動脈支架植入術。2018年7月17日超聲:大動脈炎累及腹主動脈上段、左側頸總動脈、左側頸內動脈,腹主動脈上段輕度狹窄(血流較通暢),左側頸總動脈全層壁增厚(閉塞管腔),左側頸內動脈全層壁增厚(管腔輕度狹窄,血流較通暢),左側椎動脈代償性擴張,右側頸總動脈內徑代償性增寬;腹主動脈中下段、雙腎主干未見明顯狹窄。孕前口服硫唑嘌呤(依木蘭)100 mg qd、潑尼松10 mg qd、阿司匹林0.1 g qd、碳酸鈣60 mg qd、骨化三醇0.25 μg qd、拉貝洛爾100 mg Q8h、拜新同30 mg qd,孕期阿司匹林調整為75 mg qd。
此次妊娠為自然妊娠,我院規律產檢,早孕期超聲核對預產期準確。早孕期血壓尚可,停拜新同,孕中期后血壓逐漸升高,拉貝洛爾加量至150 mg Q8h,血壓仍控制不滿意,再次加用拜新同30 mg qn。自中孕(孕22+3周)排畸超聲時即提示胎兒偏小,后期多次超聲示胎兒雙頂徑(BPD)、頭圍(HC)、腹圍(AC)較相應孕周偏小約2~3周。孕30周臍靜脈穿刺完善染色體核型及基因芯片檢測均未見明顯異常。孕33+4周因胎兒進行性偏小(各項指標位于相應孕周第1~4百分位),血壓不平穩入院評估。
入院查體:左上肢血壓135/70 mmHg,右上肢血壓149/68 mmHg。予地塞米松促胎肺成熟治療,吸氧,監測血壓情況,加強監護,同時內科會診,評估病情并指導圍術期用藥,準備適時終止妊娠。住院觀察2 d后,因反復胎心監護不滿意,孕34+2周剖宮產終止妊娠,娩1女活嬰,體重1 640 g,因小于胎齡兒轉兒科。
病例警示
一、大動脈炎概述
大動脈炎(Takayasu arteritis,TA)是指主動脈及其主要分支的慢性進行性非特異性炎癥引起的不同部位動脈狹窄或閉塞,少數可引起動脈擴張或動脈瘤,出現相應部位缺血。多見于年輕女性,男女比例約1∶4,約90%患者在30歲內發病。西方人年發病率為(1.2~2.6)人/百萬,亞洲人年發病率為(0.4~2.0)人/百萬[1],東南亞、南美洲及非洲相對高[2],在遠東人群中年發病率高達40人/百萬[3]。
TA病因未明,其病理生理過程表現為動脈壁增厚、纖維化、狹窄、閉塞和血栓形成等,可導致動脈擴張及動脈瘤形成。臨床癥狀根據受累的血管及其程度,可表現為無脈、脈搏減弱、血壓測不出及血管雜音等,或與血管狹窄相關的跛行、肢體麻木、視覺改變、癲癇、血壓改變等[4]。但TA疾病發作隱匿,早期癥狀非特異性,通常造成診斷延遲。
臨床上根據病變部位分為4型:(1)頭臂動脈型(主動脈弓綜合征):頸動脈和椎動脈狹窄和閉塞,表現為頭暈、視力障礙、偏癱,一側或雙側上肢血壓降低或未測出。(2)胸腹主動脈型:由于缺血,下肢出現無力、酸痛、皮膚發涼和間歇性跛行等癥狀;腎動脈受累則出現高血壓,以舒張壓升高明顯。(3)廣泛型:屬多發性病變,多數患者病情較重。(4)肺動脈型:約占50%。上述類型均可合并肺動脈受累,單純肺動脈受累罕見[5]。
評估TA的血管受累情況,臨床癥狀、血清學指標特異度較低,影像學是重要手段。動脈血管造影(DSA)是診斷TA的金標準,而18F-氟代脫氧葡萄糖正電子發射計算機斷層顯像(18F-FDG PET-CT)被認為是目前最能反映疾病活動性的影像學手段[6],彩色多普勒超聲作為非侵入性手段,應用廣泛,但不能檢查胸主動脈及深在部位的分支血管,在妊娠期孕周較大時評估腎動脈困難,有一定局限性。目前特殊情況下可用磁共振血管造影(MRA)代替CT血管造影(CTA)來評估主動脈病變。
針對疾病的活動性評估:最常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提出的Kerr評分[7],當患者滿足以下2條或以上時評判為疾病活動:(1)全身癥狀,如發熱、骨骼肌肉相關癥狀;(2)血沉(ESR)和/或C反應蛋白(CRP)升高;(3)血管缺血:跛行,脈搏減弱,無脈,血管雜音,血壓不對稱;(4)血管造影異常。TA活動提示血管炎癥加重,可伴有危及生命的心血管并發癥,需結合臨床特點以及影像學表現綜合評估。
TA治療包括糖皮質激素、免疫抑制劑及生物制劑、抗凝藥等,其中激素治療是妊娠期TA最重要的治療方法,可抑制動脈炎進展。糖皮質激素和CTX是常用的聯合治療方案,大部分患者初次治療可達到緩解,但2/3的患者面臨復發或依賴大劑量激素維持。生物制劑可用于難治性TA的治療。對于血管嚴重狹窄、閉塞或動脈瘤形成的患者,手術治療是解除患者臟器缺血以及改善癥狀的主要方法。TA約20%為自限性,無并發癥可隨訪觀察。本文中兩例病例均屬于TA(廣泛型),發病時病情嚴重,均行支架植入術以改善癥狀,術后需長期使用激素和/或免疫抑制劑控制病情。
二、TA對生育力的不利影響
對于診斷TA的年輕女性來說,存在因疾病影響卵巢儲備和未來生育能力的擔憂。在一項小型病例對照研究中,通過FSH、LH和E2及AMH測定或竇卵泡計數(AFC),發現TA 患者的卵巢儲備可能減少[8]。但大多數研究表明,TA患者生育率并未受到影響[9]。與正常女性一樣,高齡、手術和類固醇激素引起的下丘腦-垂體-性腺軸功能障礙均會影響卵巢儲備功能[10]。如合并自身免疫性卵巢炎和/或使用免疫抑制藥物,特別是靜脈注射CTX,更容易導致卵巢儲備減少[11-12]。CTX是用于治療血管炎的最有效藥物,但在育齡婦女中,可導致20%~85%患者不孕或生育率低,具體取決于累積劑量和患者年齡[13]。本文中第1例不孕患者28歲起病,因病情嚴重予激素沖擊、CTX累計12 g及甲氨蝶呤等治療,病情穩定后亦未盡早積極備孕,隨著年齡增長及TA的影響,卵巢功能進一步降低也在所難免。但生育力的受損往往是不可逆的,即便借助輔助生育技術,能否實現生育愿望仍是不確定的。本文中第2例患者22歲起病,病情亦較重,需手術治療和長期激素及免疫抑制劑管理,也屬高危妊娠。
因此,雖然TA 患者未來的生殖健康狀況并不明確,但有必要與患者討論這類問題,尤其是卵巢儲備功能低下的年輕患者,需盡量避免應用卵巢毒性藥物。鑒于生育力保存技術已經應用于臨床,在應用CTX前,年輕未生育的患者可考慮冷凍保存卵母細胞、卵巢組織和/或胚胎,或同時使用促性腺激素釋放激素激動劑(GnRH-a)阻斷,以保護卵巢功能[14]。
三、TA妊娠的高危所在
1.妊娠對TA的影響:關于妊娠對TA疾病活動性的影響有不同的報道。有研究觀察到TA的炎癥活性在妊娠期間會降低,類似于妊娠對類風濕性關節炎的影響[15];但也有研究提出相反的證據[16]。妊娠期間TA病情活動/加重的發生率通常小于5%,出現病情加重的患者中高達40%與研究對象大多數處于疾病活動期或在妊娠期發病有關[17]。
妊娠對大多數TA患者沒有明顯影響。但TA患者易合并慢性高血壓、腎功能不全等,妊娠后發生的循環血容量增加和心臟負荷增加,各臟器負擔加重等生理性變化都可能給TA患者帶來更大的沖擊,導致血管病變的惡化,如主動脈瓣關閉不全惡化、充血性心力衰竭、腎功能不全惡化、肺栓塞和缺血性心臟病等。TA合并妊娠還可能出現血管損傷、心腦血管意外,心腦血管事件是導致死亡的主要原因,占妊娠期TA中所有孕產婦死亡的5%~19%[18]。TA患者在妊娠期也可發生主動脈夾層甚至破裂,如發生胸痛,需進行緊急評估和治療[19]。
2.TA對妊娠的影響:TA不是妊娠禁忌證,大多數妊娠是成功的[20];但患有TA的女性易患合并癥,可能會對母胎的結局產生負面影響。妊娠期高血壓和子癇前期是妊娠合并TA患者最常見的并發癥。文獻報道,TA患者和一般人群妊娠期高血壓疾病的發病率分別為54%和8%,胎死宮內也更常見[21-22]。疾病越嚴重,母胎并發癥越嚴重。腎動脈和腹主動脈受累患者發生子癇前期和胎兒生長受限(FGR)更常見[23-25]。
影響TA患者母胎結局的因素包括:(1)疾病活動度:法國一項納入98例TA妊娠病例的研究發現,按照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之前發布的活動度評分標準,活動評分>1是發生產科并發癥的獨立危險因素[17]。疾病活動對母胎結局的不良影響可能是由于胎盤炎癥導致合體滋養細胞、血管內滋養細胞、螺旋靜脈的內皮細胞和蛻膜的淺表/腺體上皮細胞損傷,導致植入受損和胎盤灌注受損。當疾病在妊娠期間活動時,母體相關并發癥(如妊娠期高血壓疾病)而不是胎兒相關并發癥(如FGR)會增加。因此,孕前控制病情穩定至關重要。(2)高血壓和受累血管:慢性高血壓是影響母胎結局的另一個重要因素[16],受累血管越多,妊娠期母胎不良結局發生率越高。(3)疾病診斷時機:孕前或孕期診斷TA的患者一般血管炎更嚴重[26]。結合本文中的第2例病例,孕前TA累及頭臂動脈及胸腹動脈,合并慢性高血壓,需多藥聯合降壓治療,孕期血壓控制欠佳,尿蛋白陰性,不考慮妊娠期高血壓或子癇前期,但仍出現早發型FGR。
綜上所述,TA易發于年輕女性,病因不清,但無論自身的免疫損傷還是藥物治療的副反應,都可能造成卵巢儲備功能的下降;對于尚未完成生育的患者而言,應重視卵巢保護,或尋求生育力保存技術。控制平穩的TA患者可以妊娠,大部分妊娠結局是良好的。但TA固有的血管病變病理基礎仍會增加發生母胎并發癥的風險,以妊娠期高血壓疾病和FGR最為常見,但也會因急性心腦血管事件導致孕產婦死亡,需要產科和免疫科聯合管理,嚴密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