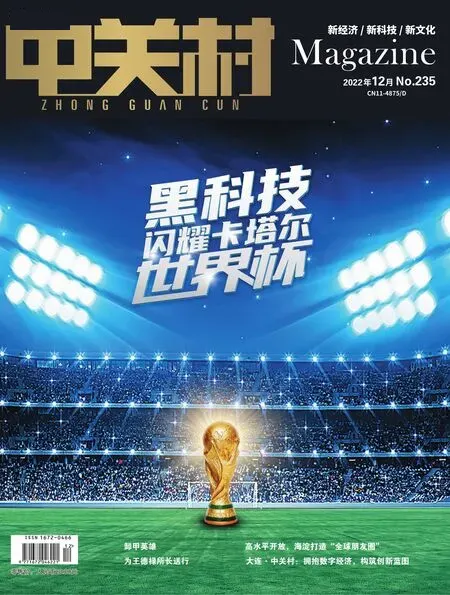學以至圣:從“為學”與“成圣”的內在關系看大學思政課的理論通路
文趙月
《近思錄》第二卷對于顏淵的“為學”觀念及其方法高度推崇,在“為學”卷的開頭,周敦頤便說“志伊尹之志,學顏子之所學,過則圣,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于令名。”孔子、周敦頤、朱熹、程頤等諸多大學問家,評價都如此之高。顏子之學其內容是怎樣的,他究竟又是如何去學的。這兩個問題實際上就已經闡明了顏淵為學之道中所蘊含的兩個最基本的問題。
一、學以致知是學以成圣的理論前提
“學以至圣”這一思想當中,蘊含著三個基本維度,一個是“學”的問題,一個是“圣”的問題,還有一個是學以至圣的可能性的問題。我們常常稱孔子為“孔圣人”,“圣人之門,其徒三千,都稱顏子為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都好者,何學也?”學以至圣的第一個理論前提便是“學”,想要學以至圣,先要學以致知,我們常用“學而知之”這個詞來闡釋這層意思。想要理解這個詞,我們就必須要清晰“知”的對象是什么,也就是“之”為何物。
首先,我們要明確“學”的問題。學而知之的“之”,不是經驗事物,從孔子與樊遲的對話中可見一斑。“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稼穡也好,園圃也好,這些經驗事物都是需要后天習得,但在孔子生而知之或者學而知之的語境之下,不可謂“之”,也就是說,這些經驗事物不是“知”的那個對象,不然孔子也不會說,自己在稼穡之事上不如老農,在園圃之事上不如老圃,更不會說樊遲是個徹頭徹尾的小人。因此孔子所說的“知之”,不是經驗事物。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第一,孔子在這段論述中提出了“生而知之”、“學而知之”的思想;第二,孔子把“知”的品質做了四個不同等級的細分,生而知之為最高。朱熹解釋道,孔子這段話“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四等”;第三,圣人生而知“之”的“之”不是經驗事物;第四,“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在品質上是不同的,在等級上有高下之分,但是對于“知的對象”而言,是一致的。事實上,在孔子這個語境下,知的對象不可能是經驗事物,只能是道體,否則孔子這樣的品質劃分沒有意義。必須針對同一個“知”的對象的不同品質,這樣的劃分才能在邏輯上說得通。
其次,我們來探究“圣”的問題。孔子把道體當作是圣人生而知的那個對象,生而知之的人,大道便是與生俱來的。在孔子那里,圣人等同于圣王。但是孔子本身并不認為自己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也。”孔子認為自己不是個“生而知”者,孔子也說道,“圣人,吾不得而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以。”《近思錄》為學卷開篇就談及,“濂溪先生曰:圣希天,賢希圣,士希賢”。圣人都是與天道合一的人,能夠參天地、贊化育,是非常難得,孔子也說難得一見。我們得見的只是君子,是賢德之人,顏淵便是最為典范的大賢之人,周敦頤認為,超過顏淵那便是圣人,趕上他便是賢者。
二、學以至圣的理論根據
學以至圣的理論根據,實際上便是用以回答“學以至圣”的可能性問題的。在孔子那里談及的學與圣,不是學以至圣,因為孔子沒有這樣論述過。“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子曰:圣人,吾不得見矣”。圣人已然被孔子標榜為德業兼備的人,的確是難以企及,孔子尚且自謙,圣人在孔子那里是難以企及的。孔子非常重視“學”的作用,“吾十余五而志于學”、“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類似的論述在《論語》文本中隨處可見,無須贅述。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孔子從來沒有把自己看作是圣人,直到宋明理學時期,才突然間掀起了一股把孔子作為“生而知之”的圣人的風潮。
孟子對于孔子的圣人思想有所發展,“曹交問曰:人皆可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孔子也把堯舜稱之為圣人,孔子文本中多處可見,毋庸置疑。但堯舜在孔子看來,是位、德、智集于一身的“神人”,而孟子談到的堯舜,較之于孔子有所不同,“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圣人,人倫之至也。”孟子這樣的論述實際上把孔子所言及的位、德、智一體的圣人觀念,轉化成了完滿德性,這樣一來,學以至圣的難度大大降低,其可能性便隨之增大,甚至可以說,這就從性善論的角度徹底打開了人皆可成圣賢的通路。
三、學以至圣的理論張力
在“學”與“圣”之間的內在關系的分析中,學而知之是成圣的一個途徑,但我們不得不考慮“生而知之”這件事,如果按照這種思路去考慮這個問題,生而知之不能作為成圣的途徑,生而知之是圣人的內在屬性,是圣人內在的知識來源,按照孔子的思路,這是一種天賦的知天和知道的能力。但是在《孟子》的文本里,我們可以發現,孟子對于生而知之和學而知之這一問題的說法,是存在矛盾的,這種矛盾賦予了這兩個理論以內在的張力。
“曹交問曰:人皆可為堯、舜,有諸?孟子曰:然。”這是學以至圣的理論根據,孟子給學以至圣提供了一條理論通路。存在理論張力的地方不是“圣”的概念本身,其理論張力處在成圣的過程中,不是“人人皆可為堯舜”與“身之、性之”存在矛盾,“身之”或者是“性之”這一觀點,按照朱熹的理解,“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無論是天性渾全,還是反身體道,這都是成圣的方式。人人皆可為堯舜說的只是可能性,而性之或是反之,說的卻是成圣的方式,兩者是不同的事情,一個是理想目標,一個是現實路徑。也就是說,存在理論張力的點,是“性之”、“身之”本身。或者說是“性者”、“復性者”之間的張力。這才是矛盾的兩極,但是兩極又共同處在一個統一體(“圣”)之中,即所謂“成功一也”。另一方面,其張力還在于,生知與學知在現實的矛盾運動中,并不是必然的截然兩分的狀態,而是存在交集的兩個集合。換言之,兩者在具體的求知方式上,有所交叉。不是說圣人生而知之就是所有,圣人也只是知道體(道體),而不知道用(經驗);也不是說賢者學而知之就一無所長,永遠都只是學習,永遠也達不到圣人的境界。“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而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當賢者能夠反身而誠的時候,能夠舉一隅而以三隅反的時候,就可以說賢者已然意識到生而知之與學而知之交集的部分,其理論張力大致存在于此。
四、學以至圣的實踐探索
孔子所談及的“圣人”如若神人,對于普通人,甚至對于顏淵一般的賢者而言,都是難以企及的。孟子發展了孔子的“生知”思想,認為人人皆可為堯舜,圣人是人倫之至。這樣“圣人”的概念就從那個遙不可及的空中樓閣沉降人本身,成為人孜孜追求的、力圖實現的道德人格理想。大賢可為圣,為學可至圣,顏淵便被后人稱為“復圣”。《近思錄》為學卷談到,“圣人之道可學而至與?曰:然”。實際上就彰顯了兩層含義。其一,為學之目標在于成圣。其二,圣人并非是遙不可及的,通過為學體道,人人皆可為堯舜,皆可以通過個人的修養和努力而達道。這便是程頤在《近思錄》為學卷當中呈現出的洞察力及其洞見,“顏子之學乃成圣之學”。“為學”與“成圣”具有其內在的關聯,圣賢的本質在于得道,生而知道亦或是學而知道,其根本(得道)具有一致性。
“為學”與“成圣”具有其內在的關聯,這種關聯具備思政指向,也是大學思政課教學的目的之一,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學以至圣”是大學思政課教學的最大目的。從思政課立德樹人的角度來看,“學以至圣”決定著學生的心靈秩序,決定著一個大學生的修養深度、道德境界和人生高度。從成人到成圣的道德飛躍,本身就是儒家倫理體系的實踐應用。大學思政課汲取儒家思想,從為學與成圣的辯證關系中,探索“賢哉,回也”的倫理價值,能夠幫助學生在面對道德問題時給予一定的道德啟示,幫助學生做出正確的選擇。
儒家倫理的這種精神維度對于現代大學思政課的啟示作用主要有兩點。一方面是儒學具有積極意義的正面啟示。現代性之后,大學生如何配享幸福?在儒家看來,配享幸福關鍵在于形成一種道德自覺,在于刪繁就簡,追求美德,才能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另一方面,是儒學所具有的反消極情緒的啟示作用,這一點也符合大學思政課立德樹人的教學目的。儒家傳統倫理精神中學以致圣的觀點,能夠賦予學生以成長的信心,學生內在體認到這種傳統倫理精神,便不會如一葉浮萍般在虛浮縹緲的網絡游戲中迷失自己,不會在利益關系紛繁復雜的社會交往中喪失初心,不會僅僅停留在感官快樂上,而是嘗試著、努力著去追求更高層次的幸福。
五、結語
學以成人、學以至圣的理論通路和現實路徑,既是大學思政課教學的理論基礎,也是思政課教學的價值指向。儒家倫理的思想精神,儒學對于最高幸福的詰問和追尋,對我們大學思政的教學實踐具有重要的啟示作用。在思政課教學中,讓學生意識到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學而知之,為學能成圣。面對復雜的社會生活時,內心便有了一種張力,在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中不至于沉淪享樂,在面對遭遇不幸的人生際遇時不會背離初心。學以至圣的理論探索帶著立德樹人的現實指向,通過傳統文化的古今轉化應用,也能夠為大學思政課賦予道德倫理之意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