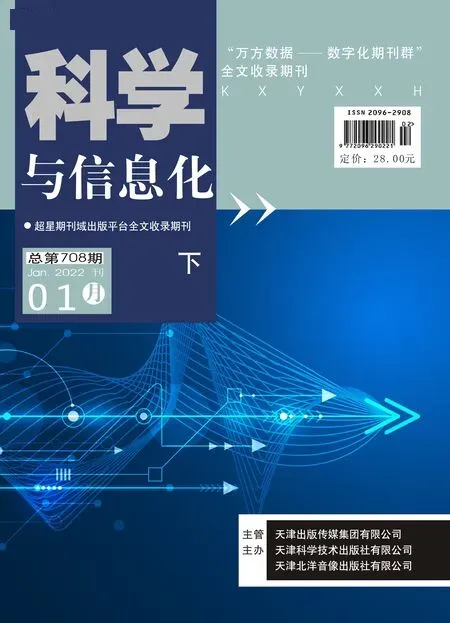b值研究概述*
王耀臨 劉偉 柴寧嬌 段昊
1.內蒙古地震局烏加河地震臺 內蒙古自治區 巴彥淖爾 015323;
2.內蒙古地震局 內蒙古自治區 呼和浩特 010010
引言
對b值的研究源自古登堡—里克特震級—頻度關系式:lg N = a-bM。之后肖爾茨和茂木清夫發現b值反映一個地區承受平均應力和承受強度的極限[1]。茂木清夫在實驗室里對各種地震活動進行了實驗關于巖石破裂的模擬,發現在主要破裂發生前,巖石均勻程度不一致,所產生的微破裂有差異[2]。肖爾茨研究在不同應力作用下,脆性巖石破裂的b值變化,他發現,在脆性的巖石破裂過程中,依賴于應力的狀態,脆性巖石破裂實驗表明,大量微小破裂發生在主要破裂前,并隨應力不同而變化[3]。Atkinson等人根據雙扭實驗中巖石的聲發射過程觀測出應力狀態與b值的關系[4]。由此可見,b值不僅僅是一個統計分析參數,而且具有非常明顯的物理含義和廣泛應用的領域。
1 研究概況
近年來,我國對b值的研究也越來越多,在1987年于軍就海城、唐山大震等多個中強震震前進行b值研究,發現選取的區域范圍和地震類型可能對震前b值的表現形態有影響。段華深等人[5]在1995年改進b值計算方法,增強了地震發生頻次在b值計算中的重要性,加大了b值的變化幅度,這樣便能非常清晰反映出地震震級和頻次結構的顯著變化,用來分析研究地震活動異常特征和規律,并結合定量指標的計算分析,探索對破壞性地震進行短期預報。2001年,鄭兆等人[6]在計算1970-1999年華北b值時空掃描時,分析了對結果可靠性造成影響的多種因素,用模糊相關分析法得到不同參數下計算的b值與對應地震震級的模糊矩陣和模糊推理,發現,有異常無地震的信息量明顯低于有異常有地震的信息量,取b<0.65為異常指標。陳培善等人[7]在2003年針對之前人們對b值計算的誤差,提出了兩點改進提議:①采用統一的絕對震級標度一矩震級標度MW;②舍棄缺失地震次數的點,然后用最小二乘擬合求得b值,使b值計算較準確。2012年,王輝等人[8]對川滇地區強震活動前b值時空分析時發現,b值的時間分布呈現系統下降在震前,58%的震源區b值在強震前顯著下降。馮建剛等人[9]在2013年對岷縣漳縣6,6級地震震前的b值情況進行研究,他們發現地震發生在甘東南地區低b值異常區域的邊緣,且震前鄰區地震Δb值異常顯著,該地震的發生并未降低該區域的強震危險性。2014年,李正芳等人[10]在利用斷裂帶上的低b值識別凹凸體方法的探討了龍門山斷裂帶和鮮水河斷裂帶,結果發現,利用小震數據通過最大似然法計算b值分布圖,歷年強震發生的位置與相對低b值區有較大的相關性,驗證了低b值區識別凹凸體方法的實用性和可行性。徐偉進等人[11]在2014年對蒙古國以及其周邊范圍進行b值研究,結果表明該地區地震空間分布具有一定的叢集性,是典型的地震活動區,b值和D值呈現正相關性。2014年,張盛峰等人[12]對云南魯甸6.5級地震進行b值的空間分布的研究,結果發現地震叢集性質與DD目錄完整性的下降有關,在叢集的邊緣下降明顯,內部下降程度較低。2015年,謝卓娟等人[13]對滇西南地區主要活動斷裂進行b值研究,研究表明研究區內斷裂帶之間不同段落的b值分布極不均勻,怒江斷裂帶、瀾滄江斷裂南段等處于低b值區域,具有較高的應力狀態。王熠熙等人[14]在2015年對河北平原地震帶的b值特征進行研究時發現,低b值區域是唐山—遷安斷裂段和昌平—寶坻斷裂段,此地區地殼介質正處于相對高應力或閉鎖狀態。劉艷輝等人[15]在2015年對青藏高原東南緣及鄰區近年來地震b值特征進行研究發現,b值的低值危險區形成時間與地震震級之間成負相關。張琳琳等人[16]在2015年對新疆天山地區b值研究發現,所研究的6級以上地震震前的震中位置的b值多數處于低b值狀態,震中附近區域b值相對較高,反映了應力主要向震中方向積累變化。2016年,張登科[17]對大同盆地與晉冀蒙三省交界地區中強震震前b值研究得出,在研究時段內的幾個震例中,地震發生在b值時間關系“先是高值異常,然后異常結束”這一特征末。韓曉明等人[18]在2016年對河套地震帶b值研究顯示,研究時段內的中強地震活動往往與b值時序變化較好地對應起來,地殼介質體性質和應力環境共同引起河套地震帶b值空間差異。張廣偉[19]在2016年對云南地區地震重新定位及b值研究表明,該地區中上地殼是主要發震層,隨深度減少b值逐漸減少,b值變化在9~10km深度時最為明顯,可能表明該地區孕震中強震在9km以下,三維空間分布體現高低b值的過渡帶往往會發生地震。2017年,于俊誼等人[20]對珊溪水庫地區b值時空變化特征分析發現,該地區ML≥4.0的地震主要發生在高b值與低b值的過渡區。韓佳東等人[21]對2017年西藏米林6.9級地震進行b值分析顯示,震前震源區的b值降低,震前震源區存在很強的應力積累;震后b值呈現上升,說明應力釋放,b值分布與地下的結構特征有關,淺層的b值變化與震源區的破裂程度相關,深層變化則反映了不同構造單元的巖性差異。2018年,任雪梅[22]對地震區劃中b值統計進行研究,結果表明模型MGR擬合的數據能表現非線性關系,我國大陸各研究區的地震震級頻度關系可以利用模型MGR擬合。張雙鳳等人[23]在2018年利用地震活動性參數b值判斷張渤地震帶中西段地震危險性,研究表明,河北涿鹿及山西大同一帶有低b值、低a值、較高a/b值的參數組合,反映該區域具有較高的應力積累,存在強震發生的危險。鄭確等人[24]在2018年對遼寧海城及其鄰區地震b值研究表明,b值隨深度增加而降低,低b值在岫巖和蓋州震區,說明地震危險性較高。史海霞[25]在2018年對汶川地震前的b值變化研究表明,在震前半年前左右,b值出現顯著而且快速下降的趨勢,可能反映了大震準備過程中應力的變化。張帆等人[26]在2018年對鄂爾多斯地塊北緣b值進行研究分析,結果顯示,中強地震與低b值區域存在一些對應關系,研究區內多數大震地震發生在低b值區域及其邊緣。2019年,吳果[27]對b值的極大似然法估計和其影響因素進行研究分析,總結了震級的歸檔效應、震級的測量誤差、樣本量、震級跨度、最小完整震級和前余震共6個因子的作用方式,并提出了相應的規避建議。2020年,劉子璇[28]對南北地震帶 b 值震前異常進行研究,得出以下兩點震前異常的形態:一是在震前小震 b 值持續降低(或持續低值過程),直至發生主震;二是震前 b值持續性降低的形態,震前1~2.5年出現b值回升的形態,稱為“降低—升高—發震”的模式。曾憲偉[29]在2020年對2019年6月17日長寧6.0級地震進行b值研究,研究發現b值下降可以有效地判定危險的緊迫程度,對判定強余震的可能發生地點夠起到很好的輔助作用。李世杰等人[30],在2021年對強震前b值研究表明,大震發生前,b值存在異常變化并有一定相似性,變化過程和應力積累過程吻合,與震源機制關系無明顯聯系,極大似然法能更好地反映強震前后b值的變化特征。余騰等人[31]在2021年對郯廬斷裂帶蘇皖段及鄰區b值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研究區中強地震發生時段與中短期b值下降時段關聯率達到80%以上。孟昭彤等人[32]在2021年對將b值隨時間和空間變化的特征做了總結歸納。陳學忠等人[33]在2021年對四川長寧6.0級地震b值變化進行研究,地震發生前,破裂區內視應力增加,b值下降,震前破裂區內存在明顯的構造應力增加過程。
2 結束語
本文研究了1987年至今國內b值研究中得到的主要結果,發現隨著對b值的不斷深入研究,我國學者在b值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多進展,發現了很多有趣的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總結b值時空分布的一些特征,以便在將來更好地運用于地震監測預警,b值的研究將會更好的解釋地震發生的部分原因,隨著計算機科學的發展,臺網監測能力的增強,數據收集能力大大提升,將會為b值的計算帶來一個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