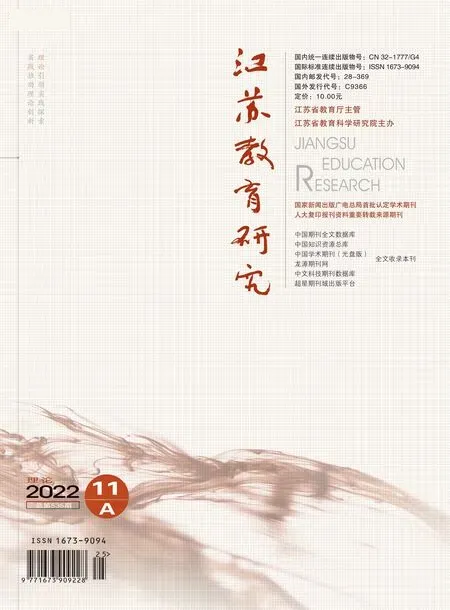核心素養視域下的深度學習:內涵、特征與原則*
鄒佳叡
我國基礎教育在二十多年的課改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績和效果,但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問題,如教師對教學方式改革的理解不夠深刻、以知識灌輸為主要方式的課堂教學及以考試分數作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現象依然存在。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全面轉入核心素養時代的背景下,如何解決課程改革中暴露的問題,應對核心素養的新挑戰,成為當前重要的研究課題。深度學習強調以學生為中心,以全面發展為目的,“契合以核心素養為目標的課程理念,有利于解決當前我國在課堂教學中存在的重點和難點問題,應對課程改革中教學改革的實際挑戰,提高課堂教學的質量和水平”[1]7。但是,深度學習作為一個舶來概念,國內相關研究起步較晚,對于深度學習的概念等基本問題也還沒有達成一致的看法。這種對深度學習認識的不明也導致了深度學習理念難以在中小學教學中順利落地。因此,有必要厘清深度學習的內涵、特征、原則等相關基本問題,助力核心素養視域下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
一、核心素養視域下深度學習的本質內涵
教育學領域首先提出深度學習概念的是瑞典哥德堡大學教授馬頓和羅杰·賽里歐。1976年,他們通過實驗觀察大學生閱讀學術文章時的不同表現,提出了深度學習和淺層學習兩個概念。他們認為:淺層學習是一種被動狀態的學習,以機械記憶和強化訓練為主要方式;而深度學習則是淺層學習進一步的擴展延伸,注重對知識的理解、建構、遷移、應用[2]。自兩位學者正式提出深度學習的概念以后,國外教育領域立即掀起了研究深度學習的熱潮。通過對相關文獻的梳理可以發現,國外目前對深度學習內涵的認識主要有學習方式說、能力說與目標說三種。雖然每種認識對深度學習概念的界定不盡相同,但是對深度學習核心價值的認識基本上趨于一致,即認為深度學習是一種具有實際意義的學習方式,它與學生的學習動機聯系在一起,追求對知識的透徹理解[3]。
與國外相比,國內對深度學習的研究則起步較晚。2005年,上海師范大學研究生何玲和教授黎加厚在《促進學生深度學習》一文中援引了馬頓和羅杰·賽里歐教授的實驗及觀點,并對深度學習的定義、特點等作了進一步闡釋[4]。這被普遍認為是國內深度學習研究的開端。自此以后,國內相關研究便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相關研究已經漸成規模,研究者們對深度學習的概念也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觀點。例如,何克抗教授從布魯姆教育目標分類學的認知層次入手,認為深度學習就是借助全新的理念、方式、資源等,使學生不僅能夠記憶、理解必要的學科基礎知識,還能具有應用、分析、評價這些基礎知識,并創造新知識和新產品的能力[5]。吳秀娟老師認為,深度學習就是學生能夠根據自己的喜好和需求,在理解的基礎上,主動地、批判地學習新知識,能夠使用多樣化的策略加工信息,建立起不同類型信息之間的聯系,從而建構起自身的知識體系并能將其遷移到具體真實的情境中解決復雜的問題[6]。郭華教授則將深度學習定義為:“在教師的引領下,學生圍繞著具有挑戰性的學習主題,全身心地積極參與、體驗成功、獲得發展的有意義的學習過程”[1]32。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對深度學習概念的理解是多角度的,概括起來大致有學習方式說、學習過程說、學習結果說三種。綜合國內外學者的觀點可以發現,深度學習并不單一地指向于一種學習方式、學習過程或者說學習結果,它指向的應該是一種融通于整個學習過程的、綜合的、理想的學習狀態。在這個學習狀態中,學習者的學習方式是主動參與式的,并能夠根據學習任務的難度與要求進行靈活調整;在學習過程中學習者是全身心投入的,并能夠主動地加工信息、建構知識的意義;學習結果是基于知識的理解、高階思維的發展以及復雜問題解決能力的提升。
二、核心素養視域下深度學習的基本特征
基于上述認識,深度學習主要具有學習方式上的多元融合性、學習狀態的沉浸體驗性、學習過程的主動建構性以及學習結果的理解遷移性等特征。
(一)學習方式的多元融合性
“學習方式具有多樣性,只有科學、理性地認識學習并了解學習方式的分類依據和標準,才能在實踐上科學、理性地運用學習方式。”[7]這一論斷說明學習方式是多樣的,對于學習方式的認識應基于一定的分類標準。例如,從學習者學習的主動性角度來說,有自主探究式學習和被動接受式學習;從學習者學習的參與度來看,有個體學習和合作學習……當然,不同類型的學習方式之間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存在著多種交叉融合的關系,分類的維度和依據不同,學習方式的類型歸屬也會發生相應的改變。深度學習所運用的學習方式不是孤立的、單一的,孤立否則會導致淺層學習。深度學習在學習方式的選擇與運用上體現的是一種多元融合性。所謂“多元”,就是指學習者能夠以一種多樣性的眼光看待學習方式,并能夠根據學習任務的實際要求對其進行靈活選擇;所謂“融合”,就是指學習者對于不同學習方式的綜合性運用,如在探究性學習中需要合作性學習的參與,同時也可能會需要借助網絡查閱相關的資料。此時,探究性學習、合作性學習、網絡學習就呈現出一種融合的狀態。因此,深度學習中學習方式的多元融合性,就是指學習者根據學習任務的實際狀況,靈活選用不同的學習方式,并且表現出不同學習方式之間的“相容度、契合度和匹配度”[8]。
(二)學習狀態的沉浸體驗性
“沉浸體驗”這一概念來源于沉浸理論。沉浸理論于1975年由美國心理學家米哈里博士首次提出,他通過研究人們參與某些日常活動時的表現,發現人們在從事某些活動時會過濾掉完全不相關的直覺,而全身心地投入活動情境中去,即進入了一種沉浸的狀態。據此,米哈里博士將這種沉浸狀態定義為當人們參與一項自己有能力解決,但又具有一定的挑戰性和難度的任務,并且這項任務的完成是由內部動機驅使時,所達到的一種特殊的心理狀態[9]。“沉浸體驗”指個體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或學習任務,全身心地投入任務中時與所處的環境構成一個有機和諧的整體,從而忘記自身存在的一種心理體驗[10]。深度學習狀態的沉浸體驗性,就是指當學生面對符合其最近發展區難度的學習任務時,能夠將自己的思維、認知、情感等全面地投入任務活動中去。在這一狀態下,學生的學習是全神貫注、積極參與的,并且能夠釋放學習的壓力,將學習中遇到的問題看作是一種挑戰,在問題解決中獲得愉悅暢快的身心體驗,感悟到學習的樂趣,培養出學習的動機,進而達到掌握知識、發展能力、培育素養等目的。
(三)學習過程的主動建構性
“建構”這一概念來源于建構主義理論。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習不只是“刺激—反應”的簡單聯結,而是一種能動的建構過程,知識就是主客體在相互作用的活動中建構起來的。主動建構性就是指在課堂教學中,學習的過程并不是教師向學生傳遞知識的過程,而是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積極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學生不是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而是知識的主動建構者。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學生的學習主要依賴于教師的講授,學習主動權被削弱,學生與教師、知識以及其他學生之間也無法形成良性的互動,因此,學生的學習主要是一種接受式的學習,學到的知識對于學生來說只是一堆無意義的符號。而深度學習強調學習的過程是其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它要求教師要轉變思維觀念,將以“教的活動”為主要形式的課堂打造為以“學的活動”為主要形式的課堂,重點關注學生應該學什么、應該怎么學以及學到何種程度,并在此基礎上開展相應的教學設計。
(四)學習結果的理解遷移性
“理解”具有哲學詮釋學和教育心理學上的雙重含義。在哲學詮釋學中,狄爾泰認為,作為對他人及其生命表現的理解具有兩種形式:基本形式的理解,即產生于實際生活的利益之中的理解,人們要交往,必須相互理解,知道另一個人要干什么,其基本形式的相互組合可以為高級形式理解的產生提供可能;高級形式的理解,即從表現出發,通過歸納推理,從而理解一種整體的關系,并且可以通過“移入”這一狀態來實現對人或者作品理解的最高形式[11]。在當代教育心理學看來,學習者學習知識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靈活地適應世界,它看重的是所獲得知識的質量以及其能否被靈活地遷移運用到其他相關情境中去,不是那種依靠背誦形成的表面的、僵化的理解[12]。深度學習的學習結果不僅指向知識的深度理解,而且要求學生能夠將學習的內容遷移到不同的情境中去。具體而言,深度學習的理解遷移性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深層次的理解是以淺層次的理解為基礎的,學生只有實現了對知識的淺層理解,才能為接下來的深度理解提供可能;二是所謂的深層次理解應該指向批判性理解,批判性理解需要批判性思維,批判性思維是思維的最高形式,建立在批判性思維上的批判性理解會在理解知識意義與價值的基礎上對所習得的知識進行審視和反思,從而使學生建構起自身的知識體系以及對于知識的個性化理解,這也是實現遷移的前提;三是深度學習的學習結果的理解與遷移是一個雙向的過程,即學生對于知識的深度理解可以將知識有效地遷移到其他情境中解決實際問題,在真實情境中運用知識又可以再度加深學生對于知識的理解。
三、核心素養視域下深度學習的原則
深度學習的根本目的是革除淺層學習的弊端,提高課堂教學與學生學習的效果。但是,深度學習也并不是萬能的理論,只有堅持科學的原則才能夠實現深度學習的根本目的。
(一)教學性原則
深度學習的教學性原則來源于對“教”與“學”關系問題的思考。“教”與“學”的關系問題是教學論研究的基本問題,我國基礎教育界認為“教”與“學”關系大致可分為“少教多學”“先學后教”“以學定教”“教學合一”“教學相長”等五種范式[13]。這五種關系范型基本上代表了我國學界對“教”與“學”關系的五種基本認識。從這五種關系范型可以看出,所謂教學是由“教”與“學”兩方面構成的,不存在離開“教”的“學”,也不存在離開“學”的“教”,“教”與“學”雙方的互動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教學行為,它們是在一個完整的系統中相互依存、彼此統一的。深度學習雖然強調學生中心和學習中心,但是“教”與“學”的統一關系決定了深度學習不是學生完全的自主學習,而是指教學中學生的學習,換而言之,深度學習就是一種好的教學,它內在地包含著學生的積極學習[1]34。這就要求深度學習要堅持教學性原則。首先,要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教師的主導不是教師的支配和控制,而是教師的引導和指導,其重心應落在“導”上。因此,教師在深度學習中的主導作用就是指教師在教學之前應充分考慮到學生應該學什么、學到何種程度,并以此展開教學預設;在實際的教學過程中,應組織和協調各類學習活動,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推動各類學習活動的順利展開。其次,要充分尊重學生的主體作用。學生的學習活動是由教師指導和引導的,但是學生學習的過程卻是學生所親歷的、教師無法代替的。因此,深度學習要建構起以學生和學習為中心的課堂教學:“在教什么以及如何教的問題上,要‘以學定教’;在教學時空分配的問題上,要‘少教多學’;在教學效果的評價上,要‘以學論教’;在教與學的先后順序上,應有不同的狀態”[14]。
(二)相對性原則
所謂“相對性”就是指深度學習的“深度”是一種相對的深度,它并不刻意追求知識的高難度和學習進程的高速度,而是在充分尊重學習規律和學生身心發展特點的基礎上確定學習的相對“深度”。首先,教師和學生要尊重淺層學習。淺層學習的主要內容是學生日常學習中必不可少的知識,它幾乎沒有歧義,即便是缺少經驗的學習者只需要機械記憶也能夠很快學會[15]。淺層學習雖然難以實現深度理解,但是學生的認知和能力的發展總是從簡單到復雜、由低級到高級的過程,這一過程是累積性、連續性以及漸進式的。因此,淺層學習是深度學習的鋪墊,深度學習的實現往往要以淺層學習為基礎。其次,教師要充分考慮學生的學情。學情是與課堂教學直接相關的學生狀況,它主要包括學生已有發展水平和潛在發展狀態兩個層面。受種種因素的影響,學生課前的學情是不同的,這也導致了學生學習的起點狀態和最終發展目標的差異。因此,必須在對學生已有認知、能力等進行有效分析的基礎上開展深度學習。罔顧學情因素,追求一種絕對“深度”或者設定一個所有學生都要達到的絕對目標的做法既不科學,也不現實。
(三)基于課標的原則
課程標準是國家課程的基本綱領性文件,是國家對基礎教育課程的基本規范和質量要求,是教材編寫、教學、評估和考試命題的依據,是國家管理和評價課程的基礎[16]。它體現了國家對不同階段的學生在不同學科的學習中所應達到的基本要求,這些基本要求是各項教學活動的依據和準則,教師的教學以及學生學習活動不能夠超出或低于這些依據和準則。例如《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2017年版)》提出了語文核心素養理念,培育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便成為高中語文課程的總目標,相應的高中語文教學都應圍繞如何培育學生的語文核心素養展開。深度學習是發生在課堂上的學習,具體來說是在一門門具體學科的學習中發生的,因此,深度學習的實現必須要堅持基于其所在學科的課程標準的原則。首先,要對其所教學科的課程標準有準確的認識和理解。課程標準主要包括課程性質與基本理念、課程目標、課程結構、課程內容、學業質量、實施建議等內容,教師通過對課程標準的仔細研讀,能夠對該學科應該“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應該“學什么、學到什么程度”等問題形成一個整體的把握和認識,從而指導自身的教學實踐。其次,要順利實現課程標準到課堂教學的轉化。課程標準屬于課程層面的內容,表達的是一種“應然”的追求,具有較強的宏觀性與概括性;課堂教學屬于教學層面的內容,表達的是一種“實然”的狀態,具有實踐性和具體性。從“應然”的追求到“實然”的狀態中間存在一定的落差,因此,需要經歷一系列的轉化或者中介才能夠順利地落實,而這一系列的轉化或者中介的提供需要建立在教師透徹理解課程標準以及科學扎實的教學設計上。
總之,核心素養視域下的深度學習賦予了學習以新的意涵,是對于教與學的一種全新闡釋。深度學習的落地生根,必將為我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注入新的活力,引導課程改革朝著高質量、內涵式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