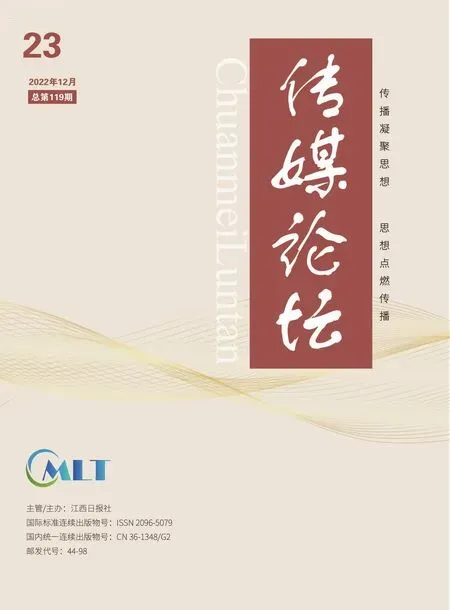基于政策角度淺析媒介生態的規范路徑
尤文靜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經濟發展逐漸從計劃經濟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文化發展的格局逐漸從文化事業向文化產業過渡,傳媒業的發展正逐漸從事業單位性質到兼具企業管理性質再到資本多元化的模式發展。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傳統媒體逐步向融媒體發展。無論是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的融合之路,還是媒介生態的良性發展,都離不開政策的引導。
一、關于媒介生態
關于“媒介生態”和“媒介環境”的研究源起于西方國家,最早由生態學的概念開始,逐漸開辟出了與“生態系統”相關聯的媒介生態研究領域。1869年,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提出了“生態學”(Ecology)的概念。“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及其周圍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1]20世紀60年代,馬歇爾·麥克盧漢提出“媒介生態”這一概念。他認為:哈羅德·伊尼斯是全球最早對“媒介技術”如何深度影響人類社會展開創新性研究的學者,其最大的成就便是提出了著名的“媒介時空論”,聚焦研究媒介與社會經濟的生態關系、媒介與人類時空的生態關系。[2]媒介生態研究屬于媒介學與生態學以及其他相關領域的交叉研究。
國外的媒介生態的相關研究大多從人的角度出發,重點從微觀的角度研究人與媒介的關系;國內的媒介生態研究大多從更為宏觀的角度出發,研究環境、觀念、文化、傳播規律等諸多因素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媒介是條魚——理解媒介生態學》(2005)一文中,首次系統的介紹了關于媒介生態的相關研究。國內學者邵培仁在《媒介生態學:媒介作為綠色生態的研究》中解釋:“‘媒介生態學’指用生態學的觀點和方法來探究和揭示人與媒介、社會、自然四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變化的本質和規律的科學。”[3]該研究構建了媒介生態領域在國內的研究基礎。
媒介生態的變遷伴隨著國家的政策導向、經濟發展以及技術的變革。媒介生態的環境變化受以下三方面的影響:第一,政治環境。媒介生態的發展變遷中唯一不變的是黨領導下政治環境對媒介環境的影響。我國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媒介首先是為黨和國家服務,媒介應充分發揮其輿論引導功能。無論媒介環境如何變化,媒介的政治屬性不會改變。第二,經濟環境。經濟環境對媒介生態的影響也越來越明顯。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媒體的發展主要依靠財政撥款,但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媒介隨之改變。外部市場環境的刺激促使得媒體之間重組和整合,形成了“事業屬性,企業化經營”的發展格局,經濟環境影響媒介生態的平衡發展。第三,技術環境。技術的革新帶來了媒體的融合發展,雖然改革開放初期的媒介更多的是較為單一的信息輸出,但隨著市場經濟以及技術的發展,媒介作為“國家聲音”和“民眾聲音”的橋梁,逐漸發揮了雙向的互動作用。
媒介生態的規范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人和社會、經濟、政治等統一互動的發展。媒介生態的規范需要國家的政策、信息內容、信息參與者等環節的相互作用,彼此互動形成生態的發展循環。
二、國家政策為媒介生態規范提供了制度保障
媒介生態的發展離不開媒介的發展和變遷。伴隨著技術的革新,媒介的形式從報紙、廣播、電視、網站到手機APP,單一的媒介形式已經不能滿足人民的生活需求。伴隨媒介發展除了技術以外,還有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等,這些構成了媒介生態發展的有機整體,在國家發展的同時媒介的生態也隨之變化。國家在每一個發展時期制定的政策為媒介環境的良好發展奠定了基礎。
1983年,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在第十一次全國廣播電視工作會議上,作了題為《立志改革,發揮優勢,努力開創廣播電視新局面》的工作報告,明確指出:“所謂四級辦節目、四級混合覆蓋,就是除了中央和省一級辦廣播臺和電視臺外,凡是具備條件的省轄市、縣,也可以針對當地需要和可能開辦廣播臺和電視臺,除了轉播中央和省的電視節目外,可以播出自辦節目,覆蓋該市、縣。”[4]在該政策的影響下,我國的廣播電視業迎來了蓬勃發展。
1997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廣播電視管理條例》,該文件奠定了廣播電視發展的的壟斷地位。隨著有線電視和網絡的飛速發展,國家對于廣播電視的經營管理以及互聯網的運營進行了調整。2004年國家廣電總局發布的《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管理規定》中引入了競爭機制,國家鼓勵和支持社會資本進入廣播電視行業。
為了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充分調動全社會參與文化建設的積極性。2005年4月13日,國務院出臺《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的若干決定》(國發〔2005〕10號)。[5]2015年10月19日,國務院印發《關于實行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意見》,按照《國民經濟行業分類》的相關門類和《產業結構調整指導目錄》等制度的銜接,在部分地區現行先行先試,探索形成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及相應的體制機制,從2018年起正式實行全國統一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6]
隨著新媒體的不斷發展,國家發布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對媒體行業的發展進行適當的調整和完善。2022年3月,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發布《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7],內容涉及農、林、牧、漁業、采礦業、制造業、金融業、批發和零售、文化、體育和娛樂等十五個類別,涵蓋了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內容分為禁止類事項內容和許可類事項內容兩大類。①該政策的發布對于媒介生態環境的規范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媒體的融合發展離不開一系列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融合發展的政策支持,未來媒介生態的平衡發展則更離不開此類政策提供的保障。
三、從政策角度分析媒介生態的規范路徑
近年來,隨著媒介的融合發展,媒介生態逐漸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媒介的生態規范如同大自然的環境生態一樣,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媒介的生態平衡需要信息的傳播渠道規范、傳播的內容健康以及傳播參與的共同努力。
(一)信息渠道規范
由于網絡的普及和信息發布渠道的多樣化,任何人都可以在網絡上自由發表言論,網絡的及時性給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但同時也增加了負面輿論的風險。一些網絡媒體為了商業利益和點擊率,片面求新、求快,而使新聞的真實性大打折扣;一些自媒體平臺為了賺取高人氣,對于一些新聞信息斷章取義、標題和內容不符、圖片和視頻與新聞內容有出入,污染網絡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版)》中的禁止準入類中增加了“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采編播發業務”。②該政策的內在邏輯,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因商業利益干擾正確輿論導向的行為。國家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合理分類傳播資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信息傳播途徑。通過相關媒體政策的調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規范傳播市場確、凈化媒介環境的作用。
(二)傳播內容規范
隨著新媒體的發展,一些社會事件經網絡發酵引發社會關注,激化社會矛盾,進而造成負面輿論,影響政府公信力。特別是時政新聞的發布和評論,可能在信息的傳播過程中,被國外的一些媒體進行不良解讀,造成負面的傳播效果,影響國際形象。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版)》中明確:“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大社會、文化、科技、衛生、教育、體育以及其他關系政治方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等活動、事件的實況直播業務。”③從傳播內容上進行優化和合理的資源分配。特別是針對時政新聞的發布,在《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第94項,增加了“時政類新聞轉載服務業務審批”④,可以提升權威信息傳播機構的話語權和公信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不規范的傳播渠道和傳播內容造成的不良國際影響,同時也從傳播內容的角度促進了媒介生態的規范。
(三)傳播參與的規范
網絡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媒介的信息傳播方式,從點對點到點對面。傳播參與的規范是影響媒介生態健康發展的重要因素,不僅包含了信息的發布,即媒體機構和從業人員,也包含了信息的接受,即接收信息的受眾,兩者同時作為信息參與進行信息傳播活動。《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版)》中許可準入類的第94項“未獲得許可,不得設立傳媒機構或從事特定出版傳媒相關業務”從傳播參與的角度對參與傳播的機構及其傳播業務內容進行了明確,從源頭上規范了傳播參與機構。而作為傳播參與的媒體從業者無論何時都應該堅定政治素養。政治素養是為媒體舉旗定向的基石,擁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是成為媒體人的基本素養。作為接收信息的受眾,同時也是信息的再次傳播者或者信息的意見領袖,作為信息參與的其中一環也應加強自身媒介素養,2022年8月1日正式施行的《互聯網用戶賬號信息管理規定》即是針對互聯網信息提供者規范信息發布的具體政策。
四、媒介生態的未來展望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版)》中禁止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發布的內容較之前更加明確,不僅增加了禁止類事項內容,也豐富了許可準入類事項內容,意味著傳媒產業發展將更加規范。隨著國家逐步完善對傳媒市場的制度化管理,從傳統媒體向融媒體集團改革的傳媒機構有了更廣闊的話語空間。由于技術的更迭,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下,媒介生態逐步實現技術融合、資源整合。一部分影響力較小的傳媒企業被優勝劣汰,新聞信息傳播生態環境更加規范化。
國家制定政策的初衷是為了遏制傳媒亂象、凈化網絡環境、正確引導輿論、有序推動傳媒產業發展。政策的建立是為了促進媒介生態更好的發展,從政策的角度出發,未來的媒介生態可以嘗試從以下兩方面進行改善。
(一)建立制度保障
國家各行各業的發展都離不開政策的引導,伴隨我國的經濟發展迅速,媒體產業在整個國民生產中的貢獻越來越突出。但與媒體產業發展相適應的政策體系尚不健全。媒體產業的資本多元化發展是未來主要的發展趨勢。如何建立與媒體發展相適應的法律法規,最大程度的保障國有經濟和混合所有制經濟之間的平衡關系,實現公有制和非公有制之間的優勢互補,盡快建立相應的制度規范,保障利益和權益,是未來傳媒生態健康發展的關鍵。無論是對媒體機構還是媒體信息活動參與者,明確權利和責任、建立制度保障、真正的有法可依是媒介生態健康發展的基礎。
(二)優化媒體政策內容
文化產業的發展逐漸成為各國經濟發展的支柱性產業,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并建立了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政策。我國從2000年以后對文化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逐漸加大,在國家制定的每五年發展規劃中都會對文化產業的發展進行調整和優化。媒體產業作為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互聯網的快速發展,網絡文化內容門類龐雜,各類別內容之間的邊界相對模糊,加之政策的制定、實施和反饋、修訂需要一個必要的時間周期,所以在媒體政策的制定方面,針對較為寬泛的媒體政策內容進行優化、細分顯得非常必要,可以更好的為媒體市場中出現的具體問題提供政策依據。
五、結語
《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中關于新聞傳媒禁止類事項的規定,對于媒介生態的規范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對媒體技術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的新聞傳播發展方向的指導是非常必要且及時的。政策的引導為進一步規范傳播市場指明了方向,提升了傳媒領域的制度化、法治化,對鞏固和加強正向的輿論引導具有積極作用。無論傳媒機構形式如何發生變化,市場化的競爭如何激烈,媒體都應該始終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不斷強化媒體責任意識。在注重用戶需求的同時,不能一味的迎合大眾需求的文化市場,充分挖掘優質用戶資源,形成良好互動,著力打造內容品牌,為媒介生態的良性發展奠定基礎。媒體政策是媒介生態健康發展的基本保障,同時為了構建健康的網絡環境、綠色的媒介生態,需要媒體機構、媒體從業者和全社會的共同努力。
注釋:
①②③《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一、禁止準入類,第6項.
④《市場準入負面清單(2022年版)》二、許可準入類,第94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