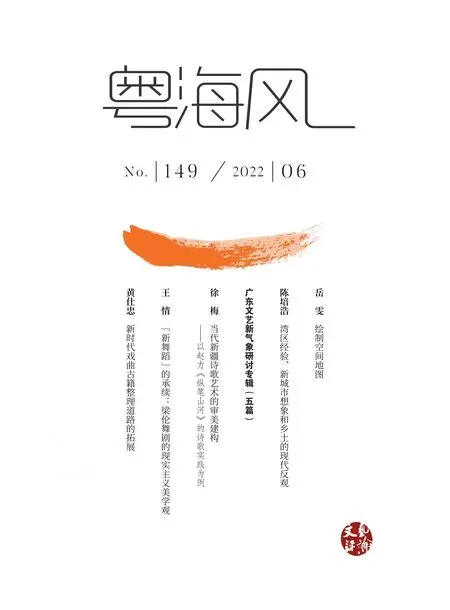做派與藝術(shù)
——廣東新音樂現(xiàn)象之樂隊微觀
文/麥瓊
文化生態(tài)決定一個地方的文明程度。廣東的音樂文化傳統(tǒng)是多樣化的,農(nóng)業(yè)時代不同的地域生長出自己的音樂文化,有幾個特色突出的板塊:珠江三角洲地區(qū)的廣府音樂、粵北的客家音樂、粵東的潮州音樂和粵西的雷州音樂,泛稱嶺南音樂。工業(yè)與信息時代的經(jīng)濟高速發(fā)展,嶺南面臨著時代對它的重塑。近年,廣東流行音樂在沉寂多年后出現(xiàn)一些新的現(xiàn)象,希望這是新一波勃興的動向。本文擬對某些具體案例作觀察與思考,拋磚引玉,借此請教關(guān)心廣東音樂文化的方家。
一、曾經(jīng)的驕傲
曾經(jīng)的廣東流行音樂是中國新音樂文化的橋頭堡,是港臺流行音樂向內(nèi)地傳播的橋梁。令人驕傲的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廣東的流行音樂有著自身的發(fā)展模式、路徑和優(yōu)秀作品,可謂人才濟濟的黃金時代。期間誕生了不少中國流行音樂的經(jīng)典。那股音樂風潮無不刻著“廣東制作”的文化標簽,是最值得廣東樂壇總結(jié)和研究的。特別是其中的時代性、對傳統(tǒng)的吸收和氣質(zhì)蛻變都有著非常突出的表現(xiàn)。千禧年之后,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WTO)、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行,中國的文化形象逐漸從歷史的模糊、現(xiàn)代化的急促步伐,到如今經(jīng)濟騰飛的波瀾壯闊,為世界所矚目和接納。而對于廣東而言,更是發(fā)生了歷史性的獨特轉(zhuǎn)型和巨變,GDP從2000年的1萬億元躍升到2021年的12.44萬億元。加之與港澳的深度融合,形成世界性大灣區(qū)的格局,灣區(qū)文化的廣闊想象是文化廣東必須接得住的歷史饋贈。但是,改變是要經(jīng)歷陣痛的,沒有了港式文化借著經(jīng)濟優(yōu)勢對廣東的灌注,隨著京滬湘等地流行文化的崛起,廣東流行音樂人才的外流,曾經(jīng)的繁華不再,21世紀后陷入發(fā)展乏力的尷尬境地。這一事實必須得到正視。雖然廣州仍然有一些音樂人在堅持粵語歌曲的陣地,以純正的廣府文化元素創(chuàng)作,挖掘、光大粵文化的精髓,與粵語廣播、電視一道在傳統(tǒng)的路徑上繼續(xù)深耕,保護者本土的文化價值。但是時過境遷,粵語面臨式微,廣東音樂要借助粵元素面臨的困難不小,尋找新的發(fā)展興奮點是當務(wù)之急。
二、樂隊的光彩
不過,文化的發(fā)展中總是有出其不意的現(xiàn)象,在新媒體引領(lǐng)文化潮流的時代,近年廣東流行音樂的新生力量又以一種沒有預(yù)見的方式闖進人們的視野。他們以客家方言、潮州方言、粵語為核心元素,以樂隊組合的形式,在網(wǎng)絡(luò)綜藝節(jié)目的傳播中“竄紅”,并打上了廣東文化的標簽,有著醒目的表現(xiàn)。包括五條人、玩具船長、九連真人、扭蛋姬、燜餅、HYPER SLASH、Project Ace、Hyperslash,還有數(shù)量可觀的更為小眾的“核類”[1]樂隊等。經(jīng)由多年的努力,他們各自積累了相當?shù)娜藲狻⒙暳亢妥髌罚瑥木C藝節(jié)目中的醒眼表現(xiàn)、商業(yè)的巡演,及至本土的回響,成為不可忽略的生力軍。這里擬聚焦五條人、扭蛋姬和九連真人三個代表性樂隊,分別就他們的創(chuàng)作、表演,以及走紅原因做一些文化上的考察評述。
(一)五條人
五條人,是一個頗有故事魅力的名字。五條人是來自海豐的音樂人茂濤、仁科早在2008年便創(chuàng)立的樂隊,近年參加綜藝和比賽,加入鼓手苗長江。樂隊的名字,就是一個代稱。然而,作為一種商業(yè)上的噱頭和標志,有歷史的敘事需要,也是流行文化的一種屬性。因此,常常在各式訪問中做各種有趣的解釋,還加上了穿拖鞋的刻意裝扮。表面上“嬉皮笑臉”,卻滲入他們的人文性訴求。給人的觀感容易形成表演上的獨特風格,即一種做派,先入為主地讓人們獲得強烈的個性化印象。見諸報刊的一些評價,就是基于他們的做派所透出的人文氣息而抒發(fā)的:“五條人有點皮、有點逗,用下里巴人,玩陽春白雪,他們有意識地把粵語、潮汕方言融入歌曲,在市井煙火中延續(xù)知識分子的底色”(《新京報書評周刊》),“是一個敘述者也是一個觀察者,是當事人,同時也是‘知識分子’,這樣的雙重身份讓他們用很江湖的一套輸出價值。他們用草根的底色和精英的話術(shù)聚攏割裂的生活。”(《南方人物周刊》)包括網(wǎng)絡(luò)媒體的很多評論,大多不吝贊美,皆因他們舞臺上的肆意表演,天馬行空式的吟唱,居然可以讀解出人們所期望的情懷。
當然,是否延續(xù)知識分子的“底色”“輸出價值”,我們須得從其音樂創(chuàng)作中做觀察。五條人從2009年開始創(chuàng)作錄制專輯《縣城記》,而且陸續(xù)在各類比賽中獲得獎項,應(yīng)該說起點頗高。如獲得華語金曲“最佳方言唱片”獎的《一些風景》,阿比鹿音樂獎“年度民謠唱片”獎的《廣東姑娘》等。2020年,參加了愛奇藝的大型綜藝“樂隊的夏天”之后,憑著《阿珍愛上了阿強》,進入Hot5,成為現(xiàn)象級的文化話題,可謂廣東音樂人久違的高光時刻。誠然,他們得到的關(guān)注和熱捧,不僅僅是商業(yè)創(chuàng)作上的成功,更在于他們長期的創(chuàng)作積累,樹立自己的文化品性和表達方式。五條人的創(chuàng)作題材廣泛,既有世情倫常(《理想世界》《拉手曲》)、家鄉(xiāng)風物(《南方戀曲》《上縣城》),也有人物素描(《陳先生》《阿虎》)、風花雪月(《傷心的人》《你好!春天小姐》)、嬉笑怒罵(《心肝疼》)和無厘頭(《城市找豬》),等等。他們的做派是草根的,甚至觀感上有一種不自然的做作,但并不影響他們在歌曲中所要表達的人文性。他們以多種語言的交匯,模糊了人們刻板的地方性概念,這種解構(gòu)態(tài)度與搖滾的精神相接,是很聰明的做法。光就其歌曲的曲名而言,就已經(jīng)具有流行音樂素質(zhì)了。譬如:《地球儀》《越南》《陳先生》《阿珍愛上了阿強》《我的頭發(fā)是這樣被吹亂的》《城市找豬》等,都有著讓人過目不忘的特質(zhì)。他們用輕搖滾的搖曳、吟唱的口吻化解生活的沉重。這種帶有民謠風的說唱是流行音樂中的一種風尚,頗有順手拈來的輕松自如。因此,他們的音樂通俗而不搞怪,聽著有赤腳走在石板路的愜意感覺,也頗能得到眾多青年人的喜歡,這一點是成功的。當然,經(jīng)過反復(fù)的聆聽,他們的吟唱中也透著韻味的不足,乃是因為音樂性的欠缺,唱功更是沒有得到發(fā)揮。音樂性的不足,自然需要其他的視覺形式的補充和裝飾,著意營造表演氣氛,勢必影響藝術(shù)上的用功。不斷依賴味精,可以持續(xù)做出美味的菜肴嗎?這個問題可能有些尖刻,但還是需要面對的。
(二)扭蛋姬
扭蛋姬,由一色的青春女孩組成,這在搖滾樂隊中是罕見的組合。尤其在中國,更顯得難能可貴。
扭蛋姬由曉肆(主唱)、焗妹(吉他手)、小加(貝斯手)、琪妹(架子鼓)、小桃(鍵盤),以及其他的編創(chuàng)團隊成員共同組成。她們的形象活潑、可愛、青春、充滿朝氣;包裝風格為卡通、ACG(動畫、漫畫、游戲)、二次元畫風,歌舞并行。
她們在表演上有著活躍的創(chuàng)作方式,游走于幻想的歐陸哥特風、日系的青春東洋風和搖滾的中國風之間。以多種主題(包括語言)的變幻,展現(xiàn)出舞臺活力,以及線上空間的內(nèi)容厚度。她們并不只專注于綜藝和線上活動,滿足于一般性網(wǎng)紅的流量與聲量,而是將創(chuàng)作活動落實到傳統(tǒng)舞臺和文化社區(qū),所以具有相對開闊的認受度。
扭蛋姬憑著青春女孩與搖滾反叛的反差式結(jié)合,突出一種清新可愛的表演風格,無疑是有著奇特的二次元效果的。她們抓住青年人追新求異的多樣化審美需求,但是并不刻意追求前衛(wèi),而是以富有張力、風格百變的舞臺形象,用稍帶稚氣的歌聲訴說著少女與青春有關(guān)“友情、夢想、奮斗、感悟”的故事。雖以翻唱為主,卻也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觀念的融入,保持歌唱、伴奏、舞蹈的風格協(xié)調(diào),沒有偏向搞怪的做派和“拾口水”的窠臼。不過,翻唱畢竟是借力別人的智慧創(chuàng)造,如果沒有自己的作品,是難以塑造自己的藝術(shù)風格的。在作品方面,扭蛋姬也交出了功課,像三部曲《水晶城卷軸》《奇幻扭蛋姬》和《夏之羽翼》就具有統(tǒng)一畫風的原創(chuàng)性,類似一組別具一格的音樂屏風。又如《異世界之門》和《謫仙青蓮》,是探索性的風格延展,應(yīng)該說從立意、編曲到演繹都有一定質(zhì)量。對于一個青春少女組合,她們?nèi)绻^續(xù)這樣的畫風,對粵語的演唱再努力用功一點,加入自己的誠意和生活理解,相信是可以給廣東樂壇帶來一縷清風的。
另外,扭蛋姬出于對傳統(tǒng)的喜愛,嘗試將傳統(tǒng)的元素注入自己的創(chuàng)作。最為突出的是她們在參加廣東電視臺珠江頻道“2021粵語好聲音——樂隊風暴”節(jié)目,其中有一段對粵劇唱腔《帝女花》之“香夭”的改編借用,表現(xiàn)出無畏的勇氣。用她們的話說,就是“不破不立”。這引起強烈的爭議,甚至惹來所謂的“眾怒難平”。筆者當然不認為扭蛋姬存在惡搞經(jīng)典的故意,而是相信她們確實有初生牛犢的勇氣和對于“破與立”的急切。不過,對于經(jīng)典的模仿、改編與創(chuàng)新,前提是要掌握經(jīng)典,吃透之后方能研磨出新的東西來。“破”很容易,“立”就很難。扭蛋姬對粵劇唱腔的改編是頗為用心的,無奈選錯了原著。且不說《帝女花》中的戲劇內(nèi)容和粵劇的精氣神等方面的主觀元素,她們沒有了然與很好把握,更重要的是,對于歌唱而言這段唱腔所達到的高度缺乏基本的認知和體會,這類似于威爾第的詠嘆調(diào)和梅蘭芳、譚鑫培的唱腔,這些經(jīng)典只有膜拜,超越非常困難,改編不好就意味著矮化,吃力不討好。前些年有著名鋼琴家對貝多芬《第五交響曲》的改編大肆流行,就留下很不好的后遺癥。對于這一類創(chuàng)作,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行。
(三)九連真人
九連真人樂隊來自粵北山區(qū)的河源市,成員都是九連山下的真人“阿民”們,建隊的歷史不長,始于2018年。樂隊主唱阿龍、副主唱阿麥和貝斯手萬里是最初的班底,鼓手吹米的加入是后來參加節(jié)目時的“外援”。原本他們都是有固定職業(yè)的人,玩樂隊純屬興趣愛好,在連平這個小城里屬于不務(wù)正業(yè)的奇葩存在,“來自山里的搖滾”作為他們的文化標簽是比較恰當?shù)摹W叱龃笊綇V為人知,是拜無處不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所賜,視頻傳播具有所謂“炸彈”的明星效應(yīng),尤其是2019年他們被邀請參加大型綜藝節(jié)目“樂隊的夏天”(愛奇藝和米未傳媒出品)之后。在節(jié)目主辦方的包裝下,他們以青澀的“阿民”形象,喊出大山青年的情感,從業(yè)余走向搖滾的圣壇,成為不少觀眾心中的最愛。
九連真人作品數(shù)量不算多,但質(zhì)量上似乎較有保證,如《夜游神》《莫欺少年窮》《北風》《一浪》《凡人歌》《三斤狗》等。演唱語言堅持純正的客家話,這是他們的本真初心,可以理解為刻意的做派,甚或理解為樂隊的文化基因和精神靈魂。筆者倒是比較欣賞九連真人在音樂上的真誠,譬如主唱在發(fā)聲基礎(chǔ)上接近傳統(tǒng),不在取巧上走得很遠,也是一種質(zhì)樸的表現(xiàn)。客家山歌的高亢喊腔、土氣的語調(diào)都有粗糲感。尤其是在樂隊的器樂表現(xiàn)上有很積極的作為,功能、分工明確,默契度和表現(xiàn)力都不錯。他們曾經(jīng)獲得滾石原創(chuàng)樂隊大賽冠軍(2018)、第11屆迷笛獎之“年度最佳搖滾新人”獎(2020)、第13屆華語金曲最佳新樂隊(2021)等獎項,在“樂隊的夏天”中以“黑馬”之勢闖入大眾視野,成為樂隊的寵兒,這些都頗能說明問題。但是能否擔得起“音樂富于文學(xué)性也富于情感,富于地域性又很遼闊,更加富于故事性和音樂性”,“樂風明亮,大開大闔,光明疏朗,居山中而瞰天下,歌曲以不正之風撫觸靈魂”(黃燎原評),“是華語樂壇的又一風向標”等評價,還需要時間來檢驗。
客家文化背景,除了語言上的特點(其實客家話并不小眾),九連真人在人文訴求上有一定的自覺。讓客家的音樂走出九連山,這種樸素的理想是值得欽佩的。“阿民”,是他們抽象出來的一個表達九連山下的生活群像,寄托的是客家人的漂泊歷史和圍屋生活的山風月影,是有故事的歌聲。相對于五條人的鬼馬任性,九連真人傾向于一種樸實的直率情感,他們的故事和情懷有較為清晰的廣東客家地域性烙印。作為曾經(jīng)的留守兒童和為“阿民”代言的歌手,無論是個性化的敘事、還是對大山的情感,在他們的歌聲中都有著明顯的親切感與感染力。他們對農(nóng)業(yè)時代祖輩的家庭文化觀有戲謔的意味,搖滾、吶喊中有來自表面的睥睨、超越,也有內(nèi)心的無奈與沮喪,可以視為對傳統(tǒng)的解構(gòu)。但是從歌詞和音樂旋律中又可以體會到他們對祖輩山民的敬重和眷戀。九連真人的樂手都有過一定的專業(yè)音樂訓(xùn)練,但并不崇洋,而是對傳統(tǒng)音樂有主觀上的親近。所以,他們音樂上嫁接傳統(tǒng)的元素頗多,像《落水天》《三斤狗》就是以客家山歌為音樂基礎(chǔ)。不過,傳統(tǒng)的繼承與搖滾的結(jié)合還需探索儀式上的合理途徑,像參加經(jīng)典詠流傳的《望月懷遠》,為遷就節(jié)目的主旨而刻意拔高,就難免尷尬。顯然這對于張九齡的詩詞經(jīng)典,對于九連真人本身都是不能加分的。目前樂隊尚在發(fā)展期,對于自己的音樂風格認定,如何堅持自身的藝術(shù)品性等方面需要更多的智慧。
以上對幾個樂隊的初步觀察,是流行音樂版圖中的一角,僅為廣東樂隊中的極少數(shù),不一定有廣泛代表性,但卻是近年較為醒眼的案例。以此窺視當下流行音樂中出現(xiàn)的新現(xiàn)象,既有可喜的創(chuàng)新與本土重塑,也有困惑和遺憾。據(jù)筆者的觀察,他們各自有著優(yōu)點和獨特個性,但令人憂心的地方恐怕還是集中在音樂的質(zhì)量和創(chuàng)作秩序上。
三、音樂的質(zhì)量
流行文化的結(jié)構(gòu)是復(fù)雜的,藝術(shù)價值的考量與商業(yè)價值的追求總是在現(xiàn)實的多維交集中糾纏。商業(yè)的需要常常不自覺地傾向于短期的目標,在做派上做文章有天然的合理性。譬如對藝人的形象包裝、玩梗(塑料袋、穿拖鞋)、方言等,又譬如在表演中的適當即興、互動、插入談話等。這些無疑對于形象推廣、增加舞臺趣味性等有積極意義。然而,創(chuàng)作作品和鍛造藝術(shù)品性是長期的。包括音樂的靈感的尋找、音樂主題的提煉、創(chuàng)作技術(shù)的成熟、演唱表達方式的研磨等,都不是一揮而就,需要時間去逐漸完成。而這些往往考驗的是音樂人的真誠、天賦與智慧。商業(yè)是流行文化的必由之途,但是商業(yè)的目的一定需要文化價值來支持,否則是走不遠的。流行音樂,包括搖滾樂,其文化屬性是音樂。也就是說,樂隊作品要有吸引力,仍然需要在音樂性上做文章,要寫出動人的旋律,要唱出韻味,才能有長久的生命力。優(yōu)秀的樂隊,遠至20世紀的披頭士(The Beatles)、滾石(The Rolling Stones)、唐朝、Beyond,近至五月天、水木年華、花兒樂隊,都有自己出色的代表作在流傳。像披頭士的《Hey Jude》和《Yesterday》、七合板樂隊的《一無所有》、唐朝的《夢回唐朝》、Beyond的《光輝歲月》能夠久唱不衰,都是人性附著音樂的精神訴求,從而形成的經(jīng)典傳承。沒有過硬的音樂性內(nèi)核,是無法穿越時空,進入人們的心里的。
那么,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便顯而易見了:音樂要質(zhì)量,藝術(shù)性就不能貧瘠。流行文化為了吸引眼球和流量,在文化行為上可能會被資本所影響、加持,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問題是文化行為的質(zhì)量和格調(diào)存在著優(yōu)劣高低。其中最關(guān)鍵的一點是作品的創(chuàng)作與表現(xiàn)的質(zhì)量問題,其他出于所謂的節(jié)目效果的做派對于作為音樂作品的未來生命都無關(guān)宏旨。作品的呈現(xiàn)可能有即興的成分,但是作品創(chuàng)作的過程是長期積累而成的,幾無例外。也就是說,好作品很難閉門造車地完成,也不是抖機靈可以獲得,需要生活的深刻體驗,靈感與智慧的凝合。否則,只能敷衍應(yīng)付,在做派與噱頭上進行炒作,或者勉強在所謂的本土元素上取巧,那是不能掩飾作品藝術(shù)素質(zhì)的虛弱的。一味地講故事,那是文學(xué)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如果沒有在音樂上的深耕細作,研磨音樂的品質(zhì),像九連真人原來的市井煙火氣和“阿民”的人文內(nèi)核、五條人的知識分子的底色、扭蛋姬的純清可愛也將會在低水平的重復(fù)呢喃中被逐步削弱。還有,既然是樂隊,在演奏上需表現(xiàn)出器樂的魅力,就不僅是節(jié)奏、鋪墊和伴奏,而是盡可能在音樂表現(xiàn)上提升藝術(shù)品格,像披頭士在《Yesterday》中的弦樂和《Let it Be》中的口琴一樣,是他們作品中不可或缺的硬核存在,有著過耳難忘的音樂魅力。雖然廣東本土的這三個樂隊都具有一定的樂器演奏基礎(chǔ),但是以他們目前的作品支撐他們繼續(xù)發(fā)展是不夠硬氣的。如果音樂創(chuàng)作上沒有向上的執(zhí)著努力,就會滋生驕氣或頹勢,除卻商業(yè)性的噱頭和關(guān)于音樂的故事,那剩下的只有歌曲的標題了,無法在音樂性和藝術(shù)品格上予人更高的期待。
四、創(chuàng)作的秩序
音樂的貧瘠是中國流行音樂的天然弱點。因此,能沉淀為未來經(jīng)典的都是少數(shù),不是靠運氣,而是對真正價值的傳承與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方面可以對傳統(tǒng)做繼承和利用,這是非常有效的途徑。但是并不見得比無中生有更容易,因為傳統(tǒng)經(jīng)典有著形式上的完整性和文化上的時代性。改編創(chuàng)新可以做努力,但蛻變出有質(zhì)量的新作品是非常艱難的,甚至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在農(nóng)業(yè)時代,磨礪一個作品是通過長期的實踐共同打造的,浸透集體的智慧。現(xiàn)代的流行文化顯然不能在時間上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所以工業(yè)時代、信息時代的文化創(chuàng)作常常寄望于新的創(chuàng)作模式,強調(diào)資本、團隊、程序,也就是尋求新的路徑與秩序。如果沒有辦法凝聚起創(chuàng)作力量,運行起有效的團隊,在創(chuàng)作和傳播上就很難成氣候。流行音樂的流行遵循一定的工業(yè)流程,創(chuàng)作、表演和傳播往往是一體化的。即使存在松散的獨立音樂人,但是團體合作仍然是基本方式,因為商業(yè)的利益訴求,必然要求適當?shù)摹⒕哂懈偁幜Φ暮献髂J健!皹逢牭南奶臁本褪且环N模式,以選秀的方式,直接催生了五條人和九連真人的明星身份和文化效應(yīng)。但是選秀與綜藝僅僅是其中的平臺和助推器,新音樂形式的生存問題還得有適宜自身生長的土壤和動力。那么,我們要思考的問題是,曾經(jīng)那些強調(diào)獨立音樂人身份的很多從業(yè)者,其獨立性的文化標簽,與大眾化的藝術(shù)性是否存在天然的排斥性?流行文化能否建立起有效的音樂創(chuàng)作秩序?
回到廣東新音樂現(xiàn)狀更為現(xiàn)實的問題,他們的生存方式和可持續(xù)發(fā)展似乎更值得思考,因為這在當下是新生流行文化行為的關(guān)鍵所在。樂隊的生存空間是寄存于小眾的劇場(Live House),積極躋身于各式音樂節(jié)、電視綜藝節(jié)目、互聯(lián)網(wǎng)空間(bilibili網(wǎng)站)?還是需要另外的一種力量凝聚這個文化群體?唱片還是否能繼續(xù)作為一種傳播方式?如果還有一種區(qū)域性的廣東流行音樂概念的話,就應(yīng)當追求一種在地資源支撐的文化創(chuàng)造機制。坦白說,九連真人和五條人的走紅就沒有這種在地資源的支撐,沒有發(fā)生在本地,而是參加外地的音樂平臺而產(chǎn)生的效應(yīng)。從外地歸來,固然也是廣東文化的榮光,但是總是一種缺憾,似乎廣東沒有意識和能力從文化機制上培育自己的音樂人才和運作自己的流行音樂模式。就從最為基礎(chǔ)的樂隊演出活動場地看,廣東這些樂隊就缺乏存在感。而古典音樂市場則不然,我們可以驕傲地說,廣東省內(nèi)的深圳音樂廳、廣州大劇院、星海音樂廳、玉蘭歌劇院等已經(jīng)是全國的高地。雖然流行樂隊的活動有其靈活、松散性和獨立性,筆者目前也缺乏仔細的調(diào)查研究,但他們總是藏身于城中村、地下車庫、校園社團中的活動場所,畢竟是無法施展的逼仄空間。類似于廣州MAO、拾叁唐、SOBER、MANTA、風馬民謠的Live House還是很少,不足以形成有規(guī)模、有質(zhì)量的演出、交流和創(chuàng)作生態(tài)系統(tǒng),難以引起年輕人對新音樂的興趣,更難有對外的輻射力。其實,粵港澳大灣區(qū)是世界級經(jīng)濟體,充滿活力,其流行文化的市場空間實在是有著巨大誘惑力的。以香港、廣州、深圳為核心的城市群,音樂文化有著國際化的格局,層次、結(jié)構(gòu)、種類都是其他地區(qū)無法比擬的。可是其流行音樂生態(tài)卻與上海、北京,甚至長沙、成都相較反而顯出疲態(tài),多少令人遺憾和費解。
結(jié) 語
流行音樂的可貴之處是接近生活,從現(xiàn)實生活中成長出來,必然是帶有煙火氣的文化。除了內(nèi)容上與生活息息相關(guān),形式上也與生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一旦脫離現(xiàn)實太遠,流行音樂就會失去生命力。所以,流行音樂的做派多于藝術(shù)精神的追求不足為奇。音樂文化的發(fā)展很難隨著人們的主觀意志而達成理想,而是多種因素作用之下的、體現(xiàn)時代特征的偶然性文化生態(tài)。做派是當今社會文化賦予流行文化的行為正當性,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我們也要明白,最終檢驗其價值的是作品中的音樂質(zhì)量,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對這個現(xiàn)象的觀察討論還需繼續(xù)深入的理論觀照與批評,為的是希望這種偶然的現(xiàn)象成為健康持續(xù)的常態(tài),并使廣東流行音樂的繁花如錦。
注釋:
[1] 指核類音樂(Hardcore music),一種源自朋克(Punk)的金屬類搖滾音樂,注重節(jié)奏律動的活力,旋律抒情性弱,和聲或者噪音被強調(diào)和夸張,有濃重的金屬品味。廣州和其他珠三角城市在21世紀以來涌現(xiàn)不少此類樂隊,有自己的演出空間和交流方式,但較少得到主流媒體的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