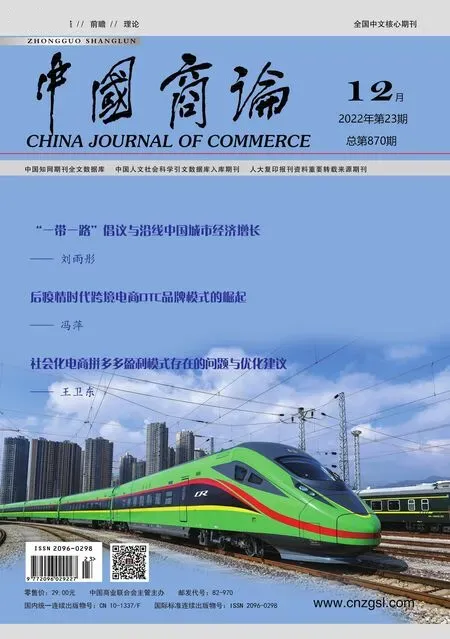活力中心、多元功能和新型社區
——淺談活力城市建設三要素
《中國商論》:活力城市研究的緣起是什么?
唐黎明:從事咨詢行業二十多年來,我去過很多地方,既有繁華的大都市,也有偏遠的小鄉村,我看過大都市中的荒蕪樓宇,也體驗過小鄉村的熱鬧集市,還去過沙漠中的消失古城,我常常在思考,一個城市的生命力來源于哪里?城市活力的關鍵要素究竟是什么?我想探尋城市繁雜表象下的本質原因。
《中國商論》:在現在的中國城鎮化階段中,活力城市研究有什么現實意義嗎?
唐黎明:中國的城鎮化經過近30 年突飛猛進的發展,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7%,年均提升1.3 個百分點,我們用30 年的時間走過了國外100 年走過的城鎮化道路,城市經過大躍進式的發展,城市規模迅速擴大,在改善民眾居住條件的同時也帶來了很多問題,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新城過剩、新區過剩、房地產過剩,一些地方投入巨資建設的新城缺乏人口和產業,淪為鬼城空城,像濱海新區、貴安新區;一些地方人口不斷流失,房子成為城市的負資產,像鶴壁、牡丹江;一些地方的中心城區出現衰敗跡象,還有一些地方出現大量的爛尾工程、爛尾園區。如何為新城吸引產業和人口?如何為老舊城市帶來新的生命力?都是活力城市要解決的命題。
《中國商論》:活力城市的概念是什么呢?
唐黎明:活力城市是一個城市生命力和發展質量的綜合體現,包括人口活力、產業活力、生態活力、資本活力、人文活力和空間活力,你可以從很多角度進行定義和解讀,這其中,人口活力和產業活力是活力城市的兩大基石,產業和人口對于城市發展來說,缺一不可。
《中國商論》:活力城市的關鍵要素有哪些呢?
唐黎明:我把它提煉為三個關鍵詞:活力中心、多元功能和新型社區。城市的活力中心,可以持續集聚人口、資金、產業等城市要素,從而使城市的功能更加多元化,在一個區域滿足人們的工作、居住、休閑、購物等多種需求,使得這個區域不再是單一的居住小區或產業園區,而是擁有多元功能的新型社區。產、城、人融合發展,共同形成產業、城市、社會協調共生的城市新生態。
從圖8中可以看出,加補償網絡的電路有一定的超調量。當有電阻串聯到電路產生擾動時,輸出電壓發生了波動,系統能迅速的調節,穩態時使輸出電壓恢復到5 V;當有電源串聯進電路和電阻并聯進電路時,產生的擾動也能夠被控制系統迅速調節。由于所加的電源擾動為1 V,輸入電壓為3 V,擾動過大,所以會產生如圖8所示的大波動,但控制系統最終也能夠穩定輸出電壓到5 V。
《中國商論》:如何理解“活力中心”?
唐黎明:凡是能夠給區域和城市注入活力的有形資產或無形資產,都可以稱為活力中心。微觀而言,可以是一所大學,可以是一個集市,一個公園或一家上市公司,中觀而言,也可以是一個大型交通樞紐,一個匯聚了上下游產業鏈產業園區,或者是政府機構組團。
《中國商論》:你剛才有提到大學作為活力中心,近十年各地興建了很多大學城,但這些大學城與城市的關系并不密切。
唐黎明:是的,很多大學城的選址出現了問題。大學校園的土地,大多象征性的交少量土地出讓金,地方政府往往會留著地段較好的土地用于商業開發,把遠離市中心位置不好急需造人氣的土地,留給大學園區。有的距離主城或中心城鎮過遠,由于教師絕大部分都住在主城區,不得不依靠校園車輛上下班,大大增加了城市交通壓力。新校區的區位選擇不當,與市區的距離過遠,削弱了教育發展的后勁,也不利于學生融入社會。因為選址不當,后期配套不完善,很多本該是城市活力源泉的大學校園,反而成為了城市中的孤島。
《中國商論》:校園如何能成為城市的活力源泉呢?
唐黎明:對于城市來說,大學是一個文化機構、文化組織,是城市中最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品位,提升城市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大學里充滿活力的學生、老師和研究人員,這些高素質的人口,會給城市帶來無窮的活力和創意。
《中國商論》:有沒有這方面的成功案例呢?
唐黎明:牛津大學城是個很好的例子,牛津大學城位于英國南部,距倫敦約90 公里。牛津大學城不是源于規劃設計,而是源自早期學術活動的集結,知識分子匯聚而發展形成的。大學和城市發展融為一體,大學內的公園、博物館和動植物園等都對公眾開放,并為市民舉辦講座、展覽、參觀等活動。大學作為城市發展的原動力,帶動了商業、住宅、工業和高科技等產業發展。所以,當地方政府費盡心思引進大學院校時,應該以更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從土地出讓的選址、城市配套完善、規模和尺度控制等方面系統考慮,讓大學園區成為城市的活力源泉和寶貴資產。
《中國商論》: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正是因為活力中心可以吸引人口、資金、技術、產業,才使得這個區域的功能更加多元化。
唐黎明:是的。城市的活力來源于多樣性。中國的城市規劃思想,深受蘇聯模式的影響,條塊分割 渭分明的把城市劃分為居住區、政務區、產業區、商務區等區域。然而人在城市中工作生活,需求并不是單一的,即便是在工業園區上班的工人,也有購物、休閑等需求。如果一個人要完成居住、娛樂、購物、就業、辦公等需求,需要跨越無數個區域,就會增加許多時間成本和交通成本,進而埋下城市病的隱患。
《中國商論》:如何讓一個區域的功能更加多樣化呢?
唐黎明:這實際上與區域現狀密切相關,首要任務就是對現狀城市功能進行梳理,查缺補漏,產業新城、政務新城、居住新城、商務新城等名目繁多的新城,從規劃、設計、建設到后期運營管理都需要轉換思維,使得居住在其中的人能夠方便的實現居住、購物、娛樂、消費、休閑、治病、就業、上學等多種需求。
《中國商論》:對地方政府而言,還需要做哪些呢?
唐黎明: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一 而就。最關鍵的是兩大要素整合:一是對土地性質進行整合。多元的城市功能,對應的是多元的土地利用格局。我們經常會在許多城市看到類似的土地規劃圖,在工業園區里幾乎全是棕色的工業用地塊,在居住區里幾乎全是黃色的居住用地塊。要實現多元功能,就要避免大規模的單一性質的土地利用規劃,進行相應的土地性質調整。二要對行政體制進行整合。產業發展和城市建設,對地方政府而言,分屬發改局、住建局和國土局等不同部門管理,產業規劃、城市功能要和土地性質整合,需要不同部門步調一致。
《中國商論》:如何理解新型社區?
唐黎明:新型社區與多元功能是相對應的。以產業社區為例,我們先來看一下產業園區和產業社區的區別:在早期的工業園區規劃建設中,普遍優先發展生產功能,注重招商引資,忽略了產業園的生活、生態功能,產業社區與工業園、產業園區相比進步之處在于,產業社區將產業反映的空間形態與城市的各個層面融合起來,是未來產城布局的創新空間模式。
《中國商論》:產業社區,是否集合了產業和社區雙重屬性?
唐黎明:是的,產業社區是以產業為基礎,融入城市生活等功能,打破了地理邊界,空間更開放、企業生態更多元、社群交流更活躍。產業聚集了大量就業人才,是社區形成的基礎,而社區強化了對人才的吸引力,通過搭建產業主體和就業人才的社群平臺,打造生態、舒適的生活環境。產業社區改變了傳統產業園區把生產功能作為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功能的發展方式,促進了產業功能與生活功能融合發展。
《中國商論》:活力城市,是否類似于把城市看作一個有機的生命體?
唐黎明:是的,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就像人的身體一樣,它會成長和發育,會發生改變。城市是一個有機的生命體,它的規模、尺度與速度,決定了城市發展的態勢。而中國城市出現的種種問題,不是在于發展太慢,而是在于發展太快,大躍進式的城鎮化,讓政府官員、企業和民眾都 及不妨,手忙腳亂。以活力城市的視角來正確認識城市的生命力,既可以為新城區集聚產業和人氣,也可以為舊城更新帶來新活力,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