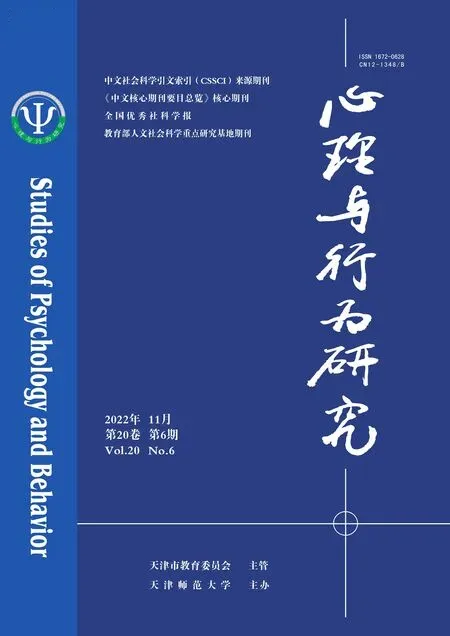大學生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的關系: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 *
朱瑩瑩 黃佳豪 唐卓儀 劉佳瑩 李 欣
(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300387) (3 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1 引言
睡眠是人類生命活動所必需的過程,它是正常運行機體功能和維持生活質量的重要保障。睡眠不足或缺失會對個體的身心健康帶來一系列的負性影響,比如焦慮、抑郁、認知受損、學習效率下降、自傷和自殺風險提升等(Biddle et al.,2019; Liu et al., 2020; Vargas & Perlis, 2020)。隨著社會的快節奏發展以及人們對電子產品的過度依賴,睡眠拖延現象也愈發凸顯,據最新發布的《中國睡眠研究報告》顯示,目前我國大學生群體中晚睡、不按時就寢的情況十分普遍,僅有約6.4%的學生報告自己從不拖延睡覺時間,而高達54.3%的學生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睡眠拖延問題(中國睡眠研究會, 2022)。睡眠拖延是指個體在沒有外部原因阻礙的情況下,習慣性地推遲其預定就寢時間的行為(Kroese et al., 2014)。研究發現,睡眠拖延不僅會導致個體出現睡眠不足、入睡困難、負性情緒增多(Kadzikowska-Wrzosek, 2018;Sirois & Pychyl, 2013),長此以往還會誘發睡眠節律紊亂、焦慮、抑郁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等身心障礙(Cox & Olatunji, 2016; Irwin, 2015)。大學階段是人生發展的重要轉折期,充足、優質的睡眠是個體正常生活學習的基本保障(Scott et al., 2021),而不良的睡眠行為和習慣則會對大學生的睡眠狀況和身心健康產生諸多不利影響(雷潔 等, 2020;Cox & Olatunji, 2016; Gellis et al., 2014)。鑒于此,本研究將選取大學生為研究對象,探討大學生的睡眠拖延行為對其日間嗜睡狀態的影響及作用機制,以期為預防和干預大學生睡眠拖延,促進其身心健康發展提供實證依據。
自從荷蘭學者Kroese等人(2014)將拖延行為首次引入睡眠領域后,睡眠拖延與身心活動的關系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人們發現隨著拖延程度的加深,睡眠不足與睡眠質量下降更加明顯(Teoh et al., 2021)。而夜間睡眠質量不佳將會直接導致個體次日的主客觀狀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一個突出表現就是易使個體的主觀警覺性變差,日間嗜睡水平明顯增加(Isac & Abraham,2020; Regestein et al., 2010)。所謂日間嗜睡是指個體在日間覺醒期間無法保持清醒狀態,且無意識地在不恰當的時間睡著,其本質是難以維持白天所需的覺醒水平(Young, 2004)。研究表明,日間嗜睡與睡眠不足、睡眠質量下降等存在密切關聯(Chen et al., 2011; Ohayon, 2008; Slater & Steier,2012)。然而睡眠拖延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縮短睡眠時長,導致個體睡眠不足、質量變差(Teoh et al.,2021; Zhang & Wu, 2020)。由此可見,睡眠拖延很可能是影響個體日間嗜睡狀態的風險因素。綜合上述研究,本研究假設:睡眠拖延可以正向預測我國大學生的日間嗜睡水平。
睡眠拖延除了會對白天的嗜睡狀態產生影響外,其與失眠的關系也頗為密切。Hairston和Shpitalni(2016)的研究表明,拖延作為一種不良的行為習慣能夠顯著預測個體的失眠癥狀,尤其對于晚睡晚起的人其預測作用更強。Li等人(2020)通過對8742名大學生的睡眠狀況和拖延行為間的關系調查分析發現,個體的拖延行為(包括睡眠拖延)與其睡眠時長、社會時差、失眠、日間嗜睡等方面均存在顯著相關,并且存在拖延行為的學生罹患失眠的概率也明顯高于沒有拖延行為的學生。另外,依據失眠的三因素模型(即易感因素、誘發因素和維持因素)的觀點,一些不健康的睡眠行為,如不按時睡覺,拖延上床時間等還是失眠長期存在的一個重要維持因子,易使個體由暫時性失眠滑向慢性失眠的深淵(Perlis et al.,2005; Spielman et al., 1987)。而失眠等睡眠問題又與個體白天的覺醒狀態息息相關,國內外眾多實驗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失眠、入睡困難等均會導致個體醒后主觀警覺性降低、日間疲勞及嗜睡增多(Amaral et al., 2017; Chan et al., 2020; Hein et al., 2017)。一項基于青少年的大樣本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明確指出,失眠是導致青少年睡眠減少和日間嗜睡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可對其白天的警覺水平和日常活動狀態產生顯著的負性影響(Johnson et al., 2006)。Angelone等人(2011)通過對醫學大學生的橫斷研究也同樣發現,失眠與日間嗜睡風險增加存在明顯關聯。故綜合前人研究,本研究推測失眠可能在大學生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之間起中介作用。
在睡眠拖延對大學生日間嗜睡的作用機制中,睡眠時型也是一個值得考察的變量。所謂睡眠時型是指個體對于睡眠-覺醒時間的主觀偏好,它是評估個體晝夜節律變化的重要指標(Adan et al.,2012; Hidalgo et al., 2009)。以往關于睡眠拖延和失眠的研究中均發現了睡眠時型差異。Kadzikowska-Wrzosek(2018)和Kroese等人(2014)通過問卷調查發現夜晚型(偏好晚睡晚起)個體相比于清晨型(偏好早睡早起)個體更傾向于出現睡眠拖延行為。Kühnel等人(2018)經過追蹤觀測進一步印證了上述結論,并指出夜晚型群體的睡眠拖延行為在一周較早的工作日內更容易出現。另有研究發現,夜晚型人的自我調控能力普遍較差,不能很好地抵制睡前干擾活動(如沉浸式看電視、刷手機等),導致錯過預定就寢時間,產生睡眠拖延(Exelmans & van den Bulck, 2017; Kamphorst et al.,2018)。此外,相較于清晨型,夜晚型個體的睡眠狀況也通常不太樂觀,容易出現入睡困難、失眠、夢魘增多等問題,清晨型則較少受到上述睡眠問題的困擾(Alvaro et al., 2014; Roeser et al., 2012)。根據睡眠的雙調控過程模型,機體內穩態系統和生物節律系統的協同工作是個體擁有良好睡眠的重要保障(Achermann, 2004),而習慣于晚睡晚起的夜晚型群體因其內在生理時鐘與外在的晝夜變化不相匹配,由此帶來的節律系統紊亂極易使其產生諸如失眠等睡眠障礙(Partonen, 2015)。有研究者曾通過大樣本數據調查分析發現,夜晚型被試的失眠癥狀要明顯多于清晨型,且該群體出現心理行為問題的概率也遠高于其他兩類睡眠時型(Li et al., 2018)。該結果隨后也得到了Yim等人(2021)的研究支持。基于此,本研究推測睡眠時型在睡眠拖延經由失眠對大學生日間嗜睡影響的前半段路徑中可能具有調節作用。本研究假設:相對于清晨型大學生,睡眠拖延對夜晚型大學生的失眠癥狀影響更為明顯。
綜上,本研究旨在以大學生為研究對象,結合以往研究,構建一個有調節的中介模型來探討睡眠拖延對大學生日間嗜睡的影響,以及失眠的中介和睡眠時型的調節作用機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方便取樣的方法,抽取天津與河南兩地高校的在校大學生進行施測,共發放問卷4521份,回收有效問卷4252份(有效率94.05%)。其中,男生1208名(占比28.41%),女生3044名(占比71.59%);大一1274名(占比29.96%),大二1763名(占比41.46%),大三929名(占比21.85%),大四286名(占比6.73%)。平均年齡為19.76±1.39歲。
2.2 研究工具
2.2.1 睡眠拖延量表
采用馬曉涵等人(2021)修訂的大學生睡眠拖延行為量表(Bedtime Procrastination Scale,BPS),共包含9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1表示“從來沒有”,5表示“總是”,條目2、3、7、9為反向計分。所有條目的平均分即為量表得分,分數越高表明個體的睡眠拖延行為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4。
2.2.2 失眠嚴重程度指數量表
采用李恩澤等人(2018)修訂的失眠嚴重程度指數量表(Insomnia Severity Index Scale, ISI),共包含7個條目。采用5點計分(0=“完全沒有”,4=“非常嚴重”),總分范圍為0~28分,分數越高表明失眠程度越嚴重。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數為0.88。
2.2.3 Epworth嗜睡量表
采用彭莉莉等人(2011)翻譯修訂的Epworth嗜睡量表(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評估大學生的日間嗜睡情況。量表由8個條目組成,采用4點計分,0表示“從不打瞌睡”,3表示“經常打瞌睡”,總分范圍為0~24分,得分越高表明日間嗜睡程度越嚴重。先前研究表明該量表在大學生人群中具有良好的信效度(Huang et al., 2014)。本研究中該量表的 Cronbach’s α系數為0.84。
2.2.4 睡眠時型量表
采用張斌等人(2006)修訂的清晨-夜晚型自評量表評估大學生的睡眠時型(Morning-Evening Questionnaire, MEQ)。量表共19個條目,條目1、2、10、17、18為5點計分,條目3至9、11至16、19為4點計分。總分范圍為16~86分:16~41分屬于夜晚型睡眠;42~58分屬于中間型睡眠;59~86分為清晨型睡眠。得分越高表明個體越傾向于清晨型,反之則傾向于夜晚型。本研究中該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數為0.71。
2.3 數據處理
首先,采用SPSS19.0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及差異檢驗。接著,通過Hayes(2013)編制的PROCESS宏程序進行中介效應以及有調節的中介模型檢驗。采用偏差校正的Bootstrap法進行參數估計,并報告95%置信區間。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中,所有變量均采用自我報告的問卷法測量,因此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周浩, 龍立榮, 2004)。為了保證嚴謹性,采用Harman單因素檢驗法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9個。其中,最大因子的方差解釋率為19.84%(小于40%),表明本研究不存在嚴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
表1呈現了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和相關矩陣。結果表明,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和失眠均呈顯著正相關,與睡眠時型呈顯著負相關;睡眠時型與失眠、日間嗜睡呈顯著負相關;日間嗜睡與失眠呈顯著正相關。

表 1 描述性統計及相關分析結果(n=4252)
3.3 不同睡眠時型大學生的睡眠拖延、失眠及日間嗜睡差異比較
本研究樣本中,有6.9%(294名)的大學生屬于夜晚型睡眠,其中男生54名,女生240名;有26.5%(1126名)的大學生屬于清晨型睡眠,其中男生390名,女生736名,另有66.6%(2832名)的大學生為中間型,其中男生764名,女生2068名。隨后對不同睡眠時型大學生在睡眠拖延、日間嗜睡和失眠方面是否存在差異進行了檢驗(以睡眠時型為自變量,性別、年齡為控制變量進行協方差分析),結果如表2所示:睡眠時型在睡眠拖延[F(2, 4247)=402.25,p<0.001, η2=0.15]、日間嗜睡[F(2, 4247)=96.05,p<0.001, η2=0.04]以及失眠[F(2, 4247)=135.04,p<0.001, η2=0.06]上的主效應均顯著。事后比較結果表明,夜晚型大學生在睡眠拖延、日間嗜睡和失眠上的得分均明顯高于清晨型和中間型大學生(p<0.01),清晨型大學生的睡眠拖延、日間嗜睡及失眠分數與中間型相比明顯偏低(p<0.01)。

表 2 不同睡眠時型大學生的睡眠拖延、日間嗜睡及失眠差異分析結果(M±SD)
3.4 失眠在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間的中介效應分析
使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4對失眠的中介效應進行檢驗。采用偏差校正Bootstrap 的方法來確定中介效應的顯著性。結果顯示,控制了性別和年齡后,睡眠拖延(β=0.25,p<0.001)對日間嗜睡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失眠的中介效應為0.16,95%置信區間為[0.14, 0.18](見表3),置信區間不包含0,說明失眠的中介效應顯著,占總效應的64%。

表 3 中介作用檢驗
3.5 睡眠時型對失眠中介效應的調節效應分析
采用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7進行有調節的中介效應檢驗,其中自變量為睡眠拖延,因變量為日間嗜睡,失眠為中介變量,調節變量為睡眠時型(根據量表劃分標準將被試分為清晨型、夜晚型和中間型三組,并進行虛擬編碼),性別和年齡為控制變量。檢驗中使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方法來確定調節效應的顯著性。結果顯示,睡眠拖延能顯著正向預測日間嗜睡(β=0.09,p<0.001, 95%CI[0.06, 0.12]),失眠對日間嗜睡的預測作用顯著(β=0.38,p<0.001, 95%CI[0.35, 0.41])。睡眠拖延對夜晚型(βsimple=0.50,p<0.001, 95%CI[0.40,0.62])、清晨型(βsimple=0.29,p<0.001, 95%CI[0.24,0.35])及中間型大學生(βsimple=0.42,p<0.001,95%CI[0.39, 0.46])失眠的預測作用均顯著。簡單斜率差異分析結果表明,相對于清晨型大學生,睡眠拖延對夜晚型大學生失眠的預測作用更為明顯(β斜率差=0.21,t=3.63,p<0.01, 95%CI[0.09,0.34]),相較于中間型,睡眠拖延對清晨型大學生失眠的預測作用相對較弱(β斜率差=0.13,t=3.81,p<0.001, 95%CI[0.06, 0.20]),睡眠拖延對夜晚型和中間型大學生失眠的預測作用差異不顯著(β斜率差=0.08,t=1.37,p=0.168, 95%CI[-0.20, 0.03])。圖1所示為睡眠時型在睡眠拖延與失眠之間的調節作用。

圖 1 睡眠時型在睡眠拖延和失眠之間的調節作用
4 討論
4.1 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的關系
正如本研究預期,大學生睡眠拖延能顯著正向預測日間嗜睡,個體的睡眠拖延行為越嚴重,其日間嗜睡水平越高。睡眠拖延的一個典型表現就是習慣性地推遲就寢時間,這樣一來就會使得個體的睡眠時間減少,出現睡眠不足或質量變差等問題(Kroese et al., 2016; Zhang & Wu, 2020)。而個體夜間的睡眠狀況與其日間活動狀態又息息相關(Atoui et al., 2021; Scott et al., 2021),其中睡眠不足、睡眠質量下降都會導致日間嗜睡明顯增多(Isac & Abraham, 2020)。此外,個體進入大學階段后,時間上較為寬松自由,對于尚缺乏成年人自控能力的大學生來說,睡前很容易因沉浸在刷手機、玩電子游戲、社交軟件等活動中而無法自拔,導致睡覺時間延遲,睡眠時長大大縮短(武欣然等, 2020),而因夜間未能得到充分休息其白天的精神狀態會受到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譬如警覺性變差,嗜睡明顯、易疲倦等(Exelmans &van den Bulck, 2017)。由此,本研究結果表明,睡眠拖延等不良的睡眠行為習慣對于大學生的日間嗜睡水平存在著顯著影響,生活中應積極引導大學生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減少睡眠拖延行為,提升睡眠質量,以保障其日常活動順利進行。
4.2 失眠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發現,睡眠拖延行為對失眠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研究結果基本一致(Hairston & Shpitalni, 2016)。進一步的中介作用檢驗表明,失眠在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的關系中起中介作用。睡眠的雙過程調控理論認為,良好的睡眠是機體晝夜節律和睡眠內驅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按時就寢對于維持穩定的睡眠-覺醒節律至關重要,一旦睡眠節律出現紊亂(如睡醒時間不斷提前或推遲)則極易造成入睡困難、失眠等睡眠障礙(Dijk & Lockley, 2002)。就睡眠拖延者而言,習慣性地推遲睡覺時間不但會縮短睡眠時長,還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睡眠節律紊亂的風險,由此導致失眠的幾率也大大增加(Kadzikowska-Wrzosek, 2018; Nauts et al., 2019)。此外,有研究指出睡眠拖延在很大程度上是個體自我調節失敗的結果,人們并不是不愿意上床睡覺,而是因為不愿意放棄其他具有更高吸引力的活動,一再推遲睡覺時間(Exelmans & van den Bulck, 2017; Kroese et al., 2016)。自我調控與反芻思維以及不合理信念又存在著密切關聯,即自我控制力差的個體對未來的控制感也偏差,從而無法有效抑制不合理的信念,反芻思維隨之增加(Heatherton & Wagner,2011)。由此推測,那些習慣性拖延就寢時間的人很可能存在較多的反芻思維和不良的睡眠信念,在未能按時入睡的情況下,這些反芻思維和不良信念不斷發酵,從而誘發失眠,這也符合失眠的認知加工模型的觀點(Harvey, 2002)。而失眠又會大大降低個體的主觀警覺性、增加日間嗜睡以及疲憊感(Chan et al., 2020; Zhang et al., 2022)。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結果說明大學生的睡眠拖延行為不僅是失眠的一個重要危險因素,還能夠通過失眠對其日間嗜睡水平產生顯著影響。
4.3 睡眠時型的調節作用
本研究發現大學生睡眠拖延行為對失眠的影響受到睡眠時型的調節,相對于清晨型的大學生,睡眠拖延對夜晚型大學生失眠的正向預測作用更強,與本研究假設相一致。這一結果表明夜晚型睡眠在一定程度上會加劇睡眠拖延對大學生失眠的負性影響。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與清晨型相比,夜晚型群體因睡眠時相明顯后移使其內在的生物時鐘與外在的晝夜變化不相匹配,易造成睡眠-覺醒節律的紊亂,進而產生失眠、入睡困難等睡眠問題(H?ller et al., 2021)。另外夜晚型個體的生物時型決定了其晚睡晚起的睡眠偏好,然而迫于社會環境的要求,多數情況下不得不早睡早起,但早睡會違背其自身的生物節律而變得難以實施,故夜晚型個體更容易出現睡眠拖延行為(Kadzikowska-Wrzosek, 2018; Kühnel et al., 2018),而睡眠拖延越嚴重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加劇其睡眠節律紊亂,誘發失眠。另一方面,夜晚型因自身的睡醒時間與外在的社會要求不一致,為減少這種社會時差對其日間工作生活的影響,夜晚型人需不斷地進行自我調節,因而會消耗更多的自我調控資源(Roenneberg et al., 2012),白天自控資源的大量消耗使個體晚上面對分心刺激或誘惑時往往難以抵擋,導致就寢時間不斷延遲,從而增大失眠的風險(Kamphorst et al., 2018)。該研究結果啟示在倡導大學生規律就寢的同時,更要關注夜晚型睡眠拖延的群體,必要時可采取一些干預措施,如自我調控和未來時間洞察力訓練等來預防和降低睡眠拖延對其夜間睡眠狀況和日間狀態的消極影響(Feng et al., 2022)。
4.4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考察了睡眠拖延對大學生日間嗜睡的影響,并探討了失眠的中介作用及睡眠時型的調節作用。本研究結果對于系統了解拖延行為與個體日間嗜睡的關系及其作用機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同時也能夠為日后開展預防和干預大學生失眠及嗜睡的本土化研究提供更為全面科學的指導依據。不過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本研究采用的是橫斷設計,無法準確推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且睡眠問題與情緒存在一定關聯,但本研究未對情緒方面因素進行有效控制,未來研究可在控制被試情緒的基礎上采取縱向設計或實驗研究對本研究結果進一步驗證。其次,睡眠拖延并不是導致大學生日間嗜睡的唯一風險因素,后續研究可綜合考慮諸如個體的身心狀態、學業壓力、周圍環境等多種因素對日間嗜睡的影響,從而更加清晰地闡釋大學生日間嗜睡的形成及發展機制。最后,在未來研究中,研究者可以通過干預訓練,例如培養大學生的時間管理和自控能力、養成良好的睡眠習慣等以減輕拖延晚睡等危險因素對其夜間睡眠和白天嗜睡的影響。
5 結論
(1)睡眠拖延對大學生日間嗜睡具有直接預測作用,睡眠拖延行為越嚴重,日間嗜睡水平越高;(2)失眠在睡眠拖延與日間嗜睡之間起中介作用;(3)睡眠拖延對失眠的影響受到睡眠時型的調節,相對于清晨型大學生,睡眠拖延對夜晚型大學生失眠的影響更為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