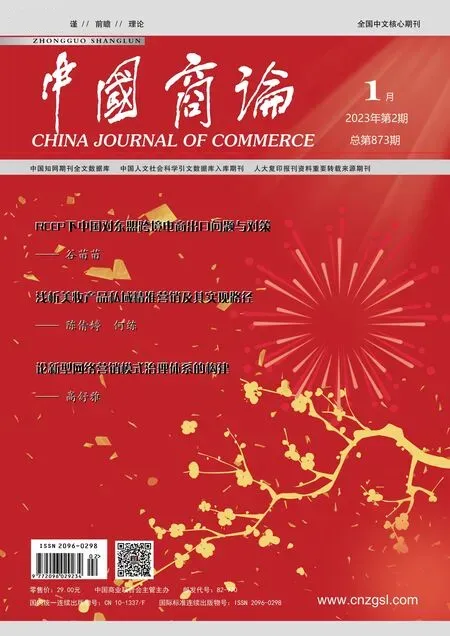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鐵網絡優化對區域可達性與經濟聯系格局的影響
藺茹 高鑫(通訊作者) 孫成彬
(重慶師范大學地理與旅游學院 重慶 401331)
區域發展與交通運輸的關系研究一直都是地理學中的熱門研究話題,可達性[1]作為衡量交通系統便利程度的重要參考依據,被廣泛運用于各項交通運輸與區域發展的研究中[2-5]。我國高鐵網絡的全面建設讓城市節點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對于加強區域間經濟協調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2009年7月,達成鐵路復線完工,正式形成成渝快速通道;2014年,渝利鐵路與成綿樂城際鐵路營運;2015年成渝高鐵開通,成渝地區高鐵逐步成網,但在環境及資料條件的約束下,成渝地區產業轉型升級壓力十分明顯。如何更好地進行高速鐵路規劃及制定相關產業經濟發展政策尤為重要。
在一系列國家政策的引導下,202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明確提出推進構建全國一體化和區域一體化現代城市交通運輸與基礎設施體系,有序高效地實施推進重慶、成都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6]。
綜上所述,本文選取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為研究對象,以市(區)作為研究單元,比較高鐵建設規劃前后兩種情況下,包括交通可達性、經濟潛力等指標的一系列變化,分析高鐵網絡優化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可達性的作用,并進一步研究可達性變化對城市經濟聯系空間格局的影響。
1 數據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本文的研究對象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四川省包括成都、宜賓等,其中達州萬源市、綿陽北川縣、平武縣、雅安寶興縣、天全縣除外;重慶市包括主城區、璧山、銅梁等。總面積大約為18.5km2,2019年常住人口9600萬,GDP近6.3萬億元。本文將研究單元劃分為市(區),將地級市范圍內的市轄區合并為一個研究單元(如將南充市的順慶區、高坪區、嘉陵區、西充縣、南部縣、蓬安縣、營山縣、儀隴縣合并為南充市區),由于成都市區及重慶主城區的情況特殊,將成都市區(市轄區、縣級市)、重慶主城區(渝中區、九龍坡區、渝北區、巴南區、南岸區、北碚區、江北區、沙坪壩區、大渡口區)合并,合并后共劃分出36個研究單元。
1.2 數據來源與處理
2021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故選取2021年作為高鐵規劃前的時間截面,交通網絡數據通過百度地圖數據源獲取,通過人工數字化得到,規劃高鐵數據來源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本文以成渝地區所轄市(區)進行數據的收集分析及處理,將行政中心預設為城市的空間節點,分別對規劃前(2021年)數據與規劃后(2035年)時間截面數據進行整理與對比分析研究,經濟數據取自重慶市統計局(cq.gov.cn)與四川省統計局(sc.gov.cn)。
1.3 研究方法
1.3.1 交通可達性
(1)加權平均旅行時間。加權平均旅行時間指的是從某一城市到研究區指定城市所花費最短出行時間的均值水平,也表示城市間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及影響的難易程度。指標值越小,表示該城市節點的可達性條件越好,與其他城市節點的相互關聯程度越高;反之越差[7]。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Tij為節點i到域內節點j的最短旅行時間距離;Mj為節點j的權重,用城市的經濟規模Gj與人口規模Pj計算。本文采用地級市的國內生產總值為權重;n為交通網絡中選定的除點以外的節點總數;Ai為節點i的加權最短旅行時間,表示i點在交通網絡中的可達性水平。
(2)經濟潛力。經濟潛力指的是某個城市以克服時間為前提所能達到的經濟活動的數量,能夠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輻射能力及接收能力,能夠衡量城市節點的可達性水平[8]。計算公式如下:

式中,Pi為節點i的經濟潛力。Pi值越大,表明該節點城市i受到其他城市經濟輻射能力越強;反之越弱。?是城市節點i與城市節點j之間的摩擦系數,取值為1。
1.3.2 未來經濟指數預測
ARIMA模型是將非平穩時間序列向平穩轉化,將隨機誤差項現值和滯后值及因變量的滯后值進行回歸建立的模型[9],數學描述為:

式中,Δdyt表示yt經過d次差分轉換之后的序列;εt是t時刻的隨機誤差,是相互獨立的白噪聲序列,滿足均值為0,方差量為σ2的正態分布,φi(i=1,2 ...,p)和pi(i=1,2,…,p)模型的待估參數,p和q為模型的階。先進行序列平穩化處理,再通過自相關系數與偏自相關系數確定模型參數,通過檢驗后,進行模型預測。
1.3.3 區域經濟聯系分析
引力模型是衡量城市間經濟聯系程度的常用方法,為深入探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鐵建設引起的可達性水平變化對區域內城市間經濟聯系空間格局的作用,本文利用引力模型計算城市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10],公式如下:

式中,L ij是指城市i與城市j之間的經濟聯系強度;L i表示城市i對外經濟聯系總量;M表示城市社會經濟規模;Tij為兩城市間的最短出行時間。
2 結果分析
2.1 加權平均旅行時間的分析
2.1.1 規劃前后加權平均旅行時間分析
規劃前,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平均旅行時間空間格局呈現出以成都市區和重慶主城區為兩大增長極的“核心-外圍”分布趨勢,從中心向外圍可達性逐漸降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可達性水平與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經濟發展水平特點及空間區位大體一致。由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發展特點及高鐵建設時間節點與規模不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中部各地區可達性水平比南北地區較高,呈現出的態勢與其產業發展和經濟水平大致相同,交通設施的完善程度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外資投資的聚集程度,南北區域發展模式的差異主要是由外向型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導致。
由分析得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由于規劃高鐵的建設與完善,東西部地區水平更加趨于平衡,未來高速公路很大一部分運輸職能將由高速鐵路代替,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加入全國生產網絡的步伐由此加快。為降低未來民營經濟產業的沖擊,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建設重點應向綜合生產性服務職能轉變,加快產業優化發展(見圖1)。

圖1 規劃前后成渝雙城經濟圈可達性空間格局
2.1.2 規劃前后區域空間可達性的變化情況
由分析得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可達性變化呈現以下特點:
(1)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可達性水平整體提升。區域平均加權平均旅行時間由規劃前的2.70降低為規劃后的2.11,平均變化率23.49%,在交通網絡體系不斷優化發展下,交通網絡整體性得到了極大改善。
(2)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可達性水平區域較為均衡。該區域所選擇的36個研究單元的加權平均旅行時間標準偏差由0.40降低為規劃后的0.33,顯示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空間格局由于高速鐵路的普及而趨于均衡。
(3)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的城市可達性變化率呈現出較為明顯的地區差異。南川、雅安等地高鐵規劃及建設涉及較少,可達性變化小,處于區域平均變化率之下(見表1)。

表1 規劃前后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各市加權平均旅行時間計算結果
2.2 經濟潛力分析
(1)高鐵規劃修建沿線區域的經濟潛力優勢隨著線路不斷擴大,外圍城市及中心城市的聯系隨著“時空收斂”效應而強化,規劃前成都市區及重慶主城區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潛力優勢區,兩大增長極間顯現出中部塌陷現象。
(2)經濟潛力指數的提高與高速鐵路的規劃修建相聯系,雖然經濟潛力有所提高,但仍顯現出一定程度的區域差異。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潛力指數總值由規劃前的44782.53提高至規劃后的60325.03,變化率為34.7%,變化顯著。成都市區、重慶主城區及萬州等地變化較大,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中所涉及的規劃線路,成渝中線高鐵、重慶至宜昌高速鐵路,大多由成都市區與重慶主城區引出,重慶至西安高速鐵路接入萬州北站,萬州可達性及經濟潛力隨著高鐵規劃得到顯著提升,城市區群內部競爭力得到加強(見圖2)。

圖2 高鐵規劃前后經濟潛力指數變化
2.3 高鐵影響下的經濟聯系格局演化
通過式(4)計算得出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規劃前后各城市節點的經濟聯系強度,由式(5)計算各城市節點的經濟聯系總量,經Arcgis 10.7 可視化處理后,如圖3所示。

圖3 高鐵規劃前后經濟聯系強度變化
(1)經濟聯系總量大幅提高,各城市對外經濟聯系總量隨著巨大的空間效應而增加。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聯系強度平均值由493(1億元 *1萬人/1min2)增長至1038,增長了約2倍,由于極化效應的產生,邊緣城市與中心城市差距擴大。重慶主城區經濟聯系總量位于前列,由1969升至3576,增幅為81.6%。
(2)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經濟聯系總量與可達性水平空間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總量較大的成都市區、重慶主城區在空間格局上與可達性同樣表現出顯著的“核心-外圍”分布態勢,城市距離衰減作用隨著高鐵的規劃建設而 縮短。
3 結語
本文結合交通可達性及引力模型,探求了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高速鐵路規劃前后可達性及經濟聯系強度格局的變化,主要結論如下:
(1)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交通可達性水平由于高鐵的規劃建設得到明顯提升,各城市加權最短平均旅行時間縮短,渝東北地區尤為顯著。高鐵規劃建設沿線地區優勢明顯,可達性水平較高。
(2)一定程度上,可達性水平的提升減弱了距離衰減作用帶來的影響,高鐵建設規劃有助于提升中心城市及次級中心城市對其他城市的經濟輻射帶動作用,高鐵沿線城市經濟潛力提升作用較強,由中心向外圈逐漸遞減。優化資源配置,提高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綜合競爭力及對外輻射能力,加速規模經濟的形成,加強成渝地區的一體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