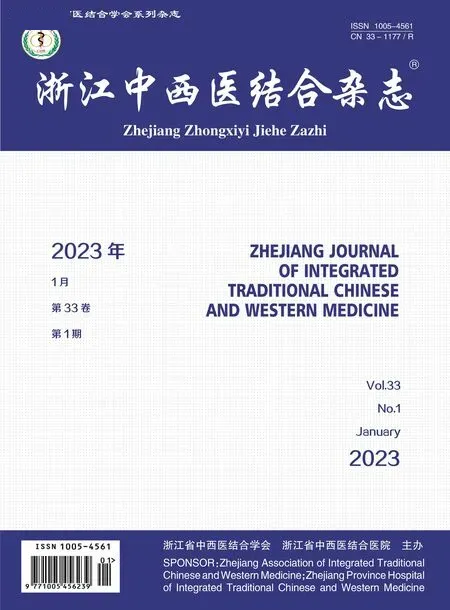孕產婦急性肺栓塞五例并文獻復習
姚鋮聰 王婷婷 李和江
栓塞(不包括羊水栓塞)是孕產婦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其中肺栓塞的常見類型為肺血栓栓塞癥(pulmonary thromboembolism,PTE),多發于深靜脈血栓形成(deep venous throm-bosis,DVT)后,深靜脈血栓脫落可堵塞肺血管,可引起血流動力學不穩定甚至猝死[2-3],改善預后的關鍵在于及時發現、救治。但肺栓塞發病突然,臨床表現復雜、體征多不典型,給臨床早期診治增加了困難。本文收集于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的5 例孕產婦急性肺栓塞患者的臨床資料進行回顧性分析并文獻復習,為孕產婦急性肺栓塞的早期發現、及時救治提供參考意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2018 年1 月至2022 年5 月在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住院治療的孕產婦急性肺栓塞5 例,患者年齡28~41 歲,初產婦4例,經產婦 1 例。肺栓塞發生時間:孕期3 例,產后2 例(均為剖宮產術后)。患者既往均無血栓相關病史,否認家族血栓病史。見表1。

表1 5 例急性肺栓塞孕產婦基本情況
1.2 臨床表現與診斷 5 例中早發臨床表現為胸悶2 例;表現為胸痛2 例;表現為血氧飽和度降低并在48 h 后出現頭頂部疼痛、四肢抽搐、意識喪失癥狀1例。5 例患者血D-二聚體變化差異大,均通過CT 肺動脈造影確診肺栓塞。見表2-3,圖1-2。

圖1 5 例急性肺栓塞孕產婦D-二聚體(μg/L)變化情況
1.3 治療與預后(1)抗凝治療:5 例患者確診后即用肝素抗凝治療,患者1、2 的肺栓塞發生在妊娠晚期階段,患者1 明確診斷后立即行剖宮產終止妊娠,術后12 h 開始抗凝治療;患者2 因“肺動脈高壓”行剖宮產終止妊娠,術后明確肺栓塞,術后12 h 開始抗凝治療。患者1、2 均首先使用微泵靜脈輸入普通肝素使血液快速肝素化,在重癥監護室監測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時間(activated partial thromboplastin stine,APTT),動態調整普通肝素用量以維持目標在正常1.5~2.5 倍,在病情穩定轉入普通病房后改用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12 h1 次;其余3 例患者入院時為剖宮產術后或孕早期患者,予病房內低分子肝素皮下注射,12 h1 次。出院后5 例患者均繼續規范抗凝,定期血管外科門診隨訪。(2)其他治療:患者1 因入院時查雙下肢靜脈血流淤滯,再發栓塞風險高,于剖宮產終止妊娠前行經皮下腔靜脈濾器(inferior vena cava filter,IVCF)置入術。(3)預后:5 例患者整體預后良好,無孕產婦及圍產兒死亡;患者2 母體心功能輕度受損,新生兒預后良好;患者3 因肺栓塞發生于孕早期,行醫療性流產結束妊娠。典型病例見圖3-4。

圖3 患者2 確認肺栓塞CT 肺動脈造影影像,箭頭標注低密度充盈缺損處即為栓塞的肺動脈
2 討論
2.1 孕產婦肺栓塞的癥狀及體征 急性肺栓塞中肺血管阻塞引起血流動力學不穩定、氣體交換障礙、機體缺氧,呼吸系統與循環系統互為因果,最終導致心肺功能障礙[4],臨床上則可表現為“胸痛、咯血、呼吸困難”典型三聯征癥狀,除此之外還可有胸悶、暈厥、心悸、咳嗽、發熱等多種不典型癥狀。在本文敘述的5例病例中,2 例患者的早發臨床表現為胸悶,2 例為胸痛,1 例為血氧飽和度降低并在48 h 后出現頭頂部疼痛、四肢抽搐、意識喪失的癥狀,均未表現出典型的三聯征癥狀。肺栓塞臨床表現復雜多樣,而孕產婦因子宮不斷增大導致橫膈上移、循環血量增加等原因同樣會出現胸悶、呼吸困難、心悸等癥狀,因此在并發肺栓塞時更易出現誤診、漏診或診斷不及時的情況。研究表明,未經治療的肺栓塞死亡率可達30%~35%,診斷明確并經過充分治療的患者,死亡率可降低至2%~8%[5],因此改善急性肺栓塞預后的關鍵在于早期診斷、及時治療。產科醫生需提高對急性肺栓塞的警惕性,不僅要對出現典型三聯征的孕產婦進行診斷,同時要重視各種不典型臨床表現,如一旦發現不明原因的胸痛、胸悶、氣促、血氧飽和度降低等癥狀,應立即進一步完善檢查,排除肺栓塞。

圖2 急性肺栓塞孕產婦1、2 BNP(pg/mL)變化情況注:BNP 為N 端B 型利鈉肽前體

表3 5 例急性肺栓塞孕產婦輔助檢查-影像學檢查

圖4 患者2 治療后1 個月余復查CT 肺動脈造影影像,箭頭標注同一部位充盈缺損面積較圖3 明顯減少

表4 5 例急性肺栓塞孕產婦治療與預后情況
2.2 孕產婦肺栓塞的診斷 對于孕產婦急性肺栓塞的診斷,我國《肺血栓栓塞癥診治與預防指南》(以下簡稱《指南》)、美國婦產科醫師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Obstetricians and Gynecologists,ACOG)等均認為“金標準”是肺動脈造影(pulmonary arteriography,PAA)[6-7],但是PAA 存在操作復雜、費用較高等缺點,而效果相似的CT 肺動脈造影(computed tomographic pulmonary angiography,CTPA)因其方便、快捷、準確性高,現已成為臨床上確診孕產婦急性肺栓塞的主要手段[8]。CTPA 是進行肺動脈掃描的一種檢查手段,影像學上可直觀地觀察到充盈缺損的血管,提示血管栓塞狀態。有研究表明,在肺栓塞診斷中,CTPA 總體敏感度為83%,特異度為96%[9]。本文5例患者均在行CTPA 后明確肺栓塞診斷。其余的影像學檢查也可有一定的提示[4],例如肺栓塞導致的心功能障礙可在心臟超聲中有陽性結果,肺栓塞同時存在雙下肢深靜脈血栓可通過血管超聲診斷,但這些輔助檢查均沒有統一性。本文中的患者1~4 心臟超聲檢查表現各異,而雙下肢超聲僅患者1 在術前有血流淤滯改變,可見心臟超聲、雙下肢血管超聲等影像學檢查不能作為明確診斷的手段。在CTPA 的安全性方面,目前研究認為胎兒可接受的放射性安全閾值為50 mSv,行CTPA 檢查時胎兒的射線接受劑量為0.03~0.66 mGy[10],遠低于該閾值,在本文的5例患者中,患者2、4、5 在接受CTPA 檢查時已終止妊娠,患者3 因處于妊娠早期行醫療性流產,僅患者1 在妊娠期間接受了CTPA 檢查,隨訪中并未發現新生兒出現射線相關的畸形。因此,臨床醫生對于高度懷疑肺栓塞的孕產婦在綜合評估后應積極行CTPA檢查以明確診斷。
D-二聚體數值升高說明體內存在高凝狀態,其作為急性肺栓塞陰性排除診斷指標廣泛應用于早期篩查中[11]。但研究表明,孕產婦血液中凝血因子、纖維蛋白原以及纖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劑水平的升高可使血液處于高凝狀態[12],D-二聚體均高于正常水平。因此,小于500 μg/L[6]這個參考閾值對于孕產婦并不適用,而在現階段的多項研究中,針對孕產婦的D-二聚體參考數值并未能達成共識[13]。本組5 例患者住院期間D-二聚體值整體波動范圍為2960~21870 μg/L,差異巨大;觀察患者1、2 完整診治過程中的D-二聚體變化可見,在肺栓塞急性發生時,D-二聚體未到達最高水平,2 例患者均在抗凝治療后24 h 到達最高點,存在一定滯后性。值得注意的是,1、2、3、5 這4例患者的D-二聚體水平隨著治療的推進均進行性下降。可見D-二聚體在孕產婦肺栓塞診斷中的作用和具體參考數值需要進一步研究明確。
2.3 孕產婦肺栓塞的治療 根據我國妊娠期及產褥期靜脈血栓栓塞癥預防和診治專家共識,妊娠期及產褥期靜脈血栓栓塞癥(包括肺栓塞)的治療措施主要包括:抗凝治療、IVCF、溶栓治療等[10]。(1)抗凝治療[6,11]:妊娠期間抗凝藥物應首選低分子肝素,分娩前12 h 停用,剖宮產后12 h 或陰道分娩后6 h 可重新開始使用。靜脈注射普通肝素需要在密切監測APTT值下進行,臨床上使用相對受限。產后可用華法林或利伐沙班口服治療。華法林與利伐沙班同為產后常用的兩種口服抗凝藥物,有學者認為相較于華法林,利伐沙班的抗凝作用預測性好,治療窗寬,出血風險較低,實際臨床應用中臨床醫生可根據患者具體情況選擇用藥,但都應警惕用藥后的出血風險[14]。產婦并發肺栓塞抗凝療程至少3 個月,產后抗凝治療至少6 周。本文中的5 例患者均在確診后進行了規范抗凝治療;(2)IVCF:由于PTE 多繼發于DVT 后,對于再次栓塞風險高的患者可在剖宮產術前臨時放置下腔靜脈濾器,于術后取出[15]。但孕產婦IVCF 的相關研究較少,不作為常規治療手段,需權衡利弊后慎重決定。本文中患者1 在急性肺栓塞發生時行下肢血管超聲見血流淤滯,患者再發栓塞風險高,經血管外科專科評估后于剖宮產術前行IVCF 置入術,剖宮產術后取取出,抗凝治療同樣遵循前文所述規范治療方案,與其余4 例患者無原則上差異;(3)溶栓治療:溶栓治療對于孕婦而言出血風險高,僅適用于那些存在危及生命的急性PTE 的妊娠患者(即PTE 導致的持續和嚴重低血壓、休克)[10],本文中5 例患者均未出現上述情況,未曾行溶栓治療。
總之,血液高凝、靜脈血流淤滯、血管壁損傷三大危險因素(即Virchow 三聯征)貫穿于妊娠的任何階段,妊娠期及產褥期女性PTE 的發病率是非妊娠期女性的4~5 倍[16]。但孕產婦的特殊生理變化使得急性肺栓塞的臨床表現較一般肺栓塞患者更難鑒別、診斷,臨床上應積極行CTPA 替代PAA 明確診斷。D-二聚體作為陰性排除診斷指標在孕產婦群體中具有特殊性,臨床醫生應更重視其治療后的變化趨勢,可將其作為肺栓塞抗凝治療的療效評價指標。孕產婦急性肺栓塞一旦明確診斷,應立即規范治療,降低死亡率。產科醫生作為孕產婦的臨床第一接觸人,應提高對孕產婦急性肺栓塞的認知,對高危患者予預防性治療(如梯度加壓彈力襪等),力爭做到早預防、早發現、早診斷及早治療,提高生存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