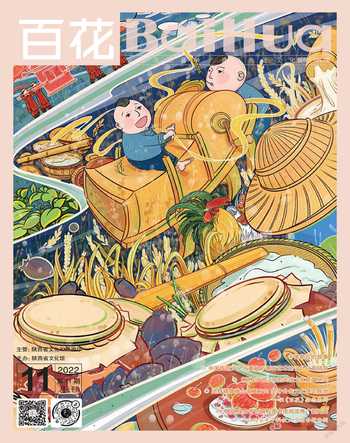《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意蘊研究
王娟

摘 要:《朝花夕拾》中有不少關于民俗文化的描寫,其中不乏淳樸而又自然的民俗文化,但也有一些地方陋俗。文章主要對《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現象、民俗文化事物、民俗文化精神寄托進行分析,探討其中的民俗文化意蘊。對《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意蘊進行分析,可以體現《朝花夕拾》特有的文學價值。隨后,本文闡述了魯迅先生透過《朝花夕拾》所要表達的民俗文化立場,即以辯證的態度看待民俗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推進民俗文化創新發展。
關鍵詞:《朝花夕拾》;民俗文化;文化意蘊
《朝花夕拾》中有魯迅先生對童年、少年以及青年時光的回憶,但這篇散文集并不只是簡單的“回憶文”,文章所描繪的特色民俗,例如日常民俗生活、民間禁忌和民間信仰、婚喪嫁娶等習俗,既有剛烈、悲涼的情感基調,又不乏幽默、詼諧的氣氛,這些故事片段為《朝花夕拾》平添了民俗文化意蘊,豐富了散文集的藝術價值。這些民俗文化,充分體現了魯迅先生濃濃的思鄉情結和對淳樸優秀民俗文化的贊譽。同時,也體現了魯迅先生對部分地方民俗陋習的批判。在《朝花夕拾》中,魯迅先生以溫馨的回憶和理性的批判來描述民俗文化,無論是贊美還是批判,核心思想始終在于重建、再造和復興地方民俗文化。
一、《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意蘊分析
(一)《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現象
《朝花夕拾》將民俗文化與日常生活緊密聯系在一起,對處于社會最底層的人和事進行了回憶,而其中較為鮮明的民俗文化現象,就包括紹興目連戲和花紙。
魯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多次描寫到紹興目連戲,例如《五猖會》《無常》中均有涉及童年時期觀看紹興目連戲的回憶。在散文中,魯迅先生并沒有將筆墨側重于目連戲文的內容,而是向讀者展現童年魯迅對觀看目連戲這一民俗活動的溫情回憶,同時,也描述出當時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民眾參與紹興目連戲這類特色民俗活動時愉快、溫馨的場景。紹興目連戲本身的戲文內容存在一些封建迷信思想,例如,目連的母親在作惡太多后被處以打入地獄的懲罰,而目連以積極反抗的態度,歷經艱險只為解救母親不再遭受地獄的磨難。這種帶有鬼神性質的民間戲與當時的封建鬼神信仰相契合,但目連戲中蘊含的勇于反抗的精神是值得宣揚的。魯迅先生以童真、童趣的筆觸來描寫自己對目連戲的喜愛,其實也體現了當時社會底層民眾奮起反抗以及堅韌不拔的生命意識給魯迅先生帶來的震撼。《朝花夕拾》借助紹興目連戲這一民俗文化現象向人們傳遞著努力執著、不畏艱險的抗爭精神。
在《朝花夕拾》中,民間花紙體現了具有溫情、童趣的民俗文化。《狗·貓·鼠》中就描寫了魯迅童年時期床前貼著的“八戒招贅”“老鼠成親”等花紙,這些民間花紙為他的童年增添了不少樂趣。而魯迅先生對“老鼠成親”花紙的濃厚興趣,則源于花紙上的老鼠歡快娶親的熱鬧場景。魯迅對民間花紙,尤其是“老鼠娶親”的喜愛,不僅是對傳統民俗文化的贊美,還蘊含著社會民眾的淳樸民風和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祝愿。
(二)《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事物
《朝花夕拾》提及了多個民俗文化事物,例如鬼、傳說故事等。這里主要從“鬼”這一民俗文化事物進行分析。《朝花夕拾》中,魯迅先生描寫了“鬼故事”“鬼世界”等。在魯迅先生的故鄉紹興,在祭祀等民俗活動中都蘊含著“巫鬼文化”,雖然社會文明發展進程不斷加快,但鬼神觀念依然深深地滲透在民俗文化當中。
《父親的病》中寫到了父親的生命將要走向尾聲,衍太太燒《高王經》并用紙將灰包起來,然后要父親將灰包攥在手里,同時,衍太太還要“我”大聲喊“父親”。在紹興當地有這樣一種說法,把將死之人的紙錠、《高王經》灰用紙包起來,可以減輕此人進入地獄后的苦痛。而《父親的病》中的“我”按照這一當地民俗執行之后,即便父親過世很多年,依然對此深感愧疚。這也體現了魯迅先生對盲目、荒誕的“鬼文化”的批判。《父親的病》中的“鬼文化”是一種病態丑惡的民俗文化,魯迅先生對這種封建陋習充滿厭憎。
《朝花夕拾》中的《阿長和山海經》也描寫了“鬼”,但從寫作基調來看,《阿長和山海經》中的“鬼”顯然更富有溫情的意蘊。童年時期的魯迅對長媽媽講的“美女蛇”的鬼故事是非常喜愛的,那時候的魯迅更是將長媽媽買的《山海經》視作珍寶。在《山海經》這本書中,魯迅看到的是一個奇幻的鬼世界,也正是因為長媽媽講述的具有趣味化、人情化的鬼故事,魯迅感受到了具有積極意味的“鬼文化”,這里的鬼是正直、純良、個性有趣的。
此外,《朝花夕拾》的《無常》也描述了一個非常具有特色和內在意蘊的民俗事物。在《無常》中,較為詳細地描寫了目連戲、迎神賽會中的“無常”形象。在紹興當地的民俗文化中,“無常”并不是陰郁、恐怖的,而是“是鬼更似人”(即外表是鬼,但內在性格卻與人接近),“明理更講情”(即按規章、道理辦事,追求真理,正義感十足,同時也很講情義,賞罰分明),“可怖而可愛”(即有著恐怖的鬼形象,但實際卻不會讓人感到恐懼,反倒有幾分可愛的意味)。在迎神賽會上寫到的無常,僅以動作就讓人看到了生動又令人感到歡樂的無常形象。而在目連戲中,無常的形象更是幽默、搞笑并且有情有義、富有正義感。這里的“鬼”的形象其實也體現了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的人生百態,以及他們對生命、靈魂的認識,更體現了人們在面對剝削和壓迫時,內心深處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魯迅先生對“無常”這一民俗事物的描寫,充分體現了魯迅崇尚公平、正義的價值觀。
(三)《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精神寄托
民間信仰是處于社會底層的民眾精神世界中的重要部分,魯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以辯證的態度看待民間信仰,他認為社會底層民眾的信仰可能會受到封建思想的影響,帶有理想色彩。但站在廣大社會底層群眾的角度而言,民間信仰也體現了人們內心深處的最為樸素的精神追求。《朝花夕拾》透過民間信仰向讀者傳遞出的,是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底層民眾有正當的生存愿望和合理的精神寄托,這種精神寄托與人們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朝花夕拾》在民俗文化的精神寄托中,飽含對現實力量的反抗。《五猖會》與《無常》中的民間信仰是富有特色的。迎神賽會上,捧飯碗“送無常”的場景蘊含著樸實而又濃厚的生活氣息,無常去勾魂時做出“還陽半刻”的決定,也彰顯著“鬼”的“人情味”,對無常的動作、言辭、衣著等方面的描寫,更體現了詼諧而又活潑的“鬼形象”。民俗文化中對“鬼”的闡述,蘊含了人們期盼從民間信仰中獲得力量與慰藉的情感。正因為如此,魯迅先生在《無常》中寫道:“但是,和無常開玩笑……因為他爽直,有人情。”這是魯迅先生對民間信仰這一民俗文化中所蘊含的公平正義等精神價值的認同。雖然《五猖會》《無常》中提及的民間信仰可能并不完善,其構建的精神世界也存在過于理想化的嫌疑,但《朝花夕拾》就是用這種方式來表達人們對民間信仰以及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向往。
《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精神寄托,還體現在魯迅先生對封建思想的厭惡與唾棄和對真、善、美的精神品質與健全人格的呼喚上。在《狗·貓·鼠》中,兒時的魯迅對花紙中具有童趣意味的老鼠娶親十分喜愛;《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叫天子、蟋蟀等,都是魯迅孩童時期最純真的意趣;在《阿長和山海經》中,長媽媽雖然愚昧迷信,但阿長講的鄉間傳聞和民俗規矩卻總是帶有溫暖的氣息。這些無不體現了《朝花夕拾》中對善良、真誠人性的呼喚。《五猖會》中,賽會是“我”期待已久的民俗活動,但在赴賽會前的清晨,“我”卻被“父親”要求背《鑒略》這本書,雖然這本被大家認為“非常有用”的書最終被我背下來了,大家為我感到高興,“父親”也允許“我”參加賽會,但“我”卻不再如赴會前那般興奮,甚至還感到五猖會沒有意思。《五猖會》中“父親”在“我”心情極好時突然要求“我”做他認為好的事,并要求“我”必須服從,否則不能參加賽會。魯迅先生認為,這種封建家長制壓迫了童趣,兒童的天性被壓抑和扼殺。因此,他在內心深處希望釋放人的天性。
二、《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立場
《朝花夕拾》中的民俗文化與魯迅的故鄉紹興當地的民間精神信仰和平民意識有著密切的關系,魯迅先生以《朝花夕拾》表達對社會底層平民的深切關注和擔憂,對人們的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更是傾注筆墨。《朝花夕拾》中,當地的民俗文化既蘊含著剛烈、悲涼的氣息,同時也有著輕快而又幽默的詼諧基調。《朝花夕拾》抨擊了封建思想和部分糟粕民俗,但也對底層社會民眾最為淳樸、自然的精神內涵表示認同。
《二十四孝圖》中,魯迅先生寫到了他反感老萊娛親、郭巨埋兒的民間故事,認為傳統倫理孝道中的糟粕思想是對兒童心靈的傷害,并且這種傷害帶有隱蔽性和永久性,不利于兒童健康人格的形成。因此,《朝花夕拾》以未明說的抗爭態度來對待民俗文化中落后、消極的內容,魯迅先生呼吁的是尊重生命,尊重人的人格健全發展。
《瑣記》中,學校將意外淹死兩名學生的池子填平后,造了關帝廟,并且每年中元節還要念咒,魯迅先生的字里行間是用略微調侃的語氣來描寫的,文中還寫道:“我的前輩同學……,就只在這時候得到一點好處,……做學生總得自己小心些。”這所學校面對管理缺口,卻以“建關帝廟”“請和尚念咒”這些方式來處理,學校的做法令人可悲,這也體現了魯迅先生對愚昧、荒誕的封建思想的諷刺與厭憎。
《朝花夕拾》中最具溫情意味的是《阿長與山海經》。長媽媽是典型的社會底層民眾,就連名字也用的是先前女工的名字,哪怕長媽媽去世多年后,“我”依然不知道她姓甚名誰。長媽媽的精神信仰與社會底層民眾長久以來的生活環境與風俗習慣相關,長媽媽也有著諸多不太好甚至可笑的缺點,比如睡相不好,總是對兒時的魯迅說很多不耐煩的規矩。但對于真誠、善良的長媽媽,《阿長與山海經》中描述的都是溫馨的回憶。長媽媽講的迷信守舊的“長毛故事”、美女蛇的故事,長媽媽在除夕時說新年要拿著福橘說吉利話,還有長媽媽做了“別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比如為小魯迅買來心心念念的《山海經》,言語間都包含幽默而又溫馨的基調。這也正是《朝花夕拾》對真誠、善良、淳樸民風的認同。
不難發現,《朝花夕拾》對民俗文化并不是一味地批判、諷刺,對于良俗,魯迅先生是贊美的。《朝花夕拾》中對民俗文化的描寫和闡述,既體現了魯迅先生對故鄉的熱愛,同時又體現了魯迅先生呼吁人們要建立健康、淳樸、真誠、善良等正面思想的精神家園。
三、結 語
民俗文化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是廣大民眾在生產、生活過程中形成的精神產物。一直以來,魯迅先生對待民俗文化的態度是辯證的。在社會發展過程中,要對至善和至美的民俗文化進行充分挖掘,要肯定民俗文化的精華并予以傳承,而對民俗文化中的糟粕,則應予以批判,并且還要探尋能夠有效促進社會文化進步和人類發展的民俗文化再造的路徑。在《朝花夕拾》中,魯迅先生將筆墨側重于優秀民俗文化,正是對重建、再造和復興民俗文化的呼喚。
(江西科技學院)
參考文獻
[1] 谷新.左翼作家的故鄉敘事:以蕭紅的《呼蘭河傳》與魯迅《朝花夕拾》為例[J].開封教育學院學報,2018,38(3):36-37.
[2] 張春茂.魯迅民俗觀論析[J].民俗研究,2017(6):95-101,159.
[3] 萬余.解讀魯迅筆下的無常[J].名作欣賞,2017(30):5-7.
[4] 賴秀俞.《五猖會》:重識民俗與文化尋根[J].江蘇教育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33(3):21-25,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