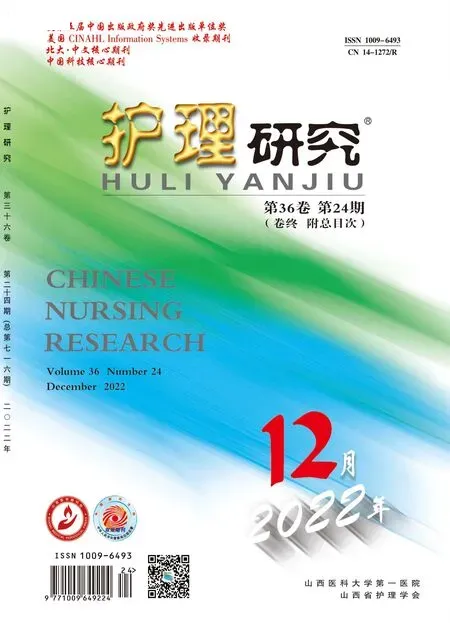基于Nomogram 模型建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壓力性損傷風險模型及護理策略
潘有蓉,王 水,張 倩
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江蘇 210000
國際癌癥研究機構2018 年調查顯示,乳腺癌居全球女性癌癥發生率首位[1]。手術是乳腺癌主要治療方式之一,術中壓力性損傷(pressure injury,PI)發生率較高[2-3]。壓力性損傷是指皮膚與深部軟組織的局部損傷,由強烈和(或)長時間的壓力或壓力聯合剪切力所致,表現為完整的皮膚或開放性潰瘍,伴有疼痛,一般位于骨隆突處,或與醫療器械等相關[4]。據統計,全球壓力性損傷的現患率為4.5%~32.86%[5]。美國每年罹患壓力性損傷病人達250萬例次,治療費用高達110億美元[6]。壓力性損傷不僅延長病人原發疾病康復時間和住院時間,還會加重病情,增加治療難度與感染風險,若感染擴散,可能會導致敗血癥、膿毒血癥及感染性休克發生,對其生命安全構成嚴重威脅[7]。因此,盡早識別壓力性損傷的誘發因素有重要意義。目前,關于手術獲得性壓力性損傷的研究大多數集中于影響因素等方面,缺乏量化預測相關風險的模型。Nomogram 圖是經過數學統計轉換成更為直觀的預測風險工具,在預測臨床結局事件中廣泛應用[8]。基于此,本研究建立乳腺癌根治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預警模型,旨在為臨床防治壓力性損傷工作提供一定的參考。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 年2 月—2022 年1 月我院乳腺科收治的856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作為研究對象,根據術中是否發生壓力性損傷分為壓力性損傷組和非壓力性損傷組。納入標準:①符合乳腺癌診斷標準[9];②經影像學和(或)實驗室檢查確診為乳腺癌;③年齡>18 歲;④行乳腺癌根治術治療。排除標準:①術前及術后出現壓力性損傷;②燒傷或急慢性皮膚病病人;③昏迷、癱瘓或長期臥床者;④TNM 分期>Ⅲ期;⑤依從性差或不接受隨訪者;⑥臨床資料不完整者。樣本量計算公式:n=Z2×[P×(1-P)/e2],其中n是樣本量,Z是統計量,P是概率值,e是誤差值。置信度為95%時,Z=1.96。當概率值為50%、容許誤差值為10%時,考慮存在數據有效性和數據缺失的現象發生,加上10%~15%樣本量,應至少納入106 例病人。
1.2 資料收集 參考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的文獻[10-11],通過醫院管理系統收集資料。一般資料包括年齡、體質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皮膚情況;合并基礎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腦血管疾病(心絞痛、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短暫腦缺血病等);手術情況包括術中體溫、體位移動、體外循環、麻醉方式、呼吸式、手術時間、術中出血量、暖風毯應用;實驗室指標包括血紅蛋白、血清清蛋白、血乳酸。
1.3 標本采集和檢測 手術前空腹抽取肘部靜脈血5 mL 并置于抗凝負壓管,檢測血常規等指標,血紅蛋白、血清清蛋白、血乳酸水平臨界值分別為90 g/L、35 g/L、1.6 mmol/L。
1.4 相關定義 壓力性損傷診斷標準: 參照最新版壓力性損傷定義與分期[12]標準評估。1 期:皮膚完整,局部紅斑,指壓不變白;2 期:部分皮層缺失,顯露真皮;3 期:全層皮膚缺失;4 期:全層皮膚和組織缺失;深部組織損傷:持續指壓不變白的紫色、褐紅色或深紅色的斑塊;不可分期:被掩蓋的全層皮膚和組織缺失。BMI 異 常:BMI>28.0 kg/m2或BMI<18.5 kg/m2;體溫異常:<36.0 ℃或>37.8 ℃。
1.5 統計學分析 采用SPSS 22.0 軟件進行統計學分析。定性資料采用χ2檢驗。采用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影響因素,以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采用R3.5.3 軟件包和RMS 程序包制作列線圖,采用RMS 程序包計算一致性指數(C-index),繪制校正曲線、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和決策曲線評估模型的預測效能。
2 結果
2.1 856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情況 856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48 例,發生率為5.61%。
2.2 兩組病人一般資料比較(見表1)

表1 壓力性損傷組與非壓力性損傷組病人一般資料比較 單位:例

(續表)
2.3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預測因素篩選 采用Lasso 回歸分析856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的臨床資料,見圖1,通過交叉驗證篩選最優λ 值為0.018。圖1 上橫坐標表示模型中非零系數變量的個數,下橫坐標表示Log(λ),縱坐標表示目標參量。兩條虛線代表Lambda.1se 值和Lambda.min 值。Lambda.min 是指在全部λ 值中,獲得1 個最小目標參量均值;Lambda.1se 是指在Lambda.min1 個方差范圍內得出最精簡模型的λ 值,本研究Lambda.1se 的值為0.018。圖2 中每條曲線代表每個自變量系數的變化軌跡,隨著模型壓縮程度增大,λ 值變大,模型選取變量的功能就會增強,從而進入模型的自變量個數也會越來越少。結果顯示,16 個自變量最終產生了7 個具有非零系數特征的預測因素,即是否BMI 異常、是否糖尿病、術中體溫、血紅蛋白水平、血清清蛋白水平、血乳酸水平以及手術時間。

圖1 Lambda 與模型誤差

圖2 Lambda 與變量的解路徑
2.4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 以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是否發生壓力性損傷為因變量,以單因素和Lasso 分析篩選(P<0.05)的因素(是否BMI 異常、是否糖尿病、術中體溫、血紅蛋白水平、血清清蛋白水平、血乳酸水平、手術時間)為自變量。結果顯示,BMI 異常、糖尿病、術中體溫異常、血紅蛋白水平<90 g/L、血清清蛋白水平≤35 g/L 以及手術時間>4 h 是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獨立危險因素(P<0.05)。自變量賦值見表2,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結果見表3。

表2 自變量賦值

表3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
2.5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預警模型的建立與擬合優度檢驗
2.5.1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預警模型的建立 基于6 項危險因素建立Nomogram 模型,見圖3。可見各條評分線評分依次為80 分、100 分、91 分、82 分、71 分、75 分,總分499 分。若1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患有糖尿病,存在術中體溫異常現象,同時又存在血紅蛋白水平<90 g/L,那么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風險為100+91+80=273 分,與之對應的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風險約為16%。

圖3 預測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模型
2.5.2 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預警模型的擬合優度檢驗 本研究結果 顯 示:C-index 為0.838,95%CI[0.809,0.867],校正曲線趨近于理想曲線,見圖4;內部驗證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模型的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0.814,95%CI[0.789,0.839],見圖5;決策曲線顯示閾值概率在3%~63%范圍內時,模型凈獲益值較高,見圖6。

圖4 Nomogram 模型的校正曲線驗證

圖5 Nomogram 模型的ROC 曲線驗證

圖6 Nomogram 模型的決策曲線
3 討論
3.1 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現狀分析 手術獲得性壓力性損傷(intraoperatively acquired pressure injury IAPI)是指從手術中獲得的壓力性損傷,通常發生于術后72 h 內,多為1 期或2 期壓力性損傷[13]。手術病人因醫療器械、體位、制動時間長、麻醉、術中體溫、應用藥物以及禁食等因素成為壓力性損傷的高發人群。美國一項研究表明,IAPI 平均發生率為8.5%,其中1 期、2 期IAPI 分別占27.2%和36.0%[14];韓國一項回顧性研究顯示,術后IAPI 發生率為3.7%,其中≥2 期壓力性損傷病人約為10.2%[15]。我國陳哲穎等[16]研究表明,610 例手術病人IAPI 發生率高達19.8%,其中1 期、2 期壓力性損傷分別占73.6%和6.6%,深部組織損傷占19.8%。IAPI 的發生不僅延長了術后病人的住院時間,還極大地降低其生活質量。據報道,當壓力性損傷發生時,住院時間延長3.5~5.0 d,重病人住院時間甚至延長≥15 d[17]。本研究結果顯示,856 例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48 例,發生率為5.61%。與上述文獻發生率差異原因可能與樣本量選取和疾病情況等不同有關,可見術后發生壓力性損傷并非罕見。
3.2 乳腺癌根治術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危險因素分析 本研究基于Lasso 和多因素Logistic 回歸分析篩選BMI異常、糖尿病、術中體溫異常、血紅蛋白水平<90 g/L、血清清蛋白水平≤35 g/L 以及手術時間>4 h是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獨立危險因素。郭莉等[18]研究表明,體質指數與壓力性損傷發生密切相關,原因是手術病人體重過大,會增加受壓部位承受的壓力;手術病人體重過輕,缺乏脂肪組織,肌肉松弛無彈力,會造成受壓部位與骨突出部位沒有肌肉組織或脂肪緩沖和支撐,增加壓力性損傷發生風險。莊秋楓等[19]研究表明,合并糖尿病是壓力性損傷發生的危險因素。究其原因,糖尿病病人機體內存在廣泛小血管內皮缺氧、增生及損傷,引起血管擴張與收縮不協調,造成肢體末梢麻木、排汗異常、皮膚敏感性低等問題,當受到外界因素(壓力、摩擦力、剪切力)刺激時,皮膚易出現潰爛而發生壓力性損傷。趙丹等[20]研究證實,術中體溫降低是壓力性損傷發生的危險因素。林秀嬌等[21]研究證實,發熱是發生壓力性損傷危險因素之一。手術過程中,低溫環境、麻醉藥物、手術暴露區域大、消毒面積大等多種因素均可導致病人熱量散失,低體溫提高壓力性損傷發生率已被研究者證實[22]。發熱多伴有出汗,從而刺激表皮,改變酸堿度,降低皮膚保護力,增加壓力性損傷發生的風險。血紅蛋白和血清清蛋白水平是營養監測的常用指標。姚秀英等[23]研究證實,蛋白質缺乏及營養不良是發生壓力性損傷的獨立危險因素,血清清蛋白水平降低會影響機體營養狀態,降低免疫力和組織修復能力,導致血漿膠體滲透壓下降,皮膚彈性下降,引發機體水腫,增加壓力性損傷的發生風險。另外,血紅蛋白水平降低會降低血液中細胞攜氧能力,使組織在受壓、缺血的情況下處于低氧狀態,對壓力的耐受性下降,增加壓力性損傷發生的風險。魏彥姝等[24-25]研究證實,手術時間越長,壓力性損傷發生風險越大。由于手術期間通常不允許病人中途改變體位,延長局部皮膚組織受壓時間,導致組織缺氧缺血。上述研究結果佐證了本研究對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壓力性損傷危險因素的研究結論。
3.3 乳腺癌根治術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模型建立及應用價值 Nomogram 模型無需傳統數學模型的復雜運算,僅通過作輔助線和簡單的求和計算即可快速得到乳腺癌根治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的風險評分[26]。本研究構建預測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Nomogram 模型顯示,BMI 異常為80 分、糖尿病為100分、術中體溫異常為91分、血紅蛋白水平<90 g/L 為82 分、血 清 清 蛋 白 水 平≤35 g/L 為71 分、手術時間>4 h 為75 分。為了防止模型過度擬合,保障其預測準確性,本研究采用多方面驗證,結果顯示,C-index 為0.838,95%CI 為[0.809,0.867],校正曲線走勢與理想曲線基本一致,AUC 為0.814,95%CI 為[0.789,0.839]。此外,決策曲線顯示閾值概率為3%~63%時,凈獲益值較高,表明本模型預測效能良好。
3.4 乳腺癌根治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護理策略醫務人員可通過該模型各變量得分情況預測壓力性損傷發生風險,盡早識別高風險病人。同時,對可以控制的危險因素給予一定的預防措施:①評估術前風險,針對高風險病人采取適當的減壓措施;②重點關注獨立風險因素,皮膚韌性、組織豐滿程度及受壓點局部骨骼的構型等因素都應考慮在內;③針對壓力性損傷高發部位,預防性應用減壓墊、敷料;④采用正確手術體位;⑤密切關注病人皮膚狀態及手術室環境溫度、濕度;⑥加強術中巡視,如果手術操作允許,可適當調整皮膚受壓部位;⑦手術前后應時刻關注受壓部位減壓情況,采用不同于術中的體位;⑧積極開展健康宣教。
綜上所述,BMI 異常、糖尿病、術中體溫異常、血紅蛋白水平<90 g/L、血清清蛋白水平≤35 g/L 以及手術時間>4 h 是乳腺癌根治術病人術中發生壓力性損傷的危險因素,構建的模型可以確切量化和評估乳腺癌根治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的風險。局限性:樣本量均來源于一家醫院,數據選擇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倚,同時也未納入其他樣本進行模型外部驗證。另外,納入影響術中壓力性損傷發生的變量不全面,可能遺漏有價值的指標。下一步將會通過完善試驗設計、豐富風險變量對模型進行優化和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