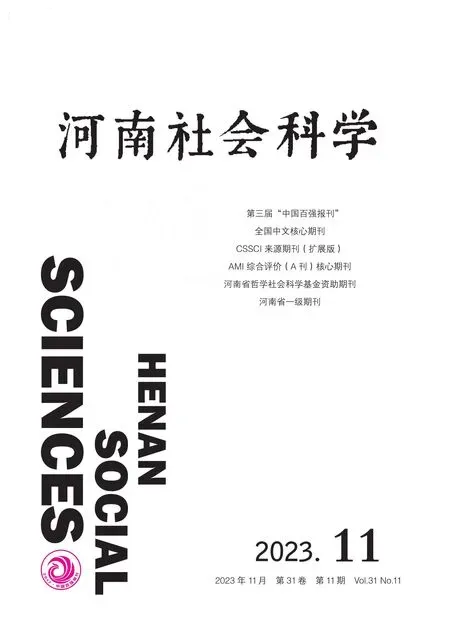宋元時期的中原文化與中華文明共同體
張昭煒
(中國社會科學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中華文明是多元一體的文明,由此可以進一步追問:多元與一體之間的具體關系是怎樣的呢?如何在多元中強化一體?又如何在一體中展現多元?中華文明是連續的文明,由此可以進一步追問:在保持中華文明傳統連續性時,如何回應時代問題,實現文明的創造性發展?如何保持中華文明內核的先進性?以上諸問題的解答關乎傳統中華文明的文化政治與文明共同體形成。在前軸心時代,中原文化是中華文明的主體;在近世中國,洛學有效應對佛教對中國文化的沖擊,捍衛中華文化,奠基道學或理學;在政治層面,與遼、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權競爭,至元朝形成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共同體。
一、引言:周公塑造的中國文化政治遺產
通常認為,前軸心時代的周公是中華文化的奠基者、設計師,“周公之才之美”(《論語·泰伯》)。他制禮作樂,使得中華文明擺脫殷商的神秘文化,禮運中華,塑造了中華文明的內核。孔子向往周公之學,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孔子開啟儒學,后人通常將周公與孔子合稱周孔。周公還是一位具有遠見卓識的政治家,他為中國確立地中:“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1]地中的特征是夏至正午太陽直射無影,通過影圭尋找夏至的無影處,可以確定地中。“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2]262周公營洛與制禮作樂近乎同時完成,洛陽地中居大地之中,氣候溫和,具有陰陽和平的特征,由此產生出“中國”哲學的中和思想,并與禮樂相呼應。禮中樂和,中和一致亦決定了禮樂同質。從人類學來看,世界各地的人類風俗習慣不同,而這種不同的風俗習慣勢必反映到制禮作樂上,因此,中國禮樂的制定具有特殊性,尤其適用于中國文化的傳統。比如《周禮》中的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之分是基于古中國主要地域處于北溫帶,中原地帶春夏秋冬四季分明,這顯然不適用于其他地帶的文明。在溫和的氣候條件之外,地中的特點還應是土地肥沃,物產殷盛,以此保證人民能夠在此穩定地生活,周公最終選擇洛邑,以日中無影的測景臺為中心,形成天地之中的建筑群,并以此建國。“《逸周書》曰:周公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以為天下之大湊,按此實王城。故孔《注》云:成周、王城也,于土為中。”[3]在測影定都、氣候因素之外,洛陽作為都城,還有以下三個因素。其一,這是三代地理空間的一貫傳統:“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禪書)“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史記·貨殖列傳》)三代都在尋找天下之中,都居于中原河洛,這是中國古老的政治傳統,并結合了當時國家的疆域。周人建都河南,是從周人的疆域而言的天下之中。其二,定都洛陽作為天下之中,在國家層面考慮了地理政治的因素。四方向洛邑朝貢的距離均等。“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筑,居九鼎焉。邑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其三,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西周衰落,“幽王為犬戎所敗,同東遷雒邑”。(《史記·封禪書》)西北退而東南興,“西周末年,開辟南國,加強對淮夷的控制,在東南持進取政策。東都成周,遂成為許多活動的中心”①。這如同宋代都城南遷臨安;反之,如果加強對北夷的控制,也將導致都城的北上,這成為元朝定都北京的現實政治需求,將在下文論述。總之,天下之中洛陽作為東周的都城,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當然,其中最神圣的因素便是日中無影,最現實的需求便是西周開辟南國的政治需求。
周公營洛,以洛邑為都城,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其地中涵蓋三重結構:(1)測景臺——洛邑;(2)洛邑——中國;(3)中國——大地。測景臺是洛邑的中心,洛邑是中國的中心,中國是大地的中心,再疊加禮樂的光華,由此塑造形成了中華文明的內核。三重結構由“中”的信仰支撐,循此構建出“宅茲中國”的政治文化之“中”。這個信仰結構之“中”的物質文化載體便是日中無影的測景臺,更大一級的物質文化載體是洛邑,當時最大的物質文化載體便是位于四方之中的中國。如果再進一步追問:中國人民如何表達這種信仰?答案就是禮。“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荀子·大略》)據注釋:“此明都邑居土中之意,不近偏旁,居中央,取其朝貢道里均。禮也,言其禮制如此。”[4]這是從四方到洛邑的距離均等來理解天下之中,中之禮是國家的禮制。禮的敬仰對象是神圣的中,禮亦成于中,周公營建的洛陽便是周禮的物質文化載體,由此導致與之相應的禮也具有神圣性,從而將測景臺的神圣物質文化載體轉化到非物質文化的禮。禮中樂和,樂與之相配,因此,禮樂文明構成中國之中的文化形態。中國人須與代表神圣的天下之中的測景臺或洛邑發生關系,也就是信仰的人須與神圣的信仰對象發生關系,才能實現信仰。通過禮樂的非物質化,中國人只要踐行禮樂,便可以直通信仰的對象。禮樂還可以進一步內化為心性的中和,這為出自《禮記》的《中庸》所重視,經此內化,中國人將神圣的天下之中內化在心中,只要致中和,便是參贊神圣的天下之中。這種內化在心的進路有待北宋洛學的出現,洛學在心性層次回應佛教心性論的沖擊,確立中華文明的主體。
周公營洛并成功經營中國,孔子稱贊周公之德:“光明于上下,勤施四方,旁作穆穆,至于海表,莫敢不來服,莫敢不來享。”“而天下大治。”[2]258中與四方共在,換言之,中既決定了四方,四方亦決定了中,周公成功處理了中國與四方的關系。中國不是孤立自生、封閉自大的,而是一開始便與四方共生,“一小塊文明之地處在野蠻部落之中,這便是中原在‘天空之下’(即‘天下’)的世界中的格局。這一格局自然地反映在中原人對世界、對其形態及居民的認知”[5]。因此,中國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的重要內容便是中原與周邊部落如何實現文化共生、政治共融,形成中華文明共同體,具體表現為以禮樂文明帶動周邊的野蠻文明。戰爭征服只能在形式上實現政治統一,但難以實現文化的內在統一,這在三代文明中已有類似的政治經驗,如《尚書·大禹謨》載有舜命禹伐有苗之事,“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6]287。但是,戰爭進行得并不順利,“三旬,苗民逆命”[6]288。在此情況下,益建議大禹:“至誠感神,矧茲有苗?”[6]288于是,大禹改變了戰爭策略,班師回朝,修文德,通過文德感召有苗。新策略果然有效,“七旬,有苗格”[6]288。據此經驗,要處理好中國與周邊部落的關系,關鍵在于夯實中華文明主體,以此感召四方,而不是討伐或征服四方。周公的政治文化遺產亦為后世儒學所繼承,如孔子言:“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這也反向要求中華文明要保持文化的優越與先進,將四方的優秀文化向中央匯聚,與時俱進,夯實中國文化政治的主體;在主體穩固、文化優越的情況下,影響四方,以此根本性處理好中國與四方的關系。然而,感召四方還要有強有力的政治基礎,如綜合國力足夠強,有強大的國防作為支撐,否則,可能會引狼入室,乃至由此亡國,如歐陽修所論,“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荊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并侵于中國”,“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異端之患至矣”[7]517。以此為鑒,中國的強盛是感召四方的前提。雖然歐陽修有此強國固本的先見之明,但宋朝仍然面臨“三代既衰”以及“戎狄蠻夷”入侵中國的險境,難以擺脫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困擾,最終走向滅亡。
綜上,周公是中國文化的系統論述者與實踐者,周公奠定了中國的文化政治格局,其文化政治遺產包括兩個主要方面:一是中華文明內核的塑造,以禮樂文明為代表;二是中國與四方的關系,也就是如何形成中華文明共同體。以上兩個方面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內核塑造得越先進,其對四方的凝聚力越強,也就是禮樂文明對于四方的帶動性越強。與河洛學會通:中國與四方的關系相當于河圖洛書的中五——中五的中間一點與周邊四點構成靜態的“環四中五”結構,四方環繞中五。中五又相當于邵雍所講的小衍之數,“五者蓍之小衍”[8]。小衍之數放大,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從動態來看,周邊的四點圍繞中五的中間一點旋轉,類似于制作陶器的均:“均者,造瓦之具,旋轉者也。”“樂有均鐘木,七調十二均,八十四調因之(古均、勻、韻、鈞皆一字)。”[9]均也是樂器定音的工具,環四中五的結構相當于中均(黃鐘、中宮)旋出諸聲,反之,諸聲可以通過中均來定聲。以中均的模型應用到中國與四方的政治關系,其要點有二:(1)作為四方中央的中國,必須有足夠強的凝聚力或向心力,才能統攝四方。(2)如果四方中的一方或多方突然強盛,會導致中均的旋轉傾斜。若要維持新的平衡,勢必導致中均的中心轉移至強盛的一方。將中均的模型應用到中國與四方的文化關系,其要點亦有二:(1)中均旋出,作為文化輸出的母體,中國禮樂文化潤澤四方。由此內在要求中國必然是文化強國,根本穩固,文化優越,保持文化的先進性與引領性。(2)中均旋入,將四方納入禮樂文明的共同體。中國文化需要保持足夠的開放性,及時吸收四方的優秀文化,保持優秀文化輸入通道的暢通,這樣才能維持中心地位的穩固,保持文化中心的統領地位。
始終保持文化政治的先進性亦是周公的遺產,“當他將自己親歷的革命與古代歷史聯系起來,并對既往的宗教與歷史進行反思之后,一個全新的上帝便從歷史深處,同時也從他的內心中浮現出來,并頒發了新的天命。這正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真正意義”[10]。因此,中華文明從周代開始,便內在要求保持文化的先進性,以此確立起中華文明的主體,影響四方,形成與四方文明共同維新的文明共同體。否則,在文化上維持舊制或故步自封,將不能及時輸入先進文明,亦難以產生與輸出先進文明,這將削弱中國對四方的文化影響力;在政治上,如果綜合國力衰弱,政治凝聚力亦隨之減弱,將會削弱中國對四方的統領關系。當然,在后世發展中,文化與政治并不總是同步,從而形成中國與四方的多樣態政治文化關系,尤其是在宋朝時期,中國在文化上面臨佛教的沖擊,在政治上遭受西北游牧民族的入侵,遼國、金國、西夏國、蒙古國崛起。在文化與政治雙重壓力挑戰之下,中國在文化上形成了洛學,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在政治上最終形成元朝的統一體,形成多民族的中華文明共同體。
二、宋代洛學文化主體的確立
周公去世兩千年之后,中國文化的中心再次回到洛陽②。西京洛陽與東京汴梁分別是北宋的文化與政治中心,洛陽地區匯聚了全中國文化的精英。“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7]1715在這個意義上,洛學是北宋時期中國儒學的集成與代表,是中國優秀文化的集中體現。“歷史上的‘洛學’‘宋學’都是‘中原學’的傳統理論形態代表。宋代則是中原哲學發展的鼎盛時期,理學成為‘中原學’的典型理論形態。”[11]從中國儒學發展史來看,洛學是北宋儒學的代表,先秦以來的儒學資源流向洛學,北宋之后的儒學亦受洛學影響,因此,不能將洛學狹隘地理解為地域文化的概念,而更應該理解為全國性的文化概念。洛學代表了北宋時期中國文化發展的最高水平,由此也不難理解,在宋朝南渡之后,洛陽乃至中原地區儒學發展的高度與規模均難以達到北宋時期。洛學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回應時代問題,在文明沖突中捍衛中華文化主體;集成中國優秀文化,實現創造性發展;承前啟后,成為中國文化連續性發展的關鍵環節。分述如下。
(一)在文明沖突中捍衛中華文化主體
中華文化在漢唐時代遭遇佛教沖擊。回應佛教的挑戰,捍衛中華文化主體,這是洛學的時代使命。佛教大約在兩漢之際傳入中國,鑒于洛陽作為“中國”文化中心的特殊地位,洛陽成為早期佛教傳入中國的重鎮。安世高于147 年到洛陽,主要翻譯小乘上座一系;支讖(支婁迦讖)于167年到洛陽,主要翻譯大乘般若[12]。小乘與大乘幾乎同時進入中國,且兩乘均在洛陽匯聚。漢明帝在洛陽首立佛教寺廟白馬寺,“至晉永嘉,惟有寺四十二所。逮皇魏受圖,光宅嵩洛,篤信彌繁,法教愈盛。王侯貴臣,棄象馬如脫屣,庶士豪家,舍資財若遺跡。于是招提櫛比,寶塔駢羅,爭寫天上之姿,竟摹山中之影,金剎與靈臺比高,廣殿共阿房等壯”[13]。由此可見佛教對于中國本土文化的強烈沖擊。按照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的觀點:“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個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說,‘偉大的宗教是偉大的文明賴以建立的基礎。’”“從公元1世紀開始,大乘佛教被輸出到中國。”“人們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適應于和被吸收進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國適應于儒教和道教),并壓制它。”[14]佛教傳入后,中國文化的時代問題便是回應佛教沖擊,更深一層,便是在回應佛教沖擊中捍衛中華文化的主體。韓愈認為佛教消耗國費,侵蝕士農商賈的利益,擾亂教化,破壞綱常。他構建從堯、舜到周公、孔子儒學道統,發掘《大學》,“然則古之所以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15],以儒學的有為對抗佛教的無為。韓愈反對迎佛骨(舍利)③,被貶潮州,被貶的悲涼源自儒佛激烈的沖突,他成為儒佛沖突的犧牲品④。唐代佛教興盛,雖然作為中華文化的禮樂還在國家政治文化層面發揮主導作用,但儒學在心性層面受到巨大侵蝕。歐陽修繼續韓愈排佛的事業,針對佛教“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的困境,他提出本論,“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7]514。二程延續韓愈、歐陽修以后對抗佛教的傳統,尤其以“中心有所守”充實新儒學的心性論,承接儒學道統,捍衛作為中國文化正統的儒學。韓愈發掘《大學》,李翱推重《中庸》,這直接啟迪了以周敦頤、程頤、朱熹為代表的宋代理學,伊洛淵源進一步強化《大學》的三綱八目與《中庸》的中和思想。周敦頤重視《中庸》的誠體,率先提出“禮,理也”[16],禮與理互通,這相當于將規范性的禮內化在心性。二程標宗天理,“今異教之害”,“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方其盛時,天下之士往往自從其學,自難與之力爭。惟當自明吾理,吾理自立,則彼不必與爭”[17]38。在佛教心性論刺激下,洛學以“理”作為新時代儒學的主要標識,強化儒學心性論,挺立心性,對抗并融合佛教的心性論。
由于禮本于中,因此,理亦本于中,洛學對中國文化的創新在于個體心性層面實現“中”的月印萬川。“極吾中以盡天地之中,極吾和以盡天地之和,天地以此立,化育亦以此行。”[17]1152據此,吾心之中與天地之中是分殊與理一的關系,由理一分殊的同質性,個體心性之中可以承載天地之中,乃至天下之中、禮樂文化之中。據胡安國所言:“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后其義可思而得。”[17]348又據朱熹總論《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于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18]17結合中國與四方的關系,中國居四方之中,亦是以“不偏”定義“中”。作為孔門心法的《中庸》還在于“庸”,也就是中之用,表現為定理。《中庸》(總—分—總)的行文結構是(理—事—理)的結構,由此顯示出“理”對于“中”的新詮釋,以及通過“事”之實防范心性之虛。以《中庸》對抗佛教:理是中之理,避免心性虛化;事是實學,避免佛教的空虛。據《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中”體現著“中國”的神圣性,“中”之體是儒學道統譜系中所捍衛的核心價值,也是中國文化的根本。強化“中”的道統,在心性層次確立中國文化之中,凸顯“中”的文化主體性與根本性,這是洛學及其后繼者閩學對于中華文明的再創新,也是兩宋文化一貫性的體現。經此創新,作為信奉、踐行“中”的中國人,并不限定為洛邑之人、中原之人,即使東南閩地之人亦可傳承踐行中國文化的內核;從中國與四方關系來看,不僅東南,西北游牧民族亦不受地域、民族限制,均能傳承踐行中國文化的內核,由此在新時代為中華文明共同體形成做好了理論鋪墊。
儒學道統的基礎經典是記錄孔孟及其門人言行的《論語》與《孟子》,承接韓愈與李翱建構道統與發掘儒學經典,洛學對于道統與經典發展的重要貢獻是引入《大學》與《中庸》,兩者分別出自《禮記》第四十二章與第三十一章。“《禮記》之作,出自孔氏。”“孔子沒后,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19]《大學》與《中庸》均屬于“禮”的詮釋。從道統來看,一般觀點認為曾子作《大學》,子思作《中庸》。曾子是孔子的學生,子思是孔子的嫡孫,孔曾授受,思孟重心性,四書經典視域下的道統相當于在孔孟之間增加了曾子與子思,由此使得已有的孔孟道統更為豐富。《大學》與《中庸》充實了禮的心性層次;程顥、程頤尤其重視《大學》,作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17]1126-1132,以《大學》作為應對佛教沖擊的經典:“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圣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于世。”[18]2這顯示出洛學對抗佛教、捍衛中華文化主體的學術使命。《大學》明明德、親民、止于至善的三綱領均可用于對抗佛教的無為:明明德凸顯了儒學實在的德性,親民屬于儒學治國的政治哲學,止于至善是儒學追求的倫理目標與政治理想。程朱將《大學》八條目的格物詮釋為“即物而窮其理也”[18]7,相當于將物與理作為心性追求的目標,以此對抗佛教心性論超越于物之上的虛無與空寂;《大學》八目的正心誠意是從心意層次踐行道德倫理,亦可有效抵制佛教的絕倫棄物。《中庸》凸顯誠體,以至誠作為儒學倫理價值的目標;《中庸》追求致中和,禮中樂和,這是中華禮樂文明的體現。
從道統來看“中”,“中即道也”。“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17]606洛學將中國文化之“中”深入到心性層次,將禮樂轉向心性,洛學的學習者便是中國文化的傳遞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捍衛者,是道統的繼承發揚者,這是洛學對于中華文明作出的重要貢獻。現代學術研究多使用“宋明理學”的概念,須注意與“道學”的區別:以二程為代表的北宋理學不僅是為了講道理,而且還是塑造中華文化內核的衛道之學,如胡安國所言:“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后其道可學而至也。”[17]349《宋史》專設《道學傳》,首列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含其弟張戩)、邵雍以及劉絢等程氏門人十位,再列朱熹、張栻以及黃榦等朱氏門人六位,“宋代道學之名,專指伊洛傳統,并不包括心學及其他學派的儒家學者”[20]。宋明理學的概念更寬泛,隨著儒學心性主體確立,后續宋明理學的衛道意識亦有所減弱。綜上,通過引入《大學》《中庸》,二程奠定了四書學新經典體系,經由朱子集注與統合,四書成為宋代之后中國科舉考試的經典,由此深刻影響了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國文化與政治。
(二)集成中國優秀文化,實現創造性發展
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時代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洛學集成了當時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實現了中國文化的創造性發展。作為中國的文化中心,洛陽成為文化精英薈萃之地。二程之學是洛學的內核,外延有周敦頤、張載、邵雍之學,由此形成濂洛關學的學術共同體。邵雍主先天象數學,其代表作是《皇極經世書》,據其子詮釋該書旨趣:“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18]1247這可視為從先天易學詮釋中國之中。二程與邵雍相唱和,三位洛陽籍的學者有共同的中正追求。張載代表的關學重視氣論,反對佛教的虛空;司馬光對于二程的經學有導源之功,來自泰州的胡瑗重視儒學的事功與經學,反對佛教,“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21]24。胡瑗對二程有啟沃之功,二程之學產生的背景是:“慶歷之際,學統四起。”[21]251通常而言,二程之學啟蒙于周敦頤,周敦頤在四川無欲主靜,養成澄靜源,屬于揚雄以來的蜀學學風。帶有西蜀之學玄靜氣象的周敦頤影響到二程、道南一系以及整個宋明理學。“明道嘗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貼出來。’”[17]424盡管二程強調學問自得,但不可否認周敦頤之“理”啟發二程之“天理”,引導二程求孔顏之所樂、明體達用,充實內在心性,踐行無欲主靜[22]。
洛學內部具有多元性,體現為二程之學的二元性。程顥與程頤的為學風格不同,程顥開闊,程頤謹嚴,二程對待弟子亦不同,“明道喜龜山,伊川喜上蔡,蓋其氣象相似也。龜山獨邀耆壽,遂為南渡洛學大宗,晦翁、南軒、東萊皆其所自出”[21]944。程顥喜楊時(龜山),由楊時傳至朱熹,則轉向程頤之學。程頤喜謝良佐,謝良佐“以覺言仁”,張九成紹續其學,乃至張九成開出陸九淵、楊簡,發展出心學的進路。北宋儒學核心是伊川之學,南宋儒學核心是朱子之學,北宋與南宋儒學一脈相承,合稱程朱理學。以二程為主的洛學與以朱子為主的閩學可分別代表北宋與南宋理學,兩者既有一致性,亦有差異性。從一致性來看,朱子之學源于道南系,集成北宋五子之學,形成閩學。朱子的《伊洛淵源錄》明確了洛學與閩學的傳承譜系,由此,閩學可視作洛學在南宋的發展。從差異性來看,閩學不能涵括洛學的多元性與豐富性,甚至不能容納作為洛學核心之一的程顥之學,如程顥以覺言仁的傾向。雖然朱子屬于洛學南傳的道南一系,但朱子并未完全契合,故有道南指訣的轉出。從歷史實際來看,朱子繼承發展二程之學,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洛學,朱子學在后世的影響要大于洛學。較之于南宋的閩學,北宋的洛學更為多元與開放。
洛學的士人主體是民間儒學,雖然這些學者多有為宦的經歷,但他們不代表官方的意識形態,由此之故,盡管程頤有經筵的經歷,但洛學主要著力于民間社會,“新的平民學者再起,這即是宋代的新儒家。他們到處講學,書院林立,儒家思想恢復了他的平民精神,他遂重新掌握到人生大道的領導權,寺院僧侶自然要退處一隅”[23]。不同于韓愈、歐陽修寄托于皇帝或政府自上而下地抵抗佛教(得君行道),以二程為代表的洛學主體是世俗社會,從學者、從游者亦是自發而來,因此重點在民間社會(覺民行道)。他們有重振儒學心性的雄心、捍衛中華文明主體的熱情以及接續道統為往圣繼絕學的使命,在民間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進而影響到官方,總體屬于自下而上的策略。民間社會的受眾廣泛,基礎穩固,心性之理根本強固后,可有效應對佛教沖擊,捍衛中華文明主體。
(三)承前啟后,成為中國文化連續性發展的關鍵環節
在中國文化發展史中,洛學具有承前啟后的作用。據程頤為程顥所作墓表:“周公沒,圣人之道不行;孟軻死,圣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先生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民。”[17]640據此,程顥以繼承周公、孔孟之道為己任,傳周公、孟子所倡導的圣學,接續儒學的道統,并且發揚《大學》《中庸》“遺經”,這不僅是程顥與程頤的學術使命與志向,也是洛學的學術使命與志向。“志將以斯道覺斯民”顯示出二程“覺民行道”的文化策略。以“中國”哲學為中心來考量,從三代以至宋代,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文化有三大高峰,分別是:以文王、武王、周公為代表的周代文化;以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為代表的先秦文化;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為代表的兩宋文化。這三大高峰的連續性可通過道統的構建實現,孔子“憲章文武”(《中庸》)、斯文在茲,崇尚周公,從而實現第一高峰與第二高峰的連續;宋代的伊洛淵源始于周敦頤,集大成于朱熹,以程朱理學為核心,以四書為經典,四書的作者分別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從而實現第二高峰與第三高峰的連續。儒家道統的骨干分別是文王、武王、周公以至孔子、二程、朱熹,以此可以實現三大高峰的連續,形成歷史時間軸上的中國文化一體。
以洛陽為中心,洛學之學影響到全國,對于中國其他地域的直接影響體現在宋代的閩學、湖湘學等:閩學傳統源于從二程到楊時的道南系,楊時傳羅從彥,羅從彥傳李侗,李侗傳朱熹[24]。湖湘學是二程到胡安國(謚文定),“私淑洛學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學之功,文定幾侔于龜山,蓋晦翁、南軒、東萊皆其再傳也”[21]1170-1171。胡安國之子胡宏與胡宏的弟子張栻為代表的傳承譜系,再傳還有呂祖謙。通過論學,湖湘學譜系的張栻、呂祖謙的思想又為朱熹所吸收。由此形成以二程之學為源,楊時、胡安國等譜系為流,至朱子而集成的學術格局。浙學源于程頤,“初辟浙東史學之蠶叢者,實以程頤為先導”[25]。從思想譜系來看,程顥與程頤之學的差異也在后學中放大。程顥及其弟子謝良佐以覺言仁,一傳為張九成,再傳為陸九淵,三傳為楊簡;程頤及其弟子楊時重視未發之中,由道南指訣傳,出朱子學。張九成之學是朱子批判的對象,被視為“洪水猛獸”;陸九淵與朱熹在鵝湖論辯,程顥與程頤之學的差異在南宋放大為朱陸之爭。在明代陽明學興起后,洛學內部的差異亦體現在陽明學,如羅洪先的兩大弟子胡直與萬廷言的為學路徑:胡直總體上繼承了程顥與謝良佐,重視以覺言仁;萬廷言則是發揚程頤之學與道南指訣。
從心性與理的邏輯發展來看,宋明理學的邏輯形態主要有四種:心即理、性即理、以心著性(牟宗三提出的五峰蕺山系)、以性即心(以覺言仁)。前兩種是將心或性直接與理對接,后兩者是在兼宗心性時各有偏重:“以心著性”偏重在性,“以性即心”偏重在心。以上四種心性與理的邏輯形態在宋明理學中都有展開,其源都可追溯至二程。由此可見二程對于整個宋明理學的奠基性貢獻,通過理來規定心性的四種邏輯形態,具有一致的對抗佛教心性論的合力,可有效抵制佛教心性論的沖擊;以理規范心性,可以對抗佛教將心性虛化、空化、禪化的做法。總體來看,宋明理學通過理對心性的規范,有效抵制了佛教的沖擊。但是,相對于漢唐儒學,宋明理學重視心性,強化了內圣,重此輕彼,由此導致外王事功的弱化,這種弱化與宋代“重文輕武”的社會風氣相助長,不利于宋朝的富國強兵。
三、中原與游牧文明的中華文明共同體
洛學形成繁榮的過程是中國文化在心性層次確立主體的過程,這一過程的完成實現了從漢唐文化向近世宋代文化的轉折,如果順此發展,中國的近世化將在世界范圍內遙遙領先。然而,在洛學發展時期的中國北方,新興的游牧民族政權迅速崛起,新的政治中心逐漸形成,如遼國的首都上京臨潢、金國的首都上京會寧府、蒙古國的首府和林、西夏國首府興慶等。這些新興的政權將阻礙、摧毀甚至退化中國近世化的過程,但同時也是中原文明帶動北方的游牧民族形成中華文明共同體的過程。與洛學有效對抗佛教并在心性層次確立中華文化主體不同,這些游牧民族尚在學習儒學文化階段,且主要學習的對象是中原文化的禮樂制度,并且受到佛教的強烈沖擊,類似于韓愈排佛時的唐代,因此,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形成需要將這些游牧民族政權的文化帶入近世心性儒學的水平,任務艱巨,過程曲折。同時,從任務的艱巨與過程的曲折可以襯托出洛學的崛起對于中華文明近世化過程的示范意義。
(一)中原與遼金、西夏的文明共同體
在宋代,中國與四方政治關系的重點在西北,尤其是北方。燕云十六州在唐代原屬中原文化圈,卻是宋朝的北部邊界,是阻止洛學北傳的屏障。燕云十六州包括北京、河北北部、天津、山西北部等地,這里不僅是中原地區抵抗游牧民族入侵的軍事戰略要地,而且是中原農耕文化在北方的重鎮。后晉天福元年,石敬瑭稱帝,“國號晉。以幽、涿、薊、檀、順、瀛、莫、蔚、朔、云、應、新、媯、儒、武、寰州入于契丹”⑤。石敬瑭獻地、獻帛、獻圖籍,為遼國經濟文化政治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遼國的官制仿中原,儒學典籍源于中原,石敬瑭割地求榮求安卻促進了中原文化在游牧民族文化圈的傳播。遼國全盛時期,“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26]495-496。遼國疆域從東邊的東海到西邊的金山(阿爾泰山),向北延伸至臚朐河(克魯倫河),疆域內部暢通,政治一統。燕云十六州作為中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納入以游牧文明為主導的遼國,使得中原文化在遼國疆域得以順利傳播,極大拓展了中華文明共同體的邊界。當然,割讓燕云十六州給遼國后,這些地區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被打斷,洛學對于燕云十六州的影響甚微,如黃百家所論,“自石晉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為異域久矣,雖有宋諸儒迭出,聲教不通”[21]2995。以上是燕云十六州脫離中原文化圈之后的不利之處。
遼國的文化淵源屬于殷商文化,與中原文化同根同源,這有利于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形成。“遼本朝鮮故壤,箕子八條之教,流風遺俗,蓋有存者。自其上世,緣情制宜,隱然有尚質之風。”[26]927遼國的禮制表現為融合遼之故禮與中土之禮,“今國史院有金陳大任《遼禮儀志》,皆其國俗之故,又有《遼朝雜禮》,漢儀為多”[26]928。遼國亦有融合中原國服的趨勢,“太祖帝北方,太宗制中國,紫銀之鼠,羅綺之篚,稛載而至。纖麗耎毳,被土綢木。于是定衣冠之制,北班國制,南班漢制,各從其便焉”[26]1007。遼國的官制效仿中原:“升北、南二院及乙室夷離堇為王,以主簿為令,令為刺史,刺史為節度使,二部梯里己為司徒,達剌干為副使,麻都不為縣令,縣達剌干為馬步。置宣徽、閣門使、控鶴、客省、御史大夫、中丞、侍御、判官、文班牙署、諸宮院世燭,馬群、遙輦世燭,南北府、國舅帳郎君官為敞史,諸部宰相、節度使帳為司空,二室韋闥林為仆射,鷹坊、監冶等局官長為詳穩。”[26]49總體來看,遼國文化與中原文化同屬一個母體,在經過獨自發展后,再次會通融合。母體的一元性,使得遼國文化與中原儒學在禮制、國服、官制等多個方面深層會通融合。從殷商到宋遼,中原文化與遼國文化總體呈現出合—分—合的格局。
遼國的禮制、國服、官員制度效仿中原,在國家制度層面保證下,中原文化在遼國深入人心。“遼起松漠,太祖以兵經略方內,禮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取晉圖書、禮器而北,然后制度漸以修舉。至景、圣間,則科目聿興,士有由下僚擢升侍從,骎骎崇儒之美。但其風氣剛勁,三面鄰敵,歲時以蒐狝為務,而典章文物視古猶闕。”[26]1593耶律德光劫掠中原中心的圖書、禮器,對于中原來說是一場文化災難;但從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建設來看,這使得圖書、禮器等中原文化載體直接進入游牧地區的核心,有利于促進游牧地區的文化發展。金國亦有類似的文化政策,“復詔曰:‘若克中京,所得禮樂圖書文籍,并先次律發赴闕’”[27]1737。通過掠奪圖書、禮器物,設置科舉,遼金全面學習中原文化,并消化吸收,結合游牧文明的特點進行創造性轉化。但由于物質基礎不同,難以在短期內實現游牧文化向中原文化的徹底轉化,遼文化傳統是“歲時以蒐狝為務”,狩獵文化根深蒂固,在轉化中產生了以農耕文明為基礎的中原文化和以狩獵文明為基礎的游牧文化之間的張力,這種張力直接導致了遼國政治體制的二元性:“置于太宗,兼制中國,官分南、北,以國制治契丹,以漢制待漢人。”[26]773這既表明中原文化與游牧文化難以在短期內融合成文化一元的統一體;同時也表明中原文化與契丹文化深度融合,在二元中尋求統一,從而有助于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形成。金朝亦崇儒尊孔,“當蒙古人入侵這個國家之后,這些人便在最廣闊的意義上代表了中國的文化”[28]。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歷史形成過程應是:首先是中原與遼形成共同體;其次是中原與金形成共同體;再次是在遼金的鋪墊下,中原與蒙古形成共同體。
西夏也采取了類似遼金學習吸收中原文化的政策,“西夏文化典籍,既借鑒吸收了中原文化典籍中的優秀成果,賡續了中華文明,又顯示出民族特色,豐富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29]。西夏對于中原禮樂文化再創造,發展出西夏的禮樂文化;在游牧文明中發展出農耕文明。這表明中原文化不僅影響了西夏的上層建筑,甚至影響了物質基礎,這是文明深度融合的體現。在成吉思汗消滅西夏之前,如西夏重臣阿沙敢不挑釁成吉思汗的使臣說:“你們蒙古人慣于廝殺,若想廝殺,我在賀蘭山住撒帳氈房,有駱駝馱子。[你們]可以向賀蘭山來找我,[在]那里廝殺!若想要金、銀、緞匹、財物,你們可以指向寧夏西涼!”⑥亡國之前的西夏呈現出一個國家兩種文明:賀蘭山(山陰處)是游牧文明,寧夏西涼(山陽處)是農耕文明。當然,西夏之所以能夠部分實現農耕文明,這與其特殊的自然資源與氣候條件有關,這里有豐富的黃河水資源,湖泊眾多,土地肥沃,適合耕種,這是其他游牧地區所不具備的物質基礎。隨著西夏亡國,西夏融合中原文化的經驗與資源為元朝所繼承。
(二)元朝的文化共同體
在元朝形成初期,蒙古的游牧文化與中原文化存在著巨大的張力。遼、金、西夏盡為元朝所滅,這些游牧民族學習中原文化的經驗為元朝所繼承,有助于張力的緩解。中原的農耕追求固定的住所與耕地、聚集的村落與郡縣、穩固的國家與政治,且父慈子孝、君仁臣忠等儒學倫理具有家國同構的一致性;而游牧民族的住所不固定,無需開墾耕地,草原茂盛之地便是他們遷徙的目標,由此影響到他們的家庭倫理與政治觀念。在游牧文明占主導時,中原文化面臨被游牧文明同化的危險,“自太祖西征以后,倉廩府庫無斗粟尺帛,而中使別迭等僉言:‘雖得漢人亦無所用,不若盡去之,使草木暢茂,以為牧地’”[30]319-320。如按此施政,則中原地區將全部變為牧場,徹底摧毀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在此情況下,耶律楚材等儒臣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時時進說周孔之教,且謂‘天下雖得之馬上,不可以馬上治’。上深以為然。”[30]320以此勸說成吉思汗從國家政策層面阻止中原農耕文明向草原游牧文明的改變,從而保證中原文化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免遭退化。從實際執行效果來看,在恢復農耕生產過程中,儒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已經被邊緣化的儒者文臣逐漸參與國家治理,恢復國家元氣,農耕生產恢復到了宋末的水平,這也促成了中原文化地位在元朝的鞏固,從而有利于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在整個元朝疆域的傳播。
繼承成吉思汗接受耶律楚才倡導儒學的遺產,元朝的皇帝多重視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以忽必烈最為突出,“在他的遠東轄區內,忽必烈顯然對于中國的制度和文化嗜好很深,正在成績斐然的做到使這個地區的新臣民歸心于他”[35]289。“無論歷史怎樣說,以為忽必烈是‘大汗’遠不如說他是中國皇帝。”[35]306“忽必烈在朝廷中重新實行傳統的儒家禮儀以及伴隨儀禮的樂舞。”[35]466此后的元朝皇帝亦多有此傾向:“裕宗孝于親,慈于眾,制節謹度,深求治道。一時儒臣如王恂、許衡輩,咸侍講幄;汗優禮遇之,德意未嘗少衰。雖未登大位,而嘉謨懿行,已足垂裕后昆矣。”[36]247仁宗“詔行科舉,以皇慶三年八月,天下郡縣興其賢能,充貢有司;次年二月,會試京師,中選者親試于廷,賜及第出身有差。謂侍臣曰:‘安百姓以圖至治,匪用儒臣,何以致此?’敕衛輝、昌平守臣修殷比干及歷代諸賢臣祠,歲時致祭”。“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嘗曰:‘儒者可尚,以其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36]249文宗“尊儒重道”,“四方享來王,誠有以感之也”[36]254。得君行道,上行下效,元朝皇帝重儒的傾向及政策有利于推進中原文化在元朝的傳播與發展,促進元朝文化共同體的形成,洛學開創的程朱理學迎來了發展的良機。
(三)中華文明共同體的宗教融合與沖突
周公敬天,敬天法祖是中原宗教文化的主要特征,敬天的傳統可以追溯至帝堯,如孔子贊嘆堯之為君:“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論語·泰伯》)由于中國與四方地緣毗鄰,中國與四方的宗教文化亦多有相近之處,尤其體現在敬天上:“突厥人敬畏的最高的神是天,即‘騰格里汗。’”[37]35唐朝疆域的西北地區接鄰東西突厥,中原宗教文化與突厥文化的敬天傳統相結合,李世民成為“天可汗”⑧,由此成為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結盟的典范。唐人認為可汗之名本自中原,“天人相合,寰宇大同”,“彼君長者,本□□□裔也。首自中國,雄飛北荒”⑨。據此,蒙古族本于中原,文化出自中原。成吉思汗亦敬天,如其討伐西夏遇到危難時說:“長生的上天啊,由你作主吧!”[38]
與洛學確立中原文化主體,有效抵抗佛教沖擊不同,儒學在游牧民族地區的影響較弱,洛學北傳與西傳受阻,且佛教、伊斯蘭教、景教等多種宗教在游牧文明中角逐,宗教沖突不可避免。宗教文化的傳播規律一般以先入為主,佛教在遼、金、西夏有先入為主的優勢,為中原宗教文化的傳播與影響帶來阻力,如反映在遼國的祭祀問題上:“太祖問侍臣曰:‘受命之君,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26]1333-1334在佛教與儒學的沖突中,耶律阿保機最終以孔子作為國家祭祀的對象。中原文化在沖突中獲勝,說明中原文化對于遼國文化政治的決定性影響,這與遼國文化源于殷商、遼國的政治現實需求、中華文明共同體內部的凝聚力等因素有關。西夏的宗教政策則向佛教傾斜,“西夏崇宗、仁宗時期是西夏佛教的興盛發展時期。其時西夏已建立了一套比較完善的佛教管理機構和管理制度”,“西夏由國家提倡尊崇佛教”,“西夏佛教興盛,寺院遍布全境”[39]。《成吉思汗法典》要求宗教寬容,“成吉思汗對所有宗教一視同仁,不偏袒某一宗教,認為所有的宗教都是服侍神的手段”[37]59。這一方面為儒學在西北游牧地區的傳播提供了政策保證,另一方面也要求儒學參與宗教競爭。儒學與道教均源自周代的中原文化,通過長春真人丘處機的先導性經營,全真教在元朝獲得了優先傳播發展的地位,在文化同源、三教合一背景下,這也有利于儒學傳播與影響。
總體來看,中原文化在西北游牧地區以輸出為主,以先進的中原文明帶動落后的游牧文明。“不論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夠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鄰近的地方,和中國或波斯接觸,這些部落就變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處過著游牧生活,他們就還是半開化人。”“在這種場合,決定歷史演變的是人種地理學的具體事實而不論其種族為何。”[35]3-4據此可知,蒙古部落變得文明,主要是中原文化影響的結果。在促進四方文明,尤其是在促進西北地區游牧文明方面,中原文化發揮了主導作用。盡管這些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權接受中原文化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都在借鑒吸收中原文化,并且促成了中原文化在西北游牧地區的扎根,帶動了西北游牧地區文明的進步。
(四)元朝中華文明共同體政治中心的形成
由于西北草原遠離北回歸線,這些政權無法像洛陽那樣測影立中建都,但仍繼承了周公營洛“環四中五”的格局。“遼國其先曰契丹,本鮮卑之地,居遼澤中;去榆關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迨于五代,辟地東西三千里。”[26]495-496遼國之始,在地理空間遠離中原文化圈(距離最近的幽州尚有七百余里),納入幽州在內的燕云十六州對于遼國具有重要的地緣政治意義,并奠定了遼國的五京格局:“太宗以皇都為上京,升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圣宗城中京,興宗升云州為西京,于是五京備焉。”[26]496五京各有所用,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上京與東京,上京原為契丹人故都,東京為遼陽,兩京都屬于中國游牧文明區;第二類是南京與西京,幽州南京是現在的北京,西京是山西大同,南西兩京本屬于中原文化圈,經濟基礎是農耕文明。中京在地域上屬于游牧文明區,承擔草原與中原溝通互鑒的媒介。東、南、西、北(上)四京環繞中京,形成“環四中五”的河洛中五小衍結構,這顯然繼承了周公營洛的政治遺產;遼國的五京制亦為金國效仿,海陵王遷都燕京(北京)為中都;金宣宗以洛陽為中都,“視中都,增置官吏”[27]352。對比周公以洛陽為都城的環四中五政治格局,遼國五京制更為具體化,尤其是在四方各有都城;遼國五京制的特色還在于綜合考慮了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的互通與綜合管理。以上都是對于周公營洛政治遺產的新發展。蒙古的故都和林遠離中原,元朝在吸收借鑒遼金五京制的基礎上,再納入宋朝全部的疆域通盤考慮,新的政治文化中心選定在幽州北京,作為元大都。從環四中五的中均模型來看,北京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農耕文明與以和林為中心的蒙古游牧文明融合博弈的結果,其中過渡階段是遼國的五京制:幽州(南京,現北京)地處遼國五京的南端,是草原游牧文明向南推進的末端;幽州(現北京)也是宋朝洛學向北輻射的末端。中原農耕文明與草原游牧文明在幽州交匯,由此形成中華文明共同體的政治中心。
政治中均與文化中均既有獨立性,又相互影響。以中均模型來看宋元政治史,東京汴梁中均形成中原文明的政治共同體,上京中均形成遼國游牧文明的政治共同體,這兩個中均同源于中華文明,在獨自發展后相互融合。其次是會寧中均形成金國的政治共同體,興慶中均形成西夏的政治共同體,兩者亦與東京及上京中均融合。最終,在和林中均鐵騎之下,以上諸中均融合成大中華文明中均共同體。儒學是促進大中均統一體凝聚的合力,無論是上京、會寧、興慶,還是和林,都深受儒學的影響;在新統一體形成后,元大都北京成為政治中心,行政力量使得和林成為儒學過化之地,并影響到整個嶺北行省,乃至四大汗國。再以中均模型來看宋元文化史,洛陽中均的文化共同體率先形成,有效應對了佛教心性論對于中華文明的沖擊,挺立其中華文化主體。遼、金、西夏、蒙古等國深受佛教影響,甚至佛教多為主導性宗教,以此可以僅觀洛學抵制消解佛教、樹立中華文化主體的重要意義。
以學生創業進行實景模擬,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興趣,可更多地進行翻轉課堂,為學生提供更多的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機會。
元大都的新政治中心形成后,程朱理學得以在整個元朝政治統一體內廣泛傳播,且程朱理學成為官學。據二程理解的文化中國:“禮一失則為夷狄”“中國而用夷狄禮,則便夷狄也。”[17]43“禮”是判別中華與夷狄的標準,由此可推出文化中國涵蓋政治中國,倡導推行使用以“禮”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則便中國之。元朝制定并實施多項有利于儒學傳播的制度,如特設儒學提舉司,“各處行省所署之地,皆置一司,統諸路、府、州、縣學校祭祀教養錢糧之事,及考校呈進著述文字”[40]2312。政府設置各級官學機構,數量與規模遠超宋朝。在嶺北行樞密院廣泛設置儒學教授,如右衛、左衛、中衛、前衛、后衛、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司,隆鎮衛親軍都指揮使司等,“教官二,蒙古字教授一員,儒學教授一員。掌諸屯衛行伍耕戰之暇,使之習學國字,通曉書記。初由樞府選舉,后歸吏部”[40]2157-2162。據大元至正四年(1344年)和林題名殘碑,有“儒學教授”“學正”等[31]34。燕云十六州在元朝與中原儒學文化圈再次統一,具有率先接納新儒學的優勢,如趙復開程朱理學北傳之先河,趙復接續伊洛道統,“作《傳道圖》,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40]4314。元初理學名儒郝經的六世祖受教于程顥,屬于廣義的程氏后學,他受召于忽必烈,認為道統高于皇統,提出“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認為“禮樂之治,王者之極治也”[41]。元代大儒許衡主國子監,通過官方上層路線傳播理學,劉因則是通過民間下層路線傳播儒學,兩者傳播儒學的主要基地都在燕云十六州。元大都北京成為中華文明統一體的文化與政治中心,其文化政治地位相當于周公營造的洛邑。北宋文化中心洛陽北上為元朝文化中心北京,北京中心的形成集成了宋、遼、金、西夏、蒙古的文化政治遺產,并體現出國家對于游牧文明區的重視。
四、結語
從周公制禮作樂和營洛的文化與政治遺產來看,宋元時期的中國面對兩大時代主題:其一,在文化上受到佛教的沖擊,中華文化的主體受到挑戰;其二,遼、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崛起,中原在政治上需要處理中原與西北游牧民族政權的關系。洛學繼承了周公制禮作樂的文化中均遺產,將中華文明內核之“禮”發展為理學之“理”,順著禮中樂和的方向,以理規范心性,有效抵制了佛教的沖擊,在延續道統基礎上帶動了儒學的新發展。朱熹在全面繼承洛學淵源的基礎上,實現了洛學的再創造,形成閩學,這也標志著程朱理學的形成。遼國極大拓展了中國西北的疆域,元滅遼金,并進一步拓展,尤其在北部形成以和林為首府的嶺北行省的廣闊疆域,并與四大汗國形成共同體。遼金五京制繼承了周公的政治中均遺產。文化中均與政治中均相互作用,洛學開創的理學文化與游牧民族的政治經驗及疆域拓展均為元朝繼承,由此綜合發展了周公奠定的中國文化政治格局。隨著元朝建立,文化中均與政治中均相會在北京,北京成為元朝的中華文明共同體中心,程朱理學得以在中華文明共同體內全面傳播并發揮主導性作用。
從中原文化政治的發展來考量宋朝,宋朝文化發達、政治軟弱,通過歲幣等飲鴆止渴的方式換取與游牧民族政權的短暫和平。以二程為代表的崇尚道德倫理心性的洛學與以王安石為代表的新學對抗,新學崇尚政治改革、富國強兵,這些措施都有助于強化政治,增強國力國防。王安石亦是周公文化政治中均遺產的繼承者:在文化上,王安石亦將禮樂內化,“禮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42]1150。通過養身正氣,可以充實內在心性,從而有效抵制佛教。在政治上,王安石將周公等圣人詮釋成立法者,“夫圣人為政于天下也,初若無為于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于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國,則一國治”[42]1109-1110。以此服務于他的變法強國。從宋元文化政治史的大視野來看,洛學與新學可視作周公的文化政治遺產發展的兩個方向,在應對佛教沖擊方面,兩者具有一致的合力;在富國強兵方面,新學顯然更勝一籌。如果新學最終獲勝,宋朝當會在與遼、金、西夏、蒙古等游牧民族政權對抗中處于強勢,形成以中原文化為主體、融合四方的政治文化格局。然而,洛學在與新學對抗中最終勝出,這與宋初采取的“杯酒釋兵權”削弱國家政治國防的政策具有一致的政治取向,這種政治取向最終導致宋朝亡國。因此,文化中心的維系需要有強大的政治國防為保障。當然,按照中華文明共同體來考量,宋元時期實現了洛學對中華文明的內核塑造與元朝國家政治疆域的空前擴張,這些政治文化遺產為后續的明朝所繼承,成為中華文明共同體建設的寶貴資源。
注釋:
①錢穆認為西周王室為躲避犬戎之禍而東遷洛邑(錢穆:《中國文化史導論》(修訂本),商務印書館1994 年版,第33 頁)。綜合許倬云與錢穆之說,周代遷都均與四夷的影響有關。見許倬云:《西周史》(增補二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05頁。
②東周在洛陽定都五百余年,此后,新、東漢、十六國時期、東晉、北魏、隋、唐、武周有定都、遷都或修建洛陽,這些舉措的內在動力是洛陽處于“天下之中”(參見黃婕:《華夏之心:中日文化視域中的洛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 年版,第58頁)。
③據《論佛骨表》:“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后代之惑。”(《韓愈文集匯校箋注》,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2905—2906頁)
④當然,韓愈的悲劇不是沒有意義的,韓愈被貶后,儒佛沖突仍在繼續,唐武宗于會昌五年(845)頒布敕令滅佛,也就是會昌法難,其沖突如唐武宗所言:“朕聞三代已前,未嘗言佛,漢、魏之后,像教寖興。是由季時,傳此異俗,因緣染習,蔓衍滋多。以至于蠧耗國風,而漸不覺;誘惑人意,而眾益迷。”“朕博覽前言,旁求輿議,弊之可革,斷在不疑。而中外誠臣,協予至意,條疏至當,宜在必行。懲千古之蠧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眾,予何讓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余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劉昫等:《舊唐書》卷十八(上),中華書局1975年版,第605—606頁)這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韓愈抵抗佛教、保護士農商賈利益的理想。
⑤這一事件始于936 年。“晉兩遣使來上尊號,及歸雁門以北與幽、薊之地,并歲貢帛三十萬匹,詔不許”(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86 頁)。成于938 年5 月。“晉復遣譴兩使來上尊號,從之”(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8 年版,第286 頁)。11 月,“帝御開皇極殿”,“公卿百官皆仿中國,并參用中國人。是月,晉復遣趙瑩來賀,并以幽、薊十六州及圖籍來獻”。(李有棠:《遼史紀事本末》,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286—287頁)。另見歐陽修:《高祖》,《晉本紀第八》,《新五代史》卷八,中華書局1974 年版,第79頁。
⑥據注釋:“由阿沙敢不的話,可知當時的唐兀惕人,已有分為農業定居和牧獵遷徙的兩種社會之傾向。其居住于賀蘭山之陽者,則為定居的農業部分”;“而山陰一帶,仍是游牧的部落”(同上,第417頁)。文明的分化基于自然條件:山陽處日照充足,適合農作物生長;山陰處陽光相對較少,適合低矮的草被生長。《蒙古秘史》第二六五節,《蒙古秘史新譯并注釋》,札奇斯欽譯注,聯經出版社2020年版,第416頁。
⑦忽必烈稱大汗后,定都北京,四大汗國與元朝的關系若即若離,學界對此的觀點基本一致,舉兩例如下:“大汗忽必烈遠在北京,因此幾乎無法從那里統轄遼闊的帝國。至于說到金帳汗國和其他各兀魯思,它們則過著自己的生活,各有自己的利益,各兀魯思的汗力求獲得最大限度的獨立性。”([蘇]鮑里斯·格列科夫、亞歷山大·雅庫博夫斯基:《金帳汗國興衰史》,余大鈞譯,張滬華校,商務印書館2021 年版,第77—78 頁)“忽必烈雖然是帝國大汗,但是龐大帝國的時空差距很大,而真正掌握實際權力的其實是周邊附屬國的可汗,尤其是中亞、西亞、東歐地區,即使不是完全自治,很大程度上也是各自為政的。”([印度]G.D.古拉提:《蒙古帝國中亞征服史》,劉瑾玉譯,魏曙光審校,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頁)
⑧貞觀四年二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后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司馬光:《唐紀九》,《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073頁)
⑨據落款,此碑立于“大唐開元二年”(714 年)。《故闕特勤碑》,《和林金石錄》,《山左南北朝石刻存目(及其他一種)》,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7—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