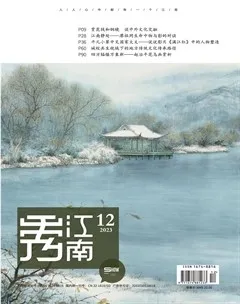千秋不變是“意氣”



鄭板橋客居揚州,史料頗多,可寫其為官生涯,可寫其繪畫生涯,還可寫其姻緣,但是寫其任何一面都不足以寫出劇作者想要表現的鄭板橋,于是羅周老師又一次展現了其對歷史輕盈把握的深厚功底,將鄭板橋為官、繪畫、為夫等故事極為巧妙地融入一部劇中,向觀眾展現了鄭板橋“三絕詩書畫,一官歸去來”的傳奇人生,同時繪就了一幅充滿市井煙火氣的清代揚州文化歷史圖卷。
羅周老師在《不曾觸及之處—我的歷史題材劇目創作》中對昆劇《春江花月夜》有過陳述:“與其說該劇描摹的是個真實的張若虛,不如說是我與大家分享了個真實的自己;它不是史劇,而是傳奇。”同樣,在揚劇《鄭板橋》中,劇作者將自己的主觀世界附會于鄭板橋,觀之有種今人對古人相見恨晚、惺惺相惜之意,并且該劇極力將這種意蘊傳達給觀眾,尤其讓我印象深刻之處是鄭板橋之“意氣”,更是劇作者的“意氣”,或許也是你我之“意氣”。
舞臺之美傳達“意氣”
揚劇主要由揚州清曲、揚州花鼓和揚州香火三源合流而來,剛柔并濟是其特色之一。揚劇不僅有花鼓戲的輕綿細膩、香鼓戲的陽剛粗獷,還有清曲的多變情感,因此,揚劇本身極富彈性和張力,與鄭板橋的守正惡邪、浪漫風雅以及乖張不從俗的人物氣質可謂相得益彰。
在舞臺呈現上,揚劇《鄭板橋》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的審美特質,與鄭板橋之“意氣”相呼相應。在秉承“大寫意、小寫實”審美原則的基礎上,該劇通過舞美、燈光等新技術手段,結合竹、石、橋等具體形象,融入詩、書、畫等元素,打造了一個充滿詩情畫意、極具寫意之美的舞臺空間。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舞臺背景采用了上窄下寬的弧形幕布,幕布以外一片昏暗,配合燈光,這兩片弧形幕布圈出來一片亮色,如一卷畫軸從高處延展下來,幕布中間的寬窄間距也是隨著劇情變化呈現不同形態,或似“風”,或似“人”,從而營造出不同的舞臺效果。畫卷緩緩展開,繁花似錦的揚州映入眼簾,從無數金箔紛紛灑落走到春風得意馬蹄疾直至進入一片空茫,古揚州的風土人情、盛亡興衰躍然舞臺之上,鄭板橋的一生也在此中娓娓道來,他“低入塵土,受盡苦寒,又躍然而出,好似海上升起明月”。待劇終落幕時,舞臺完全變成黑白色,兩側幕布緩緩收緊,在舞臺中間形成一個“風”字框,黑漆漆的幕外好似那黑暗腐朽的世道,幕內一竹、一石、一橋,鄭板橋面朝竹、石,坐于橋上,身形瘦削、孤獨泰然,周身一片清明,舞臺意境之美更顯板橋“意氣”之真。
整部劇不論是在舞臺背景、道具方面,還是在服裝設計、造型方面,多用低飽和度的色彩,背景更是以黑白為主,一股清泠素雅的氣息撲面而來。劇中鮮見的一抹亮色來自饒五娘,不僅是她的紅色石榴裙,更是她的明媚與俏麗。在第一折《道情》中,饒五娘愛慕鄭板橋的才情,芳心暗許,她一身紅色石榴裙搖曳蹁躚,與身負舉人之名卻一貧如洗、沒有能力娶妻養家的鄭板橋形成鮮明對比。到第四折《前緣》,鄭板橋已中進士,但依舊囊中羞澀,且拒絕了賣畫換錢娶妻的機會,而站立在旁的饒五娘又是一襲紅衣,將鄭板橋因“意氣”而陷入窘迫處境反襯得淋漓盡致。在水墨丹青的舞臺上,饒五娘是明亮的、跳脫的、溫暖的,她始終理解并支持鄭板橋,是鄭板橋堅持“意氣”的底氣所在,因此,鄭板橋以喜愛的蘭花喻她。“蘭花不是花,是我眼中人。竹也不是竹,為我駐精魂。漫道石頭多丑硬,我愛它丑而雄、丑而秀、不向五斗作逢迎!”蘭、竹、石是鄭板橋愛畫之物,更是鄭板橋托物言志之所在。作為全劇的重要意象,這“三畫”分別被置于《畫枷》《楔子》《石頭》三折中,為王三求情時畫蘭,為百姓放糧時畫竹,感己傷懷時則畫石,蘭、竹、石不僅多次出現在臺詞中,也作為重要道具出現在舞臺之上。以竹為例,竹子或以實景道具傲立于舞臺一隅,或以多種形態繡于板橋服飾之上,或以婆娑竹影映于舞臺背景之中,或以一竿瘦竹置于“揚州八怪”手中,處處透露著寄情于竹、以竹表情之意,令人回味無窮。
重復手法凸顯“意氣”
“意氣”一詞在全劇臺詞中共出現12次,分布于五折戲中,貫穿全劇。第一回出現在第三折《畫枷》中,縣爺盧抱孫斷王三私鹽案時采納了鄭板橋的計策,鹽商張從說:“先生一介布衣,行事意氣,倒也可敬。”“縣爺官場中人,意氣行事,豈不可笑?”此時,鄭板橋窮困潦倒,盧抱孫位居七品,雖然兩人所處境遇不同,但都是有意氣之人。第二回出現在第四折《前緣》中,盧抱孫因被張從誣告充軍塞外時,張從說:“有道是:兩淮鹽,天下咸。揚州地界,容不得‘意氣縣爺……”此時,盧抱孫因為自己的“意氣”被誣流放,鄭板橋因為盧抱孫的遭遇憤憤不平而拒絕了張從千金買畫助其成婚的提議。第三回出現在楔子中,鄭板橋欲不待放糧旨意,提前開倉放糧,盧抱孫說:“意氣了!賢弟忘了張從之言?”鄭板橋答:“一介布衣,意氣可敬……”盧抱孫再勸:“官場中人,意氣可笑!”此時,鄭板橋雖已為官,但仍然覺得意氣可敬,而盧抱孫已在流放中被磨平了棱角,磨去了絕大部分的意氣。第四回出現在第六折《虹橋》中,盧抱孫升任兩淮鹽運使,衙役問其將如何對待從前恩怨時,盧抱孫說:“為官的沒了意氣,只剩利害,哪來的恩怨!”此時,盧抱孫已然拋棄了意氣,官居從三品,鄭板橋卻“因意氣落拓半世”。第五回出現在《石頭》中,鄭板橋作畫時唱道:“……意氣堅勁、歌笑春風、倚醉江亭、千秋不變一書生!”此時,盧抱孫已被鎖拿赴京,而鄭板橋還在唱著“意氣堅勁”。
從全劇來看,盧抱孫的意氣是逐漸失落的。盧抱孫第一次談及自身意氣時,便說“本縣也有三分意氣”,開場便只有“三分”意氣,根據其后的言行不難猜想,盧抱孫初出茅廬時,也必是意氣十足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已然遭遇了許多磨滅其意氣之事,在遇到鄭板橋時,便只剩了“三分”意氣,之后在官場的泥淖中盤桓掙扎、意氣耗盡,在“唐人書、宋人畫”中清名盡毀。在與盧抱孫意氣變化的對比中,鄭板橋的“意氣堅勁”得以凸顯,如劇作者所言,“榮名利祿從他(鄭板橋)身上滑落,就像微風拂過翠竹,他始終如一”,在面對同樣的選擇時,鄭板橋所懷之意氣每一次都引導其做出了與盧抱孫截然不同的選擇,“意氣”可謂是鄭板橋身上最突出、最鮮明、最可貴的品性。那么,鄭板橋的意氣是什么?從鄭板橋的種種選擇中可見一斑:鄭板橋高中進士時,仍遵守五年之約,一片深情為佳人,換來風雨同舟到白頭,這是鄭板橋的夫妻之道;鄭板橋始終守正惡邪,一片丹心為百姓,贏得“眾百姓建起生祠爭拜頌”,這是鄭板橋的為官之道;鄭板橋一生風雨起伏、遍嘗冷暖,仍能保持赤子之心,這是鄭板橋的人生之道。相比于盧抱孫漸漸逝去的意氣,鄭板橋的這份意氣貫穿全劇始終,貫穿其人生始終,并且是逐漸向上發展變化的。在第三折《畫枷》中,鄭板橋巧用計為王三免去當眾戴枷十天,這時的意氣是書生意氣,是為報盧抱孫資助知遇之恩而生的意氣,可謂“意氣行事”,眼中所見只一人;到《楔子》中,鄭板橋不顧盧抱孫的提醒勸阻,甘冒免官殺頭之險,擅自開倉放糧,這時的意氣是深思熟慮、權衡利弊之后的意氣,眼中所見是一方百姓;到最后《石頭》中鄭板橋唱起“……意氣堅勁、歌笑春風、倚醉江亭、千秋不變一書生”,此時的“意氣”則更進一步,褪去了書生的稚嫩,卸下了官場的束縛,只剩下“冷暖嘗遍,俱是一般、俱是一般”的超然與灑脫,已臻化境。
“意氣”之蘊觀照古今
“意氣”二字說來容易,古往今來能真正實踐之人少之又少。有的人雖沒有意氣,但敬佩有意氣之人,這是常人;有的人視意氣如無物,更容不得意氣之人,如張從之流;還有的人初懷意氣,但抵不住誘惑,終拋棄了意氣,如盧抱孫之流。該劇點史成金、以古喻今,其對“意氣”二字的演繹和思考引人感喟、發人深省。
古往今來,守正惡邪一直是為官之人極為重要的品質,但亦有人用“水至清則無魚”來反駁,鄭板橋和盧抱孫的人物塑造也正是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很好的回應。在《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中,孔子提出,“故君子蒞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今臨之明王之成功,而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者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絖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顯而易見,孔子這段話說的是做官當如何治理百姓、如何為民,而不是如何為官,因而用“水至清則無魚”來闡釋為官之道是完全不合適的。為官者,做事模棱兩可、是非不分,常行走于灰色地帶,只會慢慢沉淪直至完全被灰色吞沒。在《道情》中,盧抱孫還是“愛才如命,官聲極好”的縣太爺,最后卻是“被些個唐人書、宋人畫玷壞清名陷泥沙”,落得個“鎖拿上京”的結局。從結尾鄭板橋的自述中可知,盧抱孫遭遇的那些困境、誘惑,鄭板橋也同樣經歷過,“我也曾一擲千金買脂粉,我也曾囊中羞澀無分文。也曾登第著宮錦,也曾百衲舊袍襟……一件件、一樁樁、涌入毫端淚難禁,撲簌簌、成就我、詩書畫、‘三絕名”,但這些磨礪成就了鄭板橋,也讓鄭板橋的意氣變得更加堅定。
劇作者寫鄭板橋,卻不只寫鄭板橋,是在對清代揚州琳瑯滿目的市井描繪中寫鄭板橋,他會沉醉于桃李花香美人兒,會因一貧如洗而難以娶妻買房,也因貪嘴狗肉苦酒而犯了糊涂,這樣的鄭板橋,雖負詩書畫三絕的盛名,卻也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在這樣的舞臺時空中,人物角色與觀眾之間的心理隔膜被打破,觀眾與演員的情緒和思想得以實現同頻共振,如此,鄭板橋的這份意氣就不再顯得虛無縹緲、遙不可及,與物質無關、與身份無關,只是被普通、平淡人生孕育的“崇高”,是在長久的堅守中得以實現的“永恒”。
盧抱孫曾問鄭板橋:“在朝有在朝的難處,在野有在野的瀟灑。你為何不肯為民,偏要做官呢?”鄭板橋答:“只為看花聽曲,是一身一家之事;憂國憂民,方是天地萬物之事!”當今社會,面對人生中太多的不確定性,許多年輕人給自己貼上了“佛系”“躺平”“擺爛”等標簽,處處透露著不爭不搶、無欲無求、不作為、慢作為的人生態度,但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處世態度是永不過時的,奮斗進取、追逐理想依然應該是生命的底色。“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作為新時代的中國青年,我們生逢其時、重任在肩,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志氣、“會當凌絕頂”的底氣和“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正氣,去探索人生的意義、價值和情趣,同時為當代社會的建設和發展作出自己的一點貢獻。
作者簡介:周宇,女,江蘇常州人,江蘇省文化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碩士,研究方向:文化政策、文藝評論、公共文化。
——以揚劇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