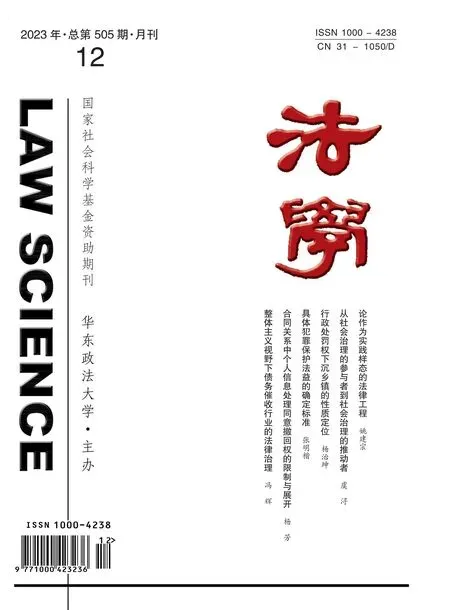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確定標準
●張明楷
刑法理論對是否承認前實定的法益概念(實質的法益概念)存在激烈爭論,但多數學者都承認方法論的法益概念(形式的法益概念)。方法論的法益概念具有解釋規制機能,其所討論的問題是刑法分則條文以保護什么法益為目的。“如果沒有方法論上的法益概念,那我們就無法對重要的教義學問題做出回答。譬如,規范所保護的究竟是某種個人法益——例如某人身體的完整性,還是某種集體法益——例如司法機關的運行能力,這對于我們解釋某一罪刑條文來說具有根本性的意義。因為,只有對于個人的法益,被害人的承諾才能取消行為的不法。相反,對集體法益造成損害的行為,則不具有成立被害人承諾的可能。因此,對于現今的刑法教義學而言,方法論上的法益概念是不可或缺的。”〔1〕[德]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法益保護與規范效力的保障》,陳璇譯,載《中外法學》2015 年第2 期,第553 頁。顯然,被害人的承諾有效與否只是一個方面,對構成要件的解釋、此罪與彼罪關系的理解、不法程度以及犯罪形態的判斷等等,都離不開方法論的法益概念。
眾所周知,刑法理論對許多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爭議,直接影響對構成要件的解釋與違法性的判斷。例如,如果認為綁架罪的保護法益包括“擔憂被綁架者的安危的第三者的精神上的自由即自己決定是否向他人交付財物的自決權”〔2〕黎宏:《刑法學各論》(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243 頁。,那么,綁架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就必須具有向第三者提出不法要求的內容;如若否認第三者的自決權是綁架罪的法益內容,則向第三者提出不法要求不是綁架罪的構成要件行為內容。再如,“刑法規定盜竊罪,是為了保護所有權及其他本權,還是為了保護占有,這是有爭議的。如果認為刑法規定本罪是為了保護所有權及其他本權,則所有權者從盜竊犯人那里竊回自己財物的,不成立盜竊罪;但是,如果認為刑法規定本罪是為了保護占有,則所有權者從盜竊犯人那里竊回自己財物的行為,也侵害了盜竊犯人的占有,因而成立盜竊罪。于是,論定刑法的各條文將什么作為保護法益,是刑法各論的構成要件解釋中的重要部分。”〔3〕平野龍一『刑法概説』(東京大學出版會,1977 年)40 頁。
若要合理確定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避免不必要與無意義的爭議,首先必須明確保護法益的確定標準。唯有如此,才能進一步依據相關規定與事實,采取妥當的方法確定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
不可否認的是,對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確定與對法益本身的認識密切相關。但本文并非討論何謂法益等抽象問題,而是聯系當下刑法理論的現狀,側重討論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確定標準。亦即,刑法理論對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表述或確定,符合什么標準才是適當的。在本文看來,法益的要保護性、法益的特定性、法益的融洽性與法益的可判斷性,是確定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四個重要標準。
一、法益的要保護性
所謂法益的要保護性,是指由刑法對法益進行保護的必要性。如果一種利益不值得用刑法來保護,就不能確定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從另一角度來說,法益的要保護性,是指法條目的或任務的合理性。“刑法干預權的界限必須來自刑法的社會任務。至于這種任務之外是什么,邏輯上就不可能是刑法的對象。”〔4〕[德]克勞斯?羅克信:《刑法的任務不是法益保護嗎?》,樊文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0 頁。確定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就是確定具體犯罪的實質不法內容。“由于違法性是刑法規范做出否定評價的事態的屬性、評價,故其內容便由刑法的目的來決定。將什么行為作為禁止對象,是由以什么為目的而禁止來決定的。在此意義上說,對實質違法性概念、違法性的實質的理解,由來于對刑法的任務或目的的理解。”〔5〕山口厚『刑法総論(第3 版)』(有斐閣,2016 年)105 頁。亦即,對具體法條的目的或任務的理解,就是對該法條規定的具體犯罪的實質違法性的理解,因而也是對該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的理解。
可以肯定的是,法益的要保護性,是確定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核心標準。由于這一點與實質的法益概念相關聯,所以成為見仁見智的問題。按照社會根據論的觀點,刑法是以社會作為其根據的前憲法的法律,應當根據社會需要決定保護哪些法益,憲法只是作為其外在的制約原理起作用;按照憲法根據論的觀點,刑法應當根據憲法的規定確定哪些法益值得保護。但筆者認為,二者并不是對立的,刑法的事實根據(判斷基礎)是社會,價值決斷根據是憲法,應當基于社會事實、根據憲法規定判斷某種法益是否需要刑法保護。〔6〕參見張明楷:《論實質的法益概念——對法益概念的立法批判機能的肯定》,載《法學家》2021 年第1 期,第86 頁以下。本文難以對此展開討論,以下僅就近幾年來刑法理論存在爭議的幾個具體問題發表簡要看法。
(一)禁忌能否成為保護法益
Roxin 教授指出:“禁忌也不是法益,因此不應該用刑法手段對它加以保護。……比如,如果已成年的哥哥和妹妹彼此同意并相互開始實施性行為,盡管不清楚它產生了什么損害,但是根據德國法并在國際上,亂倫經常受到刑罰處罰。……這個規定保護的是一種從人類公有化的原始時代流傳下來的禁忌,這種禁忌并不取決于刑法是否禁止,即便是在如今還是受到尊重,但是,就像在啟蒙時代所認識到的,對于它進行刑法上的保護并沒有充分的根據。”〔7〕[德]克勞斯?羅克辛:《刑法的任務不是法益保護嗎?》,樊文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19 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6 頁。
在《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扒竊類型的盜竊后,國內有學者從“貼身禁忌”的角度解釋扒竊行為不法內涵的提升根據。亦即,扒竊行為觸犯了一種法理和社會觀念上的“貼身禁忌”。“這種貼身禁忌,是指未經允許或缺乏法律根據,不得侵入他人的貼身范圍。這里強調的是人的身體的隱私和尊嚴。每個人的貼身范圍都是一個禁忌空間,在法律秩序上,這也是人身權和人格權的一部分。恰恰在這一點上,表現出扒竊與其他普通盜竊的區別之處,扒竊行為在打破他人占有取走財物這個所有盜竊行為共有的財產危害性之外,多出了一塊侵入他人貼身空間、違反貼身禁忌的危害性,因此,不計數額,也可以定罪。”〔8〕車浩:《“扒竊”入刑:貼身禁忌與行為人刑法》,載《中國法學》2013 年第1 期,第118 頁。
另有觀點認為,扒竊行為違反貼身禁忌仍舊只是一種表象,貼身禁忌的背后旨在對被害人人身及貼身財物提供前置性保護,因為違反貼身禁忌而取得被害人貼身財物的行為除侵犯一定的財產法益外,還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并由此導致被害人及其他人產生無法控制財物的緊迫危險感。〔9〕參見熊亞文:《盜竊罪法益:立法變遷與司法抉擇》,載《政治與法律》2015 年第10 期,第63 頁。
上述兩種觀點雖然并不完全對立,但仍然存在區別:前一觀點重視扒竊行為觸犯了貼身禁忌,同時認為貼身禁忌強調的是人的身體的隱私和尊嚴;后一觀點強調扒竊行為是否侵犯了貼身禁忌背后的某種法益,并對此持肯定態度,亦即,扒竊行為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權利與一般人對財產的安全感。
本文的基本觀點是,禁忌本身不能作為保護法益,至于違反禁忌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則是另一回事。如同道德本身不能作為保護法益,但違反道德的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是另一回事。其實,有關刑法能否強制推行禁忌或道德的議題并沒有明顯的意義,刑法不可能因為某種行為違反了禁忌或道德,就將這種行為規定為犯罪。但不能否認的是,違反禁忌與道德的行為既可能侵犯了法益,也可能沒有侵犯法益。所以,核心的問題不在于行為是否違反了禁忌或道德,而在于行為是否侵犯了法益。〔10〕此外,禁忌與道德并沒有明確的范圍。亦即,刑法有時在外觀上保護某種禁忌或道德,只不過是在保護法益的過程中產生的反射效果。沒有違反禁忌或道德的行為,完全可能因為侵犯了法益而被規定為犯罪;反之,違反了禁忌或道德的行為,完全可能由于沒有侵犯法益而不被規定為犯罪。所以,不能將禁忌或者道德本身作為保護法益,不能將貼身禁忌作為扒竊犯罪的保護法益的內容之一,也沒有必要通過貼身禁忌來說明扒竊犯罪的保護法益。換言之,即使將人身權作為扒竊犯罪的保護法益,似乎也沒有必要通過貼身禁忌來說明。因為提升扒竊行為不法程度(對人身權或人格權的侵犯)的是“貼身”,而不是對“禁忌”的違反。
(二)安全感能否作為保護法益?
有學者認為,風險社會使人們容易產生對危險的恐慌感,且該恐慌感會迅速蔓延,故國民的安全感也值得刑法保護。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就是以國民的安全感作為保護法益的。〔11〕參見呂英杰:《風險刑法下的法益保護》,載《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3 年第4 期,第32 頁。還有觀點認為,高空拋物罪所保護的法益是被害個體不會隨機“被選擇”至行為人實施高空拋物而產生的被害領域內的“安全感”。〔12〕參見張梓弦:《〈刑法修正案(十一)〉的法教義學檢視——以“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為切入點》,載劉艷紅主編:《東南法學》(第4 輯),東南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170-171 頁。另有觀點認為,所謂公共安全等安全訴求是指法益主體能夠安心支配使用其人身、財產等法益的狀態,但法益主體會因為法益何時受損的不確定而擔憂,進而產生集體恐懼,刑法保護公共安全正是要除去集體恐懼。高空拋物行為造成了集體恐懼,應當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13〕參見姜濤:《高空拋物罪的刑法教義學分析》,載《江蘇社會科學》2021 年第5 期,第113-115 頁。本文不贊成將安全感作為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觀點。
第一,公共安全是公認的保護法益,但公眾的安全感不等于公共安全,也不屬于公共安全的范疇。因為對公共安全的侵犯,意味著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身體等面臨著現實的危險,但公眾產生不安全感不等于其生命、身體等存在現實的危險。所以,“維護公共安全不等于維護公共安全感,刑法的任務是讓社會共同生活成為可能,而不是讓社會大眾感到心情愉快。單純的以穩定群眾的集體意識狀態作為刑法的目的任務,將會使犯罪行為對于公民共同生活的侵害意義從社會性層面遁入心理學的層面,而錯失了法的原初意涵”。〔14〕周漾沂:《論“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之處罰理由》,載《臺大法學論叢》2008 年第4 期,第364 頁。
第二,公眾對現代風險與其他危險的恐懼或不安全感,不是依靠刑法就可以消除的。因為恐懼是一種情緒,是獨立個體的感覺,具有明顯的主觀性。一方面,“人的想象力會極大地增加人類社會中恐懼的種類和強度……我們知道或者懂得的越多,我們的擔心與憂慮就會越多。如果我們知道的不是那么多,我們也就較少會感到焦慮或恐懼……如果我們想象較少,我們就會感到更加安全……人所獨有的形而上恐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被緩和。”〔15〕[美]段義孚:《無邊的恐懼》,徐文寧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第4頁。所以,刑法根本不可能保護人們的安全感,或者說不能消除人們的恐懼感。另一方面,“‘安心感’這種社會心理,是受到媒體與時代風潮強烈影響而形成的不安定感覺,未必存在合理根據。在國民的不安欠缺客觀事實佐證的場合,能夠消除這種不安的有效方法不是刑事立法,而是對真實事實的報道。”〔16〕松原芳博『刑法総論(第3 版)』(日本評論社,2022 年)22 頁。既然刑罰不可能成為保護安全感的有效手段,就不能將安全感作為刑法上的保護法益。
第三,刑法規定的投放虛假危險物質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與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以“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為要件,但致使國民產生不安全感并不符合這一要件。根據2013 年9 月18 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 條的規定,下列情形屬于“嚴重擾亂社會秩序”:“(一)致使機場、車站、碼頭、商場、影劇院、運動場館等人員密集場所秩序混亂,或者采取緊急疏散措施的;(二)影響航空器、列車、船舶等大型客運交通工具正常運行的;(三)致使國家機關、學校、醫院、廠礦企業等單位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活動中斷的;(四)造成行政村或者社區居民生活秩序嚴重混亂的;(五)致使公安、武警、消防、衛生檢疫等職能部門采取緊急應對措施的;(六)其他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這充分說明,僅給一般人造成不安全感的行為并不構成犯罪,只有給現實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造成嚴重混亂的,才成立犯罪。不安全感存在不同的內容或情形,只有當不安全感促使人們為了避免危險的現實化,而不得不采取各種避免措施,從而擾亂了人們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時,才需要刑法保護。所以,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不是安全感本身,而是正常的工作、生產、生活秩序。〔17〕參見張明楷:《高空拋物案的刑法學分析》,載《法學評論》2020 年第3期,第20-21 頁。
第四,高空拋物行為也不是僅因侵犯了人們的安全感而被規定為犯罪,更不是由于危害了公共安全就被規定為犯罪。這是因為,如果說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是人們的安全感,就沒有理由以情節嚴重為要件;將情節嚴重作為要件,表明必須根據高空拋物行為對他人的生命、身體、財產的危險程度來決定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刑法沒有將本罪規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也是因為高空拋物行為不可能給多數人的生命、身體、財產造成危險,更不會導致危險難以控制,但不能因此否認高空拋物罪是對生命、身體、財產的抽象危險犯。如果認為安全感是保護法益,就意味著沒有被任何人發現的高空拋物行為,即使造成了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的危險,也不構成犯罪,但這一結論難言妥當。換言之,高空拋物罪的保護法益實際上是公民的生命、身體、財產的安全,〔18〕參見黃永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立法背景與條文解讀》(下冊),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777 頁。但并沒有滿足公共安全法益的條件,且具有復合性,而不只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所以,刑法才將本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五,如果說安全感是保護法益,那么,幾乎所有的犯罪所侵犯的法益都是復合法益。這是因為,如果說投放虛假恐怖物質的行為侵犯了一般人的安全感,現實發生的所有恐怖活動犯罪就都更為嚴重地侵犯了一般人的安全感。不僅如此,其他犯罪也同樣會侵犯一般人的安全感。于是,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除了生命、身體之外,還包括一般人的安全感。這可能不合適。〔19〕關于安全感不能成為保護法益的觀點,另參見劉炯:《法益過度精神化的批判與反思——以安全感法益化為中心》,載《政治與法律》2015 年第6 期,第72 頁以下。
(三)信賴能否成為保護法益?
信賴能否成為保護法益,需要聯系信賴的內容展開討論。例如,關于受賄罪的保護法益,以職務行為的公正性為中心的學者可能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以及國民對該公正性的信賴。〔20〕參見井田良『講義刑法學?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634 頁。以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為中心的學者也可能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以及國民對該不可收買性的信賴。〔21〕參見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146 頁以下。
問題在于,上述公眾對職務行為的公正性或不可收買性的“信賴”本身是不是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國內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認為,“將‘信賴’這種內容模糊、主觀色彩濃厚的要素作為保護法益,則和廉潔性說并無明顯的高下之分。”〔22〕黎宏:《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69 頁。日本有學者認為,對職務公正性的信賴并不是獨立的保護法益。〔23〕參見山口厚 『刑法各論(第2 版)』 (有斐閣,2010 年)611 頁、松原芳博 『刑法各論(第2 版)』 (日本評論社,2021 年)620 頁。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國民對職務行為符合人民利益的信賴,其作為社會成員共同生活的必要條件而存在,是值得刑法保護的獨立法益。”〔24〕陳勁陽:《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基于“信賴說”的批判與反思》,載《法律科學》2022 年第6 期,第155 頁。
不可否認的是,個人的自由建立在各種合理信賴的基礎上。例如,一個人敢于深夜在大街上行走,是因為信賴其他人會遵守法律,而不會侵犯自己的法益。再如,“當一個人坐上一輛車,便進入了一系列充斥專門知識的環境,包括汽車設計和制造、高速公路、交通信號等,他知道駕駛汽車有危險,承擔著發生事故的風險,但他信賴上述專業系統能夠保證事故的發生率降到最低點。”〔25〕[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11 年版,第82 頁。按照盧曼的觀點,信賴是人們在復雜的世界中發展出的有效簡化復雜性的方式。如果不存在信賴關系,人們就無法面對世界的復雜性。〔26〕參見[德]尼克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瞿鐵鵬、李強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3 頁。更為重要的是,信賴并不是單純的主觀感受,而是國民對相對方的要求與權利。〔27〕這是信賴與安全感的重要區別之一。此外,信賴是針對特定對象而言,而安全感并不針對特定對象;安全感是因人而異的,而信賴是國民的一致要求與權利。例如,國民對法官公正審判的信賴,其實是對法官公正審判的要求。進一步而言,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都以國民的信賴為前提。正因為如此,國民的信賴可能成為公共法益。雖然不可能將國民的任何信賴都作為法益予以保護,但至少部分信賴是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
國民對國家制度的功能運轉的信賴,是個人實現其基本權利與全面發展的基本前提,應當作為刑法上的保護法益。我國憲法第27 條第2 款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國家工作人員必須依靠人民的支持,經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聯系,傾聽人民的意見和建議,接受人民的監督,努力為人民服務。”易言之,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必須得到國民的信賴,其中,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與公正性就是國民信賴的內容。賄賂犯罪卻“腐蝕政權與管理的基礎,瓦解國家政權與管理在居民心中的威信,嚴重地侵犯公民的合法權利和利益”。〔28〕俄羅斯聯邦總檢察院編:《俄羅斯聯邦刑法典釋義》(下冊),黃道秀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 年版,第802 頁。所謂“瓦解國家政權與管理在居民心中的威信”就是使人民對國家政權與管理喪失信賴。反過來說,人民對國家政權與管理的合理信賴,就是值得保護的法益。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就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的公正性,以及國民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不可收買性的信賴。〔29〕參見張明楷:《刑法學》(下)(第6 版),法律出版社2021 年版,第1613-1615 頁。
再如,國民對國家金融體制的功能運轉的信賴,也是值得刑法保護的法益。貨幣、金融票證以及信用卡的存在,代表人們信賴支撐貨幣背后的金融體制。市場主體不使用現金而通過金融機構的支付系統進行交易,是因為買賣雙方信賴金融機構的支付系統。“在刑法上來看,這些制度性事實,正是社會或國家等超個人法益保護的實質對象。”〔30〕許恒達:《資訊安全的社會信賴與刑法第三五九條的保護法益——評士林地方法院九十九年度訴字第 一二二號判決》,載《月旦法學雜志》2011 年11 月(總第198 期),第242 頁。偽造、變造貨幣、金融票證、信用卡的行為,損害了這些金融手段的公共信用,也動搖了人們對金融體制的功能運轉的信賴。
(四)意志活動自由能否成為保護法益?
眾所周知,許多國家刑法都規定了強制罪(強要罪)與脅迫罪。前者是指以暴力、脅迫方法,強迫他人為一定之作為、容忍或不作為的行為;后者是指以加害于他人或與其有密切關系的人的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相通告,威脅他人的行為。這兩種罪的保護法益就是他人的意志(或意思)活動自由,包括意志決定的自由與意志實現的自由。〔31〕參見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各論(第7 版)』(弘文堂,2018 年)75 頁、井田良『講義刑法學?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142 頁。
國內有學者主張將意志活動自由作為刑法上的保護法益。因為意志自由是生命、身體之外的獨立的利益,對個人而言極為重要。個人日常生活的平穩進行,是以個人具有意志自由為前提的。換言之,在個人自治的法益概念下,公民的意志自由是確定法益的基礎,對公民意志自由的保障本為法益保護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刑法應當設立強制罪、脅迫罪等罪名以保護國民的意志活動自由。〔32〕參見李立眾:《暴行入罪論》,載《政法論壇》2020 年第6 期,第36-37 頁;王鋼:《論刑法對意志自由的保護——增設強制罪的立法建議》,載《政法論壇》2020 年第6 期,第17 頁以下。
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的起草過程中,“有的意見認為,強制、暴行等行為的內涵不明確,容易造成打擊面擴大,甚至成為新的口袋罪”。〔33〕許永安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解讀》,中國法制出版社2021 年版,第313 頁。言下之意,如果用刑法來保護意志活動自由,就會導致打擊面擴大;反過來說,意志活動自由不值得刑法保護。
本文贊成將意志活動的自由作為刑法的保護法益。最基本的理由是,如果沒有意志活動自由,就不可能基于自己的意志做出某種決定,也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意志,因而不可能有行動自由,不可能實現自己的其他權利與利益。〔34〕民國時的1935 年刑法就規定了強制罪(第304 條)、脅迫(恐嚇)罪(第305 條)、對尊親屬暴行罪(第281 條),我國現行刑法也有毆打、恐嚇等概念,難以認為“強制、暴行等行為的內涵不明確”。
我國刑法雖然沒有規定強制罪與脅迫罪,但意志活動自由事實上是受刑法保護的,或者說許多犯罪的保護法益包括了意志活動自由。一方面,刑法規定的強迫交易、強迫勞動、非法剝奪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暴力干涉婚姻自由、強迫賣血等罪,都是侵犯他人意志活動自由的犯罪。尋釁滋事罪與催收非法債務罪中的恐嚇行為,侵犯的也是他人的意志活動自由。此外,許多犯罪也附帶或者同時保護意志活動自由。例如,嚴格地說,搶劫罪的保護法益是財產和意志活動自由。當人們說,搶劫罪的保護法益是財產和人身權利時,其中的人身權利并不僅限于生命與身體健康。例如,行為人通過麻醉方式壓制他人反抗進而取得財物的,成立搶劫罪。〔35〕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500 頁。但這一行為并沒有侵犯被害人的生命與身體健康,只是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與意志活動自由。當然,我國現行刑法還不能全面地維護公民的意志自由,僅將部分強制行為規定為犯罪也造成了諸多解釋論上的難題,確有必要通過增設強制罪、脅迫罪來實現對公民意志自由的周全保護。〔36〕參見王鋼:《論刑法對意志自由的保護——增設強制罪的立法建議》,載《政法論壇》2020 年第6 期,第22 頁。
二、法益的特定性
法益的特定性,也可謂法益的專屬性,是指每個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都應當具有特定的內容,而不與其他犯罪的保護法益相混同。〔37〕當然,不能排除數個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的情形。例如,應當使故意殺人罪與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相區別,而不能用“人身權利”表述這兩個罪的保護法益。再如,應當使貪污罪與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相區別,不能認為這兩個罪的保護法益都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
法益的特定性,是貫徹罪刑法定原則與實現刑法目的要求。這是因為,犯罪的種類繁多,要實現罪刑法定原則,就必須對具體犯罪進行分類。如果刑事立法采取 “危害公共安全的,處……”“侵犯個人自由的,處……”這種過于抽象的規定方式,就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為越是抽象的規定,越會導致處罰范圍寬泛,從而侵害國民的自由。當今世界各國的刑事立法將具體法益(或者目的)作為設計具體犯罪的實質標準,進而根據保護法益設計構成要件,這便形成了法益的特定性。
法益的特定性,是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由于犯罪的本質是侵犯法益,行為侵犯的法益不同,其不法程度就不相同,所以,應當承認不同犯罪的保護法益并不相同。從刑事司法的角度來說,法定的特定性,有利于司法機關正確評價不法程度,正確處理此罪與彼罪的關系,妥當區分一罪與數罪,從而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例如,只有使綁架罪與搶劫罪的保護法益相區別,才能說明兩罪的不法程度與法定刑不同的根據。再如,“在立法者看來,有些法益需要數個罪名同時予以保護,有些法益只需要單獨一個罪名予以保護。后者就被賦予了專屬性的特點。雖然罪名的區分并不完全依賴于法益的性質,但一旦確認某個法益具有專屬性,其就成為罪名區分的一個維度。”〔38〕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載《法律科學》2018 年第2 期,第134 頁。又如,一個行為侵犯一個犯罪的保護法益與一個行為侵犯數個犯罪的保護法益,在罪數評價上并不相同;數個行為最終是否僅侵犯一個犯罪的保護法益,在罪數處理上也不相同。這些都是由法益的特定性決定的。
法益的特定性,也是實現刑法分則的體系化的要求。如果不按具體法益對犯罪行為進行分類,而是按行為方式規定具體犯罪,必然導致刑法分則條文的雜亂無章。而且按行為方式規定具體犯罪,既會形成處罰漏洞,也會導致構成要件喪失類型性。由于具體法益之上存在同類法益,所以,根據具體法益設計構成要件,能夠實現刑法分則的體系化。
從解釋論的角度來說,只有使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具有特定性,才有利于對構成要件進行合目的的實質解釋。關于具體犯罪保護法益的特定性,本文從反面提出以下兩個具體要求。
第一,此類犯罪中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不應當與彼類犯罪中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或者說,對一個具體犯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內容,不應與不同類法益的其他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例如,對侵犯人身權利罪中的具體犯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內容,不應與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經濟秩序罪、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中的某個或某些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同樣,對貪污罪、受賄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不應與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瀆職罪中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
在我國,危害國家安全罪、瀆職罪、軍人違反職責罪屬于侵犯國家法益的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屬于對社會法益的犯罪;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侵犯財產罪屬于對個人法益的犯罪。除了存在立法缺陷與社會重大變化的情形之外,解釋者應當尊重立法上的分類,不能以解釋者個人的價值判斷取代刑事立法的價值判斷。如果所確定的此類犯罪中某個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可以適用于彼類犯罪的某個或某些具體犯罪,就不符合法益的特定性要求。
有學者指出,“……法益對罪名的區分能力,并不是犯罪的硬性要求。按照德國刑法,即便處于不同章節的犯罪,其法益完全一樣者也屢見不鮮,例如重放火罪(屬于危害公共犯罪)與故意殺人罪(屬于針對生命的犯罪)保護法益都是(個體)生命”。〔39〕熊琦:《刑法教義學視閾內外的賄賂犯罪法益——基于中德比較研究與跨學科視角的綜合分析》,載《法學評論》2015 年第6 期,第126 頁。誠然,不排除處于不同章節的具體犯罪,其保護法益完全相同的情形,但不能以此為根據否認法益的特定性要求。德國的重放火罪與故意殺人罪雖然在保護個體生命這一點上有相同之處,但二者的保護法益并不完全相同。
概言之,根據法益特定性的要求,對此類犯罪中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內容的確定,如果與彼類犯罪中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內容相同,或者對此類犯罪中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的表述完全適用于彼類犯罪中的具體犯罪,則不符合具體法益的確定標準。
例如,有觀點認為,破壞生產經營罪的保護法益是“生產經營的經濟利益”。〔40〕柏浪濤:《破壞生產經營罪問題辨析》,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10 年第3 期,第43 頁。然而,這種觀點實際上將破壞生產經營罪理解為經濟犯罪,既導致破壞生產經營罪的保護法益漫無邊際,也導致這一保護法益可以適用于刑法分則第三章的許多經濟犯罪,因而使本罪的保護法益喪失特定性。
再如,有學者提出,受賄犯罪的法益是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其在不法構造上不以形成交易關系為必要。〔41〕參見勞東燕:《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載《法學研究》2019 年第5 期,第118 頁以下。但不可否認的是,貪污罪、非法經營同類營業罪、為親友非法牟利罪等諸多犯罪都表現為以公職謀取私利,都侵犯了公職的不可謀私利性。所以,這一表述導致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缺乏特定性。
又如,將普通受賄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職務行為的公正性,〔42〕參見黎宏:《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68 頁以下。其實也使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喪失了特定性,即導致受賄罪與濫用職權罪的保護法益相同,而且不能說明作為抽象危險犯的受賄罪的法定刑,〔43〕如果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就意味著受賄罪不是實害犯,而是抽象的危險犯。參見中森喜彥『刑法各論(第4 版)』(有斐閣,2016 年)306 頁;曾根威彥『刑法の重要問題〔各論〕(第2 版)』(成文堂,2006 年)380 頁;山中敬一『刑法各論(第3 版)』(成文堂,2015 年)835 頁。為什么重于保護法益相同的、實害犯的濫用職權罪的法定刑。〔44〕參見張明楷:《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載《法學研究》2018 年第1 期,第150 頁。同樣,認為“對受賄罪法益的解讀應著眼于個體對公權力平等對待自己的信賴”的觀點,〔45〕陳勁陽:《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基于“信賴說”的批判與反思》,載《法律科學》2022 年第6 期,第155 頁。也不能顯示受賄罪與瀆職罪保護法益的區別。反之,只有將普通受賄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不可出賣性)以及國民對此的信賴,才能使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具有特定性。
第二,同類犯罪中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大多并不相同,不能因為不同的具體犯罪同屬于某一類罪,就簡單地將同類法益確定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易言之,同類法益犯罪中的具體犯罪的法定刑并不相同,原因在于具體犯罪的不法程度存在差異,而不法程度的差異就是因為保護法益不完全相同。即使就刑法分則第二章與第五章的犯罪而言,也應當盡可能使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區別。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根據法條對構成要件的描述,盡可能使保護法益的內容具體化。反過來說,不能以同類法益的存在而否定法益的特定性。〔46〕參見孫國祥:《受賄罪的保護法益及其實踐意義》,載《法律科學》2018 年第2 期,第134 頁。
例如,一般認為,刑法分則第二章的危害公共安全罪是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身體與重大財產的安全,進而認為,其中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都與同類法益相同。但事實上并非如此。例如,放火罪與破壞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罪均屬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在將放火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身體、重大財產的安全時,就不能認為破壞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罪的保護法益與此相同。有觀點認為,“雖然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不直接危及生命、健康,但間接地影響著不特定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以及重大財產安全。因而,第124 條規定的犯罪,具有對公共安全的抽象的危險。”〔47〕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31 頁。然而,刑法第124 條將本罪明文規定為具體危險犯,既然如此,就不能將對生命、健康的抽象危險作為本罪的處罰根據。況且,認為破壞廣播電視設施的行為均存在對生命、健康的抽象危險,也存在明顯的疑問。即使承認“廣播電視設施、公用電信設施是公眾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信息傳遞設備,一旦這些網絡被破壞,信息傳遞受阻,就有可能在公共領域造成具體的危險或重大的損失”,〔48〕同上注。也不可能一概將這些損失歸屬于破壞行為。只有承認公眾生活的平穩與安寧屬于公共安全的內容,才能妥當地解釋刑法第124 條屬于具體危險犯,也能使本罪與放火、爆炸等罪相區別,還能說明本罪與放火、爆炸等罪的法定刑差異。
再如,有的教科書指出,強制猥褻、侮辱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人格尊嚴與人身自由權利”。〔49〕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472 頁。可是,這樣的法益并不只是強制猥褻、侮辱罪所特有,或者說,這樣的表述實際上囊括了刑法分則第四章的大部分犯罪的保護法益。例如,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拐賣婦女、兒童罪等都可謂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尊嚴與人身自由權利。認為強制猥褻、侮辱罪的法益是“他人的人格尊嚴與名譽權利”的觀點,〔50〕郭自力主編:《中國刑法論》(第7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22 年,第375 頁。不僅存在同樣的問題,而且導致本罪與侮辱罪的保護法益相同。只有將強制猥褻、侮辱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他人的性自主權,才能體現本罪法益的特定性。〔51〕或許有人認為,這一表現也未能區分強制猥褻罪與強奸罪的保護法益。其實,強制猥褻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性行為自主權,強奸罪的保護法益是婦女的性行為自主權,而且,兩罪中的性行為的含義不完全相同,只不過難以在保護法益中表述出來,只能通過構成要件予以表述。
又如,刑法分則第五章的同類法益雖然是財產,但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并不完全相同。例如,盜竊罪與侵占罪的保護法益明顯不同,不能用財產所有權來表述兩罪的保護法益。這是因為,就對象為狹義財物的情形而言,雖然侵占罪的保護法益是財產所有權,但盜竊罪的保護法益還包括一定的占有,否則就難以解釋為什么盜竊違禁品的行為也構成盜竊罪。所以,將盜竊罪與侵占罪的保護法益均表述為“公私財產所有權”的觀點,〔52〕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505、514 頁。難言妥當。僅就狹義財物而言,如若將侵占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所有權,而將盜竊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本權及一定情形下的占有,可能更為合適。
不可否認的是,同類法益中的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也可能完全相同。在這種情形下,需要說明刑法分則為什么將侵犯相同法益的行為規定為不同的罪名。如果得不到合理說明,則需要考慮保護法益是否不同。
例如,刑法第114 條所規定的五個犯罪的保護法益完全相同,故規定了相同的法定刑。刑法也完全可以用五個法條分別規定這五種犯罪,只是為了節省法條才由同一法條規定。另一方面,刑法第114 條的保護法益與第115 條的保護法益也相同,但由于前者是危險犯后者是實害犯,所以,后者的法定刑重于前者。
再如,盜竊罪與詐騙罪的保護法益是否相同,是存在爭議的問題。倘若說盜竊罪與詐騙罪的行為對象不同,即前者僅限于有體物,后者不僅包括有體物,而且包括債權等財產性利益,那么,二者的保護法益就必然不同。反之,如果認為二者的行為對象相同,即均包括有體物與財產性利益,則需要判斷二者對財產“損失”的要求是否不同。如果認為盜竊罪是對個別財產的犯罪,詐騙罪是對整體財產的犯罪,則對二者的保護法益不可能作相同表述。如果認為兩者都是對個別財產的犯罪或者都是對整體財產的犯罪,則不排除對二者的保護法益作相同的表述。
三、法益的融洽性
法益的融洽性,是指對具體犯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能夠與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不法程度相融洽,從而使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保持協調一致,而不存在任何例外。〔53〕本文不使用“融貫性”概念,是因為“只有少數無法說明的異常狀況”仍然滿足融貫性的要求(參見侯學勇:《佩策尼克的融貫性理論研究》,載陳金釗、謝暉主編:《法律方法》(第7 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180 頁),但本文主張,刑法理論所確定的保護法益不能存在一個無法說明的異常狀況。
(一)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的融洽
臺灣地區學者指出:“一切犯罪之構成要件系針對一個或數個法益,構架而成。因此,在所有之構成要件中,總可找出其與某種法益的關系。換言之,即刑法分則所規定之條款,均有特定法益為其保護客體。”〔54〕林山田:《刑法特論》(上冊),三民書局1978 年版,第6 頁。雖然刑法理論需要從構成要件的表述中發現保護法益,但在妥當地確定了保護法益之后,就必須以保護法益為指導解釋構成要件。
由于構成要件是違法類型,違法的實質是侵犯法益,所以,對保護法益的確定必須與法條描述的構成要件相融洽。保護法益與構成要件融洽的基本標準是,理論上能夠對所有的構成要件要素做出妥當的解釋,實踐上所有符合構成要件且不具備違法阻卻事由的行為都沒有例外地侵犯了該保護法益。反之,如果所確定的A 罪的保護法益在理論上不能說明所有的構成要件要素,或者實踐中完全符合A 罪構成要件的行為并沒有侵犯A 罪的保護法益,就表明對A 罪保護法益的確定存在缺陷;同樣,如若對A 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并不能包含應當作為A 罪處罰的全部情形,也表明該保護法益的確定存在問題。概言之,對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的確定,必須不存在無法解釋的異常現象或例外情形。但我國刑法理論對某些犯罪所確定的保護法益就存在這方面的缺陷。
例一:一種觀點認為,“洗錢罪侵害的客體應該是國家金融管理秩序。將國家金融管理秩序作為洗錢罪的客體,是由洗錢罪的立法歸類決定的。”〔55〕劉憲權:《金融犯罪刑法學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426 頁。但這種觀點不能說明為什么洗錢罪的上游犯罪僅限于七類犯罪。顯然,只有將上游犯罪的保護法益本身也作為洗錢罪的保護法益,〔56〕參見西田典之編『金融業務と刑事法』(有斐閣1997 年)84 頁。才能說明這一點。〔57〕參見張明楷:《洗錢罪的保護法益》,載《法學》2022 年第5 期,第69 頁以下。
例二:有學者認為,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保護法益是“低齡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權”。〔58〕參見付立慶:《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保護法益與犯罪類型》,載《清華法學》2021 年第4 期,第79-80 頁。果真如此的話,本罪的保護法益就與強奸罪相同。可是,本罪的構成要件內容只是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員與未成年女性發生性關系,強制手段不是本罪的構成要件要素,即使未成年女性完全同意與負有照護職責的人員發生性關系,也不影響本罪的成立。這表明,沒有侵犯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權的行為,也能成立本罪,故不能將性自主權作為本罪的保護法益。有學者為了維護性自主權說,主張即使未成年女性同意,也擬制為侵害了性自主權。〔59〕同上注,第79-81 頁。但是,這種擬制觀點不能說明,為什么未成年女性對與其他人員發生性關系的同意卻是有效的。換言之,刑法實際上承認已滿14 周歲的未成年女性具有同意能力,否則就會提高奸淫幼女犯罪的同意年齡,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在上述同意無效的情形下,顯然不能將性自主權作為保護法益。況且,一方面認為本罪立法擬制了對被害人性自主權的侵害,同時又認為本罪是抽象危險犯,就有自相矛盾之嫌。另有學者為了維護性自主權說,通過援引對基于照護職責而產生的優勢地位的濫用或者隱性強制等因素,來說明行為人的行為實質上違背了未成年女性的意志。〔60〕參見周詳、孟竹:《隱性強制與倫理禁忌:“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理據》,載《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 年第2期,第98 頁以下。但這實際上是自行添加了構成要件要素。眾所周知,日本刑法第180 條規定的監護者性交等罪與第177 條規定不同意性交等罪的法定刑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監護者性交等罪要求現實監護的人乘有影響力之機與不滿18 周歲的人性交。在這種情形下,未滿18 周歲的人如果反抗監護人的行為,就會擔心自己喪失監護人在物質上、心理上的保護,故不得不順從監護人的意志。〔61〕參見西田典之(橋爪隆補訂)『刑法各論(第7 版)』(弘文堂,2018 年)106 頁。在這一點上,監護人性交等罪與不同意性交等罪,便沒有實質區別。〔62〕參見姚培培:《論負有照護職責人員性侵罪的規范定位與不法內涵》,載張志銘主編:《師大法學》(第8 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 年版,第64-66 頁。但我國刑法第236 條之一規定的行為主體并不限于現實的監護人,而且法定刑明顯輕于強奸罪,既然如此,就不能在構成要件中添加強制要素,〔63〕添加“強制”這一構成要件要素,不能說明為什么本罪的法定刑明顯輕于強奸罪的法定刑。更不應通過添加強制要素論證本罪的保護法益是未成年女性的性自主權。反之,將本罪的保護法益界定為少女免受具有保護責任者性侵擾的性健全發展權,〔64〕參見張梓弦:《積極預防性刑法觀于性犯罪中的體現》,載《政治與法律》2021 年第7期,第54 頁。才能說明本罪是抽象危險犯,即成立本罪既不需要具體判斷行為是否違反少女的意志,也不要求行為人利用其身份優勢,這同時能說明本罪與強奸罪的法定刑的差別。
例三:有觀點認為,強制猥褻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性羞恥心,“所謂性羞恥心,是指婦女對于不正當暴露性器官、不正當性行為的羞恥感。”〔65〕馬克昌主編:《百罪通論》(上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版,第549 頁。但是,“即使被害人沒有感覺到性的羞恥心,有時也能認定犯罪的成立。例如,違背脫衣舞女的意志強制脫光其衣服的就是如此。”〔66〕林幹人『刑法各論(第2 版)』(東京大學出版會,2007 年)87-88 頁。如若堅持強制猥褻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羞恥心,同時要將這種情形認定為強制猥褻罪,就不得不推定被害人產生了羞恥心或者按一般人的觀念判斷被害人是否產生了羞恥心。但是,動輒對客觀事實進行推定,必然動搖刑事訴訟的基本原則;按一般人的觀念判斷導致強制猥褻罪成為對公共法益的犯罪,而非對個人法益的犯罪,難言妥當。
例四:有學者認為,綁架罪的“法益是被綁架者的身體安全和其親權者的保護監督權,有的情況下還包括他人的財產權”〔67〕周光權:《刑法各論》(第4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49 頁。。按照這一觀點,享有監護權的父母不能成為綁架自己親生子女的主體(因為沒有侵犯保護監督權),但這一結論可能并不合理。例如,犯下重大罪行的父母可能將親生子女作為人質,以達到不被警察逮捕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父母的行為沒有侵害保護監督權,但仍應被認定為綁架罪。顯然,上述觀點導致完全符合構成要件且應當作為綁架罪論處的行為,卻并未侵犯綁架罪的保護法益,因而存在疑問。
例五:傳統觀點認為,盜竊罪的保護法益是“公私財產所有權”。〔68〕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505 頁。據此,對財產的占有以及債權就不是盜竊罪的保護法益。于是,一方面,盜竊毒品等違禁品的行為就因為占有者及其他人對之不享有所有權,因而不構成盜竊罪,但事實上并非如此。〔69〕2013 年4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盜竊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2013〕8 號)第1 條第4 款規定:“盜竊毒品等違禁品,應當按照盜竊罪處理的,根據情節輕重量刑。”反過來說,如果認為盜竊毒品等違禁品的行為仍然構成盜竊罪,就表明將盜竊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公私財產所有權”存在缺陷。同樣,根據上述傳統觀點,所有權人從其他合法占有者那里取得財物的任何行為,也都不可能成立財產罪。這顯然難以被接受。另一方面,如果認為盜竊債權等財產性利益的行為構成盜竊罪,〔70〕例如,將他人微信零錢轉入自己的微信的行為構成盜竊罪。那么,將盜竊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公私財產所有權”也存在明顯的漏洞。
例六:有學者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職務行為的公正性。〔71〕參見黎宏:《受賄犯罪的保護法益與刑法第388 條的解釋》,載《法學研究》2017 年第1 期,第68 頁以下。“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實施了適正的(或者至少在公務員的裁量范圍內)職務行為后才接受賄賂的(即使與職務行為的關聯性是明確的),也就不可罰了。因為在這種場合,不能認定具有侵害職務行為的適正性的危險性。”〔72〕參見井田良『講義刑法學?各論(第2 版)』(有斐閣2020 年)635 頁。換言之,將受賄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職務行為的公正性,導致部分應當認定為受賄罪的行為被排除在構成要件之外,因而難言妥當。
(二)保護法益與不法程度的融洽
根據法益侵害說,受侵犯的法益的重要程度不同以及受侵犯的程度不同,決定了不法程度的差異。例如,一般來說,故意傷害罪(不包括傷害致死)的不法程度輕于故意殺人罪,這是因為生命法益重于身體法益。再如,故意殺人既遂的不法程度重于故意殺人未遂的不法程度,這是因為兩種情形對生命的侵犯程度不同。由于法益的重要性不同決定了不法程度的不同,所以,對保護法益的確定必須與犯罪的不法程度相一致。
總的來說,由于法益存在位階區別,在重罪與輕罪的責任形式相同的情形下,法定刑較重犯罪的保護法益不應與法定刑較輕犯罪的保護法益相同,更不能輕重倒置,使輕罪保護法益的位階高于重罪的保護法益。從我國刑法理論的現狀來看,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以下難言妥當的現象:A 罪與B 罪的法定刑相同(或者B 罪的法定刑更低),將A 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a 單一保護法益,而將B 罪的保護法益確定為a+b 復合法益。
例如,傳統觀點認為,受賄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貪污罪則“既侵犯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廉潔性,也侵犯公共財產的所有權”。〔73〕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643、634 頁。既然受賄罪只侵犯職務廉潔性一個法益,而貪污罪除此之外另侵犯了財產所有權,就表明貪污罪的不法程度明顯重于受賄罪,對貪污罪的處罰就必須明顯重于受賄罪,但我國刑法并非如此。這充分說明,傳統觀點所確定的受賄罪與貪污罪的保護法益存在缺陷。
再如,傳統觀點認為,故意殺人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生命權利”,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的身體健康權”,非法行醫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對醫務工作的管理秩序和就診人的生命、健康權利。”〔74〕同上注,第460、464、589 頁。據此,非法行醫罪的保護法益比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的保護法益還多出一個秩序法益,但法定刑卻低于后者,這就明顯不協調。同樣,傳統觀點認為,保險詐騙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的保險管理秩序和保險人的財產所有權”,詐騙罪的保護法益是“公私財產的所有權”。〔75〕同上注,第427、509 頁。這種使前罪的保護法益多于后罪的保護法益的觀點,難以說明前罪的法定刑低于后罪的法定刑的刑法規定。
不可否認的是,法益的融洽性要求,實際上在保護法益(法條目的)與構成要件之間形成了一種循環,但這一循環并不異常。“正確的解釋,必須永遠同時符合法律的文言與法律的目的,僅僅滿足其中一個標準是不夠的。”〔76〕Roxin/Greco,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Bd.I, 5.Aufl., C.H.Beck 2020, S.223.既然要滿足法律的文言與法律的目的,就意味著二者必然具有內在的一致性。
四、法益的可判斷性
近年來,不少學者認為法益的精神化越來越明顯,導致法益被理解為不能出現在因果判斷中的現象。例如,Honig 對法益概念進行了社會科學的觀察,認為因果法則只能適用于行為對象,而不能適用于法益。Schmidh?user 認為,因為受到威脅的只能是具體的行為對象,而非精神意義上的要求,所以只存在對法益的損害,而無對法益的威脅。Sax 在使用“抽象的價值”或者“精神上的事實”等術語時,則認為它們只能受到威脅。〔77〕參見楊萌:《德國刑法學中法益概念的內涵及其評價》,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6 期,第67 頁。
“然而,一個精神上的法益論是沒有效用的,‘因為不可觸及的精神或者一個永恒的價值是免于損害的,因為它不可能受到行為人的直接侵害’〔78〕R.Hefendehl,Kollektive Rechtsgüter im Strafrecht, K?ln, 2002.S.29——原文注釋。。……只有將法益理解為現實的、可以在因果關系中受到改變的對象或者事實——不管它們是否具有物質的屬性——才能談的上對法益的損害或者威脅。”〔79〕參見楊萌:《德國刑法學中法益概念的內涵及其評價》,載《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 年第6 期,第67-68 頁。只要承認犯罪的本質是對法益的侵害與威脅,就要求法益能夠出現在因果判斷中的現象。保護法益是否受到侵犯以及受侵犯的程度如何,是司法機關在個案中都必須判斷的,即使是抽象危險犯,也并非一概不判斷。〔80〕參見張明楷:《抽象危險犯:識別、分類與判斷》,載《政法論壇》2023 年第1 期,第72 頁以下。如果法益缺乏可判斷性,就意味著不能判斷行為是否侵害或者威脅了法益,法益就成為沒有意義的東西,犯罪的認定也便喪失了實質依據。另一方面,法益具有構成要件解釋的指導機能,如果所確定的法益讓人捉摸不定,就不可能用其指導構成要件的解釋。
法益概念的屬性是經驗的實在性以及對人的有用性。〔81〕參見松原芳博「刑事違法論と法益論の現在」『法律時報』第7 號(2016 年)26 頁。要使法益具有可判斷性,前提是只能將具有經驗的實在性的利益與狀態作為保護法益。如果不是人們能夠感覺出來的客觀存在,就不能作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除此之外,應當注意如下幾點。
第一,法益內容不應過于抽象化,而應相對具體。
與行為對象相比,法益的確比較抽象。但正如Roxin 教授所言:“若保護的對象抽象得無法讓人把握,則該對象也不能被看做是法益。”〔82〕[德]克勞斯?羅克辛:《對批判立法之法益概念的檢視》,陳璇譯,載《法學評論》2015 年第1 期,第58 頁。在本文看來,所謂抽象得無法讓人把握,主要有兩種情形:
一是將具體犯罪的法益內容進行高度概括或抽象,進而使其既過于宏觀(成為同類法益),也喪失特定性,導致難以判斷。
例如,日本有學者認為,性犯罪侵入本應隱秘的性領域并迫使對方公開該領域的行為,侵害了人格的統合性、人的尊嚴。〔83〕參見辰井聡子「『自由に対する罪』の保護法益―人格に対する罪としての再構成」巖瀬徹ほか編『刑事法?醫事法の新たな展開(上巻)』(信山社,2014 年)411 頁以下。雖然人的尊嚴也具有經驗的實在性,但這種高度的抽象,導致在具體案件中難以判斷法益是否受到侵害,結局要么導致性犯罪成為抽象危險犯,要么只能推定被害人的人格、尊嚴受到了侵害。
再如,在我國,將公共秩序作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也是一種過度歸納的表現。所謂秩序就是一種有規范的狀態,受規范者依照規范的指示而行動,并且信賴按規范所欲造成的事實狀態而行動,整體而言就會形成秩序。而刑法和其他法規本身自然也是形成秩序的規范,其當然具有公共性。因此,整體法規范的存在就是為了架構出一定程度的公共秩序,其前提是規范具有效力,規范被違反時必須以強制力加以回應。既然法的目的本來就是維護公共秩序,那么再建立一個名為公共秩序的集體法益由某個或某幾個具體犯罪加以保護,似乎并沒有必要。〔84〕參見周漾沂:《論“煽惑他人犯罪或違背法令”之處罰理由》,載《臺大法學論叢》2008 年第 4 期,第361 頁。況且,公共秩序由具體領域、具體場所、具體行業的秩序組成,刑法理論應當根據構成要件的表述將公共秩序、市場經濟秩序予以具體化,使之成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
同樣,將人身自由、人身權利表述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也過于抽象。換言之,人身自由、人身權利只是類罪的保護法益,需要按照具體犯罪的規定予以具體化的表述。
二是對具體犯罪法益內容的表述過于抽象,讓人不能明確其具體內涵,因而無法判斷。
例如,一般認為,濫用職權罪的保護法益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85〕參見高銘暄、馬克昌主編:《刑法學》(第10 版),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版,第658-661 頁;黎宏:《刑法學各論》(第2 版),法律出版社2016 年版,第545 頁。“正常管理活動”過于抽象,人們難以知道這一表述是指行為人本身進行了不正常的管理活動,還是行為人的行為導致其他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管理活動異常,抑或是導致國家機關的管理活動本身異常。事實上,“正常”與否取決于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是否合法、公正。換言之,所謂“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也只是意味著,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根據憲法與法律的規定,在執行國家對內、對外職能,管理國家事務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保持其職務活動的合法性與公正性。〔86〕參見周光權:《刑法各論》(第4 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1 年版,第571 頁。既然如此,不如將濫用職權罪的保護法益表述為職務行為的合法性與公正性。
第二,法益內容不應是模糊的,而應是清晰的。
由于保護法益具有指導構成要件解釋的機能,故法益內容應當是清晰的,而不能是模糊不清的。即使是選擇性的保護法益,也必須事先確定可供選擇的保護法益是什么法益,而不能由犯罪行為隨機選擇確定保護法益,否則就明顯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例如,有觀點認為,“妨害興奮劑管理罪所侵犯的體育法益包含國家形象”。理由在于:從實然的角度講,法益概念抽象化與精神化已經成為客觀事實;國家形象并非不能還原為個人法益,因為國家形象仍然關系著每個國家公民個體的歸屬感與榮譽感;認為本罪法益包含國家形象,有利于解釋為何將“國內、國際重大體育競賽”作為入罪的限制條件。〔87〕劉杰:《妨害興奮劑管理罪侵犯的法益包含國家形象》,載《人民法院報》2022 年9 月8 日,第6 版。
可是,體育法益與國家形象都是不清晰的概念。一般人雖然對國家形象會有模糊的感覺,但在許多情形下如何判斷實為難題。在國際比賽中,如果使用興奮劑沒有被發現并取得了優異成績(如獲得冠軍),就贏得了國家形象,如果被發現則損害了國家形象。就此而言,損害國家形象不是因為使用興奮劑,是因為被發現。退一步說,即便使用興奮劑的行為損害了國家形象,也不過是本罪的附隨效果,因為許多犯罪都會有損國家形象。〔88〕參見李冠煜:《妨害興奮劑管理罪的爭議問題》,載《法學》2023 年第4 期,第49 頁。而且,按照上述觀點,行為人在“國內重大體育競賽”中犯本罪時,所損害的應當是某省的形象。此時,其所損害的究竟是省政府的形象還是全省人民的形象,抑或是其他機關的形象,恐怕是難以回答的。概言之,國家形象不可能成為某一個犯罪的保護法益。
再如,一種觀點認為:“由于刑法規定綁架的目的并非只為勒索財物,還可能是為了侵犯其他合法利益,因此,與搶劫罪不同,綁架罪不存在兩種特定的必然同時被侵犯的社會關系,或者說,除必然侵犯人身權利外,還同時侵犯什么社會關系是不確定的。”〔89〕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第5 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 年版,第783 頁以下。
上述觀點所稱的“侵犯什么社會關系是不確定的”,實際上是指綁架犯將他人作為人質會提出何種不法要求是不確定的,所以,本罪的保護法益由綁架犯的主觀目的來確定。然而,一個犯罪的保護法益是什么,是由立法機關決定的,而不可能是由犯罪人決定的。綁架行為可能同時侵犯財產與其他合法利益只是客觀事實,但不意味著財產與其他合法利益是綁架罪的保護法益。犯罪人只能決定侵犯何種法益,而不可能決定刑法分則的某個法條保護什么法益。易言之,上述觀點沒有明確區分法條的保護目的與案件的客觀事實。然而,不管是將客體作為構成要件,還是將保護法益作為目的,其內容必須是確定的,而不是隨具體案件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否則,就沒有罪刑法定原則可言。
第三,法益內容應盡量避免綜合性或混合性。
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內容應當盡可能是單一的,即使是復合法益(復雜客體),也必須是復數的單一法益。反過來說,如果法益內容具有綜合性或者混合性,就難以判斷。一方面,不應當用綜合性的概念表述法益內容,也不宜用多義性的概念表述法益內容(除非進一步確定了其中的具體含義)。另一方面,在行為直接侵害A 法益就必然間接侵害B 法益時,也沒有必要將B 法益作為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否則,任何犯罪的保護法益都具有復合性,這不利于司法機關的判斷。
例如,有學者認為,“將買賣人口犯罪保護的法益界定為直接被買賣之特定被害人與間接被冒犯的人類全體以人身不可買賣性為核心的人格尊嚴整體,才可能對買賣人口犯罪的不法進行充分評價。”〔90〕梁根林:《買賣人口犯罪的教義分析:以保護法益與同意效力為視角》,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22 年第4 期,第24 頁。這種觀點旨在說明被買賣者的同意不影響買賣人口犯罪的成立。
但是,尊嚴這個詞具有多種含義。例如,殺人罪中常常有“侵害了被害人生命的尊嚴”這樣的表述,但此時尊嚴這個詞所表達的含義是,生命這一法益極其重要,必須對其予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并不是為了表達超過侵害生命之上的法益侵害性。與此相對,也有以獨自的含義來把握侵害尊嚴的見解,例如,從女權主義的立場出發,有主張稱強奸是在以男性為核心的社會構造下,男性使女性服從自己權力的行為,侵害了女性的尊嚴。〔91〕[日]佐伯仁志:《日本的性犯罪》,曾文科譯,載陳興良主編:《刑事法評論》(第40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302頁。那么,認為拐賣婦女罪的保護法益是人格尊嚴整體的觀點,是為了表明人身不可買賣性這一法益更為重要,還是具有獨立的含義,可能需要進一步明確。另一方面,由于人格尊嚴整體包含諸多內容,所以,上述觀點不得不限定為人身不可買賣性的尊嚴。但既然限定為人身不可買賣性,似乎沒有必要再添加人格尊嚴整體的內容。否則,就意味著拐賣婦女的行為人同時侵犯了自己的人格尊嚴,自己也是間接的受害者。
再如,通說認為,“強迫交易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一方面破壞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另一方面侵害被強迫交易人的合法權益。”〔92〕王作富主編:《刑法分則實務研究》(中)(第5 版),中國方正出版社2013 年版,第700 頁。另參見阮齊林:《中國刑法各罪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 年版,第191 頁。
可是,雖然強迫交易罪規定在刑法分則第三章中,但本罪的成立以被害人不同意相關交易為前提。如果被害人同意與對方交易,則對方的行為不可能構成強迫交易罪。所以,本罪的保護法益是他人是否從事交易活動的意志活動自由。反之,如果行為人強迫被害人從事某種交易或者不從事某種交易,則必然侵犯了公平自由競爭的市場秩序。既然后一法益是否受到侵犯取決于前一法益,就沒有必要將后一法益作為強迫交易罪的保護法益。
第四,法益內容不應是可以隨意添加或者減少的。
由于保護法益是法條的具體目的,且指導構成要件的解釋與判斷,所以,法益內容必須是確定的,而不可以是隨意添加或者減少的。否則,就意味著構成要件不具有類型性,因而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則。
例如,有學者認為,使用興奮劑行為侵犯的是包括體育精神與體育秩序在內的“體育法益”。〔93〕參見賈健:《濫用興奮劑行為犯罪化研究》,載《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15 年第7期,第46 頁以下。可是,“體育精神說本質上是將抽象的精神具象化為公眾所能感受到的實體內容,但這會加劇刑法保護法益的稀薄化。”〔94〕徐挺笠、李勇:《妨害興奮劑管理罪的保護法益及行為構造》,載《中國檢察官》2021 年第7期,第28 頁。雖然《世界反興奮劑條例》定義了體育精神,〔95〕https://www.sport.gov.cn/n315/n20067006/c20256988/content.html,2023 年4 月10 日訪問。但體育精神的內容會不斷添加。2021 年3 月召開的國際奧委會第137 次全會,在奧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強”后面,增加了“更團結”(Together)。再如,2008 年奧運會的口號“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也可謂體育精神。將沒有邊際的體育精神作為一個具體犯罪的保護法益,不僅不具有可判斷性,而且沒有刑法學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