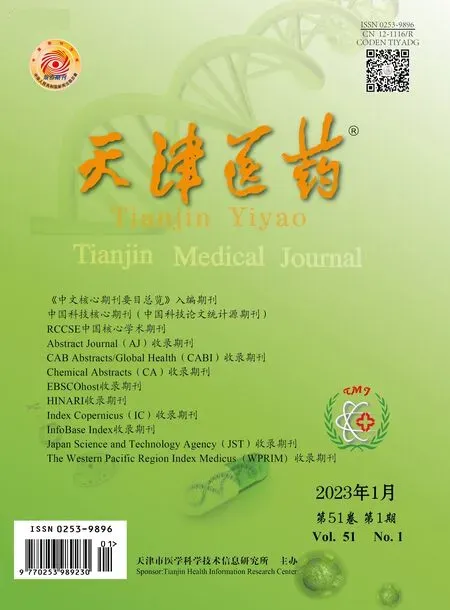重度支氣管發育不良早產兒下呼吸道分泌物分離菌的分布特點
谷名曉,劉選成,李躍,單若冰
隨著新生兒救治技術的不斷提高,超早產兒的存活率逐年上升,但支氣管肺發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的發病人數逐年增加,其中體質量<1 500 g的早產兒BPD 發病率達25%,嚴重影響了早產兒存活率及生存質量[1]。因此,如何減少重度BPD 的發生是目前國內外新生兒學科的研究熱點。BPD 的發病原因仍未完全明確,多認為與早產、炎癥、氧中毒、感染和氣道高反應性有關。在各種觸發因素中,下呼吸道細菌引起的炎癥反應、氣道內微生物群多樣性的降低及微生物群的演變均發揮重要作用[2]。然而,對重度BPD 患兒下呼吸道菌群分布特點及是否存在差異的相關研究較少。本研究通過對BPD患兒下呼吸道細菌分布特點進行分析,旨在探討其與重度BPD發生的相關性,為該病的預防及臨床治療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及分組 選取2015年10月—2021年10月于青島市婦女兒童醫院新生兒重癥監護病房(NICU)診斷為BPD 的患兒185 例。納入標準:胎齡≤30 周,有創機械通氣≥72 h,留取機械通氣期間呼吸道吸取液(tracheal suction fluid,TAF)培養≥3次。排除標準:先天發育畸形、嚴重先天性心臟病、染色體異常、非呼吸系統引起的死亡或放棄治療患兒。本研究獲得本院倫理委員會審批(審批號:QFELL-YJ-2021-19)。
1.2 診斷標準及分組方法 BPD診斷標準[3]:出生后持續用氧≥28 d。嚴重程度標準參照2018年美國國立兒童健康與人類研究所對BPD 定義的改良建議[4]:胎齡小于32 周,糾正胎齡至36周未用氧為輕度,吸氧濃度<30%為中度,吸氧濃度≥30%,或需要正壓通氣及機械通氣為重度。根據病情嚴重程度將其分為輕中度組124 例和重度組61 例。呼吸機相關性肺炎(VAP)診斷標準為(1)使用呼吸機48 h后發病。(2)與機械通氣前胸片比較出現肺內浸潤陰影或顯示新的炎性病變。(3)肺部實變體征和(或)肺部聽診可聞及濕啰音,并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①血白細胞計數>10.0×109/L或<4×109/L,伴或不伴核左移;②發熱,體溫>37.5 ℃,呼吸道出現大量分泌物;③起病后從支氣管分泌物中分離到新的病原菌。
1.3 資料收集 收集患兒的一般資料,包括性別、分娩方式、胎膜早破時間是否>18 h、產前類固醇激素和肺表面活性物質應用情況、出生體質量、胎齡;治療過程指標:有創通氣時間、住院時間,新生兒壞死性小腸結腸炎(NEC)、敗血癥、早產兒視網膜病(ROP)、Ⅲ-Ⅳ級腦室內出血(IVH)和VAP發生情況。
1.4 TAF 收集與檢測 所有患兒機械通氣期間使用一次性無菌密閉吸痰管連接負壓吸引器收集TAF。常規取樣頻率1~2周1次,如懷疑發生VAP則根據病情需要增加取樣頻次。機械通氣結束拔管時剪裁氣管插管尖端作為送檢標本行病原學培養,按照《全國臨床檢驗操作規程》要求進行檢測。分離培養的陽性標本,使用北京金山川公司MB-80微生物快速動態檢測系統和法國梅里埃VITEK-2 Compact 全自動細菌鑒定系統進行菌株鑒定。
1.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22.0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數資料以例(%)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或Fisher 確切概率法,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s表示,組間均數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以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 組一般資料比較 與輕中度組比較,重度組出生體質量、胎齡降低(P<0.05);2 組性別、分娩方式、胎膜早破>18 h、產前類固醇激素和肺表面活性物質應用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 臨床治療過程中資料比較 與輕中度組比較,重度組敗血癥和ROP 發生率升高,有創通氣時間、住院時間更長(P<0.05)。2 組NEC、VAP、Ⅲ-Ⅳ級IVH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2.3 TAF 培養結果比較 剔除TAF 質控不合格標本及生后48 h 內標本后納入合格TAF 標本276 份,其中54 份培養結果陽性。送檢的TAF 標本可檢測到的細菌有棒狀桿菌、肺炎克雷伯菌、草綠色鏈球菌、銅綠假單胞菌、凝固酶陰性葡萄球菌(CoNS)、嗜麥芽窄食單胞菌菌、奈瑟氏菌、流感嗜血桿菌和梭菌屬。與輕中度組比較,重度組檢出革蘭陰性菌(GNB)、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及棒狀桿菌患兒比例升高(P<0.05),見表3。
3 討論
早產兒在發生BPD 的過程中,早期經歷了呼吸支持治療,大多數重度BPD 患兒需要較長時間的機械通氣。既往研究發現,如機械通氣>3 d,細菌定植的概率明顯增加[5]。肺部細菌感染和炎癥反應是BPD 發展中的關鍵環節,感染時活化的中性粒細胞和巨噬細胞釋放大量的氧自由基、炎性介質及活化因子,引起炎性細胞在肺組織內不斷聚集,造成肺損傷[6-7]。因此對出生后呼吸道菌群演變過程及下呼吸道菌群特點的分析有助于了解BPD 的發生及發展。

Tab.1 Comparison of general clinical data between the mild moderate group and the severe group表1 輕中度組和重度組患兒一般臨床資料比較

Tab.2 Comparis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process data between the mild moderate group and the severe group表2 輕中度組和重度組臨床治療過程指標比較

Tab.3 Comparison of bacteria detected in TAF culture between the mild moderate group and the severe group表3 輕中度組和重度組TAF培養檢出細菌比較
重度BPD患兒下呼吸道菌群的改變與有創機械通氣時氣道的開放、廣譜抗生素的應用有關。重度BPD患兒下呼吸道條件致病菌的定植可競爭性抑制正常菌群生長,導致呼吸道菌群微環境的改變,促進BPD 的發生、發展[8-9]。其機制可能是呼吸道內的GNB 破壞了肺結締組織,進而增加了BPD 的嚴重程度,GNB外膜上的脂多糖可加重肺部炎癥,減少血管生長因子生成[10]。Tramper 等[11]發現GNB在肺部定植與BPD的嚴重程度相關,同時增加了BPD患兒住院期間的并發癥、病死率及有創通氣時間。本研究顯示,與輕中度組相比,重度組TAF 中檢出GNB 的比例明顯增加,且機械通氣和住院時間明顯延長,住院期間ROP 及敗血癥的發生率明顯增加,與既往研究一致[12]。重癥BPD 組患兒檢出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人數增加,這兩種菌是NICU中常見的條件性致病菌,長時間接觸廣譜抗生素,機械通氣、住院時間延長以及呼吸道有創操作增加,是其檢出率增加的主要原因[13-14]。此外,本研究還發現重度組TAF檢出棒狀桿菌患兒數也明顯增高。棒狀桿菌屬細菌種類較多,多為條件致病菌,但某些亞型如耶氏棒狀桿菌和紋狀體棒狀桿菌在暴露于廣譜抗生素、有創性操作等特定情況下,也具有潛在的致病性[15-16]。本研究為回顧性且受實驗條件所限,未能明確棒狀桿菌亞型,但在重度組檢出頻率明顯增高仍可認為存在臨床意義。
本研究的局限性:首先,TAF采樣可能無法充分反映呼吸道細菌暴露,如能同時對上、下呼吸道進行采樣,可以更完整地評估細菌定植。其次,細菌單次培養使得陽性率較低;而對于重度BPD 組因臨床救治的需要,其有創通氣時間更長、TAF 取樣次數增多,因而增加了檢測頻次,但也可導致重度組有更高的細菌陽性率;而輕中度組取樣次數的相對減少可能會存在觀察偏倚。
綜上,重度BPD患兒需要更長時間的有創通氣,TAF 中檢測到肺炎克雷伯菌、銅綠假單胞菌及棒狀桿菌的比例更高,但NICU內其他條件致病菌與重度BPD的發生是否存在相關性需要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