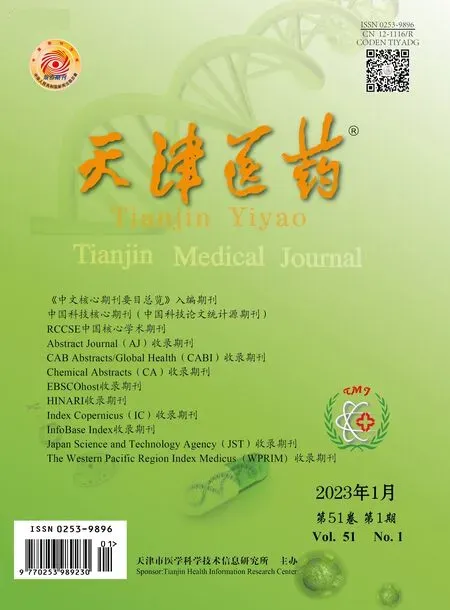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腸道微生物群及腸黏膜屏障缺陷影響機制的研究進展
孫強,宋維亮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感染后,常常會伴隨機體器官功能改變[1]。一項薈萃分析表明,17.6% 的新型冠狀病毒(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SARS-CoV-2)感染者存在胃腸道癥狀[2]。一項對14 例SARS-CoV-2 感染后4 個月已無癥狀患者進行腸黏膜活檢分析研究發現,7 例患者SARS-CoV-2 核酸及免疫反應陽性,且可持續6 個月以上[3]。鑒于SARS-CoV-2 對腸道功能存有潛在持續影響,本文對COVID-19 所致腸道微生物群及相關腸黏膜屏障缺陷機制的研究進展進行綜述,以期為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 腸道功能紊亂影響機體內環境穩態
近年來,腸道對于多種疾病發生、發展的影響日益凸顯,關鍵原因在于其獨特的微環境與區域免疫功能[4]。Rutsch等[5]研究顯示,腸道微生物群改變與中樞神經系統疾病存在緊密聯系。Lewis等[6]研究發現,腸黏膜屏障功能可作為心血管系統疾病患者的治療靶點,有效改善此類患者預后。Burberry 等[7]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可以產生神經活性分子及神經遞質,直接或間接影響腦細胞生理,從而促進腸道與大腦的溝通。Braniste 等[8]將梭菌家族特定細菌定植于無菌(germfree,GF)環境飼養的小鼠腸道黏液層后,其產生的丁酸鹽等抗炎代謝物可調節免疫及腸道穩態,誘導GF 小鼠腦組織閉鎖蛋白(occludin,OCLN)、閉合蛋白(claudin,CLDN)-5水平升高,使其血腦屏障完整性恢復至無特定病原體(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小鼠水平。Sandek 等[9]研究顯示,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腸道血流減少,腸黏膜通透性增加,且這一功能改變可能與及循環炎性標志物如C 反應蛋白(C reactive protein,CRP)、動脈利鈉肽前體(pro-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Pro-ANP)升高有關。Zhou等[10]研究發現,在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體內,與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腸黏膜滲透性標志物類似的血清標志物如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D-乳酸(D-lactate)呈高表達,證實腸功能障礙與心肌缺血程度存在緊密聯系。
2 腸道微生物群與腸黏膜屏障間有交互作用
研究表明,腸道微生物群與腸黏膜屏障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交互影響[11]。Allam-Ndoul 等[12]發現,腸道微生物群與腸上皮細胞(intestinal epithelial cells,IECs)間的相互作用是調節上皮細胞通透性的關鍵因素,其調控機制與對腸上皮細胞緊密連接的影響有關。有些益生菌,如鼠李糖乳桿菌可以通過增加ZO-1 與occludin 蛋白的表達,從而增強腸道上皮功能[13]。腸道菌群與IECs間的相互作用對維持腸道穩態至關重要,外源微生物的感染可以改變腸道微環境,包括擾亂腸道微生物群與IECs,此時,腸道微生物群會向IECs 傳遞相關信號,有助于抵御感染。Hu等[14]研究發現,在革蘭陽性菌感染時,腸道微生物群可誘導產生一種新型腸道抗菌蛋白—富含脯氨酸小蛋白2A(SPRR2A),該蛋白由Paneth 細胞及杯狀細胞分泌,可以破壞革蘭陽性菌細胞膜,阻止此類細菌突破腸道屏障。
3 SARS-CoV-2感染后腸道微生物群的改變與調節
研究顯示,SARS-CoV-2 感染期和恢復期患者的腸道微生物群均會產生變化[15]。Zuo 等[16]研究顯示,糞芽孢菌屬、多枝梭菌及梭狀芽孢桿菌的豐度與COVID-19的嚴重程度呈正相關,而普拉梭菌的豐度則與COVID-19 的嚴重程度呈負相關。Ren 等[17]研究顯示,普拉梭菌具有抗炎特性,是反映人類腸道健康的潛在生物標志物。此外,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變化可以作為識別SARS-CoV-2 病毒相關傳染范圍的特定微生物特征。研究表明,具有高傳染性的SARS-CoV-2患者糞便中,產氣柯林斯菌、田中柯林斯菌、嬰兒鏈球菌及摩氏摩根菌豐度較高,具有低甚至無傳染性的SARS-CoV-2患者糞便中短鏈脂肪酸的細菌(如擬桿菌屬)豐度則較高[18]。
目前,SARS-CoV-2 對腸道菌群影響的病理、生理學機制已逐漸明確。SARS-CoV-2感染后,炎癥刺激觸發微生物產物和細胞因子的釋放,引起微生物穩態失調,誘發炎性環境,導致腸道細胞因子釋放進入循環系統,加重COVID-19的全身炎癥反應[19]。因此,研究腸道細菌對SARS-CoV-2感染的反應機制至關重要。SARS-CoV-2主要通過S蛋白與血管緊張素轉換酶Ⅱ(angiotensin-convert enzyme Ⅱ,ACE2)受體結合進入宿主細胞[20]。ACE2受體在人類易受病毒感染的各種器官組織(包括肺和腸道)中均有表達。SARS-CoV-2 可能導致腸道ACE2 表達下調,從而增加腸道炎癥和腹瀉的易感性;ACE2 可以維持氨基酸穩態及腸道微生物群的抗菌肽表達,在腸道炎癥中發揮抑制作用,對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具有重要影響,在SARS-CoV-2感染過程中,ACE2轉運可以調控腸道微生物菌群生態[21]。Hashinoto 等[22]研究表明,在ACE2基因敲除小鼠中,抗菌肽呈現低表達,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發生紊亂。Yang 等[23]在感染SARS-CoV-2 的定菌大鼠中觀察到ACE2 表達下調,且這種變化加速了COVID-19 的病理進程。因此,COVID-19患者中ACE2失衡可能會加劇包括腸道在內的多器官組織炎癥反應。
COVID-19 患者往往存在免疫系統異常。Wu 等[24]研究表明,197例COVID-19患者中約34.5%出現中性粒細胞增多癥。感染SARS-CoV-2 可引發炎性細胞因子紊亂。研究證實,COVID-19 患者的細胞因子過度表達與疾病嚴重程度呈正相關[25]。細胞因子紊亂與COVID-19 進展過程中的肺外多臟器功能不全有關,其可能是該類患者胃腸道癥狀加劇的原因[26]。COVID-19 患者外周血淋巴細胞減少,炎性細胞因子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干擾素γ(IFN-γ)水平升高,這些因素可導致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CRS),大量細胞因子與腸道微生物群相互作用,致腸道微生物群組成改變,嚴重影響腸道細胞狀態[27]。腸道微生物群組成發生變化時,體內保護機制被破壞,多臟器組織炎癥風險增加。鑒于腸道微生物群具有重要的免疫反應,利用腸道微生物群改變腸-肺軸的方案有望保護人類免受呼吸道感染[28]。腸-肺軸是一種常見的黏膜免疫系統,腸道與肺存在關聯,在呼吸道免疫與抗感染反應中表現尤為明顯,免疫反應及失調可以影響腸道與呼吸道之間的關系[29]。遺傳因素或外源性因素(包括飲食調節或抗菌素治療)可以通過改變腸道微生物群組成,從而導致局部或全身免疫反應能力發生變化[30]。Mullish 等[31]研究顯示,益生菌具有減少該類患者上呼吸道感染癥狀的潛在用途:在COVID-19病程中,益生菌安全且耐受性良好,可在穩定及預防腸道微生物群組成變化方面發揮潛在作用,以應對上呼吸道感染。
4 SARS-CoV-2感染后腸黏膜屏障的改變與調節
腸黏膜屏障功能的維持需要保持上皮細胞種類與結構的完整性,而該特性依賴于腸道干細胞的分化。腸道干細胞可以促使上皮細胞內膜再生,促進上皮損傷和腸屏障功能恢復以防止各種損傷和感染[32]。引起COVID-19 患者胃腸道癥狀的主要機制可能為:SARS-CoV-2感染后病毒對黏膜上皮產生直接侵襲作用,促使漿細胞和淋巴細胞浸潤腸固有層發生炎癥反應,進而導致腸上皮細胞發生功能障礙、吸收不良[33]。Carvalho 等[34]研究表明,SARS-CoV-2 感染狀態下腸黏膜結構發生變化,表現為腸黏膜炎癥,漿細胞及淋巴細胞發生浸潤,固有層水腫,腸內鏡直視下即可見腸黏膜損傷。
另有研究顯示,SARS-CoV-2 感染后,腸上皮細胞與免疫細胞之間的相互作用會觸發機體固有免疫應答,引起促炎介質分泌,從而加重免疫反應,增加腸黏膜組織損傷[35]。研究表明,免疫益生菌可以通過Toll 受體3 與腸上皮細胞及固有層相關免疫細胞相互作用,誘導免疫細胞產生不同的細胞因子或趨化因子;同時,上述免疫細胞可將信號傳遞至其他免疫細胞,最終導致腸黏膜免疫系統激活及T 細胞激活[36]。其中,進入腸黏膜的效應CD4+T細胞是黏膜免疫與腸道慢性炎癥的關鍵,而趨化因子受體9(CCR9)是CD4+T細胞進入腸壁所必需的趨化因子受體。Wang 等[37]研究發現,呼吸道流感病毒感染后機體肺源性CD4+T細胞增加,小腸上皮細胞產生趨化因子C-C 基序配體25(CCL25),CCL25 結合CCR9 后誘導CD4+T 細胞進入小腸,導致腸道黏膜免疫損傷,破壞腸道菌群穩態。
5 小結與展望
胃腸道被認為是人體最大的免疫器官,其中,腸道微生物群及腸黏膜屏障形成特殊的黏膜網絡以維持腸道穩態,可在人類健康與疾病預防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細菌、病毒等多種病原體感染會破壞腸道微生物群的多樣性,影響腸黏膜屏障及其正常功能代謝。目前業界已公認SARS-CoV-2 可以通過不同方式直接或間接影響腸道生理,引起腸道菌群失調,感染和(或)破壞腸道屏障,腸道內穩態與微環境在COVID-19的發病機制及全身炎癥反應中起重要作用。關于腸道菌群與黏膜屏障在SARS-CoV-2 感染過程中的改變如何參與調節全身炎癥反應仍需進一步研究,進而可以將腸道微生物群及黏膜屏障做為重要的治療靶點,有效地緩解甚至逆轉COVID-19的病理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