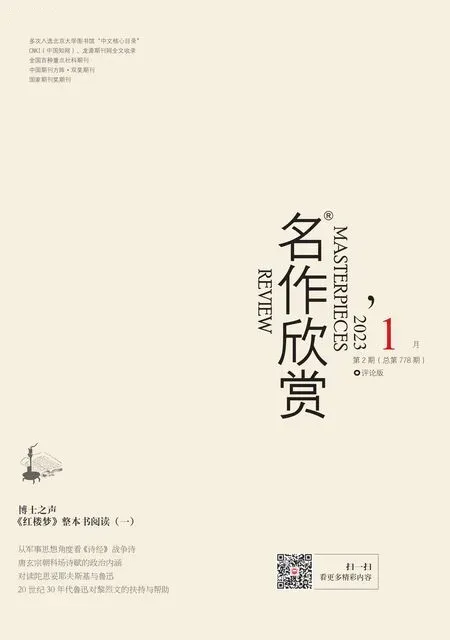形合意合視角下魯迅小說《藥》兩個譯本的對比研究
⊙錢蕾 [上海理工大學,上海 200093]
一、文獻綜述
在中國知網上,以“魯迅”“藥”“譯本”為關鍵詞進行檢索,只檢索到相關文獻六篇,除去一篇講述日譯本、一篇講述維吾爾文譯本的文章,共包括一篇碩士論文,三篇期刊。王亞敏、韋麗(2010)以巴爾胡達羅夫的翻譯學說為基礎,從符號學和語言學角度對楊譯本《祝福》和《藥》中的指稱意義、語用意義和言內意義做了具體的分析。李方佳(2010)以文章中所出現修辭手法的可譯性為切入點,對《藥》譯本中出現的比喻、習語等修辭為例,闡述其可譯性限度問題。侯松山、彭祺(2011)對比了《藥》的兩種英譯本(藍譯和楊譯),具體分析了兩者的得失優劣,并得出了藍譯更勝一籌的結論,但并未引用某些理論做支撐。楊菁雅(2016)選用了功能對等理論,對魯迅小說《藥》《孔乙己》《風波》的英譯本(藍詩玲和楊憲益、戴乃迭夫婦所譯),從文化、語法、修辭的角度展開具體分析,并討論了歸化和異化對翻譯策略的選擇及對文化傳播的差異。
綜上可以看出,在探討魯迅小說《藥》的譯本時,各學者采用的研究視角不同,但未有從形合和意合角度展開論述的,筆者接下來的研究將以形合意合為理論基礎,對比分析楊憲益、戴乃迭的譯本以及威廉·萊爾的譯本。
二、形合與意合
語言界和翻譯界普遍認為形合與意合是區分英漢兩種語言最重要的特征。從語言學角度而言,所謂“合”就是組合(syntagma),即組織手段。它基本有兩種情況:1.依附形式(如詞的曲折變化、詞綴、加詞),此為形合;2.仰仗意義(即內在邏輯關系),此為意合(宋志平,2003)。關于形合與意合的概念,不同學者有不同的解讀,而其相對性的差異往往會反映出某種語言的民族文化及思維特征。
(一)概念的提出
形合與意合是句法研究中兩個對立的概念,這組概念的第一次出現是在19 世紀,來源于希臘詞“parataxis”(para+taxis=beside arrangement)和“hupotaxis”(hupo+taxis=under arrangement)。這里的“arrangement”指的是句法結構,“beside”傳遞的是一種協調性,而“under”傳達的則是一種從屬關系。在語言學上,它們描述了兩種獨立連接句子的模式:形合(從屬結構元素的組合)、意合(平行結構元素的組合)。在漢語言研究中,“形合”和“意合”作為概念和術語最早可追溯到20 世紀40 年代,著名語言學家王力在其著作中闡述了這兩個概念。王力(1984)認為中國的復合句是一種意合法,連詞的使用可有可無,這在西洋語言里十分不常見,西文多用形合法,句子中沒有連接成分也就不成章法。國內對于這兩個概念的研究比較著名的有:一個是以連淑能為代表的觀點,他認為形合和意合這兩個術語是句法的結合方式,兩者的區別是句子的連接方式,另一種是以劉宓慶以及潘文國為代表,他們認為,這兩個概念不僅對句法層面有所體現,還能在語篇層面上作為語言表達和組織的方式。另外,劉宓慶(2005)在《翻譯美學導論》一書中提到,漢語具有模糊性的特點,因此可以用來展現語境之美,而英語則展現的是一種理性美。具體來說,在漢語中省略連詞是一種規范,而在英語中則相反,與印歐語言不同,漢語沒有復雜的句型變化,這也是為什么漢語的表達是由語義而不是詞形變化決定的。無論是語素、詞、短語、復合句、語段,其規律與其說是在顯化語法,不如說是隱化語義。只要漢語在語義和邏輯上是有意義的,各語法單位就可以連接在一起,而無須顧及形式。
(二)特征與差異
英語之所以注重形合,是因為其具有包括詞語形態變化、句法關系變化等這樣的語法手段;而漢語在語言形式上因缺乏多樣變化,而呈現出“意合對接”的基本特征。除了語法層面的差異,另一方面在文化層面,英語和中文因為有著很大的文化背景差異,對文字系統的形成造成了巨大影響。
1.語法層面
英語句型的構句方式是主謂結構,謂語動詞是核心,通過連詞、分詞、關系詞、介詞及其他連接手段,將句子其他語法成分連接起來。英文中廣泛使用代詞,但中文往往可以省略,如:He and his wife 中的代詞his 不能省略,但譯成中文就可以說成是“他和妻子”,若翻譯成“他和他的妻子”則略顯生硬,有漢語歐化之嫌;英文造句連接詞出現得很頻繁,但漢語造句則十分少用或幾乎不用。打個比方,連接詞在英文句子中就如烤串的簽子一般,沒有這簽子,自然也就串不起肉。
漢語意合句也不是那么講究形式,而是從流水句開始,層層鋪開,講究敘事順序,以求達意。接著上面的比喻來看,雖然漢語句子中沒有簽子,但也不影響人吃肉,還可以通過別的方式,即漢語會借助詞語或分句來表示其中的邏輯關系,且往往藏于字里行間,因此無法如英語那般給讀者提供某些句法層面上的提示,所以語法關系呈隱含性特征。
2.文化層面
形合與意合的差異,與英漢兩個民族的文化也脫不了干系。英語是歐美國家的通用語,西方人尊崇個體思維及理性思維,在交際方面更傾向于直來直往,不拐彎抹角,這體現在句法上英文也必須用如關聯詞這樣的顯化符號連接,因此句子結構十分嚴謹;而中國的文化注重的是傳神,東方人在與人交流時比較含蓄,有時考慮到聽者的情感,會采用暗示的策略,這同樣可以映射到句法層面上,中文的句子往往簡潔明了,以意為主,按照空間、時間、因果關系等展開,會將想要表達的邏輯關系用意合的方式傳達。
三、譯本對比
為了研究中英文句子層面形合和意合的對比,本文選取了魯迅《藥》的兩個譯本,從接下來的幾個例子中,探討形合和意合體現在漢譯英中的轉換。
(一)重構句式
例一:華大媽在枕頭底下掏了半天,掏出一包洋錢,交給老栓,老栓接了,抖抖地裝入衣袋,又在外面按了兩下;便點上燈籠,吹熄燈盞,走向里屋子去了。
楊譯:After some fumbling under the pillow his wife produced a packet of silver dollars which she handed over.Old Shuan pocketed it nervously,patted his pocket twice,then lighting a paper lantern and blowing out the lamp went into the inner room.
萊譯:Mother Hua fumbles around under the pillow,fishes out a bundle of money,and hands it to Big-bolt.He takes it,packs it into his "pocket with trembling hands,and then pats it a few times.He lights a large paper-shaded lantern,blows out the oil lamp,and walks toward the little room behind the shop.
華大媽將洋錢交與老栓,老栓裝衣袋、點燈籠、吹熄燈盞走向里屋等一系列活動,共有九個動作。原文只出現了“老栓”做主語一次,后面的動詞前面即便不加代詞“他”,以中文為母語的讀者讀來也會理解這里動作的真正發出者是老栓,而不是華大媽。楊譯也只出了一次主語,但將“點燈籠”和“吹燈盞”處理為非謂語動詞“lighting a paper lantern”和“blowing out the lamp”表示伴隨,并用三個謂語動詞連接,體現了層次上的形合特征,主次意味非常明顯,形成了一種顯性銜接,在漢語句子中只是次序先后不同,并無主要和次要之分;萊譯中出現了一次主語后,將后面的兩個半句拆分成了兩個整句,受到語法制約,需要增補代詞“He”兩次做主語,并將這九個動作并列連動,一是讓讀者可以清晰理解內容,二是使譯文語法結構完整。
例二:老栓正在專心走路,忽然吃了一驚,遠遠看見一條丁字街,明明白白橫著。
楊譯:Absorbed in his walking,Old Shuan was startled when he saw the crossroad lying distinctly ahead of him.
萊譯:Single-mindedly going his way,Big-bolt is suddenly startled as he catches sight of another road in the distance that starkly crosses the one he is walking on,forming a T-shaped intersection with it.
此句描繪了華老栓即將到達賣人血饅頭的地方。這句話四個小句之間的內在聯系非常緊密。“忽然吃了一驚,遠遠看見一條丁字街”是省略了隱形的因果關系詞,漢語意合特征明顯。楊憲益和萊爾在翻譯時分別用“when”和“as”二詞準確表達出了原文中的因果關系,即“when/as he saw the crossroad he was startled”。原文體現的是漢語中常用的語序法。
(二)化隱形連貫為顯性連接
例三:——第一要算我們栓叔運氣;第二是夏三爺賞了二十五兩雪白的銀子,獨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楊譯:Our Old Shuan was luckiest,and after him Third Uncle Xia.He pocketed the whole reward — twenty-five taels of bright silver — and didn’t have to spent a cent!
萊譯:But if you wanna talk about people who did make out on the deal,Big-bolt here is number one on the lucky list.And right after him comes Third Master Xia.Without spending a single cooper,that one ended up pocketing a reward of twenty-five ounces.
此句是康大叔在眾人面前大聲嚷嚷的場景,一邊說著小栓碰到了好運氣,一邊又唾罵夏四奶奶家的小兒子,活脫脫一個小市民形象。楊譯采用了直譯法,用最高級“luckiest”和“after him”這樣的介詞結構來表示“第一”“第二”;而萊譯是用“But if”引導條件狀語從句,意思是“如果要說……”其實是萊爾在這里揣摩了原作者想要表達的意思,認為在中文語境下隱含了假設的邏輯關系,所以添加了“But if you wanna talk about people…”這半句來描述交易人血饅頭的事。原文中康大叔說得也沒頭沒尾,前面還在說夏四奶奶家兒子的衣服被紅眼睛阿義拿去了,后邊又說起了老栓,因此萊爾在這里的揣測是有道理的,譯者主體性較強,也用形合法幫助讀者厘清了其中的邏輯。
例四: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飯,哭了一場。
楊譯:Shortly after daybreak,Old Shuan’s wife brought four dishes and a bowl of rice to set before a new grave in the right section,and wailed before it.
萊譯:Though the sun has not long been up,Mother Hua has already set out four plates of various foods and one bowl of rice before a burial mound to the right of the path.
華小栓吃了華老栓花大價錢買回來的人血饅頭后,肺癆沒有半點好轉的跡象,最終還是死了。于是華大媽早早地就去墓前擺供桌。原文中的“天明未久,華大媽已在右邊的一座新墳前面……”其實隱含了一種轉折關系,雖然天還沒亮多久,但是華大媽心系兒子,早就去墳前探望,表現了作為母親的痛心與思念之情。在漢語句子中,若不顯化關聯詞,也不會讓讀者產生閱讀困難,而轉換成英語時,隱化關聯詞顯然是行不通的,需添加關聯詞,表明邏輯關系。楊譯顯然是忠實于原文的,順句驅動,用并列謂語句串句,沒有譯出其中的隱含意思;萊譯添加了關聯詞“Though”,也把原文中的“已”用“has already”體現在了譯文中,將中文的意合句轉化成了英文的形合句,使其符合英語語法邏輯,也讓外國讀者在閱讀時體會到其中的感情。
(三)顯化時態
例五:微風早經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銅絲。
楊譯:The breeze had long since dropped,and the dry grass stood stiff and straight as copper wires.
萊譯:The gentle breeze has long since died down,and stalk by stalk the withered grass stands erect like so many copper wires.
原文中形容枯草,用到了“支支直立”和“有如銅絲”這樣的四字格形式,且原文中出現的動詞“停息”和“直立”本身并看不出時態。楊譯體現了英文重形合的特點,將該句處理成了過去完成時,并兩次用到了連接詞“and”,并用“as”做連詞,而原文中什么連接詞都未使用;萊譯則是處理成了現在完成時,顯化時態,在英語形合手段中,形式外顯是較有代表性的,以此反觀漢語的詞語、語句的粘合方式,往往大相徑庭。
例六:太陽也出來了;在他面前,顯出一條大道,直到他家中,后面也照見丁字街頭破匾上“古□亭口”這四個黯淡的金字。
楊譯:The sun too had risen,lighting up the broad highway before him,which led straight home,and the worn tablet behind him at the crossroad with its faded gold inscription: “Ancient Pavilion.”
萊譯:The sun comes out now,too.Before him it reveals a broad road that leads straight to his home;behind him it shines upon four faded gold characters marking the broken plaque at the intersection: OLD ★ ★ ★ PAVION ★ ★ ★ ROAD ★ ★ ★ INTER CTION.
這是華老栓拿到人血饅頭后回家的場景。光讀原文,其實時態語態是比較曖昧不清的,需要從上下文的邏輯中進行推理。楊譯選擇了過去時態,而萊譯則理解為一般現在時。不僅是這句,全篇《藥》的翻譯中,楊憲益、戴乃迭與萊爾所采用的時態是不一樣的。但無論是哪版譯文,時態都可以很清楚地從動詞的形式上看出來。原文這句中還包含了隱喻意義,因此有了“前面大道”“后面破匾”的對比,楊譯中用“the sun”做主語,并適當調整了語序,將介詞結構“before him”放到了后半部分,符合英語表達習慣;而萊譯則是將“before”和“behind”放在了句首形成了對比,是加入了作者自己的感受,哀嘆愚昧的人民。
四、結語
形合和意合是中英文兩種語言在句法結構上最明顯的區別,英語通過連接手段及時態變化,形成了語言的顯性銜接,長句居多,以形寓意,結構清晰完整;漢語少使用連接手段,因為中文里并不存在很多的關系代詞、關系副詞、連接詞,取而代之的是通過語序法、綜合修辭法、緊縮句和四字格來形成隱形連貫,句子往往短小精悍,多以意役形,即人們常說的“意會”。當然,英語形合和漢語意合并不是絕對的,兩者其實是辯證關系。英語中有少量的意合句,漢語中也有少量的形合句,英文中的意合表現在使用不同的表達來指代中心詞,因為英語不喜重復,而譯成中文就需要用重復名詞來表述,這樣既符合漢語表達,也使得句子形神俱在,比如《藥》中有一句:“老栓一面聽,一面應,一面扣上衣服……”原文中連續幾個動作用“一面……一面……”重復,生動刻畫了當時的場面,是漢語形合句式。
綜上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英漢還是漢英翻譯過程中,譯者不能一味地將“漢語意合、英語形合”作為真經一般刻在腦中,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方面,在漢譯英時,首先要進行句子間邏輯關系的分析,看是否需要調整語序,還要明確原作者的寫作風格,考慮譯入語國家的文化和思維方式,然后在翻譯過程中適當增譯主語、重構句式、顯化層次、添加連接詞、關系詞等,如果有必要的話,也可以加入譯者對文本深入理解后的譯文,這樣才能讓國外讀者對中國文化產生正確直觀的了解,才能更好地促進中國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傳播。另一方面,漢語存在形合句式,英語也存在意合句式,在特定語境下,也要做到特殊情況特殊分析,整合語義和形式,準確傳達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