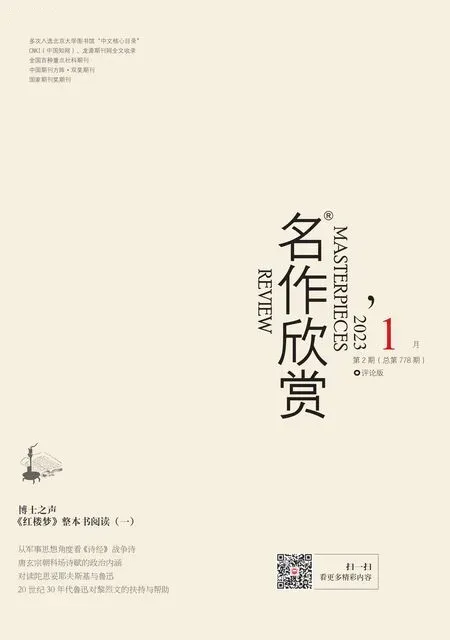論《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敘事上的恐惑
⊙方迪 [河北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石家莊 050024]
珍妮特·溫特森是當代英國極具創造力的女作家,英國《獨立報》曾評價她是這個時代最好也是最有爭議性的作家之一。她的第一部小說《橘子不是唯一的水果》(以下簡稱《橘子》)于1985 年出版,同年獲得惠特布萊德獎。該作品在1990 年被改編成電視劇,獲得了英國電影電視藝術學會獎。《橘子》講述了一個名叫珍妮特的少女在宗教和男權的雙重壓制下奮力追尋自我的故事。目前國內對于該小說的研究多集中在女性主義、后現代敘事、倫理學、同性戀主義、成長小說等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尤其針對溫特森作品中獨特的敘事方式,國內研究論文較多,但相較于國外學界對于溫特森小說的多角度剖析,國內研究仍有有待提升的地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于1919 年發表散文《論恐惑》。該文在20 世紀70 年代引起西方學術界的關注,至今該散文引發的“恐惑”概念仍然是當代西方文學和文化理論界的研究熱點。本文結合“恐惑”理論從內外敘事層次間界限的模糊以及敘述者結構上的雙重化兩方面解讀《橘子》敘事上的恐惑。
一、敘事層次間界限的模糊
溫特森的小說就像“俄羅斯套娃”一樣,將嵌入的文本用在彼此之間。在《橘子》中,小說的外層由“我”——主人公珍妮特講述自己的故事,內層則被置入各種奇幻故事,二者共同構成了一個虛實交替的世界。有學者認為,溫特森在《橘子》中虛構的這些故事反映了女主人公的個人問題和個人觀點。一方面,內層置入的奇幻故事是外層珍妮特故事的自我反射;另一方面,內層故事又是作者有意暴露自己虛構身份進入文本的敘事,是敘述者入侵敘事世界的行為。作者在該敘事中不斷暴露文本信息,因此,外層敘事并不能包裹住內層敘事,不能給內層敘事提供一個“家”,使得內外敘事層次間二元對立的結構被破壞,敘述的界限被模糊。這種內外敘事層次間界限的模糊構成了小說的“恐惑”式敘事。
界限的模糊是“恐惑”理論的要點之一。在《論恐惑》一文中,弗洛伊德認為“恐惑”就是那種把人帶回到很久以前熟悉和熟知的事情的驚恐感覺。當個體在過去遭遇的事物因種種原因壓抑至潛意識中,而該事物以其他面目再次出現時,個體會產生一種似曾相識的恐懼感。簡言之,“恐惑”是熟悉中的不熟悉、去熟悉化后的再熟悉化、意識中的無意識,或者說恐惑感位于熟悉與陌生、有生命與無生命之間的模糊界線上。在《論恐惑》一文中,弗洛伊德從詞源上考察了“恐惑”一詞,顯然證明了這一觀點。“恐惑”一詞源于德語詞“unheimlich”,英語譯為“uncanny”,顯然與“heimlich”相反。然而,“heimlich”含有兩種迥然不同的意思,一方面,它意味著某種熟悉的且令人愜意的事物,而另一方面則意味著某種隱藏的且見不得光的東西。“unheimlich”通常在習慣上只是用作“heimlich”的第一類意義的反義詞。兩個詞的含義之間既相同又相反,形成了對立雙方界限上的模糊。這種界限的模糊是引發恐惑現象的特征之一。因此,當人們模糊了小說的界限或熟悉與不熟悉的界限時,恐惑感就產生了。
《橘子》的框架敘事是女主人公珍妮特的成長歷程,在小說的第二層,嵌入了寓言、亞瑟王傳奇和童話,形成了一個嵌套式的敘事迷宮。然而,在這個敘事迷宮中,框架敘事并不是穩定不變的,它與內層敘事之間的界限總是被模糊。在周六舉行的一次集會上,布道的主題是“完美”,布道者宣稱完美是人墮落前的狀態,完美就是毫無瑕疵。結合《圣經》中亞當與夏娃的故事,人墮落前的狀態指的是人們還未被驅逐出伊甸園的時候,而墮落的原因,即被驅逐出伊甸園的原因,是夏娃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實,獲得了智慧。按照布道者的意思,完美是夏娃尚未吃下禁果前的狀態,是女性愚昧,仍以男性肋骨自居時的狀態。珍妮特對于這次布道的反應是“就在那時候,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萌生了對神學的不同意見”。珍妮特深切意識到了父權制社會對于女性意識的壓制,以及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弱勢地位。然而在珍妮特的敘事層面上,作者并沒有試圖對主題進行揭示,而是虛構出一個“完美公主”的故事,用故事解釋故事。內層敘事中完美公主的故事毫無疑問是主人公珍妮特自我掙扎的外化。它解構了傳統意義上公主與王子的童話故事,以王子砍下公主的頭作為結局,揭示了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獨立意識的剝奪。因此,完美公主的故事的意義包裹了珍妮特故事本身,在敘事結構上,外層敘事與內層敘事之間包含與被包含的二元對立結構被破壞,內外層次間的界限被模糊。
在諸多內層故事中,溫妮特的故事首次出現在“路得記”一章,其特殊之處在于,相較于其他只是部分反映主人公經歷的虛構故事,它從整體上反映了珍妮特的故事。在外層敘事中,珍妮特自幼被一對虔誠的宗教信徒收養,養母性格強勢,致力于將其培養為傳教士,青少年時期與另一個女孩相戀,被她所在的教會發現,最終被趕出家門。而在內層敘事中,溫妮特成為巫師的學徒和養女,因為與外來的男人相愛,而被巫師驅逐出城堡。這兩個具有相當大的類似性的分層文本構成了“嵌套”式敘事。其文化原型,是歐洲貴族家族的紋章,如果一個紋章內鑲嵌了另一個構圖類似的紋章,就稱為“嵌套”。然而,該小說以作者姓名重構人物名字的方式又賦予了該嵌套式敘事獨特的意味,不僅僅只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
內層敘事的特殊之處還在于對于外層敘事內容和主題的提前揭露。小說中的男巫對應著珍妮特的養母,溫妮特與男巫的關系也對應著珍妮特與養母的關系。甚至珍妮特所在的魔法世界也有著隱含的意思,它對應著宗教。因為溫特森認為宗教是一種幻覺,就像魔法一樣迷惑人。男巫將隱形的線纏在溫妮特的紐扣上暗示著珍妮特與母親之間的聯系,也預示著珍妮特最終的回歸。珍妮特在結尾也說:“她早已在我的紐扣上系了一根線,只要她高興,就能牽絆住我。”溫妮特對古城的渴望也暗示了小說自我追尋的主題。通過了解溫妮特的故事,揭示了珍妮特故事的意義,內外敘事層次間二元對立的結構遭到了解構。
溫妮特離開城堡后,從村民那里聽說有一座遙遠的古城,那里追求真理,沒有背叛。在珍妮特故事中,養母與珍妮特關系的破裂也源自于一次次背叛。一次是母親篡改了《簡·愛》的結局,告訴珍妮特簡嫁給了圣·約翰;一次是珍妮特無意中發現了自己的領養文件;最后一次背叛源于珍妮特的戀情被發現后,母親燒毀了珍妮特的所有信件、卡片和私人筆記,由此她們的關系最終破裂。“教導的方式有千萬種,但背叛永遠是背叛,無論何時何地。她在后院燒掉的不只是那些紙張和文字。”“在她的頭腦中,她依然是王后,但不再是我的王后。”外層敘事的主題再次在內層敘事中得到揭露。正如溫妮特渴望到達一個沒有背叛的地方,珍妮特也渴望著沒有背叛的愛,無論是來自戀人還是母親。溫妮特邁向遙遠的古城之旅也是珍妮特的自我追尋之旅。溫妮特的故事成了珍妮特故事的自我反射。讀者通過溫妮特的故事意義完成對珍妮特故事的解讀。內層敘事所講的故事的意義包裹了外層敘事,顛倒了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使得小說的框架敘事呈現出“家之非家”的特殊性。在敘事層次上,內外敘事層次間的界限被模糊,構成了小說敘事上的恐惑。
二、敘事結構雙重化
《橘子》中內外敘事層次中敘述者的轉變也引發了敘事上的恐惑。林登伯格認為,在敘述含有個人性質的事件時,作者仍保持著作為敘述者的距離將增加敘事上的恐惑效果,因為作者將自己置于了恐惑的內部和外部。作為一部半自傳體小說,《橘子》中含有大量自傳成分。在2014 年蘭登出版社再版的《橘子》導言中,溫特森也承認:“橘子是自傳式的,因為我用自己的生活作為故事的基礎。”因此,有理由認為溫特森在這部“自傳”中書寫了自己童年和青少年時期真實的成長經歷。在外層敘事中,溫特森采用第一人稱視角,以珍妮特的眼睛觀察周圍的一切,或者說將過去的自己放入敘述中講述一切。而在內層敘事中則采用了更為客觀全知的第三人稱視角敘事。小說中存在兩種敘事聲音,一種是寫實性敘事,一種是自我反思性敘事,通過兩種不同的敘事聲音,暴露了小說的虛構本質。凱琳·卡特認為講故事是一種媒介,《橘子》中年長的敘述者通過講故事來實現她自己的凈化儀式。這都承認了小說中的敘述者并不是同一個人,一個是沉浸于過去的敘述者,一個是保持現在自我的敘述者。溫特森通過在內層敘事中保持一個現在的自我,一個敘述者,操控著敘事。因此敘述者將自己置于了敘事的內外層,既在內部也在外部,處在了一個中間模糊地帶,這種結構上的雙重化增加了小說敘事上的恐惑。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過去的自我還是現在的自我都是語言效果下的產物。
這種結構上的雙重化,涉及恐惑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復影”。按照蘭柯的說法,復影是人的心理需要的投射。他深入研究了復影同鏡像、影子、守護神、靈魂信仰以及死亡恐懼之間的關聯,指出復影最初是對自我毀滅進行抵御的保護措施。敘事經常表現出被試圖壓縮和構造的破壞性材料所推動,然而一旦敘事開始,它就有著增殖的威脅。敘事同時支持和威脅的基本穩定概念之一是敘述者的自主主體性。正如埃萊娜·西蘇所言:“小說是死亡的一種分泌物,是非寫實的期望。”因此在《橘子》 中,溫特森保護式地在她個人的故事中分離她自己,分成可控的敘述者以及無助的主人公,以此躲避死亡的威脅。
同樣,她在《橘子》中也為主人公創造出了多個復影,如童話故事中的公主、圣杯故事中的柏士浮騎士以及魔法世界的溫妮特。實際上,這些人物都是隱藏在珍妮特心中的另一個自我。“事實上,嵌入的文本是珍妮特生活的一面鏡子。”通過復影的存在,敘述者為珍妮特開辟了生存的文本空間,以此躲避死亡的威脅,這些威脅源自于宗教以及父權制社會對個體自我的壓迫以及束縛。
在內層敘事中,匿名的“你”頻繁地出現,好似敘述者在與被敘者進行對話。“你用粉筆畫個圈,把自己圍起來,以免受自然精靈的攻擊,或諸如此類的侵害。”“因為不管你是想抵御自然精靈還是躲開某人的壞情緒,擁有個人空間總是金科玉律。”通過這樣的敘事技巧,溫特森成功地將自己的死亡塞給了讀者。通過內層敘事的故事,個體流離的無意識與自身死亡的非家從人物轉向敘述者,再轉向讀者,以達到治愈創傷的功能。作為一個擁有不幸童年經歷的人,溫特森必須通過文字將過去的一切寫下來,在文字中找到救贖的方法。正如溫特森在《我要快樂,不必正常》中曾經說過:“為了逃避溫特森太太網目細密的故事,我必須有能力將自己的故事……我在寫作中找到出路。”她在小說中將自己分化成兩個部分,既是主人公又是敘述者,一方面沉浸于過去,一方面又脫離過去、從而達到了驅逐過去,獲得救贖的效果,而這種敘事方式構成了小說敘事上的恐惑。
三、結語
綜上所述,小說《橘子》在敘事上存在恐惑特征。一方面,《橘子》在敘事上采用了嵌套的手法。外層由珍妮特講述自己的故事,內層敘事由敘述者講述了溫妮特的故事,然而外層敘事并不能包裹住內層敘事,不能給內層敘事提供一個“家”。內外敘事層次間的界限被模糊,構成了小說敘事上的恐惑。另一方面,內外敘事層次中敘述者的轉變也引發了敘事上的恐惑。通過這樣的敘事方式,溫特森保護式地在她個人的故事中分離她自己,分成可控的敘述者以及無助的主人公,以此驅逐過去,獲得了自我救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