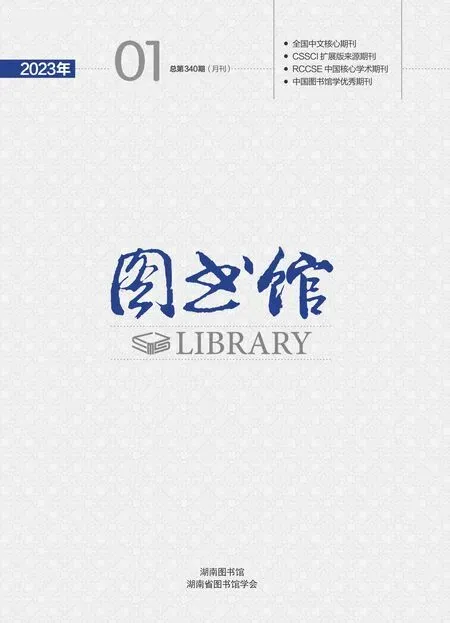圖書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服務模式的探討
阮光冊 張祎笛
(華東師范大學信息管理系 上海 200241)
1 引言
借閱服務是圖書館最基礎、最核心的服務形式。多年來,圖書館都在尋求借助信息技術為讀者提供更多訪問和使用館藏資源的途徑,以更加開放的姿態去滿足讀者的文化需求,但也帶來了合理使用圖書館數字資源的困境。與此同時,圖書館如何借助信息技術合理地將現有館藏資源數字化,改善傳統圖書館的服務模式,是在新形勢下圖書館提升社會使命,加快服務創新不可回避的問題。
為更好地實現公共利益和版權所有者之間的平衡,2018 年杜克大學圖書館副館長David R. Hansen 和哈佛大學圖書館版權顧問Kyle K. Courtney 共同發表了《圖書館圖書受控數字借閱白皮書》[1],對圖書受控數字借閱的定義和實施框架作出了詳細的解釋。受控數字借閱(Controlled Digital Lending,以下簡稱CDL)是借閱服務的一種創新探索,為開放圖書館館藏提供了理論方案。它可以使圖書館在合理使用原則下以“像印刷品一樣借閱”的方式將印刷館藏中的數字化作品以安全的方式借閱給讀者,同時限制原始副本不得被其他用戶借用。2021 年4 月,美國大學與研究圖書館學會(ACRL)發布《高校圖書館環境掃描報告》(以下簡稱《掃描報告》),《掃描報告》將CDL 作為重要內容予以討論,指出CDL 在新冠疫情期間被許多高校使用,是為讀者提供借閱服務的安全可靠的流通手段[2]。
我國學者對國外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的實施情況進行了研究。李春卉以新冠疫情下美國大學圖書館的受控數字借閱為契機,介紹了CDL 的起源、法律依據和目前主要存在的爭議問題[3]。李艾真認為CDL 得益于“合理利用”而被支持,并對“合理利用”的四個要素進行了細致分析,指出CDL 目前仍然面臨著利益相關者利益失衡的問題,對我國公共圖書館構建CDL 模式提出了法律、技術、應用層面上的實施建議[4]。魏鋼泳介紹了美國受控數字借閱的來源、概念與發展歷程,探尋其運行機制、現實困境與法律基礎,為我國圖書館引入該模式提供了參考與借鑒[5]。在這些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之上,本文將梳理國內外有關受控數字借閱的發展現狀,并對我國圖書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面臨的挑戰進行思考。
2 受控數字借閱的發展歷程
在數字借閱的實踐中,圖書館遇到了比紙質圖書借閱更為復雜的問題,這就是出版商對于數字圖書的版權限制。出于創新數字化文獻應用的目的,2010 年互聯網檔案館(Internet Archive)推出“開放圖書館:數字借閱圖書館”項目,2019 年為讀者提供超出版權年限的數字化圖書,為廣大讀者提供了便捷[6]。2011 年,喬治敦大學法學院教授兼法律圖書館館長Michelle M. Wu 在其發表的論文中首次從理論上探討了受控數字借閱的想法[7]。
2018 年杜克大學圖書館副館長David R. Hansen 和哈佛大學圖書館版權顧問Kyle K. Courtney 在兩人發布的《圖書館圖書受控數字借閱白皮書》[1]中,首次全面、系統地對受控數字借閱的法律問題和政策原則,以及圖書館在實施此類數字借閱時存在的各種風險、讀者隱私和影響因素等問題進行了詳細闡述。白皮書的發布獲得了美國52 家公共圖書館、高校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的聯合署名,以及113 位知名館長、學者和法律專家的認可。在白皮書中,David 等人認為,受控數字借閱是圖書館在合理使用原則下借出圖書的數字副本,在此過程中,圖書館只能同時借閱其合法獲得的圖書數量。白皮書強調,圖書館開展受控數字借閱是非商業性的,其目的是促進研究和學習。
對于CDL 的實施,白皮書給出了三個重要的原則:①圖書館必須對合法擁有的實體圖書創建數字副本;②圖書館必須保持擁有與借出的比例,同時借出的數字副本不得超過其合法擁有實體書數量,即CDL 必須保持自有借出比例(“owned to loaned” ratio),當電子資源被外借后,相應的紙質版本將被限制使用;③圖書館必須采取技術措施防止讀者保留數字拷貝或復制、分發數字拷貝,確保電子資源的版權安全[1]。
2018 年,美國作家聯盟(Authors Alliance)公開支持圖書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項目,該聯盟認為在數字化時代,圖書館掃描館藏紙質圖書并以數字化形式為讀者提供借閱服務,是圖書館服務的一種延續,體現了圖書館一直以來為用戶免費提供圖書的宗旨[8]。2020 年,美國一些圖書館已嘗試為不便到館的讀者提供小范圍的CDL 服務。同年7 月,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ARL)簽署聲明支持受控數字借閱,在疫情期間該模式得到了較多圖書館的使用[3]。在國內,上海紐約大學圖書館在疫情暴發初期開發了一個谷歌電子表格和谷歌應用程序腳本,創造了臨時性CDL 借閱服務,并公開此腳本以供其他圖書館進行借鑒和修改[10]。2021 年2 月,《未來思考:ASERL 關于研究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資源的指南》正式出版[9],它為正在考慮實施受控數字借閱計劃的圖書館提供了關于收益與風險的指導意見。2021 年5 月,國際圖聯(IFLA)發表了《IFLA 關于受控數字出借的聲明》,IFLA 認為CDL 有助于圖書館在現有版權法范圍內履行支持研究、教育和文化參與的公共使命[11]。2021 年11 月18 日,歐洲研究型圖書館協會簽署了由圖書館未來協會提出的一項倡議,指出受控數字借閱和其他創新借閱方式應受到法律保護,認為數字作品首次銷售原則、知識產權法中的權利用盡原則、數字對象所有權是確保圖書館和文化機構充分獲取信息的必經之路[12]。
3 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實踐與障礙
3.1 國內外CDL 實踐現狀
近年來,為尋求圖書館合法借閱圖書的數字副本,國外圖書館和業界開展了眾多實踐探索。新冠疫情期間,不少大學圖書館探索受控數字借閱。目前,國內外的受控數字借閱實踐主要來自非營利性的學術和研究圖書館合作組織的推動。表1 列出了國內外具有代表性的CDL 服務項目。

表1 國內外主要受控數字借閱項目
從案例的梳理來看,國內外受控數字借閱項目主要是針對三類館藏:第一類,無法從出版商或版權所有者處購買的絕版作品;第二類,沒有電子版本的紙質館藏;第三類,出版社或作者允許圖書館使用電子版的作品。由于第三類資源的使用存在爭議,為此,圖書館CDL 提供的服務主要針對第一類和第二類館藏資源[22]。
3.2 CDL 的法律依據及實施障礙
受控數字借閱將圖書借閱轉變為一種新的模式,圖書館創新借閱服務,在合理使用原則下借出圖書的數字副本,通過館藏紙本資源電子化,為開放圖書館館藏提供了理論解決方案。雖然其具有一定的法律依據,但在實施過程中仍面臨諸多障礙。
3.2.1 法律依據:首次銷售原則和合理使用原則
目前數字環境下首次銷售原則適用法律存在空白,CDL 依舊采用傳統首次銷售原則,即對版權所有人對其作品的控制范圍進行界定:一旦作品依法出售或者轉讓后,版權人持有副本的使用和分發的權利即告終止或“用盡”,此時,副本持有人有權對作品進行轉售或贈予。CDL 是圖書館以受控的方式對圖書數字副本進行借閱,并且保持了“自有/借閱”的比例,保證一個時間段內只能有一個用戶使用,這是防止副本惡意復制或傳播的手段,因此首次銷售原則也適用于CDL。在《圖書館圖書受控數字借閱白皮書》中,David R. Hansen 等人認為,CDL 系統與首次銷售的法律宗旨一致,圖書館使用受控數字借閱是非商業性的,其目的是促進研究和學習,并認為圖書館及其讀者將從受控數字借閱中受益[1]。
另一個法律依據是合理使用原則,該原則是對版權作品的使用范圍進行限定,明確哪些行為不是侵權行為。它是國際版權法的重要原則,被英美等多個國家認可,在國際上通行的《伯爾尼公約》、歐盟的《版權指令》第5 條以及美國《版權法》第109 條均明確規定了合理使用的判斷標準。其中美國《版權法》對于合理利用說明了例外情況,這對于CDL 的實施具有積極影響,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訴訟。
3.2.2 實施面臨的障礙
多年來CDL 備受爭議,主要在于CDL 服務過程中,可能超出了圖書館對數字資源合理使用權所允許的范圍。除此以外,CDL 服務的實施還面臨法律爭議、技術障礙和權益矛盾等方面的原因。
(1)法律爭議:如何界定作品版權保護與創新性使用
美國《知識產權與國家信息基礎設施白皮書》最早對數字作品復制件傳輸的特殊性進行了討論,并且對“復制件的復制”從傳統的物理復制擴充到以任何設備或方法發送復制件或錄音制品,但是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復制”的定義不盡相同[23]。比如美國法院審理“2012 年美國國會唱片公司訴訟美國ReDigi”案件時認為文件傳輸構成復制,但歐盟法院審理“2012 年甲骨文公司狀告德國用軟公司”一案時認為不再使用的軟件轉售符合首次銷售原則。最后,美國版權局認為目前數字產品市場的不穩定不適宜進行重新立法,這也使得版權所有人對數字作品首次銷售原則持反對態度得到了法律的認可。
在美國版權法的背景下,保護版權所有者對作品的控制權和創新使用之間長期存在著爭議[24]。2019 年,美國作家聯盟發表《關于“受控數字借貸”理論缺陷的聲明》,批評CDL 不僅侵犯了版權法對作者和出版商的保護,還合理化地構建系統進行侵權, 呼吁CDL 應當尊重作者的智力成果[25]。2020 年6 月,多家出版公司對Internet Archive 的“開放圖書館”和國家緊急圖書館項目提起訴訟,指控該組織故意開展數字盜版,并從支付掃描服務費用的圖書館獲取大量收益,并認為未經作者或版權所有者的批準和書面同意,圖書館無權將印刷材料轉換為數字格式[26]。
(2)技術障礙:如何保證有限且受控地利用圖書數字副本
CDL 服務實現的關鍵在于圖書數字副本只在合理利用的范圍內借出,能夠保證副本在借出后不被大量拷貝、傳播或修改,并且要實現與傳統紙本圖書格式的一致性,確保一旦數字副本借出,館藏紙質圖書便不再被使用。對于目前的CDL 服務系統,出版商認為其并沒有真正做到控制數字副本的分發數量,CDL 系統在提供受控借閱圖書以 PDF 文件格式下載或在Web 瀏覽器中查看后,讀者仍可以從瀏覽器緩存中繼續查看并下載[27]。
為了改進系統,2020 年波士頓圖書館建立CDL 工作組,致力于整個CDL 系統機制架構的完善,CDL 系統提供借閱的副本時,要求用戶不能在其自有設備上安裝新的應用程序進行閱讀[28]。一些大學圖書館則通過與科技公司合作,建立CDL 系統,如:俄勒岡州立大學圖書館使用ALMA 數字主機的內容和限制用戶訪問數字副本的數量和時間[29],福特漢姆大學(Fordham University)使用Google Drive(谷歌硬盤)作為后端存儲平臺,管理圖書館的數字副本并與特定的受信任讀者共享作品數字化副本[10]。但這些系統對于讀者使用副本的時間限制僅能以小時為單位,缺乏與傳統借閱相通的閱讀體驗。
(3)權益矛盾:如何平衡圖書館與版權所有人及出版商之間的利益
目前,國外對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服務爭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圖書館對市場上可以獲得電子版的圖書進行數字化,并提供相應借閱服務。如谷歌數字圖書館計劃被美國作家聯盟與美國出版商協會以侵權為由提起集體訴訟,爭議焦點是版權作品是否授權,關鍵原因則是圖書數字化作品的商業使用問題。2019 年全美作家聯盟聯合出版商等多個團體發表聲明,指出圖書館的CDL 服務侵犯了版權和作者權利,呼吁圖書館在尊重作者版權的基礎上,就如何創建真正的數字圖書館與出版商和作者進行對話[30]。
4 國內圖書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的思考
受控數字借閱所依據的首次銷售原則,最初是出現在美國版權法中,很多國家后來也相繼承認首次銷售原則。雖然我國未通過法律條文對首次銷售原則進行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傳統紙本作品和數字作品均有將其作為依據的判例。2020 年,美國研究圖書館學會的《新行動計劃》中,建議通過制定新版權政策來保護研究人員和學習者的利益,使圖書館具有一定對數字資源進行獲取、共享、借出和保存的權利[31]。歐盟也在考慮允許圖書館對其館藏進行數字化,并提出非商業目的在線服務的提案[32]。2020 年我國《著作權法》修正時首次增加了合理規避條款,改變了之前對于反規避的限制,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我國作品市場的外部性問題[33]。除了著作權問題之外,我國圖書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服務需要注意如下幾點。
4.1 在知識產權保護框架下制定實施受控數字借閱的具體方案
圖書館實體館藏中有一大部分資源是已過知識產權保護期的作品或者是特色館藏以及孤兒作品,這些資源出版商無法提供數字格式。對于保護期已過的數字化作品,2010 年中國圖書館學會出臺的《數字圖書館資源建設和服務中的知識產權保護政策指南》中,第6 條以及第7 條均作出規定,圖書館可以對這些保護期已過的作品自由地進行數字復制,但即使如此,圖書館做數字化復制仍然應當經過著作權人的同意,或者直接購買該數字化作品的版權。可見,圖書館的受控數字借閱服務仍面臨著復雜的知識產權保護制約,需要建立并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如何對圖書館館藏中較老的、稀少的或絕版的圖書建立數字副本,以降低與版權相關的風險,需制定具體方案。
對于保護期以內的作品,2013 年的《信息網絡傳播權保護條例》修訂版規定,圖書館在某些館藏獲取難度較大的情況下,可以不經著作權人同意,將未過保護期的館藏進行數字化。該條例對于獲取難度較大的限定條件為:數字化形式復制的作品,應當是已經損毀或者瀕臨損毀、丟失或者失竊,或者其存儲格式已經過時,并且在市場上無法購買或者只能以明顯高于標定的價格購買的作品。本文認為,對于這一類作品,圖書館可以根據條例規定的要求條件,制定規則,采取分批次的方式,對館藏作品進行數字化,并展開受控數字借閱服務,審慎制定具體的實施方案。
4.2 制定館藏紙本電子化的管理和流通細則
在實施受控數字借閱服務時,圖書館需要使用技術模擬紙質圖書的物理退化屬性,以使其符合紙質圖書的借閱規則。然而對于圖書館來說,一本紙質圖書在退化前實際流通的時長,需要通過大量的數據統計計算獲得。此外,還要充分考慮圖書館紙本圖書的電子化比例、借閱期限、借閱對象等問題。
圖書數字副本的保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服務能力。研究發現,為保證數字副本的使用,保存時需要多個存儲位置,其技術也需要定期升級,以確保與當前技術進行交互[34]。如果數字副本出現問題,將會影響讀者的使用,比如HathiTrust 數字圖書館,每3—4 年就會更換一次存儲硬件。
圖書館制定流通細則時,要充分考慮受控數字借閱對館藏紙質圖書和數字副本借閱比例的嚴格要求。互聯網檔案館的開放圖書館項目在疫情嚴重期間,為實施美國國家應急圖書館項目,打破了紙質圖書與數字副本1:1 的比例,提供了超出其實際擁有量的副本服務,在被多家出版商以故意侵犯版權提起訴訟后[35],2020 年6 月恢復了常規的受控數字借閱服務模式。
4.3 制定基于多方合作的圖書館受控數字借閱服務的技術解決方案
從技術上講,為保護作者的著作權,CDL 系統需要通過技術手段,確保借出的數字副本不能被惡意復制、共享或分發。因此,要將CDL 付諸實施,圖書館必須要有完善的技術解決方案與對借出數字副本能夠完全控制的技術平臺。從國外CDL 服務項目來看,技術解決方案主要有以下幾種模式:一是托管的方式,即由第三方機構作為數字資源托管方,管理各成員圖書館CDL 模式的實施。如:互聯網檔案館開放圖書館項目,采用Adobe Digital 版本的數字版權管理層(DRM)對數字副本進行托管;二是通過身份核實,對符合資格的讀者開啟CDL 服務。如HathiTrust 項目,該項目將CDL 服務限定在較小范圍的讀者群體,僅包括高校師生以及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通過技術方式,限定用戶在有限時間內查看特定資源;三是圖書館與第三方技術公司合作,借助成熟的技術(如:云技術)實現CDL 服務模式的應用。如福特漢姆大學在2021 年與谷歌合作,利用Google Drive 來提供圖書館數字副本與特定的受信任讀者的在線借閱和共享服務。除此以外,還有一些圖書館采用多種方式一起使用的混合模式。
無論是哪種解決方案,目前仍然缺乏支持單個圖書館實施CDL 服務的技術基礎設施或通用解決方案。為此,我國圖書館可以考慮借鑒總分館的模式,通過與第三方技術公司合作,建立城市級或區域級的CDL 系統服務平臺,借助多方資源,找出能夠滿足讀者借閱需求和圖書館風險承擔能力相匹配的技術解決方案。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一些圖書館已經在合理使用原則下為讀者提供文獻資料的全文檢索服務[36],為受控數字借閱的應用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4.4 建立圖書館與出版商、作者等利益平衡機制
版權所有者、圖書館、出版商是一個相互制約、相互影響的整體。《圖書館圖書受控數字借閱白皮書》指出,CDL機制應著眼于對那些絕版的、久遠的圖書進行數字化。因為這些圖書的數字轉換成本極高,同時市場的需求量并不大[1]。目前,在圖書館和出版商之間,數字作品市場出版商的話語權較大,出版商會熱衷于數字營銷來謀取市場的盈利空間,同時對于數字資源的采購價格和規模進行了較高知識付費的設定,這與圖書館向公眾提供開放共享的服務本身就存在利益沖突,也一直是出版商和圖書館之間長期博弈的關鍵問題。
CDL 的實踐是非商業性的,將受控數字借閱應用于教育以及學術研究,是目前避免圖書館出現侵權問題的關鍵,也是確保CDL 系統在圖書館應用具有合法性的關鍵。為此,我國圖書館需要尋求與出版商、不同的機構合作,做好CDL 的技術限制,并以教育和學術研究為使用目的,制定CDL 系統的合作實施方案。近年來中科院國家科學圖書館與數字出版商構建了包容聯動式發展的合作策略[37],實現“全產業鏈”融合共生,確保了多方利益的平衡。
5 結語
受控數字借閱通過館藏紙本資源電子化,是圖書館借閱服務的創新性探索,可以較好地解決用戶遠程借閱的問題,是推動圖書館借閱服務數字化轉型的一種可選方案。
作為非營利性機構的圖書館,需要在數字時代擁有一席之地,在遵循版權法的同時更需要尋求通過技術進步滿足用戶新的借閱需求,在館藏保存與創新服務方面尋找新的發力點。為此,圖書館應著眼于更為開放的數字化應用,突破傳統的信息資源“庫”的概念[38],邁出利用信息技術開放館藏資源并增加讀者可觸達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