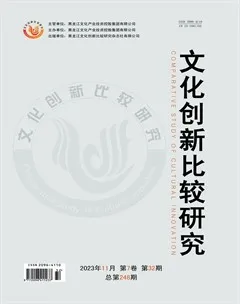衛拉特蒙古機智人物故事角色功能研究
韓慧光
(北方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寧夏銀川 750030)
“機智人物” 泛指智慧的人們。這一類人物以 “阿爾嘎其” 為代表,是在衛拉特文化土壤中生根發展的,是具有衛拉特地區特色的角色。與在內蒙古廣泛流傳的 “巴拉根倉的故事” 和蒙古國的 “巴楞僧格的故事” 一樣,它是在新疆的衛拉特人民當中流傳的機智人物故事的典型。“阿爾嘎其” 蒙語意思是 “智囊”,也就是智慧超群的無論什么時候都可以解決任何麻煩的 “智慧之囊”。這一詞的字根是 “arga” 蒙語意思是 “辦法、智慧”,其后加了名詞后綴 “qi” 構成了新名詞,意謂 “具有智慧的人”,泛指那些以超人的智慧為民除害的、解憂的人。所以 “阿爾嘎其” 一詞從它的語義來說,是形容智勇超群的人。
“機智人物” 指真實存在過的歷史人物。這類人物一般在地方志或族譜里有記載,他們 “原先也許只是一些有關該人物的片段傳聞逸事,由于受人民愛戴,日積累月,年復一年,群眾便在他們事跡的基礎上,加大豐富和發展,而逐漸形成一個民族或一個地區的機智人物的典型”[1]。在衛拉特蒙古當中,除了泛稱的如 “阿爾嘎其”“巴楞僧格” 等之外,還有一些以真人命名的故事,如 “美爾根·特門的傳說”,這里美爾根·特門是生活于16 世紀末—17 世紀初的歷史人物;還有 “瞎子章京的故事”“西日布的故事(淘氣的班弟的故事)”“金巴的故事”“梅干云登的故事”等。這類人物是生活中曾有過的真實人物,在故事中有真實姓名,而且其故事都是在勞動人民當中口耳相傳的人物的真實事跡,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故事是依托于他們衍生而來的。
1 衛拉特蒙古機智人物故事角色分類
普羅普的形態學理論根基就在于他的兩重抽象工作:一是將故事中出場人物抽象為角色;二是將人物的行動抽象為功能。角色和功能是 “使故事成為故事” 的結構要素,進展則是功能的連接,它使故事成為一個自足的整體[2]。
那么,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當中出現的角色與普羅普所研究的神奇故事相比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差異。共同之處就是兩種故事都是以 “主人公” 為整個故事的線索來完成故事;不同之處是這兩種不同類型故事中出現的角色數量不同,而且機智人物故事當中的有些角色并不是固定的、一成不變的。普羅普基于俄國 “神奇故事” 對其進行了結構形態研究。他對神奇故事進行分析,把它分為角色(可變因素)與功能(不可變因素)。他將神奇故事當中的角色分為英雄,有人譯為 “主人公”;贈與者(供養人),有人譯為 “付出者”“受害者”;叛徒,有人譯為 “迫害者”;幫助者;尋找者(和她的父親),有人譯為 “受難者的家屬”;偽英雄,有人譯為 “偽主人公”;委派者,有人譯為 “送信者”[3]。
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中出現的角色可分為:主人公、對手、受害者、求助者、派遣者、假對手。主人公(機智人物),指的是以機智的言行來為民除害、揭示不良社會現象的人,如阿爾嘎其、梅干云登、班達、巴蘭僧格等;對手,指的是殘暴、兇惡、虛偽、狡猾的統治階級或吝嗇、高傲、懶惰的人,其實在機智人物故事中的對手角色大多是巴彥、大喇嘛、商人、鄰居等。但經過仔細分析發現,并不是主人公對所有的巴彥、大喇嘛、商人都是如此,主人公看到這些人的 “殘暴、虛偽、偽善、吝嗇、懶惰” 時會攻擊他們。例如:“看到大喇嘛以作佛事來斂財或對下面的小班達(小喇嘛)的剝削” 時會對他進行還擊。受害者這一角色有3 種情況:一是受害者是主人公;二是受害者是國王;三是受害者是百姓。求助者,如果受害人是第三者那么他們就會尋找主人公來相助,幫助他們戰勝敵人,通常都是主人公扮演這一角色。派遣者,受害者是國王或百姓時,他們派遣主人公去打敗對手(解除對手迫害)。假對手,受害者受到對手的攻擊后,為了對付“對手” 尋求 “主人公” 的幫助。這時受害者為了解主人公的能力出難題考驗他。
2 衛拉特蒙古機智人物故事角色功能
“在普羅普的研究中,人物是承載功能作用的角色。”[4]由于機智人物故事是 “兩元對立” 的,所以主人公角色和對手角色在故事中是不會互相轉變的完全對立的兩個角色。機智人物故事圍繞這兩個角色的斗爭展開。
主人公與受害者。在被動的條件下(受對手的攻擊時)他既是 “受害者” 又是扮演主人公的角色,所以“主人公” 等同于 “受害者”,也就是他們屬于同一個人物來完成。其他則比較穩定。
對手。如果故事是一個簡單的 “一回合” 的故事,“對手” 這一角色一向都是相對穩定的。如故事《阿爾嘎其與小偷》[5]阿爾嘎其到外面去方便時,發現有個小偷偷了他鄰居家的東西。還有故事《為民除害》[6]中講到“有個衣著華麗的諾音見了阿爾嘎其,就奚落道:“破衣服里面還能裹個好人?” 阿爾嘎其接過他的話說道:“是啊,狼皮不錯,卻包著一顆狠毒的黑心?”諾音聽了,無言以對,只得灰溜溜地走了。這兩則故事里就只是以主人公與對手之間的斗爭來完成的。所以在這一類故事(“一回合” 故事)中 “對手” 角色是比較穩定的。
受害者。在故事當中受害者與機智人物不是同一個人的時候,受害者成為獨立的角色,并且在故事發展前期又成為機智人物的對手,向其提出難題考驗,稱為假對手。受害者轉化為假對手時,首先他是以 “受害者” 的名義向 “主人公” 求助——“求助者”;“求助者” 出難題考驗 “主人公”——“假對手”;“主人公” 經受住考驗后被派遣去對付“對手”——“派遣者”。還有一種情況為受害者為了對付他的對手求助于主人公,但并不考驗他,直接派遣。
求助者。故事當中比較穩定的角色,他通常都是受害者受到對手的攻擊或壓迫后求助于主人公。于是便完成了從 “受害者” 轉化為 “求助者” 的過程。
派遣者。它有兩種情況,一是從 “假對手” 轉化為“派遣者”;二是從 “求助者” 直接轉化為 “派遣者”。
假對手。很穩定的一個角色,如果沒有求助者的考驗就不會出現這一角色。所以 “求助者” 出難題考驗 “主人公”——“假對手”;“主人公 “經受住考驗后被派遣去對付 “對手”——“派遣者”。
3 衛拉特蒙古機智人物故事的功能
根據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的角色對其功能進行分析,得出20 個功能。這20 個功能項在故事中出現的數序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然而執行這些功能項的角色對他們的排列順序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許多功能項是從邏輯上按照一定的范圍聯結起來的”,于是形成了角色的 “行動圈”。對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角色進行分類得出主人公、對手、受害者、求助者、派遣者、假對手等角色。其中主人公(機智人物)、對手和受害者是最為核心的角色,這些核心角色有其自身的功能圈。例如:主人公的功能圈是角色登場、狹路相逢、難題被解答,或者主人公出難題、戰勝;對手的功能圈是角色登場、對手嫉妒主人公、對手的迫害、出難題、對手在第一次交鋒中被戰勝不服報復;受害者的功能圈是獲得消息、受害者求助、求助者的考驗(打賭)、給主人公出難題、災難或加害被告知、向主人公提出請求或發出命令、派遣他或允許他出發。
3.1 核心功能
歸納各角色功能,出現頻率最多的幾個功能為角色登場、獲悉、求助、派遣、出難題、解難題或無法解難題、戰勝、結果等。故事中的功能圍繞這些角色形成一個核心功能,從這些核心功能的排列組合,可以看出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的結構特征。
3.1.1 角色登場
主人公出場,即主人公第一次出現在故事里。如在故事 “找馬” 中講到,“有一天,阿爾嘎其來到一個正在舉辦喜事的艾勒(蒙古語,意為牧村),下了馬,順便參加了婚禮”。受害者出場,受害者如果是主人公,那么這一功能就沒有;如果不是主人公,而是其他第三者時才會有本項功能。對頭出場,如故事“吹牛” 中:“遠近有名的吹牛大王呼白德格聽到人們在贊揚和崇拜阿爾嘎其……” 還有故事:“狼皮包著狼心” 中 “有一個巫婆……”
分析角色出場時一定不能把它與初始情景中對主人公或對頭的描述混為一談。角色的出場是指角色在故事中第一次出現,而且它的作用是指出主人公與對頭誰處于主動地位。
3.1.2 出難題
給主人公出難題,在功能 “迫害” 當中講過,它與“出難題” 有類似之處。它們之間的區別是,前者是受到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失,其結果是無可挽回的;而后者主要指精神上的,但其結果可以經過主人公的聰明才智而解決的。例如,對頭的吝嗇,在故事 “出丑”中吝嗇的朋友給遠道而來的客人(阿爾嘎其)只做了稀飯;故事 “吃肉” 中吝嗇的巴顏自己偷著煮肉吃,卻不給客人吃。對頭的諷刺,故事 “為民除害” 中講到有個衣著華麗的諾音見了阿爾嘎其,就奚落道:“破衣服里面還能裹個好人?” 對頭打賭,通常有兩種:一是主人公直接與對頭打賭,結果就是主人公勝出打敗對頭;二是在功能 “求助者” 中已闡述,不加贅述。對頭設圈套,設陷阱、圈套讓主人公破禁忌,在可汗請來阿爾嘎其后,先是給了他一個盛滿熱騰騰的奶茶的圓底碗,之后又給他親自遞給了鼻煙。在故事中如果主人公放下碗那就灑掉奶茶出丑,而不放下又無法接可汗遞給的鼻煙而犯下不敬之罪。主人公碰到麻煩事情,在故事 “找馬” 中講到,阿爾嘎其參加完婚禮出來,由于馬很多找不見自己的馬。
機智人物故事當中不管是主人公對付對頭還是對頭對付主人公都是以 “出難題” 的形式來完成。所以該功能包括了普羅普所定義的功能 “交鋒”。普羅普認為“應區別這一形式與抱有敵意的贈與者的作戰(斗毆)”[7]。這個正與機智人物故事中求助者為了尋找能夠幫助他們的人時先是出難題考驗主人公是相同的。但機智人物故事里求助者是以主人公對頭的形式出現的,所以這里求助者與對頭是等同的。如果主人公承受住考驗就會被求助者派遣去對付求助者的對頭。
主人公出難題。主人公主動去給對頭出難題,經過第一回合主人公勝出后,主人公反過來給對頭出難題。它們的區別就是前者主動權在主人公,后者正相反。難題的形式是與初始情景中給出的對頭的行為相對應。如在初始情景中介紹是個吝嗇的對頭,那么主人公就會采取使其出丑、破財等方式,這些都屬于出難題的形式。主人公給對頭出難題往往是帶有“欺騙性” 的。
3.1.3 難題被解答或無法解答
難題被解答與 “出難題” 是對應的。如果是主人公出難題,那么難題當然會被解答。那么解答的形式與出難題的幾種情況是相輔相成的。如對頭的吝嗇,解答形式為對頭反被主人公愚弄…… 有時解答難題的同時主人公就已經給對頭出了難題,從對頭的報復中逃脫出來,對頭回答不出難題或知道自己上當。如果出難題的人是主人公,那么他的對頭必然回答不出難題,其結果有兩種,一是以對頭回答不出而告終;二是對頭回答不出來,但他不服輸繼續與主人公交手。于是下一個功能 “報復” 緊跟而來。
3.1.4 戰勝
戰勝,即所有的難題都被解決,如在故事 “你的馬死掉了” 中,阿爾嘎其打死王爺的兒子后穿上他的衣服假扮他,回到家后與王爺吵架制造了要自殺的假象。從而巧妙地逃過王爺的報復。
3.1.5 結果
這一功能里主人公最終打敗對手,使對手受到懲罰。如主人公被獎賞或晉升、對手破財、對手出丑、對手死亡、對手輸掉比賽、對手被羞辱等。
3.2 鏈接性功能
鏈接性功能對故事進一步發展起承前啟后的作用。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當中有派遣和報復兩個功能。
3.2.1 派遣
災難或加害被告知,向主人公提出請求或發出命令,派遣他或允許他出發(這項功能與普羅普的第9 項功能基本相同)。受害者求助(求助的結果是主人公答應并接受他們的派遣),如故事 “人財兩空” 中百姓受到殘暴的可汗、巴顏、奸商等的剝削和壓迫,到達忍無可忍的時候就求助主人公。當然,主人公答應他們并且戰勝對頭。阿爾嘎其看到這位窮人的女兒,在長期的接觸中,他們互相產生了愛慕之情。這個女兒為了擺脫巴顏百般虐待,求助于阿爾嘎其說:“大哥,你幫我跳出這苦海啊! 我實在受不了巴顏的虐待。我們干脆一起過日子吧! ” 阿爾嘎其看到巴顏的行為感到非常憤恨,對姑娘的悲慘遭遇十分同情。于是阿爾嘎其設計救出了這位姑娘。故事 “阿爾嘎其出使” 中有國家或國王派遣,由于國家受到鄰國的欺凌,可汗命阿爾嘎其出使鄰國來挽回國家的尊嚴。
3.2.2 報復
該功能發生在對頭在第一次交鋒中被戰勝,不服而進行報復。參照功能 “對頭回答不出難題”。報復也有承前啟后,鏈接上下回合的作用,它使故事一環扣一環變得更加精彩。在故事中第一個回合結束后,故事并沒有結束,對頭為了 “報復” 主人公采取再一次的進攻。如“能人黑娃第一次用計把驢賣給了可汗,可汗知道上當后又回來報復,又一次用計把‘寶劍’給了可汗,最終貪婪的可汗被騙致死”。
鏈接性這兩個功能是承擔承前啟后作用的。派遣是假對頭與主人公交戰結束后,求助者派遣主人公,使故事進入下一回合。報復是在第一回合中對頭輸給主人公,然而他又不認輸,于是就 “報復” 主人公。這樣又進入到下一個回合。
3.3 復合性功能
故事的功能當中有“一個行動具有兩種或以上的功能”[8],即對頭的迫害、求助者的考驗。在故事中求助者和主人公打賭的目的只有一種,那就是求助主人公的聰明才智來對付自己的對頭。然而打賭的過程有兩種:一是受害者求助主人公幫助自己對付對頭,但是主人公不同意,于是和他打賭。如果主人公輸了就幫助他們去對付對頭,結果主人公必然輸掉。二是主人公與受害者賭,如果戰勝對頭,就算主人公贏,結果自然是主人公贏取賭局,以及受害者與主人公打賭,如果戰勝對頭則給主人公多少報酬等。
這兩個功能在一些故事中是相對應的,如前者功能 “對頭的迫害”,其實可用 “給主人公出難題” 來解釋。“求助者的考驗” 則又以 “給主人公出難題” 來完成。
4 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結構特征
在機智人物故事中一般由若干個或系列的小故事組成。這些小故事有的有連貫性,有的沒有連貫性。即使有連貫性的故事情節也是單純的,而且都是直線發展。這一類故事雖然有時通過留懸念,能夠吸引聽眾,但它不會有迂回,也不曲折離奇。普羅普將故事作為一個整體加以探討。他認為:“民間故事通常始于反角的惡行或主角的某種欠缺,最后以婚禮或缺乏消除等告終,這個過程可稱之為一個‘回合’。” 根據這一方法可以把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的結構劃分為單回合結構、連環式結構及復合式結構。
4.1 單回合結構
單回合結構有兩種形式:一是對手外出—獲悉—出發—主人公出難題—對手回答不出—主人公戰勝或得到一定的報酬;二是對手外出—獲悉—出發—給主人公出難題—難題被解答—戰勝或得到一定的結果。有時會比這個更簡單,只由核心功能組成單回合故事,如故事 “狼皮包著狼心” 講道:
有個衣著華麗的諾音見了阿爾嘎其(對手外出),就奚落道:“破衣服里面還能裹個好人? ”(出難題)阿爾嘎其接過他的話說道:“是啊,狼皮不錯,卻包著一顆狠毒的黑心?”(解答)諾音聽了,無言以對,只得灰溜溜地走了(戰勝)。
該故事結構為對手外出—出難題—難題被解答—戰勝,總之故事是由這些核心功能組合起來,便成一個 “單回合結構” 的簡單故事。
4.2 連環式結構
連環式結構的特點是“由一個故事引出另一個故事,故事與故事套在一起,似連環套,一環緊套一環,非常嚴密自然”[9]。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中 “連環式結構” 主要是由受害者的行動圈和對手的行動圈來構成。也就是說受害者受到對手迫害后獲得消息向主人公求助,如故事 “阿爾嘎其贏得諾彥(官員)”[10]中村民聽說阿爾嘎其來到村子就請他整治粗暴的巴顏。但他們為了了解主人公的能力,就考驗他,考驗的形式就是出難題,經受住考驗(答出難題),這里一個回合結束。整個故事其實并沒有結束,緊接著受害者派遣主人公對付對手,這是一個新回合的開頭。具體結構如下:主人公外出—受害者受對手的迫害—受害者獲悉主人公的消息—受害者求助主人公—與主人公打賭(能否戰勝對手)—接著就是一個單回合結構故事—最后主人公戰勝對手。
4.3 復合式結構
復合式結構是把兩個以上單回合結構故事用鏈接性功能連接而成的一種結構。通常是由三篇單回合組成。具體結構如下:第一回合,主人公外出—獲悉對手是什么樣的人—給對手出難題—對手回答不出—但對手又不服—反過來給主人公出難題—主人公解答出難題—最后戰勝。第二回合,對手外出—獲悉主人公的情況并打算與他交手—對手給主人公出難題—主人公解答出難題—對手不服(這時故事有兩種可能:一是主人公反過來給對手出難題,二是對手接著給主人公出難題)—最后主人公解決難題獲得最后的勝利。
5 結束語
綜上所述,首先,在衛拉特蒙古機智人物故事中角色是有限的,故事中出現的角色有主人公、對頭、受害者、求助者、派遣者等,但這些角色在故事中出現時并不是穩定的,同一個出場人物在故事中可以充當不同的角色,如故事中的 “主人公” 可以是受害者,派遣者也可以是受害者。其次,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中的功能較為穩定,有能夠構成故事基本內容的核心功能,有在故事中起承上啟下的鏈接性功能,還有重復出現的復合性功能。最后,基于這些功能的作用衛拉特機智人物故事的深層形態結構有單回合結構、連環式結構和復合式結構。三種故事結構有著密切的聯系,單回合結構是機智人物故事的骨干部分,連環式結構是兩個單回合故事的嵌入式組合,復合式結構則是多個單回合式故事的并列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