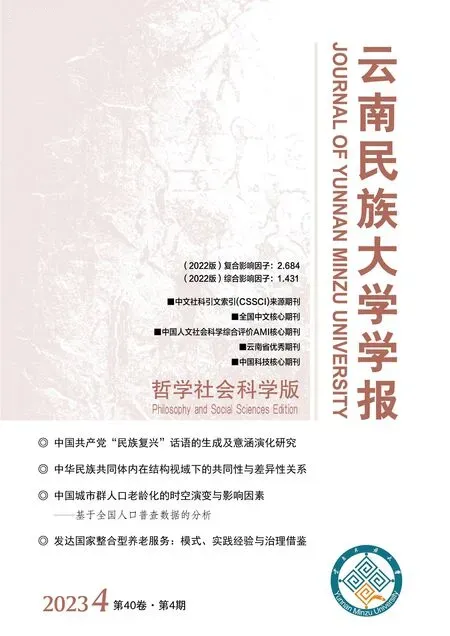近代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緣起的歷史考察
張黎波,王 珺
(1.云南師范大學 法學與社會學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省博物館,云南 昆明 650206)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要在各族干部群眾中深入開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學界隨后興起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研究熱潮,(1)周智生,李庚倫:《以“四個共同”為核心: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7期。呈現出多學科參與、多維度研究的特點。(2)曹能秀,馬妮蘿:《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培養融入學校教育研究》,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近代源流,學界亦作了一定研究。張慧真研究指出國民政府在石門坎推行邊疆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培育苗民的國族意識;(3)張慧真:《教育與族群認同——貴州石門坎苗族的個案研究(1900—1949)》,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99~102頁。汪洪亮研究發現,邊疆教育成為抗戰時期構建國族的重要途徑;(4)汪洪亮:《國族建構語境下國人對邊疆地區多元文化及教育方略的認識——側重20世紀30—40年代的西南地區》,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4期。劉波兒認為邊疆教育是近代新型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的重要一環;(5)劉波兒:《構建國族國家:民國時期民族學家的邊疆教育實踐》,載《元史及民族與邊疆研究集刊》2015年第1期。劉超(6)劉超:《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以清末民國時期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為中心》,載《安徽史學》2007年第5期。、楊梅(7)楊梅:《由“新名詞”到“新概念”——民國歷史教科書中“中華民族”一詞的概念史解讀》,載《課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8期。、黃興濤(8)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51~257頁。等則以教科書為中心探究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歷史;潘曉曈系統研究了民國蒙藏學校對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和影響;(9)潘曉曈:《民國時期蒙藏學校對蒙藏學生“中華民族”意識的培養及其影響》,載《中國藏學》2022年第2期。陳鵬等考察了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早期探索歷程。(10)陳鵬,起靖洋:《中國共產黨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早期探索:基于創建延安民族學院的考察》,載《民族教育研究》2022年第3期。總體來看,關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近代淵源的研究較為分散、有限,客觀上造成了當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研究在學理和歷史認知上存有較大缺憾。
實際上,南京國民政府曾提出和實施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在國民民族國家整合、中華民族意識生成形塑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效和影響,但也存在一些突出的問題和值得鏡戒的教訓。在發展內在理路上可歸結為當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近代形態,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值得認真研究反思的重要歷史遺產。本文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近代緣起的歷程進行系統考察,以期對當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學術研究和現實實踐有所助益。
一、從“忠君”到“愛國”:清末民初國家教育宗旨轉變與中華民族意識教育醞釀
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近代緣起,與中華民族概念的形成與傳播緊密相關。中華民族概念是在20世紀初現代民族和國家意識生成之后逐漸產生發展及擴散傳播的。起初,該概念一度被用來指稱“漢族”,進入民國后這一用法在一部分人中仍有延續。但與此同時或稍后,指稱中國國內包括漢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在內的大的民族共同體之“中華民族”概念,傳播范圍不斷擴大并廣為各界所接受,至20世紀20年代之后,成為主導國內政治輿論的“中華民族”概念的流行用法。(11)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頁。也就是說,“中華民族”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成為國內政治輿論流行用語之前,清末民初政府不可能提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然而,在此期間國家教育領域正在發生的關于教育宗旨的深刻變化,客觀上卻為之后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提出作了醞釀和奠基。
1901年,清政府命各省開辦學堂,“為我國政府正式采用新教育之第一次宣言,我國新教育史亦即以此為開始”(12)姜書閣編著:《中國近代教育制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3~14頁。。發展新教育不能沒有宗旨,學部遂于1906年奏請光緒帝頒布教育宗旨,認為忠君和尊孔兩項是當時“中國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發明以距異說者”,尚公、尚武、尚實三項是“中國民質之所最缺而亟宜箴砭以圖振起者”(13)《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折》,見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二輯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頁。,將忠君與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作為清政府“五大教育宗旨”。其中,忠君與尊孔作為“中國政教所固有”的理念,代表著傳統教育的兩大核心價值追求。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統治,新成立的民國政府認為清政府“欽定五大教育宗旨”不宜沿用。教育總長蔡元培提出“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教自由相違,可以不論。尚武即軍國民主義也”(14)蔡元培:《對于新教育之意見》,載《蔡元培論學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345頁。。1912年9月,教育部將道德教育、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美感教育作為新的教育宗旨。(15)《1912年9月2日教育部公布教育宗旨》,見朱有瓛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頁。忠君和尊孔作為教育宗旨被廢除,軍國民主義等作為新教育宗旨被提出,實際上是教育核心價值追求由忠君向愛國轉向的預示。
1915年,北京國民政府認為教育部前頒教育宗旨“部令雖頒,國內并未奉行,教育迄今無一定趨向”(16)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上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頁。,新頒布愛國、尚武、崇實、法孔孟、重自治、戒貪爭、戒躁進七項教育宗旨。(17)姜書閣編著:《中國近代教育制度》,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第17頁。此一宗旨,雖旋即因袁世凱稱帝失敗成為具文,但明確將“愛國”定為教育宗旨之一,標志著教育核心價值追求至少在表面上完成了由“忠君”向“愛國”的轉向。
至1922 年,教育部學制會議議決的《興辦蒙藏教育辦法案》,已明確強調興辦蒙藏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邊民的國家認同意識。《興辦蒙藏教育辦法案》認為,蒙藏接鄰強國,興辦教育最關重要:“今者西北邊防,日悉蒙藏一再獨立。俄人近且以其過激主義改建蒙古政府,欲使草昧之眾,一躍而成最新式之國家。……今為對外保存國權計,唯有速興蒙藏教育,取未開化之民而授以正當之知識,庶使知五族一家之利,堅其團結之力,絕其外向之心。……且蒙藏人民時為外人利用,幾不知自身為何國國民。追溯原因,實由于蒙藏人民未受國家統一教育。”(18)《興辦蒙藏教育辦法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 (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頁。其中,明確標舉興辦蒙藏教育的目的是“使知五族一家之利”,針對的是蒙藏“過激主義”帶來的危機,解決的途徑是使蒙藏人民“受國家統一教育”。
總之,清末民初雖尚未提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但愛國教育的意思表達漸趨清晰。而尚未明確提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本身,也說明此期發展教育的目的還停留在國家認同意識培養層面,還沒有上升到國族意識培育的更進一步層次,可視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萌芽形態。實際上,這與當時中華民族觀念尚未廣泛流行有關。學者研究指出,民國初年,雖然各民族構成一個大的“中華民族”整體的觀念已經基本形成,但在五四運動以前,在社會上,甚至在一般知識界和輿論界中,這一觀念都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我們只能較多地見到一些國家意識較強的詞匯,這應當是民國初建、五族并立,人們那種一體化的整體民族共同體意識,尚明顯弱于新興的國家意識、國民意識的緣故。(19)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32~133頁。雖然如此,教育宗旨從“忠君”“尊孔”到“愛國”的轉變,在內在演變邏輯上還是為后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提出作出了重要醞釀和奠基。
二、“務期民族獨立”:三民主義教育宗旨確立與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提出
北京國民政府提出的教育宗旨隨袁氏稱帝失敗而淪為具文,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才又頒布新的教育宗旨,在此過程中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
1928年5月,大學院組織召開的全國教育會議,提出以“三民主義的教育”作為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會后,發布了《全國教育會議宣言》,明確表示中華民國雖曾頒布教育宗旨,但失之于空泛和容易發生歧義;此后,“三民主義的教育”就是中華民國的教育宗旨。同時,還對“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提出初步的實施構想:為避免實施過程中理解出現差異和簡單化傾向,特別強調“決不是單單在教科書中摻入些三民主義的話,或在教育行政機關里貼幾張三民主義的文告,就算完事的”;指出“三民主義的教育”的真正目的,是“發揚民族精神,提高國民道德,鍛煉國民體格,以達到民族的自由平等”(20)《全國教育會議宣言》,見中華民國大學院編纂:《全國教育會議報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版,第1~2頁。。這段宣言說明,隨著國家教育管理機構大學院將“三民主義的教育”確立為國家教育宗旨,作為三民主義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主義,正式以國家教育宗旨的形式被提出。換句話說,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被置于國家教育宗旨的高度正式提出。
1929年3月,“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獲得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的認可。從大會通過的《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可見:一是在實施構想方面,已經明確提出了實施方針,且內容較1928年全國教育會議發布的《全國教育會議宣言》更為具體,要求各級學校三民主義教學要與全體課程和課外作業貫連,將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重點放在史地教科上,強調“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 。二是在三民主義教育的目的方面,表述也較1928年《全國教育會議宣言》更為全面和詳細,明確教育要“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于大同”(21)《確定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案》,載《中華教育界》1930年第5期。。總之,國民黨是國民政府的執政黨,“三民主義的教育”作為國家教育宗旨獲得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也意味著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獲得了執政黨的認可,為之后進一步寫入國家法律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此基礎上,1929年4月國民政府制定公布了《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22)《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見國民政府教育部編:《教育法令匯編》(第1輯),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9~20頁。標志著“民族主義教育”隨著三民主義的國家教育宗旨,進入并完成了國家教育立法的環節。1931年6月,頒布憲法性文件《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進一步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將“三民主義”明確標舉規定為“中華民國教育之根本原則”(23)《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見徐辰編著:《憲制道路與中國命運:中國近代憲法文獻選編(1840-1949)》(下卷),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7年版,第93頁。。此后,國民政府一直以“三民主義教育宗旨”來控制和規范教育。(24)趙厚勰,劉訓華主編:《中國教育活動通史》第七卷《中華民國》,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頁。這也意味著“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成為包括邊疆教育在內的所有國民教育的共同遵循,其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教育培育國民的中華民族意識和現代國家觀念,從而達到“發揚民族精神”“務期民族獨立”“闡明民族真諦”“延續民族生命”“促進世界大同”等目標。
邊疆地區是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特殊區域,受到南京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格外重視,出臺了若干專門的政策舉措。
首先是1929年6月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蒙藏之決議案》,較早對蒙藏地區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作了規劃:“通令各盟旗及西藏、西康等地主管官廳,迅速創辦各級學校,編譯各種書籍及本黨黨義之宣傳品,實行普及國民教育……撰制各種淺顯之宣傳品、譯成蒙藏文字。”同時,特別強調教育宣傳中需重點關注的兩個方面:“闡明蒙藏民族為整個中華民族之一部,并釋明三民主義為蒙藏民族唯一之救星”;“說明蒙藏民族所處地位之危險,帝國主義有侵略陰謀之惡毒,及第三國際曲解民族自決之煽動宣傳。”(25)《三屆二中全會通過〈關于蒙藏之決議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國民黨政府政治制度檔案史料選編》(下冊),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10頁。從中可見:第一,從早期規劃就不僅是針對學校教育領域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而且編譯國民黨黨義宣傳品等舉措已覆蓋到了社會教育領域;第二,教育宣傳有著明確目標,即使蒙藏人民“受三民主義之訓育”,知曉“蒙藏民族為整個中華民族之一部”。
至1931年9月,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十七次常務會議通過的《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對蒙藏地區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政策規定已有較大發展,顯得更加明確具體和系統化,內容要點可歸結為幾個方面:第一,對蒙藏教育的目標作了更加詳細的詮釋,包括三項:“依遵中華民國教育宗旨及其實施方針,力謀蒙藏教育之普及與發展”;“根據蒙古、西藏人民之特殊環境,以謀蒙藏人民知識之增高,生活之改善,并注意其民族意識之養成”;“依遵中山先生民族平等之原則,由教育力量,力圖蒙藏人民語言意志之統一,以期五族共和的大民族主義國家之完成。”顯然,三項目標均關涉到蒙藏地區中華民族意識的培育。第二,提出課程、教材方面的實施舉措和注意事項:一是蒙藏地區各級學校的課程,應根據內地學校的課程標準設置,同時可適當考慮蒙藏地區的特殊情況;二是強調教材內容需特別注意闡述中國民族融合歷史、邊疆和內地地理關系、帝國主義對蒙藏的侵略歷史和事實、蒙藏人民和國民革命的關系、蒙藏人民地方自治和民權主義的關系;三是注重用漢文編寫教材,小學教科書尚可用蒙漢文合編,但中等以上學校教科書則須用漢文編寫。第三,提出訓育中需特別注意“喚起民族精神,以破除其部落思想”;“由國際時事之講解和團體生活之訓練,養成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26)《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見國民政府教育部編:《中學教育法令匯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21~23頁。
其后不久,教育部修訂頒布《邊疆教育實施原則》,(27)《教育部訂定邊疆教育實施原則》,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五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頁。將“蒙藏教育”改為“邊疆教育”,將邊疆教育政策的實施范圍由蒙藏地區擴展到整個邊疆地區。(28)王景,王凌:《政治統治維持與邊疆國防鞏固——國民政府時期邊疆教育政策考述》,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1期。這標志著原本專門針對蒙藏地區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上述要求、政策和舉措,擴大到了整個邊疆地區。而其內容與《三民主義教育實施原則》相比,變化不大。
從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實踐的階段性特征來看,隨著1935年邊疆教育開始大規模推行,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開啟了由構想走向大規模實施階段。對此,民國教育家曹樹勛曾總結說,1935年以前的邊疆教育事業“僅限于籌劃準備,并無實際事業可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始指定的款五十萬元為邊教經費,……邊疆教育由準備時期進入草創時期”(29)曹樹勛:《抗戰十年來中國的邊疆教育》,見汪洪亮,等編:《民國時期邊疆教育文選》,合肥:黃山書社,2010年版,第183頁。。也就是說,直至1935年隨著邊疆教育進入規模化推行階段,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才由構想轉入規模發展的實踐階段。
之后,國民政府進一步頒布《邊遠區域初等教育實施綱要》《邊地青年教育及人事行政實施綱領》和《推進邊疆教育方案》等推行邊疆教育,內中均貫穿著通過教育培育邊民中華民族意識和三民主義信仰的既定方針。其中,1941年3月國民政府頒布的《邊遠區域初等教育實施綱要》,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政策舉措作了進一步優化完善,代表著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政策的后期形態。拆解剖析其內涵,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邊疆小學的校名,“不得冠以邊地種族及宗教名詞”。此舉應是為加強中華民族意識而對之前苗民教育、特種部族教育等稱呼的修正。二是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途徑更加多元化和系統化:在招生編班方面,“不分族別,混合編入各班級”;在國語教育方面,明確規定“推行國語為邊地初等教育之要務”,“邊小一律推行國語教育”;在教材方面,特別強調歷史和地理教材“須將過去種種之夸大記載及足以引起民族惡感部分予以刪除,盡量引用民族融洽史實、帝國主義侵略邊地史實、邊地與內地之地理上、經濟上之密切關系等。”(30)《邊遠區域初等教育實施綱要》,載《湖南教育月刊》1941年第16期。三是公民訓練及公民知識教育,“須依據中華民族為一整個國族之理論,以闡發愛國精神,泯除地域觀念與狹義的民族觀念所生之隔閡”。這應是吸納了顧頡剛等提出的“中華民族是一個”民族新理論之結果。總體看來,從校名到課程,從小學教育到民眾學校,從國語教育到史地教材,從國族理論到愛國精神,構建了相對完整的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體系,形成了以邊疆學校為核心引擎,輻射邊疆社會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結構和網絡。
值得注意和強調的是,邊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并不是中央政府單向度的強力推行,而是得到了邊疆地方政府的共識性互動。較具代表性的是1928年12月新疆省教育廳長劉文龍給國民政府的呈文:“現在國民政府成立,以三民主義為救國方略,訓政開始固當藉力于宣傳,而求根本辦法,非從教育進行不可。此次文龍蒙任教育廳廳長,對于三民主義在各學校不能不格外注重。學生明瞭此義,便可逐漸家喻戶曉。”(31)《新疆省教育廳長劉文龍報告該省教育狀況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862頁。這種共識意向的表達,在云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給教育部的呈文中也可以看到:“近數年來,因外國宗教士之深入傳教,設立學校,與受外緣環境之刺激與鼓蕩,其(邊民)民族意識已漸覺醒。當此國難日深,邊警時聞之秋,啟發開導,急不可緩。自二十年起,本省政府已頒布實施邊地教育辦法綱要一種,著手進行。”(32)《教育部函中央研究院請調查研究滇省各民族語言文字》,見余嘉華:《范義田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頁。新疆和云南兩位教育廳長的上述呈文說明,雖然當時邊疆地方政府具有較強的政治自主性,但并未影響到其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認知共性。
三、民族危機的教育應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近代緣起的重要驅動
總體看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之所以在近代緣起,并以邊疆作為教育的重點區域,其驅動因素固然可歸結為多個方面,但從本質上說就是對民族危機作出的教育應對。
近代以來,列強的不斷侵略已關乎到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尤以邊疆地區為烈。在廣大的邊疆民族地區,列強侵略已對邊民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意識的思想根基造成嚴重挑戰和沖擊,進而危及到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和邊疆穩定。如前文所述,1922 年9月,教育部學制會議議決的《興辦蒙藏教育辦法案》寫道:“俄人近且以其過激主義改建蒙古政府,欲使草昧之眾,一躍而成最新式之國家,所以開發而誘導之者不遺余力。無論俄國逐強,蒙古政府勢必與之同化,即幸能完全收復,而過激主義之傳播,已足以擾亂蒙眾,使邊陲永無寧日。……西北藩籬即撤,中國前途將不可問。今為對外保存國權計,唯有速興蒙藏教育,取未開化之民而授以正當之知識,庶使知五族一家之利,堅其團結之力,絕其外向之心。”(33)《興辦蒙藏教育辦法案》,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8頁。可見,當時興辦蒙藏教育的直接原因,就是“俄人近且以其過激主義改建蒙古政府”“蒙藏人民時為外人利用,幾不知自身為何國國民。”
此時,中央政府主要關注的是蒙藏北部和西部邊疆問題,實際上未受中央同等重視的西南邊疆危機也不容小覷。民國初年云南軍都督府授意編纂的《云南光復紀要》總結云南面臨的形勢稱:“滇自緬越失后,英伺其西,法瞰其南,巧取豪奪,互相生心。未幾而有滇緬劃界蹙地千里之約,未幾而有攫取滇越鐵路建筑權之約,未幾而有攬七府礦產之約,未幾而有云南、兩廣不許割讓他國之約。部臣不敢拒,邊吏不敢爭,而西南之禍烈矣。”(34)趙式銘編纂,蔡鍔審訂:《光復起源篇》,見周鐘岳總纂,蔡鍔審訂:《云南光復紀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頁。除政治、軍事和經濟侵略外,外國宗教迅速傳布的影響也同樣深重,只是后果未像軍事、經濟侵略般立竿見影地顯現,這實際上更加深了問題的嚴重性和應對的滯后性。其中,最為根本性的一點就是使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和文化認同受到了嚴峻挑戰,邊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歷史基礎和思想根基隨之遭到摧殘。(35)周智生,張黎波:《云南多民族共生格局的歷史形成機理初探》,載《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1期。1934年,云南省教育廳廳長龔自知將這一嚴重問題呈報教育部稱:緬甸和越南被英法列強侵占后,“云南之西南兩方綿延三千五百余里之邊地,及漢人足跡罕到之山間,遂為外國教士文化侵略之對象。土人之受其麻醉者,率多信奉基督教,受教會之順民教育。……文化侵略與宗教麻醉,在云南之邊地及深山,其事例幾于不勝枚舉,根深蒂固,熏陶日久。以土人與漢人鮮通聲氣之故,此種大規模有組織之文化侵略,遲至近年,始行覺查而加以取締注意。”(36)《教育廳龔廳長上教部請補助經費實施邊教文》,見余嘉華:《范義田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4~505頁。此后不久,龔自知再次向教育部呈報宗教侵略的危害說:“倘長此視同化外,不加管教,任人任意勾煽,生心害政。……如前年之蒙自、邱北苗民作亂即其一例。以故推行邊疆教育,實為國家當務之急。應予國防邊務,統籌措施,抑且為樹立國防,籌維邊務之先決前提。”(37)《教育廳龔廳長呈省府轉請蔣委員長撥助邊教經費文》,見余嘉華:《范義田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507頁。
這并不是云南省教育廳的官樣文章,長期奮斗在邊疆教育一線的彭桂萼對此有著深切的感受,他在文章中寫道:“因邊疆人種復雜,民智低闇,生活疾苦,瘴煙彌漫,故一遇天外洋人,即認為人間救主,一見嶄新醫院,即視為普渡慈航。結果,拿頭祭谷的野卡能做禮拜,唱圣詩,素乏教化的倮黑也能誦圣經,戒煙酒;從來縈絗腦際的‘大漢朝’換上了‘英格蘭得’‘ 阿美利卡’,盤據心中的‘孔明阿公’變成了‘耶穌救主’‘ 基督真神’。……變遇一生,帝國主義者的飛機大炮即應保護僑胞之聲從天外飛來,而沉醉于耶教牧師的椰子酒與嗎啡精里的數千萬苗民無不簞食壺漿,以迎外師,由中國的屏藩,轉成了掉轉槍頭的前衛,于是萬里邊荒即有改變顏色的危險。”(38)震聲:《論外國教會與邊疆政教》,見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編印:《云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之關系》,1938年版,第38~39頁。1936年,凌純聲深入調研后也發現:“沿邊的民生太窮而民智又非常簡單,所以易受外人的侵略。依據自己這次的調查,近幾年來,瀾滄及騰沖以西的邊地人民,移到外國去住的,真不可計其數。”(39)《中央研究院人種考查團主任凌博士訓詞》,載《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校刊》1936年第1期。當時代表性邊疆學校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的教導主任李英,也在文章中記述道:“帝國主義者心靈手敏,先我著鞭,……邊民無知,認賊作父,反友為敵,無形中盡成帝國主義之鷹犬而不自知。茍不及時努力,實行教化,使知祖國之當愛,敵國之當防,堅其內向之心,則班弄土王馬美廷賣國引狼之流,實不知其幾千萬也,豈止一二人而已哉?”(40)李英:《為云南邊地同胞進一言》,見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編印:《云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之關系》,1938年版,第45頁。
邊民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意識的思想根基因列強侵略而受到嚴峻挑戰,這是邊疆危機中更具根本性的嚴重問題。如何加以應對成為當時政學各界共同關注思索的迫切問題。在官方檔案和私人記述的梳理中我們發現,1920年代以來,發展邊疆教育培育邊民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進行應對,逐漸成為政學各界的共性認知。除上面所引1922年教育部文件、1934年云南省教育廳呈文外,從滇西邊疆走出的知識精英尹明德1936年在演講中也說:“將來教育一普及,他們的文化基準自然就可以建立起來了;接著加以交通政治的建設,這樣一來,那么這幾千百群之蠻族,自然會知道國家而發生愛護的觀念了。”(41)尹明德:《由會勘滇緬界務的經過說到對邊疆學子的希望》,見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編印:《云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之關系》,1938年版,第15頁。凌純聲則強調教育對于解決此問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央政府以為開發邊地,非兵事或交通所能為力,必須以開發邊地教育為先。”(42)《中央研究院人種考查團主任凌博士訓詞》,載《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校刊》1936年第1期。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校長李文林等人,甚至將發展邊疆教育視為“救亡圖存”和治理邊疆的“根本大計”。李文林認為:“欲開發邊荒,鞏固國防,亦不僅提倡文化,振興教育一事,然此終屬救亡圖存中之根本大計也!”(43)李文林:《發刊詞》,載《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校刊》1936年第1期。彭桂萼對此也有相似的認知:“要開發建設整理邊疆,自然經緯萬端,必須政治、經濟、軍事、交通、衛生……齊動員,多管齊下,然而有關百年大計的根本辦法,還是教育的建設、文化的開發”(44)彭桂萼:《云南省立雙江簡師邊城叢書總序》,見彭桂萼:《彭桂萼詩文選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156~157頁。。于是,至1930年代,全國形成了“邊地教育的呼聲乃隨邊地問題之嚴重而起高唱入云”(45)彭桂萼:《雙江一瞥》,見彭桂萼:《彭桂萼詩文選集》,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第398頁。的輿論環境。時人記述稱:“現在我們要鞏固邊疆,……而文化的建設,又一定要靠著教育為先驅,這是全國上下不能否認的進行方策。”(46)尹明德:《由會勘滇緬界務的經過說到對邊疆學子的希望》,見云南省立雙江簡易師范學校編印:《云南邊地與中華民族國家之關系》,1938年版,第15頁。
實際上,近代以來民族危機和邊疆危機一直客觀存在,并不斷加深,無論中央和邊疆地方政權幾經更迭,這都是他們不得不面對的關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問題。也就是說,作為教育應對民族危機和邊疆危機的重要和根本性舉措,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客觀需要,近代以來也一直存在。只不過受政局動蕩、中華民族觀念傳播有限等多維因素影響,直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條件成熟后,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才得以明確提出。
四、總結與討論: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緣起的影響、意義和不足
上文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近代緣起作了概要梳理,從中可對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早期探索獲得一個面上的系統了解。通過研究發現:第一,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即已提出;在此之前,清末民初國家教育宗旨由“忠君”向“愛國”轉換,客觀上為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正式提出奠定了基礎。第二,中華民族觀念形成并在五四運動之后廣泛傳播,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提出提供了概念工具和思想基礎。第三,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提出后,成為國民政府實現國民國族整合和民族國家整合的重要舉措,出臺了系列政策措施;至抗戰爆發前后基本形成了一個較為系統全面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政策體系,包括配備師資、課程教育、課外活動、編唱校歌、編印書刊等方面,實現了對各族學生國族意識的多維形塑。第四,總體看來,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緣起歷程呈現出由構想到實踐、由單一到多元、由簡單到系統的特點,反映出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逐漸提升。從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從無到有的緣起歷程中,可縷析出多維深層演變邏輯和發展脈絡。一是教育目標的內涵轉變:由清末“忠君”“尊孔”,到民國初期變為“愛國”,再到1920年代末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加入,與愛國教育并舉相融。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目標內涵的這種轉變并不是相互脫節的,清末民初強調“忠君”“尊孔”和“愛國”,也為后來提出和實施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作了醞釀、奠定了基礎。二是教育內容的發展:隨著民國政府民族政策的變化,教育內容發生了由注重民族同化到強調國族意識培育的演變。三是教育模式的轉型:即以王朝國家認同和儒家文化認同為核心的傳統教育模式,向以現代主權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為重心的現代教育模式的轉型,這實質上是現代民族主義思潮傳入中國后在教育領域滲透的結果。
在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緣起的歷程中,邊疆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別具特點:一是由于邊疆民族特殊性和應對邊疆危機的緊迫性,邊疆被南京國民政府作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重點區域,專門出臺了系列政策舉措。二是相對中央政府的面上規定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政策,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邊疆實踐和基層運作更為靈活和全面。三是雖然邊疆地方政府在政治上有較強自主性,但在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上卻與南京國民政府中央有著共性認知。而這種共性認知的形成,與其說是邊疆地方政府的政治自覺,不如說是邊疆作為列強侵略一線對邊疆危機的深切體驗和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意識自覺。
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的近代緣起,不僅在中國教育發展史上有著開創性意義,而且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影響:一是在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中華民族意識教育,并創建了較為系統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政策舉措體系,為后世中華民族意識教育開創了先河、奠定了基礎,甚至在內在發展邏輯上可視為當今民族團結教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的早期形態和歷史源頭。二是對于邊疆地區的中華民族意識教育而言,創造了教育應對邊疆危機切實有效和具有根本性意義的舉措,推進了邊民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意識的培育和強化,進而在列強環伺的艱難時期發揮了維護邊疆穩定、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的重要作用。三是從民族國家建構的視閾看,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亦即通過教育培育國民的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意識,從而實現國民的現代國家整合和國族整合。中華民國成立,中國初步完成了由王朝天下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也意味著以王朝為核心的傳統的國家和民族認同體系的結束。在初建的民族國家中,其國民是由具有明顯文化差異,普遍缺乏現代國家認同和民族認同,且利益訴求多樣的各類族群所組成。雖有基于漫長歷史積淀形成的整體性和統一性,但也因不同的地域、文化、利益和身份等因素而分離為不同的圈層和群體。對于這些支離的國民,民國政府迫切需要一種有效途徑將族群和個人在國家中的新身份植入“國民”認知體系,實現國族整合,謀求民族獨立,聚力民族復興。而教育則是完成這一認同和認知重構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新成立的民族國家有效推進了國民身份塑造和國家民族歸屬感培育,國民現代國家認同和國族認同逐漸形成。
當然,作為早期探索階段,中華民族意識教育緣起還存在著發展不充分、不平衡等問題,治理能力、治理體系和治理效能還比較有限。同時,中華民族意識教育中的大漢族主義和民族同化傾向也比較嚴重,這在云南省教育廳長龔自知向教育部申請邊教經費的呈文中有明顯表露:“(云南夷族)皆椎愚錮塞,蒙昧無知,為政教風化之所不及,尚在無教育半開化之狀態。而外國教士,則認為文化侵略宗教麻醉之絕好對象,……此類民族,能與漢族同化,則邊圉自固,地方自安。”(47)《教育廳龔廳長呈省府轉請蔣委員長撥助邊教經費文》,見余嘉華:《范義田文集》(上),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506頁。作為一省教育廳長,在同國家主管機構教育部的來往公文中明確說目的是“此類民族能與漢族同化”,民族同化思想傾向表露無遺,以現在的視角看當然是應給予批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