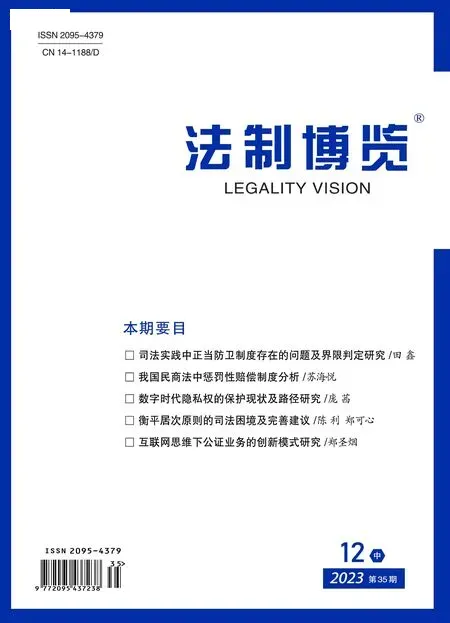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價值與司法適用
史曉慧
太原科技大學,山西 太原 030024
期待可能性源于德國法院對“癖馬案”所作出的判決,其指的是從行為人當時所處的特殊情況來看,可以期待其實施合法行為,而不為犯罪行為的現實可能性。若當時的情形具備了一定的異常性,無法再要求行為人實施適法行為時,即使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也不能對其進行法律上的苛責,即不能對其予以責任非難。故期待可能性實質上是一種責任阻卻事由,一種實質的出罪機制,是對行為人所進行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相結合的判斷結果。
因此,德國將期待可能性寫入其《刑法典》中,日本將其作為超法規的責任阻卻事由來適用。我國雖未以法律形式對其進行規定,但在理論界與司法實踐中多有提及。
一、引入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有學者認為,期待可能性理論以三階層的犯罪構成為基礎,若引入該理論會對我國現在通用的四要件的犯罪構成造成干擾,且《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下簡稱《刑法》)中亦有關于正當防衛、緊急避險和但書條款,已經可以將處于特定情形下的行為排除在犯罪之外,引入該制度會造成重復性評價。此外期待可能性的有無或大小并沒有統一的判斷標準,評價標準具有模糊性,加之現階段法官的素質參差不齊,若允許法官對行為人進行期待可能性考量,則會賦予法官過大的自由裁量權,不利于裁判標準的統一。筆者認為,在當前社會環境與法律框架下,引入該制度確有必要且實際可行。
(一)引入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必要性
伴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人們也面臨著越來越多的具有復合性的潛在風險,為了防控社會治理中的風險,功能主義刑事立法觀盛行。隨著我國刑法修正案出臺的頻率增加,刑法也由最初的“法網較疏但刑罰較重”過渡到“法網漸密刑罰漸輕”的階段,一些原本屬于行政處罰范疇的行為(如襲警罪)也納入刑法調整范圍內,犯罪圈不斷擴大。如果過度強調法律理念中的安定性與合目的性,而忽視其正義性,則會導致刑法的過度工具化,在發揮其打擊犯罪的作用時,其人權保障功能的實現可能會受到阻礙。作為最嚴厲的懲罰手段,刑罰的動用對國家、社會和個人都會產生較大影響,因此需要設置一個合理的邊界來避免刑事立法的非理性化擴張,限制刑罰權的肆意使用,以平衡法益保護與人權保障,實現個案的公正。
此外,正當防衛和緊急避險屬于違法阻卻事由,其以“不法”為考察視角,而期待可能性則是在行為人的行為符合犯罪構成要件時,對其是否“有責”進行判斷,是一種免責或減輕行為人責任的超法規的事由,是對相對自由意志論的認可。且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嚴苛的認定標準、承辦法官的辦案壓力以及認知習慣等原因,其辯護的成功率很低,影響了私力救濟的作用發揮[1],若對行為人在面對不法侵害時的高度精神緊張的狀態進行考量,則有助于正當防衛與緊急避險制度發揮其效用。
《刑法》第十三條的“但書”條款側重于定量分析,而期待可能性除大小外,還包括有無,故可從性質上對行為是否構成犯罪進行判斷[2]。此外,該制度的引入還可以彌補但書條款在行為主體具有特殊身份時的出罪機制的不足。如當犯罪嫌疑人的近親屬為幫助其逃避追究而實施毀滅、偽造證據行為時,認為其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較小,既契合了“親親相隱”的文化傳統,也有利于法律維護社會安定功能的實現。故其可作為但書條款的補充與具體化,充分體現了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
(二)引入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可行性
我國《刑法》中雖沒有明確規定期待可能性的條款,但在一些條款中蘊含了其精神。如《刑法》第二十條、二十一條關于防衛過當和避險過當的規定,在行為人的防衛行為或避險行為超出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時,對行為人減輕或免除處罰,即是考慮在緊迫情境下行為人的判斷力和意志的自由程度受到重大影響,不能期待行為人能恰好把握救濟力度,從而對其從寬處罰或不予處罰。再如《刑法》第二十八條關于脅從犯之規定,也是出于行為人意志不自由的考量而對其減免刑罰。
在法院判決與辯護人的辯護詞中,對該制度也多有援引。尤其是在交通肇事罪、妨害作證罪以及詐騙類犯罪的案件處理過程中都有該理論的體現,故其引入具有社會基礎。
此外,該制度的引入與我國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相契合。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要求“該寬則寬,當嚴則嚴”,且側重于“寬”,將情理作為出罪依據的期待可能性制度正好迎合其需求,使刑事政策中的“寬”得以落實[3]。
二、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司法適用現狀與存在的問題
(一)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司法適用現狀
筆者以“期待可能性”為關鍵詞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進行檢索,發現從2015 年開始,提及該詞的判決書增加,所涉及的罪名種類較多,但其中大部分罪名出現次數較少,如非法占用林地罪等,出現頻率較高的是詐騙類犯罪、妨害公務罪、窩藏包庇罪等。
因辯護人承擔著辯護職責,大部分期待可能性的適用由辯護人提出,但因辯護理由不充分等原因,法庭最終并未對此作出回應或未采納其有關辯護意見,認可比例低。少部分案件中也有法庭主動對該理論進行闡釋與適用,如在高某某窩藏、包庇一案中(參見(2021)豫1324 刑初81號判決書),法院認為被告人幫助其弟逃匿,鑒于被告人與犯罪人的特殊關系,在量刑時予以考慮,對其從寬處罰。有的判決中,也以無期待可能性為由,認定行為人不構成妨害公務罪。
(二)司法適用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司法實踐中對期待可能性理論的援引頻率在上升,但其多存在于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中,法院的最終判決中對此接納程度很低,除了目前對超法規的阻卻事由的忽視以及刑法功利化傾向等原因外,也與實踐中的不當適用有關。
1.對期待可能性的理念認識不清
通過關鍵詞搜索出的含“期待可能性”一詞的判決較多,但一些辯護詞和法院說理部分存在對該詞的誤用,將其理解為未來可通過履行而獲得的利益或實現的某些情形。如樂某某受賄、詐騙一案(參見(2019)贛1029 刑初27 號判決書)的辯護人主張“被告并非在無履約現實可能性及期待可能性的情況下,與對方約定和發生權利義務關系”,將其理解為期待某種利益的實現可能。再如陳某故意毀壞財物罪一案的判決中(參見(2019)瓊9027 刑初235 號),法官將其理解為未來可能得到修復的家庭關系。
2.對期待可能性制度的引用標準過低
期待可能性制度應當是在異常情形下,由于行為人一定程度上的意志不自由,即主觀瑕疵而實施了違法行為時,出于人道主義和刑法謙抑性的考慮,對行為人減輕或免除刑罰。但在司法實踐中,被告人、辯護人對該理念的援引過于隨意,將被告人文化程度、身體狀況、經濟條件甚至權利監管機制缺失都作為難以期待行為人為適法行為的原因,對一些明顯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也以此理論為由進行開脫,違背了該理論的設立宗旨,顯然會造成此制度的濫用。
3.裁量結果不統一
由于期待可能性適用標準的模糊,以及其作為一種超法規的阻卻責任的事由,司法實踐中關于其適用結果出現了截然相反的情況。尤其是在關于妨害作證的案件中,有的法官認為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哥哥為包庇其弟弟而妨害作證的并不能作為免除刑罰處罰的理由(參見(2021)魯17 刑再1 號判決書),而也有法官認為被告人之間的特殊關系可以從輕處罰(參見(2021)豫1324 刑初81 號判決書)。
三、期待可能性制度的適用建議
(一)實體方面
1.明確判斷標準
關于期待可能性的有無及程度的判斷標準,主要有以下幾種學說。一是行為人標準說,其認為該制度的設立依據是“法不強人所難”,故需以處在異常情形下的行為人的自身因素為判斷標準。從其自身情況如認知能力、心理素質等出發,如果行為人不可能實施合法行為或可能性很小,則期待可能性受到影響[4];二是平均人標準說,要求以特定情形下一般人的選擇為標準來進行判斷,若一般人在當時情況下會實施犯罪行為,那對該行為人行為的定性或定量就應從寬;三是類型人標準說,主張應以與行為人在經濟條件、職業情況等相似的人為參照來判斷其期待可能性的有無及大小;四是國家標準說,其要求從國家角度出發,只要法律規范期待行為人實施合法行為,那行為人就具有期待可能性。
如果只采用行為人標準說,可能會使被告人找各種理由為自己脫罪,從而造成法秩序的混亂;若僅采用平均人標準說或類型人標準說,此強調的是大眾的或具有某些共性的人的平均能力和經驗,在某些異常情形下忽視了對行為人自身情況的考慮,有悖于該制度的設立初衷;國家標準說實則會導致期待可能性制度形同虛設,因為法律規定的即為國家所期待的,其排除了該制度的適用空間。因此,需綜合各種學說,根據具體情況選擇判斷標準。
期待可能性是法律在異常情況下對公民刑事責任的豁免,因此其判斷標準不能脫離行為人自身,故實踐中,以行為人標準為主,一般人和類型人標準為輔更為適宜。具體而言,應先從行為人的履行能力以及主觀方面出發,尊重個體差異,但在一些特殊情況下,繼續采用行為人標準說會導致案件處理結果的不合理,有違一般的社會觀念,影響刑法的安定性時,則應參照平均人標準,若是一些與專業知識高度相關的犯罪,如金融類犯罪等,則以類型人標準為判斷依據。
2.限制適用范圍
期待可能性制度的不當適用會影響刑法的規范性與安定性,因此有必要對其適用的案件范圍進行限縮。錢葉六教授對該制度的適用案件類型進行了羅列,主要有以下幾種:為求生而犧牲他人生命的緊急避險;執行上級命令;被長期家暴的受虐女性殺夫;近親屬為避免本犯受到刑罰處罰而實施妨害司法的行為;因生活困頓而出賣子女;婦女在特殊情形下重婚;安樂死[5]。筆者認為,結合我國目前的司法實踐,可在以下幾類案件中適用期待可能性制度。
對于被迫執行上級的違法命令而構成犯罪的行為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規定,公職人員有服從上級命令的義務,而且實際生活中,對于領導命令的抵觸很可能會使公職人員陷入艱難的處境,因此不能要求其拋棄未來的工作利益而反抗上級指令,所以此種情形下公務人員的期待可能性減弱。
貝卡利亞在其著作《論犯罪與刑罰》中寫道:“違背人的情感的法律的命運,就像一條堤壩,或者被水沖垮,或者被自己的漩渦侵蝕。”行為人由于與本犯存在著非常密切的關系,為使本犯逃避處罰而實施了窩藏、包庇、妨害作證等干擾司法活動的行為,不具有期待可能性。我國自古就有“親親相隱”的文化傳統,且要求近親屬之間不念及親情而“大義滅親”,實屬強人所難,這種情形下以本犯的近親屬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出罪,也具有道德基礎和社會基礎。
長期受到丈夫虐待、不堪被欺凌而被迫殺害其丈夫的婦女也不具有期待可能性[6]。被虐待的婦女常常會受到男方的威脅而不敢離婚,只能長期忍受暴力行為,身心受到極大傷害。若在被虐待者被迫自救時以法律對其嚴懲,顯然是不公平的,對其施以刑罰也難以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故實踐中可對此類案件寬緩處理,使判決同時具備合法性與合理性。
(二)程序方面
期待可能性制度賦予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為了防止該制度的濫用,以及法官個人理解的偏頗,對此制度的適用須在程序上嚴格把控。當僅是對行為人在法定刑幅度內進行從寬處罰時,可按照普通程序審理。若在法定刑幅度外減輕或免除處罰的,則須經過審判委員會討論后再決定所判處的刑罰。此外,還可以對一些典型案件進行整理,發布指導性案例,以指引司法工作者對該制度的運用,提高適用的準確性和有效性。
四、結語
“當我們還沒有真正進入解釋的時代時,事實上卻進入了立法的時代。”在刑法功利化的傾向下,其工具性逐漸增強。且我們身處的社會愈發復雜,意志的不自由和專業知識的匱乏使人們比之前更容易陷入被追訴的境地。因此在法定的違法阻卻事由外,引入期待可能性制度確有必要。雖然其適用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通過不斷完善其適用的實質條件與程序要求,必然可以更好地服務于實質正義的實現。